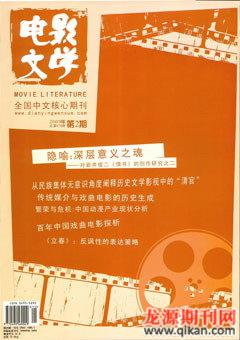劳伦斯与非理性主义
李金奎 王华军
理性主义哲学使人们能够改造自然,洞察宇宙万物之本质,破除宗教蒙昧主义,并且给人们带来了物质财富的丰硕成果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但同时它也给西方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一是生产者不仅是机器的奴隶,而且是强大经济体的奴隶,机器不仅取代了人的肢体,而且取代了人的大脑,这意味着人不再是世界的主体。二是理性主义无法为人们提供人生价值判断的尺度。人不能根据理性去爱、去恨,从而解决精神的、情感的、道德的和信仰的种种矛盾和需求问题,因为人是具有灵魂和精神的动物。
非理性主义哲学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以D.H.劳伦斯为代表的小说家不再强调对于外在客观世界的描写,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手法——心理分析技巧去展示人的内心活动。D.H.劳伦斯(1885-1930)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对人的心灵及生命本质的认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自然与文明的对立,提出自己的非理性哲学——“血性意识”,主张从工业的异化中解放自己。在他看来,“只有通过重新调整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通过性爱获得解放而变得自然健康,建立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才能拯救人类。性爱是再生的必由之路”。本文试图借用非理性主义来探讨劳伦斯追寻的“自我”之路,解读劳伦斯对社会的认知。
一、非理性心理与自我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共同点是到人的内心世界去寻找生命的本质,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理性的局限性,从人类本能和自发的情感中寻找出一片新天地。劳伦斯的非理性心理主要集中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人物的本能、潜意识、直觉,欲望的发生、发展以及由此给人物命运带来的影响。他认为“人生之真正的美只存在于下意识的纯真状态中”。个人生活以及20世纪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对自我压抑和对人性的挫伤,是劳伦斯个性萌生的基础。他认为对无意识的本能和欲望的压抑是人类为物质文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问题上他和弗洛伊德思想走到了一起。这也促成了他对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非理性世界的审视和关注。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说:“现代小说家想要了解的主要是心灵,它被看成是最基本最高尚的现实,决定着其余的一切”。劳伦斯小说的艺术倾向始终对照人的心灵、人物激越多变的心理过程。他的小说情节内容的逻辑性与完整性往往决定于人物内心活动某一阶段的逻辑性和完整性。他总是透过这段心理活动的必然内容和合理性揭示人物的性格、际遇和命运。“劳伦斯的创作已经跃过了人物性格表象的刻画和典型形象的塑造阶段而进入了心理分析阶段”。这种艺术视角的内向性和审美倾向使作品颇具深度和感染力,同时也势必解构和淡化了情节。活跃明晰的心理现实,淡化了完整自足的情节内容。客观说来,劳伦斯的小说“不是描绘历史变迁和阶级冲突的画卷,而是人物心理过程和情感波澜的载体”。
劳伦斯所表现的心理活动主要是人的非理性心理活动。劳伦斯在表现这一心理内容时,确有独到之处。比如《普鲁士军官》写的是战争时期的军营生活,然而我们看不到两军血战的惨烈、军旅生活的硝烟和血腥,我们目睹的是一位普鲁士军官和他的勤务兵之间紧张的心理对峙。勤务兵单纯、温顺、敬畏上司,他熟练得体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之所以冒犯了上司不是因为别的,只是由于他年轻生命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所产生的影响,已深深渗入上尉顽固僵化的生活,使上尉心烦意乱。“每逢勤务兵伺候他时,他总不免要感觉到这个血气方刚的人,就像一团烈火烧灼这个上尉的紧张、僵硬、死气沉沉、转动不灵的身体。小伙子有一种自由自在,心平气和的神气,上尉总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里有点什么。这叫那个普鲁士人很生气。”这种潜意识,这种带有傲慢、嫉妒和敌意的非理性心态使他与勤务兵之间构成了激烈的心理抗衡,导致了他对勤务兵肆虐、残暴的毒打,导致了他被勤务兵勒死的结局,而年轻、稚气的士兵也因此在紧张和恐惧之中绷断了生命之弦。在这个小说中,劳伦斯让读者领略了非理性心理的巨大力量,和他倾向心理探索的艺术风格。
非理性心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是潜意识,而潜意识的主要内容是性本能。在这种本能被激发之前,人物是茫然的、萎靡的、死气沉沉的。一旦这种生命能量被激发出来,人物的周身立即充溢了强旺的元气和神采。他们的自我由此获得了新生。劳伦斯认识到这种追求自我新生的冲动是不可遏制的,生命走的是一条上升路线,需要不断地更新,持续地上升,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却是生命的真正目的所在。比如《虹》中的厄秀拉全身心地追求新生,她与英格小姐和斯克里宾斯基的关系遭到挫折,还大病一场,但她坚持探索,生命终于得到提升,最后看见了象征获得新生的彩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在和克利夫的婚姻中失去了真正的自我,生命之花几乎枯萎。她到树林中去散步,认识了猎人梅勒斯,在梅勒斯情爱的激发下,沉睡的本能和欲望被唤醒,获得了新生。综观劳伦斯的全部小说创作,我们会发现他提供的个体生命追求自我新生的途径五花八门,有基于性爱的新生,有基于自然人性的新生,也有基于原始人性的新生。有的新生实现于英国乡村的自然中,有的完成于意大利灿烂的阳光下,更有的新生要远赴重洋,到美洲西部的大荒野中,到印第安原始部族中寻找。劳伦斯说“你切莫在我的小说人物中去寻找那种老式而稳定的自我。在我的小说人物中有另一个自我,从他们的行动来看,个性是无法识别的,事实上,个性已经消失。”这种浑朴天然、充满生机、活生生的自我是人作为真正的、纯粹的、卓然独立的个人的本质。人只有首先成为真正的自我,才有可能达到与他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一切联系的基础便是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独特的、无与伦比的活生生的自我。
二、“丧己”与“葆真”
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在世不外采取两种态度:一是“获得自己本身”,即“葆真”,一是“丧失自己本身”,即“丧己”。但既然是“在世界中存在”,那么,人也就可以说是必然地被抛入一种人世状态之中,而人在这种状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按照一种外在的标准和并非本己的意志行事。
在劳伦斯的小说中所谓的“工业之子”在工业社会的影响下逐渐“丧己”,退化成资产阶级的附庸与代表。例如:《白孔雀》中莱斯利是个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煤矿主,但却是个肉体与精神严重失衡的人。他那健壮的体格没有真正的“生命力”,因为他的身体已失去了自然的野性,这位矿主已融入机器世界,他的自然属性已被异化,《虹》中的小汤姆·布朗文是劳伦斯笔下的第一个煤矿经理,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作为一个工业化的奴仆,认为人世间的一切,无论是男是女,灵魂或肉体,上帝或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厄秀拉的情人斯科里宾斯基是个机器人。他的内心生活死如僵虫,灵魂进入了坟墓,他的生活纳入了已经建立秩序的事物之中。他曾到非洲打过仗,也梦想着到印度去当个殖民统治者,他成了这个工业文明的牺牲品,而《恋爱中的女人》中杰拉尔德体魄健壮,精力充沛,但精神萎靡,感情冷漠,他体现着工业意志与机械
性,他是工业巨子,驾驭着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但是他的情感世界则处于冰冻状态,麻木迟钝,毫无人性,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机械运动,他是个缺乏情感的空心人。在他眼中工人不仅是用来生产煤的工具,也是他所占有的一项资本。杰拉尔德冰冷的意志不仅反映在他的贪婪的人性中,更体现在他违背人性的“机械主义”原则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克利夫则更是机械的化身,他代表着金钱、理智、秩序和机器,是一个完全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资本家,信奉“工业先于个人”的原则,把金钱上的成功当作其人生的最高目标。他既具有英国贵族的虚伪和自私,又具有资本家的冷酷无情。如果说杰拉尔德还具有一种强悍、野蛮的生理冲动,那么双腿瘫痪的克利夫则完全丧失了自然的情感,是一个丧失人性和人的机能的人。当他坐着机动轮椅在庄园里转来转去时。他完全是个半人半机械的怪物。可以看出从《白孔雀》中的莱斯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克里夫,这些代表着“社会的自我”在文明的社会中沉沦,愈来愈被异化,越来越远离自然,退化变成了工业社会的附属品,其人性丧失已尽。
然而,像厄秀拉、康妮、梅勒斯这些代表着本真的自我的人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要保存自己的自然状态,回到本真的自我。厄秀拉用自己内在的自然力量抵抗住了外部世界的壓力,没有“丧己”和被异化。她仍坚持探索世界,迎接彩虹。康妮和梅勒斯不甘沉沦、不敢异化,在“丧己”与“葆真”的斗争中,他们勇敢地反抗工业文明,回归森林,回归自然。这种回归是灵与肉的完全的、完整的、亲密无间的融合与升华,是一种向原始方向的返璞归真,是神圣的、不无宗教色彩的自我超越。他们的结合从而使机械统治下暗淡无光、郁郁寡欢的人类生活发出艳丽的光彩,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恢复和谐的关系。
三、结语
非理性主义哲学丰富和深化了劳伦斯对现代人心理世界的理解,加强了他的小说的社会批判力量。20世纪初骚动与危机构成的生活氛围,使他充分领略了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备感压抑、倾向分裂的自我,遭受扭曲的人性和深受挫折的本能。生活促使劳伦斯去关注人的内在世界,去探寻实现自然、和谐生活的道路。他着力表现非理性的精神世界,并在人类潜意识的纯真状态中看到了人生真正的美与希望。劳伦斯在其创作中可谓一路高歌人的肉体、本能、欲望、血性,反对理性主义、机械文明把人类僵化、异化、非人性化,并在男女两性的自然本能中寻找实现和谐人性的信念与力量。劳伦斯的这种“自我”,究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试图直接从痛苦的自剖中完成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是一种心理需要。他的这种失去了与客观现实的确切联系的“自我”,离开赖以存在的整体社会的“自我”是幻想,是主观色彩下的片面追求,没有实际意义。但劳伦斯不是社会改革家,他是文学家,他只能用他富于艺术性的作品,以深入作品人物灵魂的笔触来探寻人类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他和他的作品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