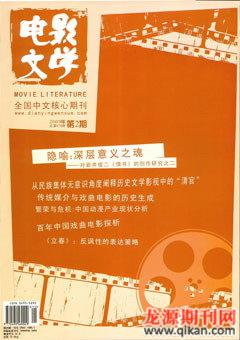“痴”、“迷”简·奥斯汀与张爱玲
郭丽萍
[摘要]简·奥斯汀和张爱玲在当代世界获得广泛热烈的追捧,而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成为当代流行文化符号,把这两位作家作比较阅读,探寻其流行的“足迹”,挖掘接受者“痴”、“迷”其作品的内外因素,可以发现她们笔下的流行文学经典长盛不衰的秘密。
[关键词]简·奥斯汀;张爱玲;流行文化符号,雅俗共赏
英语里有一个词——“Janeites”,是由简·奥斯汀的热爱者吉卜林生造的,意为“简痴”,无独有偶,不同文化、生活背景下的中国作家张爱玲,在全球华语读者中也拥有大批的“张迷”。张爱玲以传统技法与现代主义强调“日常生活”的女性感觉传奇,与简·奥斯汀集中表现她那个时代生活圈子里年轻小姐们猎取夫婿的喜剧经历,同样在当代世界获得广泛的热烈追捧。把这两位业已成为“消费精品”的女作家作比较研究,探寻其流行的“足迹”,挖掘接受者“痴”、“迷”其作品的内外因素,可以发现她们笔下的流行文学经典长盛不衰的秘密。
一、不断被“影”、“视”的简·奥斯汀与张爱玲
简奥斯汀生于1775年,一生只写了6本书,而这丝毫不影响垒世界掀起“简·奥斯汀热”。她的作品持续热销,更引发了无数奥斯汀小说的续集和仿作,在2007年3月1日世界图书日的调查中,《傲慢与偏见》位居英国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100部著作之首。中国天才女作家张爱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引发了覆盖面广及中国内地、港台乃至海外的“张爱玲现象”,甚至有人称为“张爱玲神话”,在读者群中有大量的“张迷”,在文学研究中出现“张学”,在作家中亦有所谓的“张派”,“张爱玲文集的正版、盗版合计起来印数已达上百万(如果这个统计属实,则张爱玲大概是鲁迅、金庸之外拥有最多读者的现代作家)。”而在影像挂帅的消费社会中,这两位女作家也不能摆脱被视觉化的命运,简·奥斯汀的小说是反映英国传统文化的影视题材的首选,她的每一页文稿、每一个人物都以影像的方式予以彻底还原,仅根据小说《傲慢与偏见》改编的影片已经有9个版本,每个在其播放的年代都大受欢迎。张爱玲的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影视改编的热潮,绵延至今。近期更是由名导演李安将其《色戒》改编成同名电影,引发一场热烈的大讨论。这位将东西方文化结合得出神入化的华人导演几年前也曾将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搬上银幕,取得数项国际大奖。
两位作家虽然在全世界拥有无数的“简痴”、“张迷”,但都存在评论者与流行者两不相干的情形,其作品内涵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成为当代流行文化符号。
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她们的名字一再被放大。简·奥斯汀被列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4位女作家之首,甚至“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奥斯汀永占一席之地。但这些来自庙堂的评价仿佛与简流行的真正原因无关,“简迷”们更醉心的是她作品的“通俗”性,永远是几对年轻的男女,在恋爱的得失中权衡,在世俗功利一番之后,她又不忘为主人公安排幸福的结局,为此她会让男女双方至少一方富有。这样的幸福才既合情又合理。在简·奥斯汀的作品里,读者可以在三姑六婆的家长里短中得到乐趣,可以看到复杂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及人性的各个剖面,现代都市写字间里的八卦消息与19世纪乡间邻里的飞短流长本质上是一样的:女人们依然对华美的衣饰眷恋不已,依然对男人和两性关系津津乐道又一无所知,一个职场女超人也会觉得简·奥斯汀的“小道理”与自己贴心贴肺。
观察张爱玲在华语世界的流行情况,其“另类”特色、“边缘化”作家地位是最初的吸引要素,之后媒体不断推波助澜,使由文学研究界的“挖掘”、“翻案”、“补充”工作而开始的张爱玲研究,扩大到公众领域,逐渐成为流行符号。而来自学术界的评价焦点,诸如张爱玲作品中“惘惘地威胁”、“悲悯与同情”、“体察女性的背后,是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却被消费时代浮躁的阅读心态给消解了。张爱玲作品中摹写的表象成为引人注目的画卷,贵族趣味观照下的世俗人生的一切欲望,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对平民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共鸣,于是,“‘张爱玲在不断的文化生产中一层层的被剥去丰富的内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
搜寻这两位女作家的流行轨迹,我们发现的是不断被“影”、“视”的奥斯汀和张爱玲,在商业炒作中成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产业”:“影”,即两位的作品不断地被翻(影)印,不断地被进行影视改编,甚至不断被改写或拥有自己风格的继承人;“视”,即她们在作品内外总处于被“观看”的位置,她们生平的蛛丝马迹成为人们永远的话题,不断衍化为传记和传奇并产生周边效应,如张爱玲在海外仙逝的消息却令其再度“活”跃在大众视野中,奥斯汀的故居与博物馆更是她家乡旅游业的代言。这种被“影”、“视”的命运主要来自于她们作为商业文化符号的号召力,而这种号召力的源头便是——“她们都擅长刻画女性、婚姻和家庭,洞察男女间情爱之战的表象和本质;她们都具有睿智精细,象牙微雕般的叙述技巧,她们都能透过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表现出对人生的大欢喜和大悲悯”。
二、“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
观察奥斯汀与张爱玲作品的接受情况,不难发现,二者的共通之处即为“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这种“雅俗共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宏大历史边缘”的个人世俗叙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作家大多抛弃了单纯以儿女秘隋为主题的文学创作,转而为苦难的时代呼喊。而张爱玲却独树一帜,她以入世近俗的态度,坦言自己,“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而是“设法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张爱玲力图使人们在人类社会天翻地覆、变动不息的现代化演进中找到人自身的支点——天长地久的渴望,因此归向对琐碎人生的世俗关怀。19世纪英国乡间的奥斯汀也同样善于从平凡的婚姻嫁娶中挖掘素材,进行精雕细琢,“人们往往不认为简·奥丝汀是时代的女儿。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人常说她未提及法国革命或拿破,仑战争,而20世纪的批评家则将这一指责现代化,对她遗漏了工业革命表示遗憾,……”因而奥斯汀的作品往往被喻为“二寸牙雕”,既不刻意追求紧张或浪漫情节,也不反映社会时代问题,更不揭示什么重大道理。她最擅长的是用嘲讽的笔触和轻快的手法对日常生活做细腻逼真的描写和喜剧性的处理。在市场经济深化,消费主义泛起的今天,仓促的步履与迷乱的视线使人们普遍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更加关注个人生活,张爱玲与简·奥斯汀这种对世俗人生的肯定、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和理解,显然呼应了当下无数凡夫俗子被遮蔽了太久而又蠢蠢欲动的心声。
在对世俗生活有着深切热爱的同时,二位作者都表现出了对世俗价值取向也有着自觉的认同。古往今来,知识
分子耻于谈钱,女性文学更是清高独立于金钱之上,而奥斯汀和张爱玲在这个问题上却有着颇为相似的“世敌”,奥斯汀曾言:“爱情令人神往是锦上添花,金钱是布帛菽粟必不可缺”,她笔下的男男女女尽管恋爱种种,但最终走向婚姻殿堂并且也为作者所欣赏的都是那些讲理智、讲现实、守传统的青年男女。他们的婚姻普通、实用。可概括为:婚姻不能没有爱情,但更不能离开财产。张爱玲也公开宣称:“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这两位女作家把对金钱的重视如此堂皇的放在台面上,与她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奥斯汀一生未婚,最大的苦恼就是经济上的拮据,而张爱玲虽生于贵族之家,但早年父母离异,在成长的过程中深受金钱势力所左右,上大学,成名之后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女性,更是常常感到经济上“惘惘地威胁”,因此,“女性谈恋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始终是张爱玲作品关注的焦点。正是“经济独立”的困窘使她们对于爱情与金钱之间的冲突倾轧有着独特的兴趣。
而张的冷眼的世故却又和简·奥斯汀把金钱写上台面的世故不同,在简·奥斯汀的小说里,每一个人物出场时,作者都要旁白道出一组数字,告知读者这个人物的年收入有几千磅,这种坦荡又反讽的交代有一种世俗的明亮与喜气。张爱玲却把金钱的力量写到了心理的底层和道德的纤维里,所以显得阴暗冷酷。随着简·奥斯汀的调侃,世俗的金钱追求和女性独立人格魅力可以得到统一,“灰姑娘”式的结局成为现代人冷酷现实中的一点幻想安慰,不像张爱玲的却是彻底的绝灭,只有悲凉。张爱玲作品对现代人的启示即在于:尽管认清了人世的苍凉,却仍旧牢牢把握住“微末”的人生喜悦;尽管参悟了人生的悲剧,却也没有着意夸大人生的苦难,而是坚韧地承受着个体生命的宿命,从而达到了对现代人的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关怀。
二是坚持女性叙事视角。在女性文学泛滥的今天,女性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写婚恋,写婚恋中的女性,本身就是一大看点。女性文学的民间阅读视角往往不是集中在所谓的反抗男权的“女性主义”,张爱玲真正吸引众多读者的是她叙写的具体婚姻、恋爱、调情等过程中的人性、人情。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既不是多愁善感的情种,也不是追求自我的强人,而是“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即“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的为谋生而结婚的女人”。所以,与“五四”时期一些女性作家以一种理想化的姿态表现女性不同,张爱玲对女性始终持一种反浪漫主义的姿态,在她的多数作品中,女性婚恋表现的不是真正的爱情、不是真正美满的婚姻。而是展现了生活在乱世而又一无所长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及为了生存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和挣扎,这种女性的生存最终都指向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方面的生计需求和情欲上的生物欲求。她消解了“圣母神话”,颠覆贤妻良母传统范本,赋予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一直遭受忽视或诬蔑的普通女性以话语权,从而丰富了现代读者的视阑,也在这些“不彻底”的女性形象中找到现代女性凡俗欲求的心理依归。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女性意识的启蒙者和先驱者。她的六部小说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而她在这题材单一的六本书里始终坚持作为女性成长的导师,她告诫全天下的少女,要想得到让人羡慕的婚姻,首要的女性人格魅力即在于理性。在作品中,她侧重探讨了少女们在成长过程中怎样丢掉幻想、认识现实,认识自我。理性使女性更加睿智,从而看清楚在男权社会中自己的艰难处境,认识到惟有自尊、自立、自爱才能得到来自男性和传统社会的尊重,一味的屈从和唯唯诺诺反而会使自己被看轻。理性为女性在步履维艰的社会里树起一道屏障,是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体现。奥斯汀正是凭着自己理智的女性意识成为一百多年来女性的婚姻顾问,教导女性如何既能保持自我的完整又能融入社会,在女性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道路上迈出蹒跚的第一步。而这一步,直到21世纪似乎还没有走完,也正因为如此,奥斯汀的女性启蒙对今天的读者依旧充满魅力和启示。
三是作品的趣味性。说到底,小说还是要有趣才好看,张爱玲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写作者,奥斯汀一生致力于成为一个以笔为生的独立女性,她们随意嘲弄,都成妙文,而这种看似随意地挥洒中却包含着对读者大众趣味的考量。张爱玲对于民众的阅读审美趣味持宽容态度,她主张“把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这种对于作者与读者关系所持的宽容、平等的观念,使张爱玲小说既区别于“鸳鸯蝴蝶派”和晚清社会言情小说对于读者的一味俯就、迎合的媚态,又异乎新文学作家以精英身份对待读者的高高在上的教导姿态。因而,张爱玲的小说既属于纯文艺作品,也可以作为言情小说来阅读。她有着天才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文字的自然流畅,比喻的新颖生动,意象的丰富蕴藉等绝非一般通俗作家所能比。张爱玲对人生、人性透彻的领悟与冷静的关照,还体现在她散落在小说中的一些警语,而这也是吸引一部分读者的原因所在,各大网站纷纷贴出她的名言警句集锦借以增加点击率,那些精彩道尽世情男女仙机的警句成为“白领”们“看透”滚滚红尘的“冷限”。研究张爱玲的创作,都会注意到她对多种艺术因素的兼收并蓄,指出她风格的杂糅。其实她出入古今、新旧、雅俗、中西之间,兼容传统方式和现代技法,都有争取和兼顾更多读者的潜在目的,是一种高雅的通俗表达。
简·奥斯汀被弗吉尼亚·伍尔夫称为“最完美的女艺术家”。虽然奥斯汀的小说主题很有限,但令她小说得到很高评价的原因在于她精致合理的技巧,优雅简洁的叙事形式以及其无限睿智、无与伦比的警句式措辞。读奥斯汀的小说,觉得是在欣赏轻喜剧,她的文字机智、洗练,不时有小小的讽刺,从而使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变得富有韵味,狭窄的场景中也展示出人生的诸种真知灼见。她的讽刺不是尖利的,而是不动声色、微言大义、反话正说,在名著《傲慢与偏见》里,她曾用戏谑的口吻说班奈特太太的“毕生大志”就是把五个女儿都嫁出去。这部小说著名的第一章描写班奈特太太一听说有个阔少定居在附近,就盘算着如何把一个女儿打发给他。不管是哪一个,任他挑选。这段鞭辟入里的刻画,便是奥斯汀喜剧风格的典范。奥斯汀温情的反讽也是射向现代人内心一支绵软的箭,这种反讽往往浑然天成,《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开始称天下男人都死光了也不会嫁给达西,但她最终还是成了达西太太并为自己的这个身份感到快乐,令读者会心一笑,因为主人公是和我们大家一样“不彻底”的平凡人物,从而感到一种贴心的共鸣。太浪漫了只能是通俗言情小说,太冷峻了又让人没了勇气接近,这样的“理智与情感”兼备的文字才是其畅销的灵魂。
“张爱玲神话”的形成有诸多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她作品的魅力,她能够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奥斯汀长盛不衰的秘密也在于此,她富有人情味的喜剧和生活摄影,让历代读者在阅读时忽略时空的变迁并反观自己的生活。美国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这样总结:“一百多年来,‘英国曾发生过几次趣味上的革命,文学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惟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经久不衰。”归根结底,这种“趣味的翻新”怎么也翻新不了读者对文学的永恒期待:寓教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