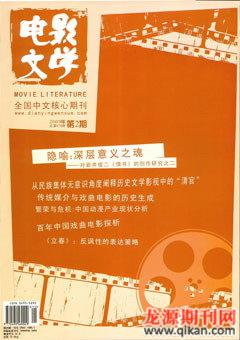隐喻:深层意义之魂
符 抒
[摘要]在现代主义电影中,隐喻的使用多种多样,已经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作品的主题意义和编导的态度,常常就是通过隐喻的方式介入的。对作者来讲这是把握现实世界中的人物的一种手段;对观众来讲,读懂了隐喻,就能更有效地进入影片;对影片文本来讲,乃是实现雅俗共赏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那些贯穿作品始终的隐喻,极有可能就是作品主题意蕴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隐喻,发现;“影子”;空缺性描写
对岩井俊二这部影片的故事,我们稍作研究便可以看出,这部影片跟我们常见的中国某些电影大相径庭:即使是拍摄青春期的同一成长题材,我们通常关注的是家庭、学校与社会,而这部影片几乎让家庭、学校与社会全部“退出”影片。我们总是少不了要描述学校的干预、家庭的介入和社会的影响,其理由正大光明,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部影片描写青少年的青春期,并不受这些看法的影响,自始至终把关注的重心就紧紧瞄准青春期的孩子们,描绘他们的独立的世界,让他们真正成为影片中的主人。
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与设置,产生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效果:一个是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完全是一个自足的充盈的艺术世界,它既不是高于现实的艺术世界,也不是等同于现实的艺术世界,完全是属于艺术家所营造的一个与现实世界似乎相似,实际上又完全有别的,却又是引人入胜的迷人的艺术世界。另一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仿真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不是非现实的艺术世界,因此可以自信地宣称,它所描绘的这个仿真的现实世界,可以全部或者局部跟真实的现实世界相对应,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类影片是绝对真实的,也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我们的失误大概就出在这里;我们似乎总是处理不好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总是把“反映论”当成描写创作的不二法门,强调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客体决定一切,一旦作品上不去,或者作品不好,就认为是生活不够。却往往疏忽了创作主体的先导地位。可是,当今的现代艺术家们,包括这里谈到的岩井,他们已经明显地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真实经验,不再满足于仅仅依附于“反映论”所揭示的皮相真实。这些在国外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讲,他们并不在乎生活现象的真实,他们不受此迷惑,他们更相信他们所体验到的内心的真实,认为这种真实才是一种抵达这个时代精神核心的真正的本质真实。而且事实上,我们看到,各种艺术流派的产生,如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后现代主义……早已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藩篱,它们采用了许多新的表现方法,如怪诞、梦幻、悖谬、黑色幽默、隐喻等手法,而对这些作品的存在,我们已经很难用“反映论”的观点去解释,去做所谓的艺术分析。正如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所说:“因为在巴尔扎克的时代,现实是明晰的,是可以把握与认识的;而今天在加缪看来,现实是荒诞的;在梵高看来。现实是模糊的;在毕加索看来,现实是割裂的;在《铁皮鼓》的编导看来,现实是道德沦丧混乱无序的,在卡夫卡看来,现实是扭曲的异化的,乃至面目全非。”为什么现实在这些艺术家笔下,甚至人物被扭曲乃至变形,变成了甲虫(卡夫卡《变形记》),我们仍旧会感到是一种真实?这个问题不是正好说明艺术中的真实观的标准,不是参考生活的外部逻辑,而是看它在何种程度上揭示了生活与人的精神本相么?所以,传统的“反映论”的观点,面对当今这些复杂的艺术现象,自然显得无能为力。更重要的是,“反映论”所反映的现实,比如在中国某些电影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仍然是“创作客体决定论”,作家、艺术家眼里看见的现实,实在无异于常人,并没有多少对于现实的超越;这些艺术家所认定、所表达的现实,只是对现实的一种复制,而不是创造一种现实,往往只对个人的生活经验、记忆、习惯性的传统思维负责,却很可能不对人们的内心感受,不对人物的复杂情感,不对已经变化了的时代精神负责。这就是今天为什么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满腔热情,倾注心血,却备受观众冷落与斥责的深层根源所在。
轻慢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主体性,把艺术客体看成是“唯一”,这个影响既来自“反映论”,但同时更来自于巴赞的纪实主义美学理论。巴赞受到我国一些电影人的热捧,认为电影对现实的复制,完全可以排除创作主体的主观干预,复制出一个真正的“完整现实”,达到让生活本身说话的目的。这其实是一种纪实“神话观”,并非任何时候都起作用,都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巴赞的纪实理论致命的偏颇在于,为艺术等同于生活,艺术混同于生活,提供了一种所谓的理论依据,这值得我们注意。须知,当我们的艺术创作,在削弱与否定创作主体而只强调创作客体之后,电影岂不成了纪录片?那么,电影艺术还能拿什么东西来吸引、征服我们的观众?观众又有什么理由非要进电影院看电影不可?这不是一个明摆着的很现实的问题,还用得着讨论吗?
在艺术欣赏方面,其实我国自己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会看戏的人看门道,不会看戏的人看热闹。这个说法说的就是作品的雅俗共赏,不仅指艺术的欣赏,我认为,更主要的是艺术创造,而艺术创造要做到雅俗共赏,没有创作主体的努力光有创作客体的存在,是绝对难以实现的。道理非常简单,雅俗共赏必然涉及故事表达的最起码的两个审美层次:一个是故事的表层意义,一个是故事的深层意义。故事的表层意义比较容易实现,甚至单纯依靠创作客体就能达到目的。而要实现故事的深层意义,没有创作主体的“思”,绝对难以实现。
前面,本文在一开始就指出,岩井是个“擅长将传统和现代融为一体”的导演,影片中所涉及的传奇性和言情性,当然是非常大众化的娱乐内容,应属于传统的通俗元素。然而岩井的表达方式却又是现代主义的,因此使他在面对青春与成长题材时,能够游刃有余,得以焕发出新的征服人心的光彩,而并不显得他所描绘的题材陈旧与过时。在现代主义电影中,作品的主题意义和编导的态度,常常更多地通过隐喻来喻示,而不是直接地用议论来揭示。现代主义电影对这种隐喻的使用,其实也就是编导的一种介入,只不过这种介入或者用象征,或者用隐喻来代替原有的议论与情节传递,即通过影片预设的人物、事件、细节,对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与精神世界,表达编导的看法与评价。尤其是那些贯穿作品始终的隐喻,极有可能就是作品主题意蕴的表达形式,编导借它来引导观众对作品内在意义进行发掘、思索与把握。对观众来讲,读懂了影片的隐喻或象征,就能更有效地进入影片,最终实现与编导的契合性交流与沟通;对影片来讲,隐喻与象征的设置,避免了故事情节仅仅停留在观众瞧热闹的浅显阶段,避免了单调与单薄,而使其变得丰厚并具有深层意义。
黑格尔曾经谈到艺术的象征。他说:“什么是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他提醒我们,“这里的表现,即感性、事物或形象,很少让人只就它本身来看,而更多地使人想起一种本来外在于它的内容意义”。
对黑格尔的这段话,我们不妨将它视为对隐喻的解
释。实际上,在象征中往往就包含了隐喻。隐喻与象征,有时候甚至以一种混合的形式并存于一个形象体系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隐喻:一切隐喻都具有一种具象化、符号化的性质,它是用一个形象来象征一种意图,一种观念,一种内在的含义,一种对世界对人物的情感态度。一般来说,隐喻都借助于自然物象,如《情书》中飘飘洒洒的雪花、杨树、冻僵的蜻蜓等等。借助于这种自然物象与主观情感在本质上的同构性或相似性,通过赋予主观情感以客观对应物的方式,来含蓄地表达编导的评价态度,以帮助观众更好地掌握理解作品。
博子与女藤井树在影片中出现,由同一个女演员饰演(日本著名女星中山美穗饰),其实这并不是影片真正的卖点,许多影片都曾经重复这样的尝试,所以算不得新奇,它们往往将其设计为孪生姐妹,而《情书》中却并没有走这样的老路,它表达的是: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影子,同时她们俩又代表了两种类型人物的不同隐喻:一种是被爱却只是一种自我的虚假感觉,一种是被爱而不知其爱。影片有意识地将她们俩设计为相貌相似,不仅她们俩为在小樽蓦然投出的一瞥互感惊讶,就连观众有时对她们也难以区分。影片在这里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典型的隐喻:博子在这场爱的角逐中,在男藤井树的心目中看来,其实她是他暗恋追逐的另一个女藤井树——也就是说,博子是女藤井树的一种化身而已,当然是一个影子罢了。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假设,如果博子长相不像女藤井树,失恋后的男藤井树——博子的未婚夫还会爱上她吗?这恐怕就很难讲了。然而这个问题对博子来说,应该讲最初是根本不存在的。博子完垒相信未婚夫对她“一见钟情”,因为他就是这样对她说的。所以,当博子的未婚夫因登雪山而不幸坠亡,沉溺于爱河的博子,在时间过去两年之后,还曾经一度希望大雪将自己掩埋,其内心深处甚至渴望随他而去。
有一种看法认为,博子这种痴情,这种一往情深,纯粹是一种“自恋”。我认为这个看法欠妥,对人的复杂的感情有简单化之嫌,而且似乎也没有很好地理解编导的真正意图。影片之所以一开局就围绕藤井树的两周年祭,展开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描写,目的决非为了表现博子的“自恋”,而是要描写这个女孩用情太深,反衬她随后的伤感的“发现”。为此,影片的片头一开始就别出心裁地安排了这样一个场面,用以强化博子在观众心目中的印象:一袭黑衣的博子,躺在雪原中,任大雪将自己掩盖,冻醒之后,她踏着纷纷大雪,走向祭扫的墓地。从她痴情的眼神里,我们明白她心里的藤井树并没有死,他不过是在天堂,即换了一个地方生活着,他仍在爱着她。博子这种深沉而强烈的爱,在墓地两周年祭中,更进一步得以彰显。亡人的父亲希望在仪式结束后,与朋友们赶快去找一个地方一醉方休-亡人的母亲甚至调皮地佯称生病而借机溜走一亡人生前的好友们还带来口信,准备天黑来坟场像游戏一般祭扫。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死者的父母,都不过只把这个祭祀当成一种必须完成的仪式过程的时候,唯有徒步顶风冒雪前来的博子,目光深情而执著地,无语凝视着墓碑上那熟悉的照片,双手合十,默默地久久伫立,似乎爱的思绪依然在心中无声地流淌。应当讲,年轻的博子在未婚夫亡故后,她完全有权利可以选择逃避,可以重新开始生活。毕竟过去的已经永远过去了,人死不能复生,再悲伤也无济于事。那么,博子不愿选择解脱,仍然一往情深,她并不想将藤井树从心里抹去,我们只能认为,博子对藤井树实在爱得太深太深了,在她心里也许深埋着一个忠贞的理念,她觉得人虽然可以死去,但并不代表爱的生命也会轻易消逝。对这样的古典主义态度,我们难以谴责,只有由衷地尊重。我们理解她的选择,时间并不能磨去她的思念,她依然沉浸在曾经拥有的爱的幸福中不能自拔。所以,当博子在无意中获得了未婚夫藤井树在小樽读书时的家庭地址时,便毫不犹豫地寄信“天国”问候:藤井树,你好吗?
但是,观众看罢电影,却有一个惊诧的发现:博子倾心相爱的藤井树,很少或几乎没有在博子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稍微具体的痕迹,的确这个未婚夫在她的心里只有一片空白。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而博子似乎徒自爱恋了一场,到头来却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无论是两人世界的浪漫温馨的画面,抑或是一件可以用来睹物恩人的珍贵的遗物。这是为什么?博子因为思念心切而模糊了自己的记忆,还是因为博子这个人不习惯。也不善于怀念?可是回头一想,又不对了:博予不是那种冷漠绝情的女性。假如博子是这样的人,她就绝不会对亡夫产生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而且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甚至是非常“任性地”向女藤井树索取有关未婚夫初中时代的一切有趣的记忆。这恰恰表明,博子企图迫不及待地要尽快进入男藤井树的内心世界,要了解把握他的中学时代的所有生活。我们对此当然也可以作这样的解读:这是学习中国绘画中的“留白”,留下这样一块艺术的空白,让我们的观众可以尽情地去挥洒自己的想象。可是,中国绘画中的“留白”并不等于真的什么也没有啊!它表现的是山川之秀美,天地之灵气,“无”中却包含了“有”,“有”中却似乎为“无”,表达的是虚实相间互为补充的旨趣,悠远而宏阔的境界。然而影片中的博子,却实实在在一无所有。
有人也许就会讲了:博子在秋场的陪同下,去雪山向她的未婚夫藤井树告别,不是她就有所回忆吗?没错,博子的确有过这么一次回忆。博子原话是这样说的:
那个人并没有向我求过婚。他把我叫到磨耶山的掬星台,手里拿着戒指盒,却始终不说话。两个人就这样看着夜景。大约过了两个钟头,时间久了,我觉得他可怜了,没有办法,所以我才说:请跟我结婚吧!然后他马上就答应了。
请不要忘记,博子说这番话时,是在大雪封山的一座木头房里,与秋场和原登山队员尾老头三人围坐在桌前,在温暖的橘红色的炉火映射之下,共同怀念着他们已逝的朋友藤井树。这是整个影片里,在博子的回忆中,唯一提到她与未婚夫藤井树的单独相处、接触。而且,这仅有的一次还是在交代与思念的叙述中出现的,所以弥足珍贵。但问题是,对待这仅有的一次,影片并没有出现任何相应的闪回镜头画面。换句话说,具象的、感性的“两人世界”的画面,并没有在影片叙事中呈现过。观众完全“看不见”、也感受不到博子与她的未婚夫曾经拥有过的相恋相爱的场景。影片做这种“空缺性”的描述处理,显然不是编导考虑不周的疏漏,而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安排,应该说其中大有深意存焉。这其实就是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告诉我们观众,博子因为是女藤井树的“影子”,所以作为别人“影子”的博子的爱恋,自然只能是观众难以“看见”的一片“虚无”。过去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在她的记忆深处留下任何具体的“真实存在”。
这种人物设置上的隐喻,较之画面造型上的隐喻,其艺术魅力,无疑是这部作品真正的意义之魂魄所在。岩井的这个艺术独创性,主要是依靠“发现”这一艺术手段来加以完美地付诸实现的。首先,是搭乘她们的出租车司
机最先“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盯着邻座的博子看了看,惊讶地对秋场说:“奇怪!这位客人跟刚才回家的那位很像!真的很像!”出租车司机“发现”的只是两个女孩相貌上的酷似设计,这是属于故事表层意义的“发现”,而真正的内在深层意义上的“发现”,却是由博子自己完成的。
小樽之行,博子最初并不情愿前往,因为追求她的秋场已经弄清楚了从“天国”来信的藤井树是一个同名同姓的女孩,她觉得此行已经没有必要。但在秋场一再怂恿下,终于她还是勉强答应了。我们注意到,电影文本为博子和女藤井树这次相会见面,提供了绝好的难得机会。而事实上非常遗憾,这次相见由于阴差阳错而未能如愿。在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秋场和博子踏着积雪好不容易找到了改造后的5号线公路,找到了女藤井树的家。然而不巧,女藤井树并不在家,当他们在门外久候,最后离开之际,又与女藤井树错过。等女藤井树闻讯之后,出门再寻找,他们已经准备搭车欲去机场。此时两人终于在大街上相遇,因为彼此不相识,从未谋面,当藤井树从博子身边骑车经过时,那一瞬间,似乎有某种心灵感应,博子从女藤井树背影判断,这就是她要找的人,于是情不自禁,脱口叫了一声:“藤井树!”而藤井树似乎也隐隐听到了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她停车驻足,回头张望了一会儿,两个人的目光因“陌生”而又自然地移开。这使我们想到那部叫《薇罗尼卡的双重生命》的影片。波兰的薇罗尼卡在华沙广场看见来此地旅游的巴黎的薇罗尼卡,奇异的目光仿佛来自于冥冥中的一种力量,她们注定要经历短暂的相遇,因为心灵中似乎有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存在。
意味深长的是,电影中的博子和女藤井树的这次相遇,却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见面,她们最后是擦肩而过。博子也许没有注意到,观众却清楚地看到,女藤井树茫然的骑车背影,逐渐远去,消失隐没在茫茫人流之中。著名教授戴锦华女士以拉康的“镜像”理论,对这一“相遇”作了深刻独到的精彩分析,认为“当博子发现了树(女),她同时在发现自我的地方发现了‘他者——她在异乡的街头邂逅了‘自己,同时惊心地感悟到‘自己可能正是‘他人”。
“发现”在艺术创作中是很重要的技巧之一。亚里士多德对其解释为,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它可以是主人公对自己身份或者与其他人物关系的新的发现,也可以是对一些重要事实或无生命实物的发现。”
的确,这次博子与女藤井树相遇而产生的“发现”,虽然在她们之间并没有任何语言的交流,而只是匆匆擦肩而过,但是带给博子心灵的震撼,必然会让她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两个人的长相如此相像,就跟复制出来的一样,那一瞬间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惊诧莫名,将会永远定格在她的脑海里。所以我们看到,博子从小樽返回,就径直奔赴未婚夫家,查找那本毕业纪念册,果然发现了有那位女孩的名字,原来是自己抄错了地址。博子显得极其不安地问未婚夫的妈妈:
这个照片跟我很像吗?
——不知道像不像。(端详了一会,笑了)如果像呢?如果像你怎么办?
(博子先掩饰)不,没什么。
——骗人!博子啊,你的表情都写在脸上了。是在骗人(树母捧起她的脸),如果像你的话又能怎么办?
如果像的话,我就不能原谅……如果这个就是他选择我的原因。妈妈,我该怎么办呢?……
博子与未婚夫妈妈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成是两位苦恼的女性,彼此之间的坦诚的心灵交流。这是博子在继“发现”之后的情节转折,十分重要的场面。现在博子感觉到,当初男藤井树对自己信誓旦旦所说的“一见钟情”。其实未必可靠。博子已经产生了怀疑,情不自禁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此时此刻,这对心灵相通的女性,当她们一想到这点,都很尴尬而难受,双双几乎要哭出来。
在此之前,就博子而言,她对未婚夫藤井树是深信不疑的,因此她才从亡夫的伤痛中难以自拔。这次小樽之行,让她有了惊人的“发现”:跟自己通信的女藤井树,不仅跟亡夫同名同姓同班,而且相貌还跟自己长得酷似。她想,也许他正是这个缘故才爱上了自己吧?果真如此的话,自己岂不成了他人的替代品?那么,未婚夫当初许下的爱的承诺,到底还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是不是一种虚假的谎言?对此,苦恼不堪的博子,虽然眼下并没有掌握什么可靠的“证据”,而且从当初的求婚情况来看,“那个人也并未主动开口”,而是博子“看他可怜”,自己说出了“请跟我结婚吧”!而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们两人之间似乎又不存在谁欺骗了谁的问题,因此博子这时候仿佛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对亡夫进行责难。但博子一想到自己在未婚夫眼里,完全可能被当成了别人的影子,这个念头却又让她局促不安,始终挥之不去。怎么办?那就做一个索取的“任性的女人”,通过女藤井树这位亡夫的同班同学,对国中读书时期的藤井树来一个全面透彻的了解。我们看到,在博子“发现”之后潜意识深处的这个行为动机,随后成为推动影片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
虽然,博子的预感决不是空穴来风,影片情节的发展最终证实:中学时代的藤井树,果然追求的是跟自己长相酷似的同班的女藤井树,只是后来因为追求未果,这样便移情于自己。
“隐喻”,在现代主义电影中的表达,不能单独存在,单独存在就没有意义。从《情书》这部电影的表达来看,它遵循了:第一,依附性原则。比如,博子是别人的“影子”,这个“影子”是一种象征性的喻示,它不仅随博子这个人物而存在,而且构成了作品的情节与主题。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影子”的隐喻设计,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博子仍然是活生生的、独特的“这一个”。第二,强调性原则,即没有强调就没有隐喻。如果我们认为隐喻只是一个自然符号或者一个符码,其能指与所指,从一开始就已不可分离地融为一体,这个看法其实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也难于成立。它的能指和所指,只有通过逐渐加强才能被最后联系起来。以“影子”论为例,倘若砍去女藤井树对中学时代的回忆,“藤井树爱藤井树”怎么获得证实,两个女孩长相相似还很难说明什么。就因为影片对“影子”这个事实反复强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才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和追索性的思考。
少女藤井树是影片中的另一个隐喻:因患感冒而视而不见。这个感冒自始至终一直伴随着她,从她在影片中收到博子的来信开始,我们观众所看见的这位现在进行时中的藤井树,不是捂着口罩卧病在床,便是几次在医院就诊。她不愿意将感冒传染给别人,对邮递员的拒绝靠近,就表现得非常单纯可爱。甚至这个感冒还在她的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她因为高烧而突发性地晕倒在地,爷爷和她的母亲还产生了尖锐激烈的冲突:是顶风冒雪马上背着病人送到医院,还是苦等救护车的到来,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女藤井树获救的意义,同样就是这种隐喻的表达,自然并非指生理的获救,而是暗喻少女的封闭沉睡的心灵的获救。
隐喻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在《情书》中就有一种
是反复强调。女藤井树家的老宅,既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隐喻。要不要搬迁新居,几乎成了全家的一个令人揪心的话题。女儿的父亲就因为感冒转成肺炎,而在这里送了命,妈妈、叔叔等人之所以力主搬迁,就是不想让同样的命运再次降临到亲人的头上。爷爷却故土难离,坚持不愿搬走。最后还是爷爷的意见取胜,老人家在大风雪之夜,固执地冒死救了垂危的孙女,这种来自老宅的人间温暖感动了妈妈和叔叔,大家最后决定还住在老屋。隐喻传统的东西还有新鲜的生命力,特别是亲人间的彼此关心,不能轻易舍弃。
隐喻还有一种布局性强调,指把具有隐喻和象征意义的物象,或对它的描述,安排在影片中特殊的重要位置,如影片的开端、高潮或结尾部分,从而达到突出其隐喻和象征作用的目的。《情书》一开始就是纷纷扬扬的雪花,晶莹剔透,纯洁,在影片的现在进行时中,剧情的展开都是放置在一个雪的世界。即使是在那些回忆过去的镜头里,我们也依稀看到了大片大片飘落的雪花和地上厚厚的积雪,还有图书馆那被微风缓缓拂动的白色窗纱。日本民族喜欢白色,这个白色是为了隐喻与象征人的心灵的美好与纯洁的感情。影片为什么绝大部分场景都选择在小樽拍摄,就因为这里以雪景著名。漫天的大雪由始至终都飘在观众的心里,男藤井树的少年之恋,博子对未婚夫的深情眷恋,女藤井树渐渐发现以往所不知的爱情真相……直到最后,已经释怀的博子,终于放弃了对男藤井树是否真爱自己的追问与折磨,来到他遇难的山下,站在及膝的雪原中对黎明时的庄严肃穆的山顶,放声大喊:“藤井君,你好吗?我很想念你!……”隐喻寒冬后,依然存在溫暖的浓情世界,让人落泪。
至于隐喻的抒情化强调,更是日本电影普遍具有的一个长项。在艺术家的笔下,自然物就是某种观念和情感的物态化,这形成了日本式的细腻的抒情方式:托物寄情,借物传心,把具象作为抒情的载体,即意象的创造。岩井的电影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托物寄情的抒情传统。比如在电影中,有只冻僵的蜻蜒,显得非常可怜。少女藤井树在爷爷和妈妈的陪伴下,从落满积雪的山坡上欢快地滑下,正高兴之际,她蓦地发现了它,便骤然止步,久久地投去无限怜惜的目光。这隐喻的是日本文学的“物恋”,将人与自然界生物的生命神秘地联系在一起,传达出一种对生命的理解与感叹。以后,当她高烧昏迷,已经奄奄一息,其生命像蜻蜒一样脆弱的时候,蜻蜒对她又是一种隐喻。要不是爷爷的倔强,坚持自己的主张,及时将她护送至医院进行抢救,她的生命不也会像她的父亲,象这只蜻蜒一样瞬息夭折吗?在日本文化里,他们对死亡,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乐于以细腻的笔触加以刻画与表现。
这种抒情化的隐喻,一般由两个不同向度的因素构成,一个方向是向心的或内部的,它指向编导的情思,另一个方向是离心的或外部的,指向与之同一的客观世界。《情书》这部影片因属主观型、情感型的表达,其隐喻特别受到抒情性因素的强调,故而增添了与众不同的诗的气质与神秘性、模糊性。我们看到,在影片的结尾,冰雪开始融化,春暖花开即将到来,藤井树家的老宅,树木抽出了嫩芽。爷爷让她在庭院里指认一棵亲手为她栽种下的树,经过辨认认出之后,爷爷意味深长地告诉她:“在你出生时,我种下了这棵树。我给你们俩起了相同的名字。”这其中的温情、寄予的期望以及观众对老人的心,自然能够深切体会,应该说,这样的表达胜过千言万语。
后记:本文的撰写得到两位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真诚致谢: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林敏教授、重庆大学电影学院葵阳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