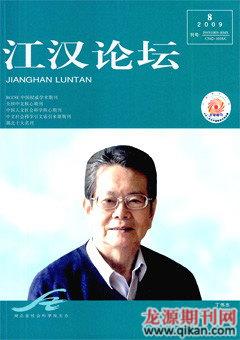试论清末民初中国航商的诡寄经营
张代春
摘要:清末民初的中国航商,采取境外注册船籍、直接在境内购买外国航行证及旗帜、将轮船委托给洋行经营、以外商名义报关纳税及附股外轮公司等方式托庇洋行诡寄经营,利用外商特权逃避政府管制和繁重赋税,躲避战乱和匪患,并从航运经营中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诡寄经营是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分析其成因及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对于我们正视并妥善解决在今天中国航运界广泛存在的船籍外移问题将不无裨益。
关键词:航商;经营;中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8-0054-05
所谓“诡寄”,源于明朝,在“一条鞭法”实施后,大户人家为人命偷逃赋税,将田地伪报、隐藏在他人名下,借以逃避赋役。所谓航商的“诡寄经营”,即中国航商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和繁重赋税,躲避战乱和匪患,利用各种方式寻求列强庇护,利用外商特权从事航运经营并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是一种由于政府对于航运业的严格限制及外国航商特权泛滥引发出来的现象。举凡外国航商特权所及之处,大抵就有中国航商的诡寄经营。航商的诡寄经营现象始于1840年代五口通商后,在1850-1880年代达到高潮,并且延伸到民初。清末航商的诡寄经营重在逃避政府管制及沉重赋税,而民初则重在躲避战乱和匪患。
一、中国航商诡寄经营的方式
中国航商诡寄经营活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船只悬挂洋旗,假借外商名义进行航运经营。而要达成诡寄经营目的的方式方法很多,有境外注册船籍、直接在境内购买外国航行证及旗号、将轮船委托给洋行经营、以外商名义报关纳税、附股外轮公司等等。
(一)境外注册船籍
将船舶在境外注册,今亦称船籍外移。这种活动最早见诸于“实为划艇贸易与贩运猪仔之中心”的澳门,“盖以华艇船身系为西式而帆则为华式,且什九系华人所有而为之驾驶,惟图悬挂洋旗以为保护起见,故在澳门政府注册。”而华商船舶“在英国香港殖民地的注册能够很便当地用通过殖民地的特别法规的办法而予以批准”。以后这种恃洋旗为护符的划艇在整个沿海泛滥,“(1843-1858年)期内悬挂洋旗航行中国沿海之华艇,为数甚多。此种船只,常驾赴未经开放之各埠贸易,故某评论家只谥之日走私船只。彼等名义上俱属洋籍,多数悬用葡国旗帜,亦有悬用英旗者,实则全为华人所有。且均由华人驾驶。因在澳门香港注册之故,遂恃洋旗为护符,从事于不法贸易焉。”也有中国航商将船只在西方殖民地的槟榔屿、新加坡、暹逻、爪哇、菲律宾等地进行注册,然后开回国内以外商名义从事运输及贸易活动。
(二)直接在境内向外国驻中国领事购买外国航行证及旗帜
鉴于葡、英两国可以借助澳门、香港两块殖民地很便利地对华商船只进行注册,而“这个需要是如此迫切,这个引诱又如此巨大(从注册费和船舶费来看)”,于是其他国家的领事们当仁不让在中国境内干起了原本在法律上并不属于他们本国政府授权的事情,争先恐后地向华商船只出售航行证和外国旗帜。在中国境内将一艘华商船只挂上外国旗帜,其实在各国领事的鼎力相助下,运作程序并不复杂,“即将快艇的理论上的(按即名义上的)所有权转让给外国人,再由该外国人按照船只的十足价值以一纸抵押单。连同经营该船的权利一并给还这个中国人。外国旗于是悬挂起来以为外国所有权的证明,但是除非在和中、外当局发生纠纷的情况下,他的名义上的所有权足以使随时发生的这种法律纠纷被提到领事裁判权法庭的时候,船舶证件上所开列的这个外国人是向不露面的。”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白干的,其间每一个环节都须用银子来衔接,“我相信一个洋人通常都是接受约一百圆钱来宣誓该船为其所有。同时以高于原船的价值把船出赁出去。另一个洋人每月接受四五十圆作为名义上的船长。第三个洋人每次航行接受十圆来办理划艇的装货和卸货手续,与海关发生纠纷时由他出面。这种船和洋人的关系大致就止于此了。航行与经营则完全是由华人来办并为华人所有。”当然,华商可以较为自由地选择悬挂哪一个国家的国旗,“中国船主都喜欢悬挂西班牙国旗,因为它比其他国家的国旗来得便宜。用较低的工资就可雇得西班牙国民和马尼拉的土著居民当船长,昼夜都在船上值勤;此外由于无论在宁波还是在其他长江口岸都没有设西班牙领事馆,也就用不着向领事馆交钱。”因此,在1850-1860年代的长江航线上,悬挂洋旗的现象与轮船航行的改善相偕俱来,以致一面洋旗和一本外国护照售价高达白银50至200两。也有华商直接在境内购买洋行船只,连同航行证和外国国旗一并收购。
(三)将轮船委托给洋行经营
也有航商为规避政府管制而将轮船委托给洋行经营。1866年。中国航商购买了一艘773吨的轮船,交英商轧拉佛洋行代理经营。1868年,又有一些中国航商购买了一只665吨的“虹口”号轮船。把它委托给美国同孚洋行经营。1870年2月,怡和洋行与“天龙号”的船东达成协议,由怡和洋行来经营该船,这样就可以“获得总收入和一般码头费的5%”。同年7月,北清轮船公司的“南浔号”亦交由怡和洋行经营。这样的结果是,中国航商有足够的资金但不能建立起由自己来独立控制的轮船企业,却使外商乘机获得了巨额利润。
(四)以外商名义报关纳税
有的华商为规避繁重的捐税,以外商名义或完全委托外国公司报关纳税。“凡报关完税等事,固由洋行出面,即自行贸易之船,亦多托洋行代报。缘洋商之货进出只须完税,并无捐项。华商之货进出既应完税,又须报捐。华商避捐,因托洋行;洋行图利,愿以代报。”还有的外船承运的华商货物,“往往洋商认为己货,包揽代报完税,希图避重就轻。”1880年九江关呈报:“近来有华商投托洋行,私买单照,扯用洋旗,将所贩木植雇佣土船跨带两旁,在江汉关报完洋税一次,到九江时查验放行,经过常关厘卡,向不完纳钞厘。”
(五)附股外轮公司
附股是近代中国航商诡寄经营的一种常见形式,买办最早以附股的形式参预外商在中国创办的轮船公司。早在19世纪50年代,广州地区就已有华商投资于轮船业,“‘威拉麦特号(四百十四吨),‘星火号(一百二十七吨)和‘金发号(八十吨)是三艘美制轮船。这是早在1855年为两家本地的公司投资航驶于广州河面上的轮船。”1860年代附股于外轮公司者,更是屡见不鲜。如外商在上海成立的旗昌、公正、北清三家轮船公司中,买办商人的投资就占了全部资金的三分之一。公正轮船公司是由买办唐廷枢、郑观应、郭甘章等共同创办的。唐廷枢不仅在公正,而且在北清轮船公司也有投资,并同时任两家公司的董事。他自1869年起将注意力日益集中于轮船的投资,1870年他投资三万两于“南浔号”,委托怡和洋行经营:随后三年他又投资于另外两艘轮船,其中一艘委托琼记洋行经营。
唐廷枢先后投资的轮船有:苏王那达号、洞庭号、永宁号、满洲号、汉阳号和南浔号等,同时他还“在港集股银十万元,先租两船,来往港沪”。有西方学者曾指出:“特别在最近几年,在航运事业的投资以及在航运服务的组织方面都已习惯于密切合作。许多由外国人控制的公司,中国人握有的股份占很高的比例,中国人还据有董事会的席位。”1866年海关贸易报告中甚至说:“我相信,在当地(上海)的轮船公司中,大股东都是中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的东南沿海贸易中,外国轮船公司就以附股的方式来吸引中国资金。其中英国琼记洋行购买轮船时,后来成为上海旗昌洋行买办的陈裕昌一人投资就达69000元,占到买价的85%。旗昌、公正、省港澳、华海、北清、怡和等外轮公司都曾诱招巨额华商资本。仅旗昌轮船公司100多万元的资产中,华商的投资估计就占一半以上。不仅轮运企业,与之相关的仓栈业、码头业、航运保险业几乎没有例外,甚至很多兼营轮运的洋行经营的轮船亦是如此。
二、中国航商诡寄经营的原因
中国民族航商之所以托庇洋行诡寄经营实出于无奈,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独立的华商航运公司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一)政府的限制及阻挠
引进机械动力的轮船可以获得进入航运市场的机会并从而牟取利润的事实,当然也被中国一部分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所看到,他们也有把这种外部利润内化的能动性。然而清政府对民族航运业的萌芽及发展采取了种种限制和打压的政策。1864年,清政府致函各通商口岸,查询华商购买轮船是否先由地方官报明立案。1864年拟定的华商买雇洋船方案,船中无论用洋人或华人,均不准随意进泊内地河湖各口岸。此外还有手续的繁杂、官吏的干涉与敲诈等种种限制。曾经有一位在科举考试中已金榜题名的人士张禄升看到社会潮流的变化而弃文从商,购置轮船在沿海地区从事护航活动,当他随船行抵“从未见过轮船”的胶州港时竟被地方当局逮捕,虽未投入监狱,却遭皇帝谕旨被摘去顶戴花翎。原因是“他开着‘火船闯入宁静的海港使当地居民受到惊吓”。就在张禄升事件大约20年后的1886年,有一位浙江候补知县黄日章,置轮船往来于外轮早已畅行无阻的苏沪,“商民均称其便捷”,而江苏巡抚崧骏竟派水师炮船拦截,理由是“方知该轮之行,并未奉准宪示”。在这条航线上不久又有上海人吴子和、宋珊宝等人经过两江督宪批准经营的小轮行驶于外港,后未经同意驶入内河,崧骏令吴县地方当局“立将该轮封闭”,管驾之人被拘留候讯,连搭客等人“俱舍其行李,只身上岸”,理由是“遽尔驶入内河,招揽生意,殊属冒昧”。至于内地小轮公司的创办则更为艰难。以湖南小轮公司为例,1880年代初,从它开始创办起就遭到来自各方的节节阻难。“凡三次呈请,涂公一阻之,卞公再阻之。”继而李黼堂更是“肆意阻挠,上书中丞,其言绝悖”。这里的“涂公”即原任湘抚、光绪八年官迁湖督的涂宗法,“卞公”即原任湘抚、光绪九年暂署湖督的卞宝第,李黼堂即咸丰年间曾任湘粮台总办、后任江西布政使、署理江西巡抚的李桓。一家小轮公司自然难以承受这些大权在握的督抚们的一再阻难,湖南小轮公司的创办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长期搁置下去。1882年,沪商叶成忠请求置造轮船,另设广运局,“经直督李鸿章批饰不准独树一帜。”
(二)逃避捐项
首先。清政府在税收方面采取贱内惠外的政策。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洋商就获得了商品进出口只纳正、子两税的特权,其税率大致相当于货值的7.5%。而华商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负担远较洋商为重。时人指出:“盖进口之税重,其成本必昂,销路必滞,而本国之货乃可畅行,保护利权,固当如是。乃中国抽收厘税,竟反其道而行。”当时有人测算:以煤斤而论,洋煤每吨税银为五分,而土煤则每吨须纳银一两有奇,大约相当于洋煤的二十倍之多。就连总理衙门官员也承认:“洋商仅完正、半两税,便可畅行无阻,利权较华商为优。”除了厘金之外,华商还得缴纳各种捐项。时人称,自咸丰军兴之后,捐款林立,“逐项抽取,无非出自商民之脂膏。”官方这种内重外轻的税务政策,就连李鸿章也看不过去,他曾指出:“此举不啻抑华商而护洋商”,致使“商民交困”,后果“何堪设想”。其次,在行政管理方面,清政府官员体恤洋商,苛待华商。清政府各级官衙,尤其是厘卡对华商态度粗暴,种种威逼勒索,不足为奇。张之洞在光绪十五年的一则公牍中痛陈过当时厘局员司巡役“颇有以搜求为能事,以苛罚为示威者。即或不然,亦皆习成骄惰”。其他官员也不讳言厘卡弊窦丛生,厘卡员司巡役莫不将其职业“倚为婪财致富之资”。同华商过关纳税“每遇稽滞。掣肘必多”的情形截然不同的是,洋商则可获得清政府官员的格外照顾与恩施。除厘卡员差之外,其他官员也多有对民办实业敲诈勒索之举。时人记述:“民间有利之事,必为奸胥蠹役所垂涎,往往以稽查为名,假公济私,百计阻挠,诸多掣肘。故民间欲为之者,必须将衙门内外人等,各予以年例规费而后其事得行。迨其事行,丽其利已无几矣。又复多为名目,横添枝节,俾规费年增一年,非但盈股其脂膏,必使之削骨见髓,而犹噬吮之不已。”这实际上是对封建官场普遍存在的贱商、剥商之举的概括描述。因而为了躲避官方的苛捐杂税和胥吏劣差的欺凌勒索。华商只能想方设法托庇于洋商。三是报效对民族航运企业的制约和伤害。所谓报效,就是企业对于政府的回报,这种回报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只可有不可无。新成立的轮船公司既要交厘金又要向清政府提供报效,难以与既不需交厘金又不用提供报效的外国轮船公司竞争则是明显的事实。
(三)外国船商的特权及垄断
鸦片战争后,外国航运势力开始侵入中国。轮船在技术上所显示的优越性及对中国木帆船造成的竞争压力,使得中国木帆船的传统航运业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东南沿海的许多口岸,木帆船都遭到了轮船的排挤,经营范围也开始受到严重削弱。外国商船“资本既大,又不患风波盗贼,货客无不乐从,而上海之商船船户,尽行失业,无须数月,凋敝立见”。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也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从本地船只转移到外国船只手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口岸,扩展航线,进一步降低了关税和子口半税税率,给予外国船商更多的优待,并正式放开豆禁。从此大量外国轮船涌进牛庄港,使该埠沙船进口量减少1/3以上。同时。本国木帆船又受到了来自清政府的盘剥。1862年,清政府规定,对中国商船除原定征收商税、船钞外,又增加海船商号输捐,商船承载量为300担的需捐银25两;而自400担起,每增加200担即加银25两,并依次递增。这就是说,一艘1500担至2000担的船只出海,非先交数百两银子不可,这对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