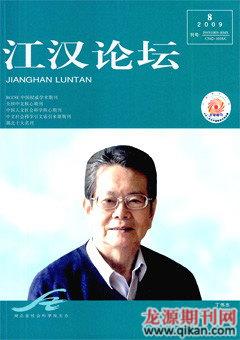传统汉语批评的主体自在性
褚 燕
一、自由之身
文论以人类的精神产物文学为研究对象,其自身亦是人的精神产物。言说者的知识素养、生存方式、言说时的心理状态必然或多或少地呈现于批评话语之中。传统汉语批评的主体性尤其鲜明,并直接影响到文论传统的生成和沿续状态。而这种鲜明主体性和言说者身份的模糊性形成了有意思的比照。
传统汉语批评的言说者是很难进行清晰界定的群体。首先,中国古代没有纯粹的文学理论家,或者说汉语批评的写作并不是一种职业。“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中国传统文论从自觉期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文学素养是进行批评言说的基本要求,“诗必与诗人论之”。历史的事实是,言说者的创作越突出,其批评话语越受到重视。如曹植所言:“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以断割。”譬如唐初反对南朝诗风,唐宋古文运动,明代的复古与反复古之争,历次文学运动的理论提倡者和大力推行者都是文学创作中的领袖人物,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和对他人的影响推行其文学思想,从而引导文坛风气的走向。其次,传统汉语批评的言说主体缺乏自觉的身份意识:“中国古人也很少有意识去做一个职业理论家或职业批评家,在他们,讨论文学问题或从事文学批评只是一种业余的爱好,而不会成为终生的事业。”
正是因为这种非职业性,传统汉语批评写作似乎成为随时敞开的场所,故而汉语批评的言说主体呈现为一个成份复杂且变动不居的群体——除了以文学创作见长的文士之外,还有皇室成员、国士重臣、文坛领袖、下层士人,市井书商……哲学家、经学家、史学家对于文学现象的关注也同样的强烈。言说者的身份地位、学养构成、兴趣取向、个性特征,直接影响着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
二、自然之性
汉语批评从来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言说主体的“自由之身”——身份的开放性。导致了绝大多数言说者采取了一种诗性的“自在”态度——主体的体验和情感占据了主要的空间:感性话语多于哲学思考,情感体验多于理性梳理。言说者坦露出才性的自然和率真。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就曾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对古代文论鲜明的“主体性”作过如下论述:
我们翻开我国所有的论文的书来一看,觉得他们都是兴到而言,无所拘束的。或友朋间的商讨,或师弟间的指点,或直说自己的特别见解,都是兴会上的事体。……但是我们要知道,惟其他们都是兴会所到真情流出的批评,所以我们现在把他整个的叙述出来,才可以使人从许多个别的“真”得到整个的“真”。
虽然并非所有言说主体都是在如此随意的状态下进行批评和研究,但“兴到而言”、“无所拘束”、“真情流出”数语,确乎能描述出汉语批评所由产生的那种相对自由的语境,以及言说主体所采取的开放无拘的姿态。士人们无所顾忌地炫耀着自己的艺术才华,以自由任性的姿态标榜着自我的审美态度和兴趣偏好,把文论写作当作自己人生理想、人格追求、人生趣味的象征和安放之所。早在先秦诸子文论中,我们便可发见这种对个体生命之关照的言说。
先秦诸子言诗的内在动机,是出于对文化理想的构建和播布。与后世士人言论喜涉及文学艺术等人生闲趣不同,先秦士人言说的主要内容是以政治、社会、伦理和道德为核心的“人文理想”,无关宏旨、无益于治国之道的玄说清谈在他们的话语中极为少见。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士人对于文学艺术的关注是相当有限的,先秦文论思想被笼罩在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之中。然而,在诸子文论宣扬文化理想、描绘政治蓝图的显性话语之下,存在着另一层面的隐性话语。这些隐性的话语,往往与言说者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合,甚至背离。如从显性上来看,孔子重言是因为言可以助政事、助德行。另一方面,孔子又陶然于文学艺术给他带来的“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与弟子对话中所描绘的理想生活场景,似乎与政治教化干系甚远。《论语》里常可见到孔子弦歌鼓舞的悠然之乐,可见文艺活动乃是这位老夫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在这隐性的话语层面上,孔子更为看重的是文艺的抒发怀抱以及精神愉悦功能。这种显性动机和隐性话语的冲突在先秦道家的文论言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了。一部《庄子》充满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在言说话语上,反文艺的先秦道家最为鲜明地体现了艺术精神。在济世之心和对自我生命的关怀的双重心理动机的作用下,形成了诸子文论中政治功利和自由和谐的人生境界相结合的内外张力。而这种美善并兼的人类生存,正是中国传统士人们的文化理想。
三、无用之用
随着封建大一统政权的建立,构建于先秦的士人人格在强权政治下遭受冲击,士人沦为政权的工具,“为帝王师”的理想成为狂人臆语。在统治者眼中,士人没有学术流派之分,只有有用之人和无用之人的区别。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南朝之后士人知识结构中心转向文史之学,传统士文化中雅的一面发展起来。士人热衷于文学艺术,沉醉于审美境界,通过对文学的言说来展示个人的才华,追求高雅的情趣。文学艺术成为了士人安放身心的优游之所和构建主体审美型生存的途径。于是在诗酒之会、酬唱赠答的轻松环境中,产生了大量“以资闲谈”的诗话、词话——“可以资闲谈,涉谐趣。可以考故实,讲出处,可以党同伐异,标榜攻击,也可以穿凿傅会,牵强索解;可杂以神怪梦幻,也可专讲格律句法,钜细精粗,无所不包”。似乎可以有许多用处,却无一与经邦经国相关。这些正是言说者轻松自在的言说状态所直接导致的。
传统汉语批评的言说者常常视文学研究为失意于仕途时的情感寄托:“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当刘勰之心还未找到理想的载体时,文学便是寄托心灵的林间旷野。政事追求是传统士人自我人格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入仕济世的理想无法实现时,便在精心营构的文心之梦中宣泄情感。出于这样的心理动机,文论家往往视文论之作为疏离仕途之外的名山事业,在其文论言说中贯注大量的精力和情感。这样的“发愤之作”中寄托着论者的鲜明个性和锦绣才情,是传统文论中的精粹。李贽因与上司冲突,辞去官职后奋然著述,这位不合时俗的思想家,选择了评点小说来表达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
和尚自入龙湖以来,口不停诵、手不停书者三十年,而《水浒传》、《西厢记》尤其所不释手者也。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故评之为尤详。据和尚所评《水浒传》,玩世之词十七,持世之语十三,然玩世处亦俱持世心肠也,但以戏言出之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语言文字之外。
玩世之词、持世之词构成了出世和人世、超脱之雅趣和济世之情怀在文论话语中的矛盾张力。因而,传统汉语批评的“无用之用”,并非完全不涉功利,只是功利之心失落后无奈的宣泄和寄托,本是不得已,但却恰恰在“无用之用”的文
论话语中,去除蔽障,摆脱外物,使得主体自在性得到充分展示。
毋庸讳言,传统汉语批评的写作中也往往掺杂着对名利的追逐,有的人以文论写作为进身之途径。有的人则直接是针对市场的需求。这种动机下创作的文论,当然也不乏佳作,但由于绝大多数是为“投人所好”而作,失去了主体的自在性,其文本价值也大打折扣。譬如冯梦龙编评“三言”便是应贾人之请。冯氏很聪明地把握了通俗小说趣味性和教化功用之间的平衡点,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而另一方面,他为满足市场需求,有意回避了文学性的评论,其小说评点的理论价值并不高。金圣叹的评点之作则不然:迄今为止,很少有资料显示他的评点改编工作与书商有直接关系,他甚至是有意地与商业操作保持距离,但这一点却恰恰使他的批评工作具备了更高的价值,实现了无用之大用。
传统诗学与文学创作一样,最终成为主体内部生命能量的自然流露,成为人们安顿心灵的家园。言说主体的自在性使传统汉语批评成为士人精神气质和人格的体现——先秦诸子的哲学思辨,两汉士人的人世情怀,魏晋士人的超脱飘逸,宋代理学家的道学气象,晚明士人的世俗化,无不贯注于其时的汉语批评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神命脉。
然而在今天,汉语批评“性灵的言说”越来越为“谋生的言说”所取代。与千人一面的文论格式相对应的,是言说主体自在性的丧失。文论写作的目的很单纯很直接,就是为求发表,以作为评职称、学科点建设的筹码。这样的批评文本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远远不及对学术制度和市场逻辑的遵从,主体自我的表达更无从说起了。托尔斯泰认为,写作的职业化是文学堕落的主要原因,对于文论写作而言同样如此。当汉语批评成为谋生的手段,成为换取利益的直接工具时,不被败坏真的是一件难事。
注释:
①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②刘克庄:《跋刘澜诗集》,《后村先生大集》第109卷,《四部丛刊》本。
③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④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页。
⑤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页。
⑥《水浒传》卷首《批评<水浒传>述语》,容与堂刻本。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