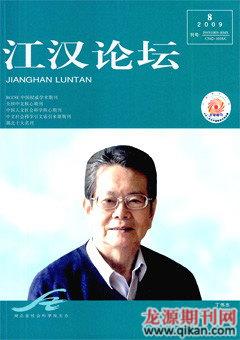汉语批评之诗性言说及其美学渊源
一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是一种诗性言说,明显地异质于西方诗学话语。这表现在其言说的高弹性和其句法的自由性两个方面。传统文学批评重意会、重气韵、重兴象,具有极强的人文化和风格化的色彩。这些特征都必然而当然地吻合于传统文学批评诗性言说。即如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在其《词与物》中所指出的,中国“所使用的语言,它的句法,它对事物的称谓和命名,甚至该语言中联系词语的语法规律,都与我们已知的一切相左”,传统文学批评的内在性、此岸性、意蕴性等诗性言说方式都与西方不同:其诗性言说的核心范畴味、神、韵、气、象等也是独特的,所以德里达认为汉语批评的诗性言说是“所有逻各斯中心之外所发展起来的强有力的文明态势的明证”。传统文学批评的诗性言说方式首先表现在其非逻辑形式结构之上,具体说来,则表现在汉语批评诗性言说的高弹性以及其启迪性、开放性等方面。汉语批评的诗性言说很难划分词类。比如“风、雅、颂、赋、比、兴”,在《周礼-春官·大师》中所谓“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为六种诗体,而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而“风、雅、颂”中的“风”,《毛诗序》中有这样的解释:“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同样一个“风”,有的是名词,有的则是动词,即感化、教化、讽谏等。在这里,一个基本词根,作名词、动词、形容词时,读音各不相同,同时字也各不相同。词性使用的随机性、滑动性可以说是传统文学批评诗性言说方式的第一个鲜明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
传统文学批评诗性言说方式常常是隐喻性的,具有一种集体表象的朦胧的互渗性质。它们的内涵外延也常常是流动的、不确定的和发散式的。例如,在中国古代,作为一种意指系统,“文”的涵义极为丰富,就“形文”看,是彩色交错,是杂多的统一,是纹理、花纹;就“人文”看,是文章、文辞、文字、文词、文采,是鼓乐,是表现形式,是法令条文,是社会与自然界的现象,是天文、地文、水文,是美,是善,是文德;同时,在中国古人看来,“文”是生成而不是现成的,“文”是“与天地共生”,发生构成于终极的构成域“道”,其自身的缘发构成态表征为“自然”,可以说“文”就是一种不确定形式,体现了一种发散式功能,展示了汉语的流动本性,这其中有自然之文,有人文之文,也有文学之文。纵观整个意义域,其中“文”的含义有文化、文明、文学、天文、人文、文字、文采等等。但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看来,这些“文”的横向连锁关系和纵向层次关系都是“相当混淆”的,因而也是缺乏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常常用意象性名词而不习惯用抽象性名词,于是在中国传统诗学中,“不同的写作方法被称为‘隔岸观火(一种超俗的格调),‘蜻蜓点水(轻描淡写),‘画龙点睛(提出作品的要点),‘欲擒故纵(起伏跌宕)……”正因为如此,索绪尔才认为汉语是不可论证的语言。
传统文学批评诗性言说方式非常注重再创构中意义的建构生成,即再创构中意义在批评文本与接受之间的互动、生成。因为,在中国传统批评家看来,“文”是“与天地共生”的,是在天、地、人三才间,通过相互作用、互交互动而建构生成的。其生成与建构过程展示了人的本性不断完善、丰富的历程,显示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即如《周易·系辞》所云:“物相杂故日文。”《国语》也云:“物一无文。”“文”是杂多的统一。所谓“物相杂”就是“天文、地文、人文”的杂多统一。单一的事物,是不可能构成“文”的。而在《易传》看来,众多事物的最基本构成要素是乾与坤,即天与地,宇宙万事万物及其各种属性,包括阴阳、刚柔、动静、仁义等等,都是由乾坤天地所构成的。因此,韩康伯解释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刚柔相错,玄黄错杂。”《易·贲卦·彖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就是以天文、地文、人文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相互统一、相互构成的观点来解释“文”的发生构成的。“贲”的本身就是“文”。所谓贲卦,离下艮上,离代表火,属柔,艮代表山,属刚。“文明”指“离”,“止”指“艮”,所谓“文明以止”也就是“刚柔交错”。可见,无论是“天文”,还是“人文”,都是由“刚柔交错”而相构相成的。天文、地文、人文是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相互统一的,即如天道、地道、人道的相融相合、相交相流、相互统一,都是自然而然、遵从天势的。汉代王充也曾运用天文、地文、人文是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相互统一、相构相成的观点来论述人不能无文的。在他看来,“人文”的构成也是自然而然的。他在《论衡·书解》中说:“山无文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采。”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认为,
“文”及其审美意味是生成与建构而成的。并由此而重视文学批评中的诗性言说。
生成与建构体现了人类文化形式的多样统一。可以说,正是由于“文”是建构而成的,所以其意义具有多重性,并表现为一种意义系统。
传统文学批评的诗性言说确是重意义的构成与生成,而不重形式论证的语言,它表现出很强的人文性、风格化和诗意化。
重意会。传统文学批评诗性言说方式追求以意逆志,强调意会意合。注重意会意合而不重形式结构,给传统文学批评留下了相当广阔的再创作空间。即如叶维廉所指出的:“中国传统上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为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
重自然。传统文学批评认为“文以气为主”。传统文学批评对文气及其自然生动的重视,来源于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首先,气是万物之源;其次,气是精神之源;再次,气是文章和语言之源。所以,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性”之际,文学家、诗人就要感应宇宙之生气,充实自己之灵气,最后使文气和语气与这些“气”相通相应相和,从而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重感兴。传统文学批评诗性言说方式显然不喜欢抽象的概念,他们习惯于“观物取象”,使概念生动可感,并有所依托。传统文学批评更多的是从读者一方出发,在读者和作品中充当桥梁的作用。它往往用极精练、极隽永的语言来点出作品的关键,以启发读者更准确地领悟作品精微、含蓄的意旨。钱钟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中
说:“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蓄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这种用“三言两语”说出“精湛见解”的方法,就是诗性言说方式。这种传统诗性言说方式讲究言简意赅,点到为止,看似只言片语,其中却包含着深刻的理论见解,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二
传统诗性言说方式的这种重意会、重自然、重感兴是有其深刻的美学渊源的。它建立在中国古典美学“大象无形”、“大美无言”、“言有尽而意无穷”和“妙悟”说之上。
“大象无形”之说见于《老子》第四十一章。王弼《老子指略》解释说:“大象,天象之母也”;“有形则有分,有分者不温则炎。不炎则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大象”是诸形(物象)的抽象,“故象而形者,非大象”。“有形则有分”,“形”具体而可分,“无形”的“大象”便是诸形的抽象的“集合”,是不可分的整体。“大象无形”之“大象”,乃是超越有限个别事物的直观形式,是无形体可求,与“气”相融、为“道”的呈现。“象”表征着万物自然的生命运动,来自圣哲对宇宙万物的宏观把握,并在道家的哲学体系中成为沟通“道”、“物”、“气”、“意”、“言”的重要的中间环节。
老子“大象无形”的“象”说,通向“气”与“道”,包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重视“象”的虚空超越,对“象”的意象而非言语的符号指涉功能作出了种种描述和规定。《老子》书中多处提到“大象”,如云:“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四十一章),老子以“大象”来表征“道”,以体现“道”的虚空无名之状。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嗷,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十四章)这里所谓的“夷”、“希”、“微”都是就作为生命本原的“道”而言的。道化育自然万物,并且作为生命的核心存在于自然万物的底蕴;自然万物可见、可听、可触,所以说有“状”、有“物”;而作为自然万物生命本原的“道”则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触,所以说“无状”、“无物”。然而这里所谓的“无”又不是真的什么也没有,而只是“无序”、“无形”,“是谓惚恍”,是“夷”、“希”、“微”。
在老子美学看来,宇宙万物的生命本原是“道”,这种“道”是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音希声”。所谓“大音希声”,王弼注云:“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声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王弼集校释》)换言之,即“无物之象”、“大音”、“大象”之类都是美的生命本原“道”的呈现,因此无论用什么具体的言辞声音都不能把它传达出来;或者反过来说,一旦诉诸任何具体的言辞声音。它就不再是“道”本身了,因而也就不是“大音”与“大象”的“知者”。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又说:“绳绳不可名、复归于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十四章)“道”呈现为“物”与“象”,表征为无形无状,惟恍惟忽,同时在恍忽无形之中又有“象”有“物”。应该说,这种若有若无之“象”,对作为宇宙万物构成之本源的“道”的存在作了极其精微的阐发。这种构成是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只能凭借意象,存在于人的意象感悟和体验中。《老子》全书充满了这种意象感悟的符号,如“水”、“谷”、“母”、“朴”、“阴”、“玄牝”、“婴儿”等,它们都指向“道”这一不可言状,难以穷尽的宇宙万物构成之源。老子这种虚象非言的意象符号指涉功能的确认,使他进一步提出了有关美学创造和再创造中的一系列范畴,如“虚”、“实”、“有”、“无”、“妙”、“味”、“玄鉴”等。其中,“虚”、“无”、“妙”、“味”、“玄鉴”等具有形而上超言语意义的范畴,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建构尤为重要。特别是“无味”之“味”范畴的提出,以“味无味”言“大象”之“象”的审美境域方式的确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诗性言说方式的生成,因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诗性言说,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味象超象、形而上超经验的文本审美意味的生成与构成。
老子以后,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大象无形”的“象”说思想。庄子美学对现时存在的把握,无时无刻不保持着一种“象”的体验的完整性。在老子“大象无形”的“象”说思想上,庄子又进一步提出“大美无言”说和“至美”、“全美”,提倡“无言而心悦”。庄子承继了老子道、气、象的哲学,执“大象”而言“道”,道、气、象三者融通同一。不过,相对于老子,庄子所说,更是以“虚”、“无”为本,强调不可名状和不可言说。他说:“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庄子·天地》)这就是说,“道”视而无形,听而无声。但无形无声中又见明朗之象,又闻至和之音,这便是“道”的呈现和显现,所谓“视”“冥冥”、“听”“无声”、“独见”、“独闻”,乃是一种对生命境域和审美意味的体验和感悟,语言文字当然是无法表述的。《庄子·田子方》言老聃游心于“道”,“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但其内心体验却能再现翱游天道的景象,从而得“至美至乐”,达到“至人”的境界,这亦表现了“道”意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庄子言“象”,蹈虚非言,重体验感悟,可以从他关于“象罔”、“浑沌”、“滑疑之耀”等寓言比喻更明显见出。《庄子·天地》中讲了一个寓言:“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口契)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这里的“玄珠”表征“道”;“知”表征思虑、理智:“离朱”是传说中黄帝时代视力最好的人,表征视觉;“(口契)诟”表征言辩。寓言的意思是说,用思虑、视觉、言辩得不到的道,用“象罔”却可以得到。“象罔”表征有形和无形、虚和实的结合。吕惠卿注云:“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瞰不味,玄珠之所以得也。”(《庄子义》)郭嵩焘注云:“象罔者若有形若无形,故眸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庄子集释》)对此,宗白华解释说:“非有非无,不皦不味,这正是艺术形象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真理闪耀于艺术形相里,玄珠铄于象罔里。”按此解读,“象罔”似有若无、恍惚朦胧、“浑沌”、“滑疑之耀”的状态,就是一种虚幻的“境相”,它“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是超言语超经验的,是一种以“象”的虚空为极诣的深刻人生体验和人生境界的实现。庄子这种对“象”的描述和规定,与其《天道》篇中所说的“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有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的思想是相互一致的,上承老子“象”论,下启魏晋玄学以“无”为本体的对“象”的义理发挥,并直接引发了佛学的“象外之谈”,同时,由此而构成传统文学批评诗性言说方式赖以形成的美学渊源。
传统文学批评诗性言说方式虽然从总体上讲,以老庄“大象无形”的“象”说和“大美无言”思想为出发点,言“境”不离“象”,但其重点又在象外之象,在诗性言说所构成的象外虚空中揭示人生意味并构成审美境域,所以,应该说是老庄“大象无形”、“大道之象”的哲学和重“象”外虚空、非言味象的提出,奠定了传统文学批评诗性言说方式的理论基础。
注释:
①转引自盛宁《道与逻各斯的对话》,《读书》1993年第11期。
②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③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④李天道:《中国古代“文”符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11期。
⑤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