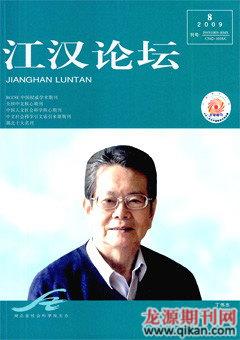从先秦诸子的对话体看汉语批评
袁济喜
汉语批评的理念与方法,肇始于先秦诸子的思想文化。其中一个显要特点便是采用对话的形式来从事文化批评,而文学批评从属于这种思想对话。汉语文学批评的文体特点是好用随笔即兴的方式,通过讨论与对话来开展批评,《六一诗话》一般认为是诗话的开端,清代袁枚《随园诗话》最为有名。诗话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最有民族特点的方法与形态。它的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具体说来就是从生活出发,随机应变,善于在实践与体验中来把握对象。领悟诗性,升华精神,培养人格。这一传统在先秦诸子,特别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当中表现得很明显。
先秦诸子的思想对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对话的滥觞,也是汉语批评的母体。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形成,直接促成了思想对话的繁盛。百家争鸣从现代对话精神来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与思想得以生成的良好发端,争鸣与对话向着“和而不同”、融会百家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段话说出了中国古代自先秦开始的思想对话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争鸣是对话的表现形态,对话则深化了争鸣,光有争鸣而无对话,则可能走向对抗乃至于斗争与毁灭。因此,对话是争鸣的基础,对话与争鸣相比,更能彰显出其中的人文蕴涵与“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的特点。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班固的说法虽然有张扬儒学的意思在内,但他也看到了先秦诸子思想对话与争鸣发展的路径,是由各执一端走向百川归海。证之以先秦两汉以来的思想发展轨迹,从经典形态的演绎,比如由诸子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发展到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可知此言不虚。而这种发展与演进的基本条件是对话。百家争鸣如果没有思想对话的展开,就会导致秦朝焚书坑儒的悲剧出现。要想避免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则自由的思想对话是前提,从先秦到两汉时代,这里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都曾出现,成为令后人感思的历史现象。
先秦诸子对话与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文化的看法上面。礼乐文明是整个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血脉,它建构在深刻反思人性与人生问题的基石之上。具体说来,先秦时的各家各派都专注于人性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由此而生发出礼乐文明对于人性与人生的价值与作用的讨论,这一点在儒家的孟子与道家的庄子中可谓针锋相对。即使在儒家内部,孟子与荀子也是分歧与争议颇大。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生问题都被汇集到这一范畴中来。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诸子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儒家的孔孟力主在传承中对于礼乐文明重新解释;而道家的老庄则主张回到人类的原初状态。废弃礼乐器具:法家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提出用法术权势代替传统的礼乐;墨家从节用的角度提议废除礼乐。当时的文论属于所谓杂文学的范畴。由于中国古代的文学问题一直与社会人生和政治文化相关系,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乃是社会人生,人性学说乃是这一问题的底蕴,儒道两家的对话与争鸣,促进了两家思想的融合与互补,为秦汉时代的思想融合与发展作了铺垫,奠定了中国文化中儒道两家互相补充又互相对立的格局,是中国文化“和而不同”风采的体现。
孔子是先秦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他对于中国古代文艺对话的思想智慧与语录体影响甚深,其门人记录下来的《论语》直接开启了以语录体来教育学生,从事思想阐释与建树的先河。《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关于文艺的对话,堪与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文艺对话录相媲美,从中可以见出中西文艺观念的不同与各自风采。孔子将仁学与礼乐文明结合起来,用诗书礼乐教化学生,培育人格。孔子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仁学与礼乐思想,他从精神文化的高度奠定了汉语批评的核心价值观念与批评方法。《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具体解释道:
梁皇侃撰《论语通》曰:《论语》者,是孔子没后七十弟子之门徒共所撰录也。夫圣人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或负(户衣)御众,服龙衮于庙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缝掖于黉校之中。但圣师孔子,苻应颓周,生鲁长宋,游历诸国,以鲁哀公十一年冬,从卫反鲁,删诗定礼于洙泗之间,门徒三千人,达者七十有二。
但圣人虽异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则朽没之期亦等。故叹发吾衰悲,因逝水托梦两楹,寄歌颓坏。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后,过隙叵驻。门人痛大山长毁,哀梁木永摧,隐几非昔,离索行泪,微言一绝,景行莫书。于是弟子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
从孔颖达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论语》是其门徒为了传承孔子的思想事迹而编成的一部书。值得关注的是,孔颖达用了三国时魏国玄学家王弼关于圣人有情而不累于情的观点,说明孔子是一位深于情者,平时应对各方,随机而教。至于为什么采用《论语》这种载体,孔颖达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又分析道:“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孔颖达在这里谈到,《论语》这部书是适应着孔子生平事迹与思想特点而编就的,孔子虽为圣人,但是生平为教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其思想的特点适于采用《论语》这种体裁。
从人物性格来说,孔子与学生相处,本来就很随和,他的思想理路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实践理性特征。即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开掘其内在理性与道德思想的火花。这种从当下性生发出来的思想品格,本身就具有感兴特点和审美价值,而且孔子与学生对话中产生出来的隽言妙语,极具文学性,直接影响到后来汉语批评中的诗话体。现代学者和作家林语堂说过:
孔子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于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得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做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
林语堂为此在上个世纪提倡语录体,被称作《论语》派。林语堂认为孔子在漫不经心时说出来的话之所以“妙不可言”,显见得是即兴而言的,
本身就是审美经验的一种。因此,从对话的角度去考察孔子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后世汉语批评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论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与古希腊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中的对话有所不同,前者重在理性的昭彰,而后者则重在知性的感发。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批评孔子至多是一些道德箴言,没有什么体系。这说明他不了解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与理论观念。孔子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承载者,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实践理性,符合中国人的人生观与理性观念,中国人不喜欢将理论变成灰色的思辨的对象,而喜欢知行合一、履践为上的知性与悟性。而黑格尔自己大约也没有想到,在他死后二百多年,他的故乡德国也兴起了一股反对唯理论,倡导现象学与当下性的思潮,影响到文艺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东方孔子式的语录体语境中。
先秦诸子文论集中在对于周代礼乐的看法上面。而礼乐涵括了道德与文艺的内容,先秦儒家思想是从礼乐角度去体认道德与文艺问题的,这一点在孔子思想中表现得很明显。孔子本人十分重视文艺的对话与沟通作用,这是由农业文明与继之而起的宗法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以血缘宗法作为纽带的社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时候主要通过对话与讨论来进行。学问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切磋,所谓“百姓日用即为道”的观念很早就在中国古代社会萌发了。而诗歌与音乐在当时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承担人际关系的交流。列夫·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艺术源自个体与社会的沟通,是祛除个体孤独的重要渠道。这一思想与孔老夫子的诗学倒是颇为相合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所谓“群”,据后人解释,也就是“群居而切磋”,即互相交流思想感情的意思。可见在对话中能够拓展人的思想境界。古代中国人对于诗乐舞的功能与作用,是从农业文明中的人际关系去体认的,强调诗乐之中通过思想交流,促进对话,和合人际关系。“诗可以兴”与“诗可以群”的关系如何处理呢?这一问题值得探讨。实际上,诗的“兴”、“观”、“怨”,都是在“群”的基础之上得到认同的,而不是游离于此而展开的。此一点要特别强调。明末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一中提出: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而怨,怨亦不亡;以其怨而群,群乃愈挚。
王夫之在这里强调了群与怨之关系。“群”的对话与交流是解读诗作的人伦基础。孔子自觉地强调《诗经》中的这种对话与沟通功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君子应当知命知人,而知人在于知言,即能够和别人沟通与交流,而这种知人也是智者的本领之一,与仁者爱人是互相配合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知是仁的运用,仁是知的基础,二者是互动的关系,不能够知人又怎么能爱人呢?这是孔子仁学的重要观念。孔子在教育儿子时说:“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意谓不学习《诗经》,就像面对墙无法前行一样,不能与别人进行对话与交流。《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召南》,反映了受周文王德化熏陶的周地的良好古风,也是孔子推举的仁义之风的来源。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诗经》中《周南》、《召南》中弘扬的这种道德观念与思想感情,就会以仁者之心去待人接物,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
中国古代的宗法社会很早就将艺术纳入社会宗族群体之中,这便是所谓“礼乐相须为用”的文明教化体系。礼之中既有内在的属于同一性的原始血缘伦理基础,又有显在的差异性。因此,这种特殊的政治伦理、宗教体制便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审美文化与操作体系来修饰。《礼记·乐记》指出:“乐合同,礼别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在儒家看来,宗法社会中的礼是用来区别不同等级之人的,乐是调合不同等级与身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由于处于同一个血缘体系之中,于是在情感上也就有了互相认同与交往的基础了,而艺术可以承担调谐人际关系的职能。孔子还教训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还有意识地强调,《诗经》学得再好,如果不能应对出处,虽多也无益。“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从这些方面来看,对话意识的自觉与运用,是基于孔子的仁学思想品格的。
从孔子与弟子论诗的资料来看,孔子对弟子的启悟通过对话而得以实现。比如《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而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所引的诗见于《诗经》的《卫风·淇奥》,内容是赞美一位有才华的贵族宽厚待人。孔子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虽然是一种好品德,但还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后者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的启悟下,子贡立即想到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两句话,意为君子要达到最高的道德境地,还必须不断切磋磨练自己,孔子因此高兴地对子贡说,我可以与子贡谈论《诗》了。从这一段饶有风趣的对话来看,孔子与弟子论《诗》,首先是从感兴的方式出发,启发学生,让学生通过艺术欣赏的方式来举一反三,也就是所谓“引譬连类”,从个别的作品出发升华到对含有普遍性的宇宙人生哲理的把握。
由于孔子《论语》对话中蕴涵的农业文明的特有语境,不离形象与感性色彩,故这种对话体与含蓄性,使后人在阅读时有极大的感受与阐释性,从而引起精神人格的升华。朱熹在《孟子集解》之《孟子序说》中引北宋理学家程颐的话说:
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气质!”
程子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这两段话若从当代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认识,是极有价值的。从中可以看出,《论语》的开放性与其文体样式(即语录体)是直接关连的。程颐提出,读者不妨设想为孔门弟子,与圣人对话与交流,从中汲取营养,他并且强调读者读了后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响,有读了后全然不知晓者,有读了后得一二语者,有读了后手舞足蹈者。他自称读《论语》后意味悠长,历久弥深:“程子曰:顾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朱熹《孟子序说》引)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阅读效果,显然与《论语》的文体样式即言说方式有关。
谭家健先生认为《论语》是后世语录体的鼻祖:“《论语》除了在语言艺术、个性描写,故事记叙等方面给予中国文学史以广泛影响之外,它所首创的语录体,也常为后人所效法。”孔子及其思想通过这种语体与后人对话和沟通,其思想风采和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使后人睹其风采而不能忘怀。孔氏书的对话魅力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对话与语录体是承载孔子思想并流传后世的重要文体,既是形式也是内容。从这一意义去认识孔子与汉语批评,我们就不至于光是注重其中的思想而忽略语录体本身的蕴涵了。
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去分析的话,孔子《论语》中出现的对话体思想学说,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世俗性,排除了宗教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治。任何宗教,不管它是何种形态的,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依据信仰来建构,而精神信仰则由一些绝对性的律令与教条构成,它是神圣不可逾越的,由此而造成它的原教旨,往往杜绝对话与沟通,崇拜绝对真理而忽略当下性。而孔子的思想虽然也带有精神信仰的色彩,如他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是更注重其现实品格与实用性的一面,孔子所倡导的“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与中庸之道,更是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重视对话的人性基础与现实品格。因此,先秦诸子的对话风格对于汉语批评的言说方式的影响至大至深。
注释:
①林语堂:《中国哲人的智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9页。
③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32页。
④谭家健: 《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