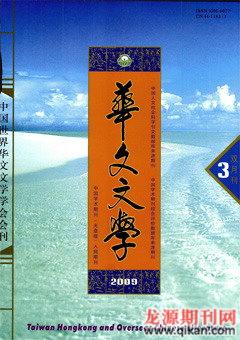从意识与技巧之争看海内外文学观念差异
吴宏娟
摘要:着眼于张爱玲研究中的意识与技巧之争,从张爱玲的女性写作切入,探讨海内外学者在意识与技巧关系问题上的差异:大陆学者多是就意识而谈意识,将张爱玲甘于“第二性”弱者的女性立场,以“补充”的姿态“纳入”中国新文学女性文学传统;海外华人学者在重视技巧的同时,将技巧联系意识,借张爱玲的女性写作技巧对中国男性主流文学传统进行破坏和颠覆。在双方文学观念冲突的背后,则是其各自文学研究方法——社会历史批评与文化研究方法的历史落差。
关键词:张爱玲;大陆学者;海外华人学者;女性写作;文学观念
Abstract:With the focus on the rivalry between idea and writing technique in Eileen Chang Studies,this thesis studies Changs feminist writings so as to probe into the divergence between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 and technique: Most scholars in Mainland pay much attention to idea and tend to incorporate Changs inferior position of the “second sex” as a supplement into the feminist literary tradition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Besides emphasizing technique,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associate technique with idea by interpreting Changs feminist writings as subversive acts to undermine Chinese androcentric literary tradition. Behind this divergence of literary view is,actually,the historical gap between their literary approaches:socio-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ds:Eileen Chang,mainland scholars,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feminist writing,literary view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006-0677(2009)3-0058-06
一、意识与技巧之争
20世纪40年代,当张爱玲在上海风头正健时,著名评论家、学者傅雷曾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成为第一篇正式评论张爱玲作品的文章。
傅文开篇便把矛头指向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重意识而轻技巧的问题:“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并进一步说:“瞧瞧我们的新作家为它们填补了多少”,亦即张爱玲在这个问题上对新文学“主张缺陷”的弥补作用。在这里,张爱玲的创作技巧被首次挖掘并得到了重视,如结构、色彩、节奏的成就,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的心理分析法,电影手法等。但是,“这巧妙的技术,本身不过是一种迷人的奢侈;倘使不把它当作完成主题的手段(如《金锁记》中的这些技术的作用),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古董”。傅雷此文似乎是由张爱玲创作技巧的独特性“有感而发”的对新文学重意识而轻技巧的弊病的批判,但他在盛赞张爱玲的某些技巧的同时,亦对她的滥用技巧非常不满。
在傅文发表后,张爱玲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对傅雷的批评作了远兜远转的辩解:“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重视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所以,她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向来特立独行,对别人的批评不屑一顾的张爱玲,居然撰文回应傅雷的评论,可见傅论若非戳到其痛处,也至少说到了关键问题上。
这番批评家与作者的对话的关键问题便是意识与技巧的关系。傅雷重视技巧,但坚持技巧应为意识服务,意识是第一位的;张爱玲则强调自己的写作技巧与其“人生安稳的一面”的意识是一致的。如果说傅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对技巧的忽视问题,那么张爱玲的“妇人性”则不动声色地把问题转移到了当时男性主流文学观与女性文学创作观念的冲突上,或者说,把问题引向了深入。
在半个世纪后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大陆学者刘再复与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也有一场争论。在该次会议上,刘再复发言称:“鲁迅看透人生,但又直面人生,努力与人生肉搏,因此形成男性的悲壮;张爱玲看透人生,却没有力量面对人生,结果总是逃避到世俗的细节里,从而形成特殊的女性语言。”他还进一步指出:“这里有一个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问题。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要看其文字功夫,而且要看其精神内涵与灵魂深度。”夏志清对此的回应颇耐人寻味:“张爱玲从来不想做‘男人,她总是坚持女性角色。坚持女性角色使她缺乏英雄气,有点‘难为情。作为女性就应该低声下气吗?”这仿若当年傅、张之争的翻版!然而,同一个的话题,随着争论的主角换成隔海相望的海内外学者,益加彰显了其中的差异和矛盾。而意识与技巧、男女性别政治这个话题,在半个世纪以来,又为什么值得张爱玲本人、傅雷这样的大批评家以及海内外学者一再争论不休?我们不妨以张爱玲的女性写作为着眼点,探讨海内外学者在意识与技巧的关系以及文学观念上的具体异同,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进程做出一点思考。
二、女性意识与大陆的“补充”、“纳入”说
张爱玲作为女作家的女性写作,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批评家的视野。女性文学史家谭正璧1944年发表了《论苏青与张爱玲》一文,把张爱玲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女作家苏青作比较,认为:“张爱玲在技巧方面始终下着极深的工夫,而苏青却单凭着她天生的聪明来吐出别的女性所不敢吐露的惊人豪语,对于技巧似乎从来不去十分注意。就文艺来论文艺,两个人的高下应该从这地方来判分和决定。”可见谭正璧多少受傅雷的影响,同样肯定张爱玲的创作技巧,技巧在这里相对意识而言占了上风。但是,在拿张爱玲与比她稍早的冯沅君、谢冰莹、黄白薇等女作家比较时,谭正璧认为后来者不能居上,因为“前者都向着全面的压抑作反抗,后者仅仅为了争取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前者是社会大众的呼声,后者只喊出了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面的苦闷”。在这里,谭正璧采取的是意识标准,而且此“意识”还有全面与片面、社会与个人之分。这两段话的明显矛盾暴露了谭正璧“意识第一”的批评潜意识。由此,我们又一次见识了“意识第一”这一文学观念在中国大陆批评家思想里根深蒂固的地位,这种根深蒂固,即便在他们已经认识到并有意识地试图纠正时仍会在某些环节不小心露出“马脚”。不过,从谭正璧的评张,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大陆张爱玲研究关于张爱玲女性写作研究的一些线索:一是张爱玲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在被拿来跟中国新文学以来的“女性主义”文学作比较时,其独特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凸显;二是张爱玲的创作技巧受到了重视,但是没有被明确与女性意识联系起来。
关于第一点,谭正璧在意识内涵方面对张爱玲创作中片面的个人的女性意识并不特别认同,但是,在80年代后期以来大陆对张爱玲的重新接受中,这一方面有了较大改进,对张爱玲女性写作中女性意识的独特意义有了更大的发掘。钱荫愉《丁玲与张爱玲:一个时代的升腾飞扬与苍凉的坠落》一文把丁玲与张爱玲相比,认为相对于丁玲早期小说中倔强的“第一性”女性,张爱玲“笔下的女子则是道地‘第二性的弱者”,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些女人人性中的弱点是导致她们命运悲剧的深层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如果说张爱玲是女性世界的深刻剖析者,那么丁玲则是彻底的批判者。40年代中国女性的心理情感结构,由于丁玲和张爱玲的描述凸现的完整、立体而富于历史感和文化感。”在这里,张爱玲被作为女性弱者及女性内省意识的代表、新文学女性反抗外部世界的反面而被纳入中国新文学女性书写的传统中。此后于青关于张爱玲创作中的女奴原罪意识的论述也大概是沿袭这一思路的。可见,关于张爱玲的女性写作,大陆多着眼于其女性意识,致力于发掘其中的独特意义和补充作用而将其纳入中国女性文学传统。
值得一提的是孟悦和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该书在指出新文化女性观实质上是五四男性的女性观——只谈男女平等而不谈性别差异,抹煞了真正的女性话语——的基础上,提出女性写作中女性自己的视点、立场及审美观物方式的重要性。这一观点的提出对大陆女性文学研究有重要影响,可以说是开中国现代文学女性性别政治研究之先河,对海内外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都有很大影响,甚至波及海外华人批评家,例如林幸谦的女性“闺阁政治论述”观点,周芬伶对张爱玲放弃女儿、妻子和国民身份的分析。因而,这本出自大陆学者之手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堪称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浮出历史地表”的标志性著作。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女性话语”的提出。这不仅与张爱玲的“妇人性”、钱荫愉的“道地‘第二性”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还在女性意识之外提出了女性的审美观物方式,这就涉及女性写作技巧。女性写作技巧终于随着真正的女性话语的提出而浮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水面。这不由令人深思:中国现代文学长期以来对技巧的盲视是否也正是源于五四以来的男性主流文学观?近代中国的内外交困使中国现代文学不得不肩负起国家、民族存亡的重任,强大的社会功能使它无形中更加注重意识的“宣传”而忽视了对技巧的选择,从而也更倾向于男性的阳刚气而忽视了女性第二性的特质。由此,我们可概括出大陆对张爱玲女性写作研究的基本历程:由男性主流文学观所决定,大陆重意识而轻技巧,导致对张爱玲的女性写作研究一开始更重视其女性意识研究,对其写作技巧的有限论述也并没有从女性写作的角度与女性意识明确联系起来;而在对其第二性的女性意识的研究中,则由一开始的否定到后来的肯定,再由此引起对其女性写作技巧的重视,从而使其写作技巧与女性意识联系了起来。然而,遗憾的是,即便是这本影响很大的《浮出历史地表》,其专论张爱玲的一章《张爱玲——苍凉的莞尔一笑》也并没有对它所提倡的女性写作中的女性视点、立场及审美观物方式就张爱玲这个对象作出详细的分析。而这一点,正是海外华人学者的张爱玲研究之所长。
三、女性写作技巧与海外
的“破坏”、“颠覆”说
在海外张爱玲研究中,张爱玲的女性写作技巧,作为其女性视点、立场及审美观物方式的具体体现而得到重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细节描写;二是电影技法。
(一)细节描写
周蕾《妇女和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的阅读笔记》一书着眼于细节,对张爱玲小说做出卓有洞见的分析。她认为“女性的特质就是细节”,一针见血地指出细节描写作为对抗整体、宏伟、统一、国家等父系符号的策略,在女性文体和美学上的重要意义,而张爱玲“把这些互相毫无关系的细节并列……把细节戏剧化,如电影镜头般放大,其实就是一种破坏,所破坏的是人性论的中心性,这种人性论是中国现代性的修辞中,经常被天真地采用的一种理想和道德原则”。
周芬伶在《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一书中对周蕾的观点有所发展。她从几个方面分析了“细节描述一向被视为女性文体的特征,亦是女性文体被排斥于主流文学的明显‘缺陷”这一关键问题的原因,具体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在小说场景铺陈、对话处理、作者语调上的体现和作用,认为张爱玲的细节描写作为一种女性特质,对新文学的“重要”、“伟大”主流采取“规避”和“破坏”策略,从而形成了她个人的苍凉美学。
许子东将钱钟书和张爱玲的意象营构特点进行比较,认为相对于钱钟书的“以抽象形容具体”,张爱玲往往“以实写虚”,“她笔下的人物常常以服装素描出场,最后性情命运又化为衣饰意象”。他最终把张爱玲的这种意象技巧与“贯穿其作品的美丽的苍凉感”联系起来,以《第一炉香》末端的一段文字作为“张爱玲对自己‘以实写虚意象技巧的一个理性注解”,认为张爱玲的这种以实写虚技巧,是其作品中女性借助实物寻求安全感的心理体现,也是张爱玲作为作家对其笔下人物体察入微并且贴切表达的结果。从而,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的苍凉体验与其文学写作技巧联系起来了,相对于其他五四女作家的从家庭走向社会,张爱玲借助细节描写“逃回”家居实物,正是其独特女性意识的体现。
这样,大陆学者孟悦和戴锦华所提出的对女性文学中女性特质的重视,在海外学者的张爱玲文学技巧分析中,得到了具体的阐释:张爱玲的细节描写通过对女性特质的标举和家居实物的回归实现了独特的女性意识与女性书写方式的展示。相对于大陆仅仅从女性意识、作品内涵方面把张爱玲纳入中国新文学女性文学史,周蕾等海外华人批评家的论述却是从写作技巧方面指出了张爱玲对中国新文学女性书写模式,甚至男性文学传统的颠覆。
(二)电影技法
周蕾在一篇名为《技巧、美学时空、女性作家——从张爱玲的<封锁>谈起》的文章中,提出妇女解放与其所处时空的变迁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时空变迁亦连带男女社会关系的彻底改写,而张爱玲的《封锁》正是利用“封锁”期间的公车,这一“与平常生活隔绝、疏离的时空”的技巧而达到对男女社会关系的改写的。也即,“以一个反父权主义的立场来看,张爱玲选择的,正是放弃了以男性为权力中心,放弃了以家庭、家族,甚至以理想人性这些连续性的历史观念为生命平衡点的‘正常时空”。她指出这种关系的变化与张爱玲对技巧的理解分不开:她深谙隔离带来的美学效果,在因为隔离而成的非常性时空里,种种平常生活中不可能的事都变成可能。而她对技巧的这种理解其实与电影“基于摒弃时间的连续性”的定义有着相通之处。从而,在这一点上,“她的文字却是绝对与新的技术意念、媒介意念走着同一步伐的”,也是西化的。
对周蕾提出的张作中运用电影技法而造成的美学时空,李欧梵除了表示这有助于打破由男人确定的日常时空外,还受此启发,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张爱玲与电影的“不了情”。他认为张爱玲与电影的渊源关系,首先体现在其文字中的视觉感以及电影蒙太奇方法的使用,更重要的是她对当时好莱坞爱情“谐闹戏剧”的借鉴。由此,李欧梵认为傅雷对《倾城之恋》的批评,实际上是其高调文学立场与好莱坞喜剧电影技巧冲突所致。李欧梵在稍后发表的《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一文中,更把“电影和电影宫”单列为一小节,分析电影如何“构成了她小说技巧的一个关键元素”:“在她的故事中,电影院既是公众场所,也是梦幻之地;这两种功能的交织恰好创造了她独特的叙述魔方”。他认为张爱玲借助电影技法而形成的隔离的美学时空以及好莱坞电影谐闹技巧,“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叙述造成了某种颠覆”。
与此相联系的是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及其作品的电影改编。郑树森最先对张爱玲的剧本创作予以关注,认为中国电影史应该有张爱玲的一席之地。周芬伶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发掘出张爱玲作为“女剧作家的反男性凝视”眼光。她认为在早期中国电影编剧的作用甚于导演,且男导演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张爱玲作为女编剧,其剧作无疑就像电影镜头,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男性凝视眼光而表达出了一个女性编剧的镜头语言,从而对主流电影用男性的潜意识,以女性为永远的凝视对象而构组的男性观众机制有所冲击。由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推及其文学创作中的电影手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如下理解: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电影手法,也是其女性视角与立场的一个体现?
在关于张爱玲文学创作电影技法的研究中,周蕾和李欧梵突出了这种创作技巧的实质及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第一,是张爱玲运用电影技法在隔离而成的美学时空里改写日常男女社会关系,在性别政治上具有打破由男性确定的日常时空的作用;第二,“这种把‘故事、‘内容与‘形式自觉性交叠在一起,使‘意识与‘技巧不能干净分辨开来的暧昧创作法,正是现代性的‘技巧问题的关键”;第三,“这一种新的视觉媒体往往不为五四作家的重视,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亦复如此。”
他们的观点颇引人深思。首先,与张爱玲的意识与技巧合而为一的创作手法相对应,海外批评家在这里可以说明确表达了自己关于意识与技巧关系问题的看法。但是,何以这是“现代性的‘技巧问题的关键”?海外学者如何识别这个所谓“现代性”?其次,关于张爱玲的电影技法,其实傅雷早在其评论张爱玲的那篇文章里就提及张的“节略法的运用”,并指出“这是电影的手法”,起到时空转换的作用,但是长时间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并没有更多的论述,倒是海外学者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在这里面,是海外学者的得风气之先,还是大陆真如海外学者所言的文学传统里有着对视觉的忽视?
我们不妨倒回来看这几个问题。首先,海外学者对视觉的重视,来自于对电影影像研究的重视,而电影研究在西方是由女性研究发展而来的——西方女性学者发起由性别政治的角度研究电影,一般认为偷窥女性的行为奠定了好莱坞的电影模式,同时女性研究、电影研究与视觉研究又一起构成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主流。可见,海外学者关于张爱玲的女性写作及其电影技法、文字中的视觉感的研究,其实是一体的,是西方文化研究模式的影响所致。其次,海外学者所谓现代性“技巧”问题的关键,即“意识”与“技巧”不能干净分辨开来的暧昧创作法,如周蕾所说,实际上是提倡一种跨感官性及跨媒介性的叙事方式——在从文字到视觉的跨越中实现细节感官的跨越。这种对“跨越”的提倡,意味着边界的模糊和界限的打破,实际上反映出整个西方文化研究潮流的本质特征之一——在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上的跨专业、跨学科与跨领域。这样看来,海外学者对所谓现代性技巧的理解,仍然还是由西方文化研究思维模式决定的。因而,在张爱玲的女性写作技巧这个问题上,海外学者的背后是一个大的西方文化研究背景。这一点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最后,海外学者的这种跨越性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是与张爱玲的跨越性创作手法——“参差的对照”相契合的。张爱玲对自己“参差的对照”的写法的解释是:“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张爱玲认为这种手法比较适宜表现她当时的时代,比较适宜写出现代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的特点。也即,张爱玲“参差的对照”的写作技巧正好表达了其作品“参差的对照”的意识内涵,意识与技巧是合而为一的。因而,“参差的对照”之于张爱玲,是一种写作手法,也是一种美学原则。这种写作手法与美学原则,在海外华人批评家的阐释下,则是与完整、宏伟、统一相对的琐碎细节,与正常的连续性时空相对的隔离的美学时空,与战争、革命、力量相对的苍凉,与高调文学立场相对的通俗谐闹喜剧立场及与文字相对的视觉感。总而言之,“此一手法,不正是‘女性视点最特殊的运用吗”。问题最终又回到了女性写作上——归结起来,无论是细节描写还是电影技法,最终都是“参差的对照”的女性写作技巧与美学原则的体现。这样,海外批评家通过对张爱玲女性写作技巧的发掘和研究,高张了张爱玲对中国男性文学传统的破坏和颠覆作用。但是,与其说这是海外华人批评家对张爱玲的创作之于中国男性文学传统的破坏与颠覆作用的肯定,不如说这是其对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的高张——不仅是在意识与技巧的关系问题上注重技巧,坚持意识与技巧合而为一,更重要的是其文化研究的思维和方法论,一种跨越性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海内外学者在张爱玲女性写作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对意识与技巧的关系以及文学观念上的差异,这可以做两个层面的理解:
一是从研究结果来看,女性写作研究不仅仅是作品意识、内容上的性别之争,更是文学传统、文学研究上的性别政治。这可以从台湾学者周芬伶的一句话中得到印证:“女作家的地位纳入正统文学史总有扞格不入的地方,如果纳入女性文学史中,没有名次之争、正统非正统之分,她无疑是现代极重要的女作家。”
二是从研究方法来看,海内外文学观念差异的背后,隐藏着双方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落差,反映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不同进程。大陆学者坚持社会历史批评的路子,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其对文学本体的理解,因而其对“技巧”的忽视与后识也就在所难免;海外学者持西方文化研究方法,从对技巧的重视出发,导向意识和技巧的完美结合。从整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历程来看——文学研究在社会历史批评之后走向新批评,又在文化研究中走向对社会历史的回归——两者的差异正好反映了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不同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外华人批评家的研究方法的确是得风气之先并且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在吸取新批评对文学本体的重视的同时返回社会历史,既贴近文学本体又不乏社会历史的广阔视野——尽管其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大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避免理论先行的嫌疑。因而,可以说,海外“张学”在张爱玲研究中是占据强势地位的,对大陆学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的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14页。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
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第51页。
夏志清:《讲评:张爱玲与鲁迅及其他》,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谭正璧:《论苏青及张爱玲》,陈子善编《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的张爱玲评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第41页。
钱荫愉:《丁玲与张爱玲:一个时代的升腾飞扬与苍凉的坠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于青:《女奴时代的谢幕——张爱玲<传奇>思想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Ⅱ: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
周蕾:《妇女和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笔记》,麦田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272页,第353-359页,第33页。
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83页。
周蕾:《技巧、美学时空、女性作家——从张爱玲的<封锁>谈起》,杨泽编《阅读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107页,第101页。
李欧梵:《不了情——张爱玲和电影》,杨泽编《阅读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8-268页,第261页。
李欧梵:《张爱玲:沦陷都会的传奇》,《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317页。
郑树森:《张爱玲的电影艺术》,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7页。
梅家玲:《烽火佳人的出走与回归——<倾城之恋>中参差对照的苍凉美学》,杨泽编《阅读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