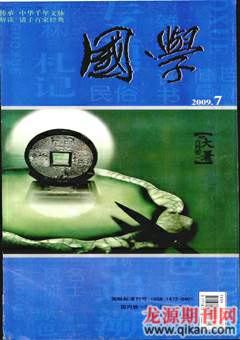迷途的帝国
蜀中狂客
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他们都是大气磅礴的传奇君主,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在17至18世纪中把各自的国家带入鼎盛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然而,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雷池半步,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辉煌,盛极而衰,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在被西方列强鲸吞蚕食的同时,竟还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
远在西方的马克思,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今天,重新翻检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盛衰无常的历史周期律无可逃遁,还是幸运女神偶然间与中国擦肩而过?这是一首悲欣交集的凄凉挽歌,令人回味,发人深省。
壹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驾齐驱。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层层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是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术,谨记祖母当年“得众则得国”的教诲,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他对于老百姓的仁慈宽厚,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
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卧地上。拦挡圣驾非同小可,侍卫正要严加惩处,康熙立马阻拦,令人问明情况,得知他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回家路上因为饥饿晕倒了。康熙说不要惊吓了他,你们马上热粥给他喂了救他。王四海喝了热粥之后苏醒过来了。康熙了解到这个人家里的确很困难,又送他盘缠让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尽,四处传颂当今圣上的爱民功德。这件小事是康熙治国爱民的一个缩影。他常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
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家给人足”作为最高的治国目标。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小农社会里,这不仅仅是家家户户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历代君主的政治理想,构成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康熙竭力维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他清楚地给自己设计了为政的蓝图:“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位六十一年中,康熙废寝忘食,鞠躬尽瘁。有时为追杀敌军,一连三天不下马,其骁勇与顽强绝非常人可比。他对送来的奏折是有奏必签,右手患病拿不住笔,左手也要执笔批签。即使秋季围猎习武,白天纵横奔驰,每晚仍不辞劳苦,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康熙起居注册》真实地记载,他每天早上“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把御案搬到乾清门前去办公,辰时准时上朝,御门听政,巡游在外也要在行宫的大蒙古包里按时办公,无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由于康熙的榜样一直到光绪都坚持下来。
当康熙终于看到天下太平,国势日盛之时,随即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满足于百姓岁足年丰、人民鼓腹讴歌的社会图景,到处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另一条道路上,彼得则用严酷的鞭子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进行急行军。
如果说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质外,还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时刻潜藏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驱使的话,彼得则几乎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价“用铁索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普希金)
他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为了推行他的强国梦想,他不惜一切代价。用普希金的话说,彼得的某些诏令“是用鞭子写成的”。有一次彼得和首都警察局长乘车过河,彼得发现桥梁出了故障,他觉得这是警察局长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所致,不由分说给了这位局长一顿好打,以示警告。彼得说:“这是要你好好记住,一定要让大街和桥梁畅通无阻,以后你自己要多加巡视。”沙皇在给警察局长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课后,又挥挥手说:“上车吧,老弟!”
挥舞着鞭子的彼得并不是一味蛮横,他自己就是尽职尽责、身先士卒的楷模。彼得堡早期每年总要着上几场大火,时任法国驻俄大使儒埃尔写道:“我多次看见他第一个来到失火地点,雪橇里带上他的消防水泵。他参加全部的灭火工作。由于他的思想异常敏捷,他能立即判断出应采取什么灭火措施。他爬上房顶,哪里最危险就到哪里去。”
是的,彼得天生就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接过手来的俄罗斯实在是太蛮荒、落后、野蛮了!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国摆脱孤立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为此,他绝不容许任何俄罗斯人有半点松懈,首先从他自己做起。
他向来一身几任,除沙皇外,他还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等身份“为国服务”,并对各种身份的直接上级保持尊敬。从十九岁开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甚至亲自驾驶小船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在行军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冻受饿,在肮脏的泥泞里摸爬滚打,有一次战斗中还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穿了帽子。因战功晋升将军后,他要求人们不要拿他当皇帝,要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一天,用挣来的八块钱买了一双新鞋子。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整个俄罗斯都在这位威武强悍的命运之王手中颤抖、嬗变。
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他动辄抡起棍棒殴打,强迫大臣执行命令,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应有尽有。他的改革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直到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一次酒宴后,醉酒后的太子终于忍无可忍地公然喊出:“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来到的,我父亲和继母的朋友们将会尝到尖桩刑的滋味……”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彼得借助武力强迫太子回国之后,亲自参与了对太子的刑讯。对这位想走回头路的太子,执意改革的彼得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参与了拷打以及致儿子死亡的整个过程。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所有反对改革的风波中,即便是自己的母亲、叔叔、岳父、儿子,彼得也会断然与之决裂!
谁也想不到的是,历史的悖论竟然出现了。康熙仁政爱民,彼得凶暴治国;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扩张;康熙激于道义,彼得唯利是图……结果却是俄罗斯一飞冲天,中国却走向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
一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总值的23.1%,而俄国仅占3.2%;而俄国1700年—182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远远超过欧洲和世界平均速度,更远远超过中国,大踏步跨入西方列强行列。
很明显,站在道德的立场,康熙似乎是胜者。而站在治国的立场,他被后来居上的彼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盛衰无常,世事难料。两个同样勤政有为,励精图治的帝王,为何治国的效果迥异?难道儒家宣扬的道德理念敌不过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难道千年难遇的贤明圣君敌不过从不体恤百姓的俄国“秦始皇”?是真理战胜不了强权,还是仁政输给了暴政?在令人丧气的事实面前,谁都会憋气纳闷。
其实,中俄两个繁荣强盛的帝国,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
正如俄罗斯人自己所说,彼得“出于高贵心灵的奇特本能,他一眼洞穿了祖国的所有疾病,给了俄罗斯可怕而有益的一击”。
彼得是一位天才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的领域。他一生主持颁布了三千多条法令,改革行政机关、军队,建立军事工业,引进千余名各类专家,建立众多实利主义性质的学校和科学院,并派出一批批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俄罗斯在狂飙突进的改革风暴之下,理性冲破禁锢,科学压倒愚昧,重商主义盛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俄国终于紧跟世界先进潮流的步伐迎头赶上,正如彼得骄傲地说:“我不能亲手建成和看到一个强大的俄国,但我的继承者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直到目标的实现。”
康熙继承的是儒家文化“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老真理,完全回归到传统的轨道,把儒家设计的政治道德蓝图当做完美的理想去追求。他虽然呕心沥血地试图开辟一条富国之路,但他只是在中国重建了小农经济,却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半步。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然世外桃源一般宽松安闲,实力却弱小得多。“康乾盛世”只能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夕阳,从当时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已远远落后于时代。而对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康熙茫然无知,毫无准备,反对变革,满足现状。他对内强化封建专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官场贪腐横行,百禁不绝。他重农轻商,致使明末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对外则闭关自守,使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他在竭力开创盛世局面的时候,其实已经走上了与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
大凡治国不进则退,欲单纯以保守为目的,其势必然难以长久。这,就是一个迷途的帝国留下的最大教训。
贰
人类进入18世纪后,中、俄两国渐行渐远,走向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俄罗斯在彼得开创的工业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而中国则在康熙营造的小农经济形态下盛极而衰。
正当康熙和他的子孙雍乾二帝,把一代盛世推向繁花似锦、高潮迭起之时,大清国这架承重已达极限的大车,早已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没有人知道,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几乎完全耗尽,国家发展潜力即将陷入油尽灯枯之境。社会动荡加剧、行政体制僵化、内部调控失灵,中国社会长夜无歌,如一潭死水。小农经济萎缩破败,手工业生产也陷于停滞。传统政治捉襟见肘,已无力消弭各种社会矛盾,诸如“地少人多”、“通货膨胀”,孤陋寡闻的统治者一筹莫展,无力应变。
相反,在俄国,朝气蓬勃的崭新帝国飞速崛起。彼得树立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启动了社会内部存在的潜能。他结束了草原化和东方化的俄国历史,开创了海洋化、西方化的俄罗斯新时代,把一个黑暗愚昧的俄国引向了一条全新的光明之路。
康熙和彼得正是这样两个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影响了中、俄两国命运走向的巨人。彼得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抗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清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俄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康熙尽管也是一代雄主,他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甚至远在彼得之上,但在超越阶级、环境的局限,引进新技术和学习、了解外国新事物的远见卓识上,却明显逊色于彼得大帝,始终没能为中国指出一条通往近代化之路。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康熙与彼得治理国家的最终宿命。看似个人选择的背后,其实是两种文明的撞击。
古老而持久的中华文明,具有非同一般的坚韧性和超乎寻常的消融性,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封建大国,中国长期处于孤立封闭状态。中华文明几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独立发展、内部协调的道路。千百年来,试看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无论是纷扰如斯的五胡乱华,还是铁骑横渡的蒙元入侵,都不过是一段段小小的插曲,中华文明从未出现过彻底推翻和重新建立的局面。
岁月长河静谧而缓慢地流淌,难以激起惊天的狂澜。康熙王朝只是一朵绚丽的浪花,缺少左冲右突的磅礴之势,只能沿着原来的河道奔流到海不复回。他不是圣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在理学唯尊、儒学治国的环境下,英明的康熙内心深处,是否也有无尽的苦衷?他把自己关在深宫中研习西学时,也许最能体会这种滋味。身为一国之君,他连看一本书也要偷偷摸摸。当他的教师法国人巴多明要将人体解剖学绘图准备出版时,他深知解剖人体是与儒家观念直接冲突的。他小心翼翼再三告诫说,这在中国可是“特异之书”,你们可千万不要让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同时要求传教士们翻译西洋书籍时只能严格按规矩在衙门里工作,禁止带回家去。
而彼得给俄罗斯带来的是一场全面的真正的蜕变。他手操一把剪刀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彻底的革命。三百多年前,长胡子是俄国人最自豪的标志,东正教甚至把胡子看做是“上帝赐予的饰物”,身体的灵魂全部凝聚在胡须之上,把刮胡子视为异端。而在彼得看来,这却是俄罗斯落后的象征。1698年,当俄国的贵族们举行一场宴会,欢迎彼得顺利从欧洲返回时,穿着西式服装的彼得却二话不说,掏出剪刀就动手剪他们的胡子。第一个牺牲品竟是俄国元帅、对他忠心耿耿的谢英。贵族们大惊失色,号啕大哭,不明白他们的沙皇为什么这样做。剪胡子遇到上上下下的顽强抵制。彼得完全不管这些,他宣布:剪胡子是全体居民的义务,要想保留胡子就得交重税。官吏和贵族每年要缴六十卢布,平民三十卢布。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税种了。他要剪掉俄罗斯上千年的积弊和不文明,打破闭塞守旧的价值观念,重新为俄罗斯注入全新的活力。正如列宁所说:“彼得为加快野蛮的俄国学习欧洲文化,不惜采取野蛮的方法和野蛮做斗争。”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大清国初创之始,同样喊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口号。中国人的辫子,俄国人的胡子,似乎遭遇到同样的厄运,都维系着一国之前途。但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剃发是满族人家天下的标志,剪胡子则是一场新革命的开始。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改革的艰难,甚至于远远胜过流血的革命。
剃刀与剪刀背后,是两个民族命运的挣扎。强盛的汉、唐王朝当年就想跨越荒凉的西域大漠,寻求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然而巍峨的青藏高原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阻挡了中国人的视线,也阻碍了欧洲人的东来。长此以往,沉醉在唯我独尊的“天朝”迷梦里,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小小的化外蛮邦,何曾入我大清国的法眼?殊不知此西洋非彼西洋。社会经济的发展唤醒了思想的觉醒,欧洲一改从前停滞不前的状况,加速向前发展。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此其时也,彼得生正逢时,天时地利,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引领俄国人民,一路高歌猛进。而同一时期,如台湾的柏杨先生所说,中国起自14世纪的凶潮毒雾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新生的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的雾潮又将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反扑而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被酱死在即将迈步前行的刹那。
叁
历史是十分复杂的,“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与彼得性格粗犷,甚至凶残无情相比,康熙的性格却是刚柔相济、经书礼仪,雍容大方。他全面实施儒家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真正实现了儒家的“大一统”理念,使中国不再有内外之分、华夷之别。尤其是与彼得不同的是,他牢固树立“民为邦本”的信念,与民休养,改善民生,有清一代,豁免钱粮之巨,百姓普沾实惠,为历代所仅见。可惜到康熙晚年,尤其是最后十五年,由于精力不济,失之于“宽”,导致政务荒弛,吏治腐败,风气日衰,许多地方开始民不聊生,国库亏空极巨,连黄河决口也无钱拨治。连带纵容自己的儿子,最终发展到九龙夺嫡悲剧。他提出“持盈保泰”的思想,想防止盛极而衰,满而不溢,原来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作为指导国家的政治方针并不错误,而发展到后来却陷入保守落后,不思进取的误区,无法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当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把皇位禅让给嘉庆时,白莲教起义爆发,敲响了盛世的丧钟,这正是儒家保守理念下治国的悲惨结果。
纵观历史,将国家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明君”身上,而不是形成制度保障,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君主意志,一旦君昏臣庸,或“明君”出现重大失误,国家命运就将出现危机。
欧风美雨,东西角逐;盛衰无常,胜败有凭。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环境的时代,重新审视康熙和彼得两个人物曾为国家发展制定的方向,会更清楚我们将要走一条怎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