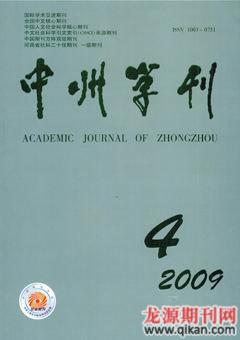论张洁创作中理想爱情的四大关键词
郭怀玉
摘 要:张洁创作了短、中、长几十篇爱情小说,但几乎所有爱情故事的过程或结局都很不理想。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张洁在创作中对理想爱情的追求都绕不过崇拜、尊重、可靠和呼应这四个关键词。在张洁的文本中,这四个关键词的基本阐释和基本关系是这样的:女性对男性的崇拜是前提;男性对女性的尊重和男性在女性面前必须可靠则是基础;而男女双方的相互应答是理想爱情的最后保证。
关键词:张洁;理想爱情;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4—0214—03
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爱情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至今,张洁作为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整整30个年头了。在这期间,张洁创作了短、中、长几十篇爱情小说,但几乎所有爱情故事的过程或结局都很不理想。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张洁在创作中对理想爱情的追求都绕不过崇拜、尊重、可靠和呼应这四个关键词。在张洁的文本中,这四个关键词的基本阐释和基本关系是这样的:女性对男性的崇拜是前提;男性对女性的尊重和男性在女性面前必须可靠则是基础;而男女双方的相互应答是理想爱情的最后保证。
笔者认为,张洁并不是一个女性意识很强烈的作家,相反,她在绝大多数文本中却表现为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因为她“看女人常常是以一种男人的眼光或中性人的眼光”①,但这也并不是说她就像1995年首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中人们私下议论的那样:张洁是一个既不适合结婚也不适合做老婆的恶女形象②。其实,在潜意识之中,张洁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女人,她也会十分虔诚地崇拜男人,甚至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张洁首次提到了“崇拜”,她以叙述者的姿态判断女主人公钟雨对“老干部”的崇拜:“对了,她准是崇拜他。她说过,她要不崇拜那个人,那爱情连一天也维持不了。”③小说中的那个“老干部”确实是值得许多人崇拜的,他既有高雅的气度,又有丰富的革命经历,还有艺术才能,等等,可以说除了年龄大,没有任何缺陷,甚至于年龄大在女主人公钟雨眼里也成了一个优点。所以,钟雨才会“至死都感到幸福:她真正地爱过,她没有半点遗憾”④。看来,在钟雨爱情的幸福感觉里面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崇拜。无独有偶,在1981年张洁创作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中,一个22岁的实习医生郁丽文嫁给了一个37岁的汽车制造厂厂长陈咏明,他们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但这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因为在郁丽文的少女梦幻里经常出现的就是像陈咏明这样的“让她崇拜渴慕的理想丈夫”,“征服困难的、强大的男人”⑤。这正是张洁女性爱情观念中的崇拜情结不断显现的结果。1994年,张洁在散文《最后一个音符》中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一语道出她本人对爱情的真实感受:“我对先生不仅深爱,更还有热烈的崇拜。”⑥直到20世纪末,张洁在她最长的小说《无字》中还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但这时她在作品中对男人就有所调侃和不恭了,因为这个时候她发现,与她一度崇拜的男人真正地生活在一起时却没有她原来想象的那么好,甚至还很失望。《无字》中的白帆对胡秉宸也是“无条件的崇拜”⑦,吴为也是非常过分地崇拜胡秉宸,结果是什么呢?正如张洁在小说中写道:“只有女人才会崇拜一个男人,而男人只能把玩女人,却不会崇拜一个女人。”⑧白帆崇拜胡秉宸的结果就是婚后扇他的耳光,“吴为把胡秉宸视为神明的崇拜又持续了多久”⑨?这可能也是张洁创作中的无奈,既爱又恨,爱恨交织,此消彼长。
由此观之,在张洁创作的理想爱情观中,女性对男性的崇拜是经常有的,但是,只有女性对男性的崇拜还是不能得到爱情正果的,在此前提下,男性对女性的尊重与男性的稳定可靠两个条件就浮出了水面。
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⑩女性地位的低下、女性意识的减弱是世界性的问题,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更是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不是女权运动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产物。所以,张洁发现,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意识“仍然存在着对妇女能力的怀疑和某种程度上对妇女的不尊重”(11)。在小说《有一个青年》中,张洁以一个男性的叙述者出现,写“我”“真不爱和那些漂亮的小妞们扯淡”,只有在“我”遇到一个长相和打扮都很平常的、有知识的女孩徐薇时才对对方产生了敬佩之情、爱慕之情,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赢得了对方的爱情,所以,“我不由地想起有人说过的一些蠢话:爱情是从漂亮的脸蛋开始的!不!真正的爱情应该是从尊敬开始的”(12)。妇女研究专家李小江说得好:“人自身的尊严感和对他人是否尊重,都会在性关系中充分体现出来——性,其实是人格的一面镜子。”(13)试想,得不到异性尊重的女性,那还谈什么爱情呢?《方舟》中的曹荆华、柳泉和梁倩都是在得不到异性的尊敬的情况下才“先先后后地离了婚”,组成了所谓的“寡妇俱乐部”。柳泉的丈夫“明明没有把柳泉当做自己的妻子,而仅仅当做‘性的化身”(14),以致柳泉害怕“黄昏来临”,因为“每个夜晚,对柳泉都是一个可怕的、无法摆脱的灾难”(15)。梁倩的爱人白复山“尊重”的是他老岳父的身份和地位。曹荆华的爱人更是把她当做了一个生孩子的“性机器”。《无字》中的胡秉宸婚后对吴为很不尊敬,他居然在床第上说出让吴为大为不解的话:“想不到你身上的肌肤,已经松弛下垂得这样厉害。”(16)吴为感到这句话“简直可以和一九四五年美国人扔在广岛上的那颗著名的炸弹相提并论”。评论家王蒙曾说胡秉宸这个“男人的说法对于一个敏感的女人太不礼貌了”(17)。比胡秉宸年轻20多岁的吴为没有去直面评价胡秉宸那已不像男体却很似女体的衰老皮囊,而胡秉宸却说出这种话,分明是对女性的不尊重。正如女性主义批评者所言:女性总是处在被审视之中。女性的这种尴尬处境势必造成男人对女人的不尊不敬。
埃•弗洛姆说过,尊重和有责任感是爱的两个重要因素(18)。仅仅有男性对女性的尊敬是不够的,男性对女性还得有可靠感或者说责任感。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女性由于生理的原因已经越来越不适合承受力量型的重活,与此同时,她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在不断地式微,所以波伏娃就说:“女人在被决定扮演他者角色的同时,也被判决仅仅拥有靠不住的力量。”(19)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女人更需要保护,需要男人可靠的支撑。《波西米亚花瓶》中女主人公梧桐对老干部简一往情深,“在没有他以前,她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任八方的风撕扯着她,在没抓没挠的空间里沉浮。那是一种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的,没着没落的失重感。”(20)而只有在有了他之后,她才感觉到“她懒了,眼睛睁不开了,睡着了。梦里,她分不清她是枕在他的胸膛上,还是枕在海的胸膛上”(21)。这种女人对男人的依靠并不是偶然的,在张洁的很多作品中,女性需要的都是男人坚实的肩膀。《方舟》中的柳泉多么希望有一个为她“遮风挡雨”的丈夫啊!这样,在她受了委屈之后,就“可以躲進丈夫的怀抱,把眼泪流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但是柳泉的丈夫虽然有“一个宽阔的胸脯”,但并不能让她有可靠感。在《沉重的翅膀》中经常把头靠在陈咏明宽阔的肩上的郁丽文;《七巧板》中只想靠在袁家骝的臂弯里的尹眉;《知在》中的金文萱有了一个即使天塌下来也不会让她受一点苦的可靠的约瑟夫,就不再需要思考爱情了。从远古时代至今,男女两性的生理结构特点并无多大变化,男人作为力量的象征由来已久,作为心理上的依靠当然更好,兼而有之当属少数,但是张洁在创作中总是对此充满了希冀:“‘高大好像是中国女人的死结,只要男人高大,人格似乎也跟着高大起来,不论是天下的责任还是对女人的责任,都会一律毫不含糊地承担起来。”(22)
在张洁看来,有了女人对男人的崇拜、男人对女人的尊敬和男人对女人的可靠,这些还构不成理想爱情的全部,只有在此基础上相爱的两个人能相互呼应,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爱情。只有男性主动呼唤女性而对方却没有应答的,那是一厢情愿;只有女性深情呼唤而男性没有回应的,也不是知音。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张洁运用“呼应”和“呼唤”频率最高的一篇小说,它企图彰显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心灵感应和心理默契,尤其突出的是女主人公钟雨在她的有生之年那种强烈而迫切地寻找另一半来呼应的主观意愿,以至于女儿珊珊都能感觉到在“老干部”去世以后她的母亲钟雨似乎有一半也随着什么离去,也发现她经常去那条柏油小路上去和“老干部”的灵魂相会,死后还要去天国相会。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情是一种永不分离而且还能互相呼应的人间至纯至真至诚至尊至高无上的爱情神话故事。这是一种永恒的爱,一种完全重合的精神之爱。张洁是爱情上的理想主义者,她所描绘的理想爱情是要求对方必须有呼应,以此达到两性和谐与统一的爱的最高境界。在《方舟》中,曹荆华、柳泉和梁倩三个女人都从当时无忧无虑的女学生陆续结了婚,但她们的婚姻实际上都不是互相爱慕的结晶:曹荆华并不爱那个森林工人,她只是为了养活父亲和妹妹才嫁给他的,而那个人也只是把她当做一个生孩子的“性机器”;电影学院毕业的梁倩倒是曾经爱过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的白复山,但白复山“爱”的却是老岳父的身份和地位;外语系毕业的高材生柳泉的爱人是一个什么派别的小头目,他性欲旺盛,每天夜里都要与柳泉做爱,否则的话,他就觉得蚀了本;而对柳泉来说,却恨不得抱住太阳,不让它下沉。张洁在文本中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议论:“爱情这东西既不像冬瓜,也不像茄子。有一半烂了,把那烂了的一半切掉,另外一半还可以吃。爱情是一种对应,只要一方失去了情感,爱情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23)《祖母绿》中的曾令儿和左葳之间其实原本没有什么爱情可言,如果非说有的话,那也是一种错位的爱情。曾令儿当时从大海的漩涡中救出左葳,并不是因为爱他,实际上,当时只要是有人落水,她都会救的,因为她是渔家的女儿,救人是她们的基本义务。但左葳却认为:“曾令儿是他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他要报她的恩。”而曾令儿“她实实在在地希望听到的是爱的回声,而不是一种交换。她也错了,把那交换,当做了回应”(24)。所以,左葳和曾令儿之间的故事纯粹是一场误会。因此,当他们度过那一夜后,曾令儿如释重负地对左葳说:“我们已经结过婚了,你已经还尽了我的债,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分手了。”(25)曾令儿还告诉左葳说:“婚姻并不等于爱情。”最后与左葳结婚的卢北河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生活全部是在演戏:“左葳总装出一副如痴如狂的钟情样子,她姑且装出一副为他的情爱所动的样子。就这样,他们演了几十年的戏。演到现在,连他们自己也相信了,或是习惯了:这大概就是真的。”(26)这也就是说,左葳“最后和卢北河结婚,从实质上来说,和从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女人结婚,没有什么两样”(27)。但卢北河“她不后悔,因为她爱左葳”(28)。“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左葳到现在也不完全知道卢北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对她的话应言听计从。”(29)因此卢北河感到很“幸福”,她说他俩“幸福得如同一个随心所欲的主人,和一个惟命是从的奴隶”(30)。不过,最后卢北河还是非常真诚地告诉了曾令儿她俩与左葳之间的本质关系:“其实过去你在和他的关系里,扮演的也是和我同样的角色。”(31)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曾令儿还是卢北河,她们都不是左葳的另一半,却只能充当一个奴隶主的角色。对于这些,左葳始终都是一个可怜的局外人。爱是平等的交流,心灵的对话,而绝对不是一种交换,任何一方缺少爱的资质和爱的灵感,爱就是不完美的。
从文本叙述来讲,《无字》和《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互不相干的两个故事,但是从这两个故事创作的原型来看,这两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真实事情的两个阶段。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作者苦苦追求和呼唤的理想在《无字》中变成了现实,然而这个现实却很不理想,爱情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龃龉。因此,笔者以为,《无字》实际上是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理想爱情的全盘否定。也许张洁也感到了困惑:人世间到底有无真正呼应的爱情?到了《知在》中,张洁所写的所谓相互呼应的两对爱情男女都是一个短暂的呼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作者对爱情呼应模式的一种悲观消极情绪。三格格金文萱流落异国他乡,碰到了好心的约瑟夫收留并救助了她,但他绝无趁火打劫之嫌,他并不爱金文萱;而对“爱情的萌生、感觉、呼应并不陌生”(32)的金文萱也不爱他,但经过一番磨砺之后,最后他俩终于呼应了,生下了安吉拉,然后他俩就在一起意外而不能逃离的火灾中相拥去世了。
人类发展的历史虽然已经到了21世纪,但是人们对于两性爱情上的“回声”和“呼应”的捕捉和把握还处在十分幼稚的阶段。虽然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悲壮举动,有电影《知音》中小凤仙发出的“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己最难觅”的凄美呼唤,但是,这些充其量不过都是做了“牺牲品”。所以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末尾才发出了中肯的劝言:“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33)
从写《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到现在,张洁在创作中对理想爱情的探求一直没有停止过。她说:“创作是追求,不仅是事业上的追求,而且是作家在生活中追求的继续。在生活中尚未得到实现的理想,往往在作品中得到实现。”(34)不过,以“崇拜、尊重、可靠和呼应”为关键词构建的理想爱情可能是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乌托邦,那么,张洁可能就永远是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注释
①刘慧英:《女人,并非特殊——张洁访问记》,香港《文汇报》1989年6月25日。
②荒林、张洁:《存在与性别,写作与超越——张洁访谈录》,《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③④(33)张洁:《中国国外获奖作家作品集:张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109、111页。
⑤张洁:《沉重的翅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5页。
⑥张洁:《张洁文集》(二),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542页。
⑦⑧⑨(16)张洁:《无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95、302、171、22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11)张洁:《一个中国作家的艺术——纽约访张洁》,《文学报》1986年10月16日。
(12)张洁:《张洁小说剧本选》,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13)李小江:《解读女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14)(15)(23)(24)(25)(26)(27)(28)(29)(30)(31)张洁:《张洁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0、70、10、229、211、198、194、199、212、249—250、250页。
(17)王蒙:《極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读书》2006年第6期。
(18)埃•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
(19)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Ⅰ),陶铁柱译,中国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20)(21)张洁:《波西米亚花瓶》,《花城》1981年第4期。
(22)(32)张洁:《知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8、75页。
(34)转引自许文郁《张洁的小说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
责任编辑:一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