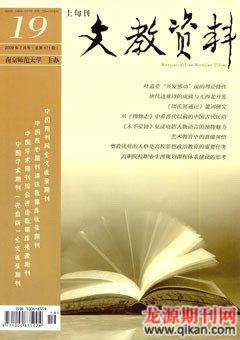女人,替罪的羔羊
乐丽萍
摘要:对于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女性主义批评家争议不断。本文作者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运用主题分析的办法。探索了康拉德对于小说的女性角色及其小说的黑暗主题的阐释:女人正是导致男人沉沦的阴暗源头。在《黑暗的心》中,女人成了替罪的羔羊,而《黑暗的心》也因此成为了康拉德的厌女症的佐证。
关键词:康拉德 《黑暗的心》 女性角色 女性观厌女症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因其前瞻性曾备受批评家的褒奖,但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主义批评者开始对该作品褒贬不一。Elaine ahowalte逭称《黑暗的心》不仅是一个赞扬殖民主义的文本,更是一个推崇男性至上主义的文本:施特劳斯认为康拉德“展示给男性的是事情的本来面目,留给女性的都是谎言”。但也有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为康拉德辩护,认为其在该文本中反映了当时男性中极为普遍的将女性他者化的观点,体现了康拉德对于女性生存状况的深刻忧虑。随着《黑暗的心》中文译本的出现。大陆学者如李宏、高灵英也对康拉德塑造的女性形象及其传达的女性观进行了分析。但迄今为此,尚未有文论探讨《黑暗的心》的黑暗主题与其女性角色的关联。在此,笔者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运用主题分析的办法,探索康拉德对于《黑暗的心》的女性角色及其黑暗主题的阐释。
从康拉德在《黑暗的心》对于文中女性角色的描绘篇幅来看,三位女性:马洛的姑妈,库兹的未婚妻,库兹的土著情人都貌似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正是通过这些有限的笔墨,康拉德借助马洛的声音,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将女人视为黑暗的源头的女性观,为女权主义者对其厌女症的批判提供了佐证。
文中马洛首先提及的是他的姑妈,受马洛之托,姑妈想方设法为马洛争取到了一个船长的职位,对此马洛原该感恩,但马洛却是另一番心情。在19世纪末的英国,男性将自己视为女人的救世主的大男子主义极为普遍。马洛深受这种观点影响,对于自己没落得竟要靠女人来谋得一官半职深感羞愧,他甚至公开地告诉别人自己是通过女人才谋来这个职位,以自嘲的方式来排遣心中的羞愧。当他听到姑妈把殖民者的行动评价为开化野蛮人之旅时,更蔑视地评论说生活在小世界的女人们都极度无知。19世纪末的英国女人的世界确实很小,她们受的教育止于文法;没有男士的陪同她们不得进入图书馆和教堂等公共场合;她们更享受不到工作的乐趣,仅限于从事一些低廉的工种;当时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很多适婚女性找不到配偶,只好沦为已婚男人的情妇。所以,对19世纪末的英国女性而言,最好的出路就是嫁个有头有脸的男人,然后守住他。所以她们的世界里几乎容不下公共事务,充斥的是只是私人家务。在这样的世界里,她们是没有途径去通晓世事的。马洛对此却视若无睹,他尖酸地嘲笑着姑妈,试图以鄙视的态度来淡化她对自己的恩情,以及排遣自己蒙恩于女人的羞愧。而更为荒唐的是,当库兹发表和马洛姑妈类似的言论时,马洛的反应却是极尽赞誉之词,大加褒扬。马洛对于姑妈不仅没有感恩之情。反而在不停地怪罪着她。马洛在出发前有人告诉他要去的那个殖民地尚未有人返回英国,因此必是不祥之地,当时他就对姑妈的“无能的举荐”很是恼火。虽然最后他仍然决定冒险前行,但在旅途结束之后,他却没有去拜访和面谢他的姑妈,因为在他看来,姑妈的推荐带给他的并不是光明的前程,而是让他前方的路更加艰难、黑暗。他对他的同事抱怨道:“大家应该合力把女人关在她们自己的世界,否则她们必要搞破坏,添乱!”马洛还说库兹和他的命运一样。也是受一位太太的举荐才开始了他的殖民之旅。通过这番话,马洛不但怪罪着自己的姑妈,更将库兹的黑暗之旅归罪于女人的愚昧而错误的指引。
相对马洛的姑妈而言,马洛对于另一位女性——库兹的未婚妻似乎要仁慈一些,对其的叙述不乏溢美之词。首先他提到了她在肖像中的神态:“她看起来没有一点私心,一副随时准备洗耳恭听,无所保留的姿态。”在与她见面时,马洛在她看似安静的表情里发现了对她库兹的近乎疯狂的膜拜。在马洛看来,她毫不怀疑甚至已经完全内化了男权社会的基本信条,自愿接受了其低男人一等的命运,也心甘情愿地对他们唯命是从。马洛还详细描述了库兹的未婚妻的行为:库兹远在殖民地的时,她精心照顾库兹的老母亲直至其去世;在库兹去世后,她把马洛的谎言——库兹的遗言是她的名字一当成了精神食粮,每日穿着丧衣悼念库兹,丝毫没有改嫁的打算。库兹的未婚妻的言行举止迎合了马洛男性至上的大男子主义,他称赞了她,将她描绘成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天使:“她接受自己的他者地位,愿意依靠男人,全身心地服侍男人,从一而终!”但马洛却在赞扬库兹的未婚妻的端庄的举止的同时,还用了另外一个词:“不祥的影响!”不祥在何处?马洛给出的答案是迂回的。他数次提到了库兹的话:“我的未婚妻”“我的象牙”“我的河流”等来强调库兹的贪念,然后马洛还讲述了一件事情:库兹并不富裕,对此库兹的岳父母很不满意。在19世纪末的英国,虽然妇女已经取得了财产权,但妇女却仍然被视为男人的财产,并成为男人们彰显其魄力的重要指标。因此通过对库兹这番话语的一再复述,马洛暗示库兹正是为了将未婚妻娶进家门而去殖民地敛财,为了敛财而狂暴地收集象牙,而收集象牙的野蛮行为又给库兹带来了灭顶之灾。一言以蔽之。对未婚妻的贪念是库兹前往殖民地的动力,也是其悲惨结局的原因。所以当库兹的未婚妻问他库兹的遗言是什么时,马洛告诉她是她的名字,而实际上库兹说的是:恐怖。借用这个谎言,马洛迂回地说出了他对于库兹的未婚妻的真实观点:让人恐惧的正是不祥的她,正是她对于库兹的阴暗的摧毁性的影响。
文中另外一位重要的女性是库兹的土著情人。虽然马洛对她的叙述不多,但却将她刻画得与前面两位女性迥然相异。首先她的外表不是压抑的,而是华丽的、炫耀的:她的装饰品闪闪发光,价值不亚于几副象牙:她的举止不是柔顺的,而是大胆而狂野的:她对库兹没有低眉顺眼,而是敢于大声和他争辩;她在当地的男性中也很有影响,当马洛将库兹带走时,她竟然率领一群男人拦截。库兹的这位土著情人的标新立异之处其实正是当时土著女性生活现状的真实反映。在被殖民前,很多土著妇女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拥有自己的财产,经济上的独立让她们享有更多的精神自治。而英国妇女直到1870年才开始拥有财产权,且男女的两元论——女人如野蛮的自然,需要男人用开化的文明来驾驭等观点早已深入人心。在英国男人看来,好女人应该是温顺的、被动的、自我否认的、等待男人征服的。所以当英国的殖民者在殖民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同时,独立而野蛮的土著妇女也成了他们的征服目标。但库兹并没能征服他的土著情人,她仍然敢和他吵闹;非但未能降伏她,库兹还身陷于她狂野的同化中无法自拔。马洛发现这种可怕的同化已经侵蚀进库兹的大脑、肌肤,深嵌进库兹的血管和灵魂,让库兹逐步萎缩,无力逃脱。作为殖民者,马洛对于库兹的失败很是愤怒,他将库兹的败坏嫁祸于他的土著情人。马洛不但对她在帮助库兹了解殖民地,充当与当地居民沟通的桥梁,以及排遣库兹在异乡的寂寞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视而不见,反而将她视为邪恶的夏娃:违反上帝的指令,用野性做诱饵,将库兹一步步引向黑暗的深渊。所以马洛要奋力带库兹远离其危险的土著情人,但库兹却已经对她的野性中了毒、上了瘾,拒绝离开,这就加深了马洛对于库兹的土著情人的憎恨,他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在叙述时没有让库兹的土著情人发出只言片语。
在《黑暗的心》中,康拉德借用马洛的叙述,表达了他的女性观:表面看来,男人们利用了女人,受益于女人,但实际上女人的作用远非如此。马洛的姑妈虽然推荐了马洛,但其无能的举荐带给马洛的却是黑暗而凶险的旅程:库兹的未婚妻虽然为库兹默默付出,不求回报,但她却是库兹种种贪念的根源,而库兹正是被这些贪念牵引着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库兹的土著情人,虽然作为库兹在殖民地的活字典,为库兹的殖民进程排除了很多障碍,但却成了引诱库兹远离文明、靠近野性的致命诱因,导致库兹踏上了不归路。在康拉德看来,正是因为女人们无知的牵引,阴险的蛊惑,男人们才会身陷黑暗的深渊,在贪婪的掠夺、野蛮的杀戮中沉沦。在康拉德笔下,女人就是黑暗的代名词,她们的领域就是危险地带,男人们要涉足须谨慎,否则他们难逃恐怖力量的同化,难逃厄运的侵袭。在《黑暗的心》中,女人成了替罪的羔羊,而《黑暗的心》也成了康拉德的厌女症的有力佐证。
参考文献:
[1]Nina P.Straus:The Exclusion of the Intended from Secret Sharing [A].In Elaine Jordan Ed., Contemporary Crit-ical Essays:Joseph Conrad [C].Basingstoke:Macmillan,1996.
[2]约瑟夫·康拉德著.黄雨石译.黑暗的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海伦·费希尔著.王家湘译.第一性.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4]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