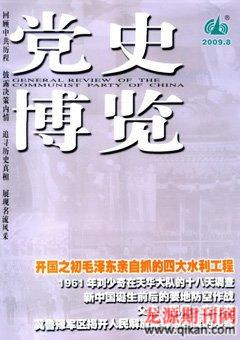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钱 江
一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登上人生的顶峰,被列为中国“第四号人物”。此后,他和江青的冲突也日渐激化。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的1966年5月31日晚间,陈伯达带领“文革”中第一个中央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在6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由他定题并修改、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拉开了在全国各领域进行“文革”的大幕。当此之时,陈伯达俨然是《人民日报》的太上皇,发号施令,好生了得。
然而好景不长,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代组长后,陈伯达的权威明显受到制约。他本人的情绪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狂躁,不可一世;有时低落,闭门窥测方向。他对《人民日报》的控制也有变化:有时亲自前来坐镇频率较高,有时又降低了频率似乎懒得过问。更值得寻味的是陈伯达的做派和言语,有时字斟句酌,反复琢磨;有时出言荒唐,形同儿戏。1968年2月7日,他和姚文元夜访人民日报社就演了这样一出滑稽戏,倏忽而来,大放厥词,然后扬长而去,留下了极为恶劣的记录。笔者向一些当事人调查了在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
二
1968年2月7日,北京天气寒冷,《人民日报》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这天深夜,陈伯达和姚文元突然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视察。
陈伯达和姚文元算是轻车简从,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后直奔三楼的大办公室坐下,要求召集“文革报道部”全体编辑、记者到场。马上有人到宿舍区通知,“文革报道部”的成员全部被召集来了。
陈伯达、姚文元落座之后,报社方面向他们提供了“文革报道部”的花名册,陈、姚二人看了一遍。
看到大会议桌边差不多坐满,陈伯达开始了讲话。他说,今天和姚文元前来,要对每个人进行一番了解,弄清楚你们的社会关系。接下来,他吩咐给每人发一张纸,当场写下自己的出生年月、籍贯、学历、政治面貌等基本情况。
这些纸张很快收了上来,送到陈伯达面前。陈伯达一张一张地翻阅,姚文元在他身边手拿花名册对照。
陈伯达开始询问每一个人的情况。他询问的方式仿佛开玩笑一样,在两个多小时的询问中把在场的人都弄得摸不着头脑,紧张万分。
陈伯达首先问跟前的老编辑白夜:“你为什么要叫‘白夜这个名字?是不是看俄国小说受了影响?”此话倒是显示出陈伯达读书范围的宽广,《白夜》是19世纪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小说。
白夜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回答说:“我没有读过这篇俄国小说。我原来姓费,白夜这个名字是后来参加革命时改的。”
没容得白夜再说什么,陈伯达已经自作解答说:“你是地主家庭出身,是有意要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剥削贫雇农啊!”
一句话引得在场的人都笑出声来。
陈伯达问在场的中年编辑崔筱桐:你是什么出身?
崔筱桐回答:中农。
没有想到陈伯达马上说:“不对,你明明是富农出身,怎么说是中农了?”
一句话说得崔筱桐愣了一下,他知道这可是重大问题,马上解释说,土改开始的时候,当地将父亲的成分错划为富农。后来进行了纠偏,将他家划定为中农。
崔筱桐是老革命,山东宁阳人,1940年还不满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入伍的时候,他告诉部队领导,他家有一个雇工。指导员对他说,那你就把家庭成分填为富农吧。崔筱桐依此办理。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已经划定为中农。
这个情况显然在档案中有清楚的记载,姚文元看了出来,用胳膊肘儿捅了捅陈伯达。陈伯达会意,不再说下去,但还是对崔筱桐说了一句:“你改出身是不是为了好混?”
崔筱桐没有回答,心里被陈伯达的询问弄得老大不痛快。
接下来,陈伯达问中年编辑赵近宇:“你解放以前是干什么的?”
赵近宇1918年3月出生于安徽亳县,1937年参加革命。他的经历要曲折一些。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后到抗大学习,随后到八路军冀南军区五分区司令部工作。这期间他遭受过挫折,但献身革命的决心从未动摇。在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主动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参加晋察冀边区的情报系统,编入北平地下工作组。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调入新华通讯社北平分社当记者,同年调入人民日报社。
面对陈伯达的询问,赵近宇回答,以前当过记者,解放前曾在北平《益世报》工作。
陈伯达马上说:“这个报纸很坏,很坏,是个特务报纸。你有电台没有?”
这句话问得出乎意料,赵近宇一时语塞。
座中的年轻编辑李成华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的。陈伯达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
李成华回答说:是旅大市人。
看来陈伯达熟悉这个地方,他说:“旅大嘛,日本人在那里统治了40年,后来‘苏修又来统治了10年。”
显然,以李成华的年龄够不上“日本特务”,陈伯达问李成华:“你是不是‘苏修特务?”
这还了得,李成华清清楚楚地说:“我不是‘苏修特务。”
陈伯达又问了一遍,李成华也重复了一遍。
这时候,倒是姚文元为李成华解了围,他对李成华说:“这是和你开玩笑。”
陈伯达只管问下去。座中有一位女编辑名叫郝洁,这年39岁。陈伯达问她:“你是什么地方人?”
郝洁回答:东北人。
陈伯达说:“那你就是溥仪的臣民了?”
郝洁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陈伯达问:“你父亲在哪里工作过?”
很糟糕,郝洁的家庭出身不好,她坦率地说,我小的时候,父亲曾经在北平卫戍司令部当过司令。
陈伯达说:“他都干过些什么?”
郝洁说:“我那时太小,不知道。”后来,郝洁和母亲一起生活,早已离开了父亲。母亲没有文化,并不知道究竟。
陈伯达勃然大怒,厉声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郝洁说得很坦然:“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这时,陈伯达奇怪地说:“卫戍司令的小姐不要搞我的情报。”
陈伯达掉头询问林晰——1946年参加革命,1949年底进入《人民日报》工作的编辑,问他是什么家庭出身。
林晰回答:我出身高级职员,父亲是留学德国的航空工程师。
林晰的父亲是一位老知识分子,不幸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后来自杀了。此时,他的老父亲还在备受折磨的困窘之中。
陈伯达一听,像条件反射一样马上说:“你的家庭出身有问题。”
陈伯达说“有问题”,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弄不好会带来杀身之祸。陈伯达对林晰说:你说得太笼统,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林晰回答:工程师。
针对林晰的父亲曾在德国留学,陈伯达说:“在希特勒时代,受希特勒教育。工程师,那是资本家。”
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工程师和资本家原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按说陈伯达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但这时他充满了偏执,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搭错了神经,完全不顾逻辑信口开河了。
三
陈伯达把编辑、记者大致都问了一遍,然后开始讲话。像这一时期他经常说的那样,他连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然后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开始讲话说:《人民日报》的工作,1966年6月到12月是我管的,1967年上半年我没怎么管。但是你们不要分阶段,我管的只要有错误就可以批评,陈伯达也可以打倒。官僚主义可以打倒,打倒可以做肥料。
陈伯达说:要“斗私批修”,办学习班,要言行一致。《人民日报》天天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自己不执行。发表“最高指示”又不懂“最高指示”,又要宣传,又不学习,还用大帽子压人。
陈伯达自言自语地说:“用大帽子压人是不行的。”这是说别人,还是指自己,他没有说,也就无人知晓了。
最后,陈伯达要求,大家坐下来“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而“文革报道部”嘛,陈伯达说:“其实你们也报道不了什么,就不要下去采访了。”
问题是,谁也不知道陈伯达“亦庄亦谐”地说话究竟是真还是装模作样。面对《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陈伯达说,你们不要出去了,都留在家里,一个月不要出去,要“斗私批修”,要自我批评,互相批评,要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像你们这些人,有饭吃,有房子住,不破坏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座中的编辑、记者个个目瞪口呆。
陈伯达讲完话,他和姚文元的视察就结束了。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大会议桌四周的人鼓掌,表示欢送。
陈伯达已经离席往外走了,听到一片掌声,突然转过身来说道:“你们不要鼓掌欢送我,你们这里有卫戍司令的小姐,你们不枪毙我就不错了。”
这句话一出,全场的鼓掌声马上停住了。这句话使郝洁的心情非常紧张,不知道接下来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她还感到奇怪,陈伯达这样大的大首长,讲话太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时近午夜,陈伯达、姚文元扬长而去。
经受了陈伯达一番奇怪询问的人们,心情都非常别扭和紧张,不明白陈伯达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事后,赵近宇因为陈伯达问他是不是有电台而受到追查,被关入“牛棚”遭受严厉的批判和审查。结果查无实据,又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陈伯达、姚文元这番视察后,“清理阶级队伍”在人民日报社全面开展起来了。■
(作者注: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前辈何燕凌、林晰、郝洁、崔筱桐、李成华的帮助,核对了陈伯达的讲话内容,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