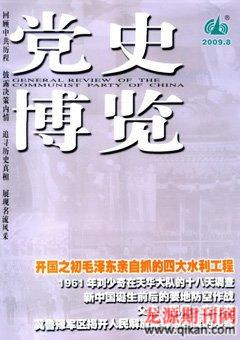父亲·恩师·忘年交
铁竹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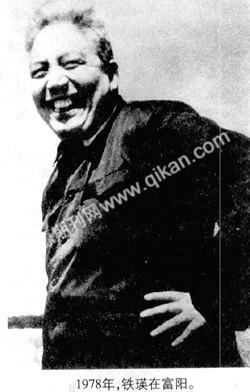
仙逝竟能如此从容美丽
今年2月6日凌晨,电话铃骤响,我赶到杭州,93岁的老父亲已经离开病房,睡在了鲜花盛开的地方。
爸爸的面容,就像往常熟睡时一样,红润、平静、安详。恍惚间,那分明闭着的双眼在努力睁开,抿着的双唇在微微嚅动,耳边响起电话中他最后留给我的亲切的声音:五一来,好,要健康噢,好!
我找众人问起昨天,几乎人人都说到“最后的握手”。
一天里,来病床前看望的院长、查房的科主任、问候的保健医生、探病的侄儿侄媳妇、送文件的秘书,临走时,爸爸都说谢谢,并招呼道:来,我们握握手!
傍晚,司机阿龙已经走到门口,侧身躺在床上的爸爸,口吻亲切地招呼说:阿龙,你过来。他拉住回到床边的阿龙的手,用力一握。阿龙着实感到意外:给首长开车八九年了,熟得像家人,过去从来不用这个礼节。
晚上,爸爸的小女儿、小儿子两家看望老人,两个多小时里,祖孙三代在一起笑声朗朗,其乐融融。
爸爸坐在高背沙发椅上,边吃着小儿子带来的黄岩最好品种的橘子,边听他说着去基层调研的情况。家中第三代的“小句号”觅觅,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和爷爷特亲。20出头的她笑吟吟地依偎在爷爷身边,双手捧起老人的手贴着自己的脸颊,嘴里呢喃着:“爷爷,你的手好软、好暖和噢!”爸爸微笑着点了点头。
警卫员用木桶打来热水给爸爸泡脚,小女儿习惯地蹲下身去,先试水温,然后帮爸爸脱鞋,再用自己的两只手在水里为爸爸轻轻地搓揉着双脚。
电视里在播赵本山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关东大先生》,大家陪着一起看了两集。爸爸几次念出画面上的字幕,模仿着角色的台词,惹得众人哈哈哈笑个不停。
谈笑中,爸爸与两家儿女约好,三天后回家过元宵节。
晚上9点多钟,爸爸说:“好了吧,我想睡了。”
于是,大家像往常一样,起身围到床前依次与爸爸道晚安。
爸爸有点不同,一反招手道别的习惯,儿女们刚来时,他与每一个人都用力地握手,这时又一次与每一个亲人紧紧地有力地握手,嘴里清楚地说:“好,再见!”
出门后,大家喜形于色:爸爸握手这么有力,很快就可以出院了!谁能想到,当晚,这充满希望幸福的一握,竟成为与爸爸天各一方最后的握手。
说到“真正的最后”,警卫员小刘眼闪泪光,仿佛自己还不能相信:
凌晨4点40分,首长醒,侧左小便后,呼吸有点急,我问:“首长,你有没有不舒服?”首长当时话说得很清楚:“我没有不舒服。”谁想他向右一翻身,呼吸声突然没了,我急忙打铃,医生护士赶来,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可首长再没醒……
我情不自禁地抚摸着花丛中爸爸的手,补上了自己最后的一握。爸爸的手还是像往常一样的柔软,只是稍稍有点凉。
我的心开始与爸爸对话:
亲爱的爸爸,要说您的走,可以算真正的善终,走得安详、轻松,没有一丝痛苦。这真是人们常说的用一生做好事才能修来的福分!让女儿近年来一直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下了。
谢谢您,亲爱的爸爸!您熟睡般的面容,您与众人最后有力的握手,您留下“我没有不舒服”这最后一句话,真让我惊叹您把生命的句号画得如此圆满,潇洒。也让我第一次身临其境感受到:仙逝竟能如此从容美丽,善终竟能如此平静温馨。
当然,女儿对您也真有点小小的意见,您生命的句号不该画得这么快啊!快得让儿女心痛,让您身边所有工作人员和上上下下所有爱您的人,太难以接受这天各一方的永别事实。
父亲
一进家门,小妹景沪拉着我泣不成声:伟姐,你一定怪我帮爸爸劝你春节不回来,你没能见上爸爸最后一面。我反复说没有,还真心感激她多年对爸爸的照顾。

爸爸的一群儿女,最后一直不在身边的,只有我。细想起来,从妈妈搬家去了天堂,我几乎年年都回杭州过春节。当然,我们不能和爸爸一起过年三十,我南京还有一位比爸爸年长一岁的公公,我们小家总是先陪公公过完年三十,年初二或初三,再一起回杭州看爸爸。
2008年春节,一是因为公公重病躺在医院,二是我将要当外婆了,不能回杭州过春节,于是节前一人回杭州看望了爸爸。记得乘长途大巴刚回到南京,多年未遇的特大雪灾便不期而至,而我竟逃过了大雪封路的一劫。
今年春节,我们决定一家五口回杭州过春节,带着八个月的外孙女小树,给杭州西湖边的“老树”拜年。尤其是电话里听小妹景沪说过这段与爸爸的对话,我更是归心似箭。
去年夏天爸爸从医院回家后,以往利落的行动变得吃力迟缓。每次饭后,看着爸爸想站起来却力不从心,多年来吃饭时一直坐在他左边的小女儿景沪总会伸手搀扶他。今年元旦后,她明显感到搀扶爸爸越来越要用大力气。那天,沪妹帮爸爸倒水漱口、擦嘴,嘴里真情地念叨:“爸爸,你一定要长寿噢,你这棵大树不能倒噢!”
近一年来已经很少主动讲话的爸爸,这时接口很快:“大树倒了还有小树!”
小妹一下没反应过来:“什么小树?”
爸爸回答:“南京不是有棵小树嘛!”
是啊,爸爸分明说的是谁也无力改变的自然规律,可听话听音,我的心猛一咯噔,突然联想起多年前访问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先生的一段对话。
那是1988年夏天,为写一篇有关周恩来的文章,我去北京黄维家中采访。谈完要离开时,85岁的黄老先生执意起身送到门口。我看他腰背挺直,步履稳健,忍不住称赞:“黄老,你的身体真好!”
黄老爽直地摇了摇头,笑说:“这是表象,老人都是中空的大树!”果不其然,半年后我便听到了老人驾鹤西去的消息。
今年的春节日渐临近时,天气变得异常寒冷。一天,我与爸爸通电话,老人用永远与人商量的口吻说:“小伟啊,小树才八个月,太小,能来吗?”
我多次领教过杭州冬天的阴郁湿冷,大人尚且极易感冒,何况婴儿!我接受了爸爸的提醒,虽然心里不舍,但也觉无奈:是啊,这就意味着我也不能春节回杭州!
记得在电话里我与爸爸约定,五一长假小树一岁时,全家再去杭州看望他。当然,我决心已定:节后自己一人先回杭州看爸爸。
丈夫李洋执意自己去邮局给爸爸寄去一万元“压岁钱”,用他的话说:“平时我们不在老人身边,不能像杭州的姐弟那样随时尽孝心,过春节一定要给老人寄点钱,让爸爸多吃点冬虫夏草壮壮身体。”
收到钱后,爸爸让警卫员小刘拨通了我的电话:
“小伟,你好吧?”爸爸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我好!爸爸,你好吗?你是在打牌吗?是输还是赢啊?”我看手表正是上午11点20分,为抗老年痴呆,家人总在这个时间陪爸爸打牌。也因为近年来爸爸的话少了,每次通电话我总主动不断提问,就想多与老人说说话。
“打牌噢,都是我赢……”话筒里隐约传来抗议声,接着我耳边响起了爸爸的笑声:“呵呵,我是孔夫子搬家都是书(输)了!”
顿时,我心中百味杂陈,但主调还是安慰:毕竟爸爸在笑,毕竟爸爸还能说出歇后语,我掩饰着喉头哽咽大声说:
“爸爸,我们全家五一长假去看你,要健康哟!”
“五一来,好,要健康哟,好……”
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爸爸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仰望着灵堂里爸爸满脸阳光笑容的照片,我在心中祈祷:爸爸,谢谢您和妈妈给了我生命,并让我在战火中存活,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1948年4月,爸爸正指挥部队攻打潍县,属鼠,也确实黑瘦如鼠的我在诸城呱呱坠地。高烧的妈妈没有一滴奶,靠爸爸派人送来的两斤羊奶撑了两天。第三天,望着饿得哇哇大哭的女儿,无计可施的妈妈只能默默垂泪。
听到信儿,姥娘拐着小脚从老家赶来,抱过我,拿了块窝头在自己嘴里嚼了又嚼,嚼成糊状,对着嘴喂过来,我立即收住哭声,吧嗒着嘴,又吞又吸。姥娘笑了:看,这妮子三天就能吃窝头,命硬,死不了!

我也感激任斌武等前辈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教会我先做人,后作文,并在38年后告诉了爸爸为我而登门拜托这件事,让我真切感受到爸爸对儿女的尊重和无私的爱!如果38年前爸爸就提出让我当作家为其圆梦的要求,那无异于揠苗助长,使从小不太自信,有点自卑的我,犹如仰望珠峰心惊胆战,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恐怕早就度日如年,一事无成了!
反映新中国成立初陈毅当上海市长的《一个人与一个城市》一书,是我与人合作完成的,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初生牛犊不怕虎,1982年10月,我毛遂自荐争取到了写陈毅元帅在“文革”中文学传记的任务。军区副政委孙克骥鼓励我说:小铁,要想方设法在老同志中搜集材料,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材料丰富,感受深刻,才能事半功倍!文章能发表最好,即使发表不了,也能给后来人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万事开头难。我永远感谢爸爸慷慨大方地为我“开后门”。他帮我联系了叶剑英、徐向前及几位上将、省委书记。他言语诚恳:我的女儿太年轻,只有请你们指点,才能把陈老总写得神似!于是,我在北京迈开了高层采访的第一步。加上我在《解放军报》当过记者,磨厚了脸皮,锻炼了口才,只要敲开了一家门,就“粘”上去,努力实现“三部曲”:一、请首长把所了解的陈老总的点滴情况“竹筒倒豆子”;二、请首长谈自己在“文革”中的坎坷经历和对“文革”的认识过程;三、请首长推荐和帮助我,再联系几位采访对象。于是,采访网终于在中央领导层和各部委、军区领导中撒开了:三位元帅、十数位将军、几十位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像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王震、谷牧、方毅、余秋里、姬鹏飞、宋任穷、阿沛·阿旺晋美、乔冠华、黄华、张震、张爱萍、萧华、秦基伟、叶飞、李德生、张劲夫、程思远以及黄维、沈醉等,还有陈毅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他的厨师,逐渐积累到224位。其中有23位曾数次为我提供材料,解答疑难。
写完《霜重色愈浓——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后,1985年送给王震审阅。王老欣然为此书作序推荐。
《霜重色愈浓——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书中大量涉及“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高层斗争的内容,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批准出版。后来,此书五次再版,香港也出版了繁体字版本,更名《陈毅将军传奇》。同时,《昆仑》杂志,全国60多家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连载连播,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1997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为十大精品书之一三次再版,更名为《陈毅元帅最后的岁月》。
在随后的20多年的采访、写作中,指点过我的老师增加至上千位,但爸爸永远是我的第一恩师。
忘年交
随着我采访的老一辈党政军领导、科技文化文艺名人和世界华侨华人精英的日益增多,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一点不假。在这过程中,特别是爸爸1993年彻底离休后,我与爸爸的父女之情也在不断升华。不知从哪一天起,我和爸爸成了挚友,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而“重情重义,名利身外”,则是爸爸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生启迪。
记得是1994年6月,住在医院里的妈妈病情日益严重。请来会诊的著名专家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他读过妈妈的胸片后,面部表情异常严肃。但是,让我意外的是,他从走进妈妈病房直至走出,眼睛里一直闪动着惊讶和尊敬。
我充满希望地说出了自己的观察,那位专家感慨直言:读你妈妈的胸片时,我以为是位已经奄奄一息、不能说话、只有最后一口气的垂危病人,万没想到,你妈妈坐在床上谈笑风生,她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还为老朋友的病情向我询问。据国际统计,这种病只能活9个月,你妈妈已经存活两年半了,已经是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说明她老人家原来的身体素质好,更说明她的心理素质好……
我的心陡然结冰,明白不可能再有奇迹在妈妈身上发生。
于是,白天在医院陪妈妈的我给爸爸下了道“命令”:“爸爸,您知道吗?每天下午3点以后,妈妈的眼睛总看着您来病房时坐的椅子。您以后每天下午一定来病房看看妈妈。”
记得爸爸以商量的口吻问我:“需要每天都去吗?”
我知道爸爸虽然已经离休,但方方面面请他参加的活动还很多。但我仍然坚持说:“是的,因为您一直专心当‘公家人,欠了同甘共苦、甘当后勤的妻子一辈子情,这是最后的补偿机会。”
爸爸没再说什么,他交代秘书调整好时间,每天下午3点左右就会坐在妈妈病床边,直至亲自送走妈妈……
15年后,2009年2月13日下午,爸爸的追悼会肃穆又温情,前后两层花圈只能放上中央领导人、中央各部委、浙江省、南京军区领导和各厅局、著名企业的哀思。更多单位、个人的思念,只能是挽联一张张、一层层地叠加、排开,挂满了三四十米长的两面墙。《渔光曲》、《我的祖国》等爸爸喜爱的优美旋律在空中回荡。正面墙上,鲜花环绕着的爸爸的照片,笑容绽放,双手合十,仿佛在说:让孩子们代表我谢谢所有为我送行的朋友们!
长龙一般的人流,在给爸爸献花鞠躬并与我们子女一一握手时,一位位银发老者、朝气壮年和青春男女,含泪说的最多的三句话是:
“铁书记是我们敬重的老领导,他为浙江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我们见的首长不少,像他这样从不知道自己职位高的领导真不多。”
“铁书记走得太快了,让我们好伤心。”
双手重复1400多次握手动作、两腿已经发软发颤的我,流泪在心中感叹:是啊,要说老爸您做官时间真不算短,容女儿说句大实话,您老人家还真不会做官!
您亲口对我说过,参加革命60多年,无论在部队还是到地方,您经常明明是副职,却在做正职的工作。
抗战结束后,爸爸是团政委,三野领导找他谈话,拟提他当警卫旅政委,原团长提为副旅长。他当即表态:我也当副政委吧,团长是位老红军,这样能调动他的积极性,对警卫旅工作有利。于是,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两人同提副职主持工作,不久后再一起扶正。
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采访,爸爸参加人大、党代会和各种会议,我们常在北京见面。我曾问过爸爸:有没有去过小平同志家?他说,工作事情会上都谈了,干吗休息时间去打扰。我说,爸爸您是三野陈老总的部下,小平是二野的,他不了解您,何况您“文革”中又一直在台上,他会不会对您另有看法?您要让他了解您,熟悉您才行!再说,我采访过许多省委书记、大军区领导,有几个像您这样大会小会都认真参加的?利用到北京的机会去看望老领导,向中央争取优惠政策,这才是上策。爸爸笑着摇摇头,只说了三个字:我不会。
其实,爸爸虽然不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但在省委书记中他是最早反对“批邓”的一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委书记的打招呼会议。爸爸听华国锋主席布置回去怎么传达,怎么批判“四人帮”时,也提到还要继续“批邓”。一向讲真话的习惯使他憋不住了,开始征求意见时,爸爸第一个站起身,大声说:
“华主席,粉碎‘四人帮我坚决拥护,但我认为,揭批‘四人帮和‘批邓是一个正反面,我希望停止‘批邓,专一揭批‘四人帮。”
“对,我赞成铁瑛同志的意见!”坐在我爸爸旁边的江西省委书记江渭清立即表示支持。
华国锋主席平静地说:“这慢慢地会转过来。”
散会时,有同志向我爸爸伸出大拇指,也有人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老铁,你怎么还是当兵的作风?
当年的秘书马寿根事后回忆:当时在会场上,铁书记第一个站起来表示反对“批邓”。大家都为他捏了把汗,但事后,首长并未因此惹来什么麻烦。
1983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杭州过春节。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第一次到杭州,也是我爸爸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接待小平同志——因为当时省委机构改革的计划已上报中央,爸爸将出任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已获得政治局批准。
一辆黑色红旗牌小轿车缓缓停下,邓小平从车中下来,步履平稳,满面笑容,近80高龄的老人了,谢绝休息,进屋就开始工作。
邓小平很高兴。他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现在苏州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接近800美元。
于是,爸爸汇报了浙江1982年工农业生产情况,当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已经人均600美元,分析了全省工农业发展情况,到2000年翻两番半或三番是可能的(1993年浙江省工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已经提前7年达到翻两番)。
听完汇报,邓小平满意地说道: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你们的工作不错,我很高兴!是呀,到2000年,江苏、浙江是应多翻一点,不然青海、甘肃这些基础落后的省可能会有困难,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指标。铁瑛同志,你要继续抓。
爸爸说:“我和省委大多数领导将退二线。”
“噢,铁瑛同志你退了?我怎么不知道。”小平同志表情有点惊讶。
按常理,邓小平在杭州居住期间,陪同责任应该是现任省委、南京军区主要领导。年初三,爸爸约了孩子们一块去灵峰探梅。刚要走,接到警卫处电话:小平同志谢绝了要去陪同的两位主要领导,准备自己出去。我爸爸考虑,让小平同志独自出游似乎不太礼貌,便驱车赶到刘庄。
“小平同志,你好!”我爸爸迎着刚出屋的邓小平行了个军礼。
“铁瑛同志,你怎么来了?”小平同志抬手回礼并微笑着发问。“我休息没什么事,出来看看你。”我爸爸笑着解释。
“好,上车!”小平同志爽朗地一挥手。
邓小平属龙,他的夫人卓琳和我爸爸也属龙,只是他们两人都比小平同志小一轮。沿着云栖竹林间的石阶,小平同志拉着我爸爸的手,一边聊天,一边缓步向前。说实话,第一次与邓小平牵手而行,我爸爸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邓小平对我爸爸说,你要把南京军区一起管起来。后来,南京军区确实派人来向我爸爸汇报工作,他只如实告知自己在大军区没有职务,当面谢绝了。
走到一处上有翠竹挺拔,下有一片竹笋破土而出的地方,小平同志主动招呼说:来,我和铁瑛同志合个影!那天没跟摄影师,只有台黑白照相机。“咔嚓”,“咔嚓”,照相机把这珍贵的瞬间变成了永恒!
望着爸爸和邓小平的合影,我真是感慨万千,爸爸确实是“名利身外,上下自在”!如果他稍微把个人的官阶名利放在前,面对邓小平的重托,自己提出要个南京军区的职务似乎也顺理成章。但他不会,他一生真的不会!
今年元宵之夜,饭桌抬进了爸爸的灵堂,我们姐弟相约:陪爸爸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元宵节!不料只有我失信!
无意间抬头看见二楼爸爸的书房里黑着灯,我再也忍不住泉涌的泪水,心里在大声呼唤:爸爸,您知道吗?自从妈妈搬去天堂,您的书房是我最暖心的地方!您是我的父亲,是我的恩师,老年后更是我的忘年交!我荣幸地阴错阳差地当了作家,圆了您未成的文学梦,我庆幸您的安详善终没有痛苦,生命句号画得如此圆润!我祝福您在天堂里百病全消,与妈妈朝夕相伴,笑声朗朗。我更会用您的追求和人品来精心培养小树,让她健康、幸福、茁壮地成长,直至成为参天大树。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
(2009年4月写于爸爸百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