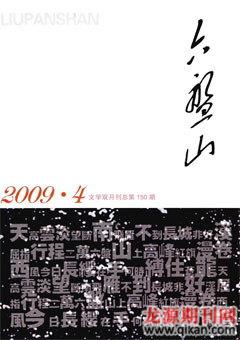洋芋
王新军
洋芋就是土豆。
除了土豆之外,洋芋还有山药呀马铃薯呀等等好多种别的叫法,但在沙洼洼这地方,一律叫洋芋。
洋芋四月进了地,五月就扯秧,到了六月头上,顶稍上的花儿就一层一层开了,引得蜂儿蝶儿满世界嗡嗡嗡乱飞。
洋芋开白花,花脉上带些许粉色,像自嫩嫩的脸上搽了淡淡的胭脂红。于是这种红,便渗进了嫩嫩的白里,洇成粉嘟嘟的一个软团儿。
到了顶稍上开花的时候,洋芋通常就要起垅了。两行为一垅,垅与垅之间的土,要用锨往两边培。有些会务习洋芋的庄稼人,还要在两行洋芋的中间,填上羊粪猪粪,或者架上一股上年盛夏晒干的苦蒿子。顶稍上一扬花,根下面就结籽,这时候的洋芋,最需要肥料。
起垅培土,不能一次完成,要跟着洋芋,且长且起。一般要三次,也有人嫌麻烦,两次就罢了的,但一般都要壅三次。
三次土培完,洋芋的花儿也开到了后期。到了粗粗胖胖的土塄上憋开口子的时候,从上面没淹过水的虚土里插进手去,就能摸出捶头大的洋芋疙瘩来。这时候,时间大约也就到了七月了。
七月里,喜鹊嗦子都晒得开窟窿哩。到了这样的天气,一般中午没有人愿意出门,都躲在屋子里睡大觉。早上牵出去吃草的牛和马,早饭之后都要拉到树底下。出牧的羊群,到了中午,羊把式也是要吆进圈里歇个晌午觉的。猪最怕热,偶尔便有跳出圈来的,也必然是冲着河湾里那片紫泥塘子去的。鸡哩,在地上张大嘴爬着,眼睛却不闭,随时准备翻身跑掉。狗趴在自己的窝里,把长长的舌头伸出来,咝咝地不停吐热气。这时节的太阳光,小刀子一样簌簌往地上插,就说沙洼洼靠戈壁近,人特经晒,这样的时候,该避还是要避的。下地干活,要等到日头偏西树影子拉长的时候。那时候会有一丝儿风从远远的戈壁上刮过来,虽然照旧是热烘烘的,但耳朵后根处,多多少少还是能感觉到一些凉意的。
七月过去,八月秋风就来了——秋风能吹来满鼻子的香气。如果仔细分辨,这香气里必定有那么一缕是从花花家的洋芋地上吹来的。
到了七月里,洋芋地里的活就少了。除了去滩上拔蒿子,花花的爹爹常常要在太阳偏西的时候,来洋芋地里走一走,看一看。仿佛每天不走那么一回,洋芋就会长出另外一种他预料之外的样子来。
爹爹来的时候,花花也要来。
爹爹说,花花花花骑马马,花花是爹爹的尕尾巴。
听爹爹这么一说,花花就咯咯咯咯笑了。
花花是上过学的,后来不上了。
那是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吧,每天花花都会被爹爹早早叫起来,和村里许多孩子一样啃着硬馍,往河对岸的小学校赶。河水不宽,也不窄,三脚两脚是断然跨不过去的。但只要卷了裤腿,瞅准地方,五脚六脚的,从浅水处也就蹦过去了。他们一般不蹦,他们多是踩着大人码在水里的方石头过河的。只有到了夏天,小河里的水浅了,花花他们才喜欢在清水河里跳蹦子。光了脚丫下到小河里,不跳不行。水浅的地方,河底上的小石头像大人的手指头,见着娃娃的脚心就想抠一抠。
它一抠,你就非跳不行——痒得很。
偶尔的,花花也会和别的丫头一起脱掉衣服,去河水没膝的地方凫鸭子。她们的小肚皮紧挨着河底的细沙子,两只手和两只脚在水里胡乱划拉着,叭嗒叭嗒,叽叽喳喳,果真像一群下了河的小鸭子。她们于是就把这种浅水里的小游戏,形象地叫做凫鸭子。如果远远看见有男生背着书包过来了,她们就会惊慌失措,纷纷用自己的小手去遮身上的一些地方,但每一次都觉得自己的手实在太小了,尽管费了很大的劲,能遮住的地方还是太少太少。如果有男生跑过来搞恶作剧,她们也不敢从水里站起来。但她们会腾出一只手向他们撩水,也会向他们扔石子。总归她们是不会吃什么亏的,她们蹲下身子,就觉得把该遮的地方大多都遮住了。男生们介于“五讲四美三热爱”什么的,自然也会适可而止,远远地嘻嘻几声,也就罢了。若是果真闹得凶了,也怕她们会告秃头老师。碰上秃头老师心情不好的时候,男生们是会为这样的事,挨秃头老师手里那根竹板子的。
给花花他们上课的秃头老师,是个中年男人,身子瘦长得像秋天的玉米杆。时常戴着个眼镜,两只镜片中问的横梁上,用白色的胶布缠了一个小疙瘩。花花觉得那白色的胶布疙瘩,肯定是从保健站柳大夫那里弄来的。因为有一次花花上学路过保健站的时候,看见柳大夫手上就拿着那样的一条白胶布。而且花花还发现,当时他们永远正确的秃头老师就坐在保健站白色的铁架子床上,正和左边嘴角上长着一颗黑痣的柳大夫有说有笑的。柳大夫可是村里的大美人,在外面学过好几次看病打针的手艺,据说在县城大医院都实习过。也许是外头的世面见多了,沙洼洼的男人就横竖看不上一个,老大不小了还不张罗着嫁人。这情形与秃头老师有些相像。那一天,花花看见秃头老师出门时用他经常在黑板上写字的那只手,从后面拍了下柳大夫裹在白大褂里的圆屁股。花花想,秃头老师拿粉笔拿竹板子的手,怎么能随便去拍一个女人的屁股呢!她觉得秃头老师这样做,真的不好,很不好。她当时就莫名其妙地笑了笑,然后朝远处的某个地方瞪了一眼。后来秃头老师用那只拍过柳大夫的手在黑板上写出的粉笔字,在花花心里就不如以前那么白了。他的那颗脑袋上,看上去头发又少了一撮。
其实,秃头老师的脑瓜并不是真的秃,就是头发茬子生得高了一些,头顶上的头发稀了一些罢了。按沙洼洼人的说法,鬓高绷额头大——这应该是一颗能够当官的好脑袋。但它生在一个找不到婆娘的村小学教师脖子上,他就只能有这么一个通俗的称谓——秃头。这种样子,看上去他的头发就是比旁人少得多嘛。因此说来,叫他秃头老师,也不是全没有道理,更没有完全的恶意。没有完全的恶意,村人也一般不当面叫他秃头老师,因为这样的叫法,对一个老师来说毕竟不大礼貌。
后来,秃头老师来找过爹爹一次。
秃头老师对花花的爹爹说,算了吧,搁在身边做个啥吧,花花这丫头,上学终究是个样子。
秃头老师说完,也不去看花花爹爹脸上的反应,就起身背搭着手走了。
秃头老师走后,爹爹定定坐在院子里,嘭——嘭——嘭——抽了一后晌烟袋。
原指望上了学会渐渐好起来呢!
当然,秃头老师对爹爹说这些话的时候,花花并不知道。反正那天早上她早早起来要背着书包去学校的时候,爹爹用手比划着,告诉她不要去了。她还以为秃头老师大约是有事,没有人给她们在黑板上写字了呢。接下来一连几天,都是那个样子的,爹爹用同样的手式阻止了即将出门上学的花花。
那天早上,花花跟在爹爹的屁股后面走进洋芋地的时候,花花哭了。事实上爹爹一路上都在劝着她。爹爹用悲伤的神情说着一些能够宽慰花花的话。花花不知道自己已经连读上了三个一年级了,和她一起开始上学的那些孩子,都已经上到三年级了。花花就把爹爹不让自己去上学的事,与秃头老师联系在了一起。花花觉得秃头老师这样一个瘦长的男人,一个头上头发生得很稀的男人,不让一个孩子上学了,这不好,很不好。
花花不上学了,就跟着爹爹务习起洋芋来。
爹爹给洋芋起垅的时候,花花就帮着一缕一缕地往洋芋中间架蒿子。花花的小手拨开毛茸茸的洋芋叶子,把已经分好的干蒿子塞进去,爹爹锨里的土一丢,就牢牢压住了。有时候爹爹丢过来的土,不小心压住了洋芋秧,花花就紧忙着扑过去,小心地拨开土,把压倒的洋芋秧秧扶起来,再用小手轻轻拂去叶片上的土。那样子,就像一个刚刚做了母亲的小女子,在拂自己孩子被风吹乱了的头发。
花花家的洋芋,是要起三次垅的。
爹爹不嫌麻烦。
爹爹说,起三次垅,一次一浇水,洋芋才能长得好些。
洋芋起第一次垅的时候,花花操的心最多了。头一次壅的土最多,洋芋秧也刚刚扯起来,秧子脆,中间又要架东西,不小心不行,不小心就给压折了。到了起第二次垅的时候,洋芋秧已经蹿起来了,就不会担心被土埋掉了。即使是偶尔地埋掉了一两片叶子,也不打紧。到了第三次,基本就是对前两次的修整和加固,一锨半锨土想压住它,已经不大可能了。
三次垅起完,花花就开始心慌了。
感到心慌的时候,也就是花花盼着的时候了。花花坐在洋芋地边上,两只圆手手支着尖下巴,看着那片白里透出一层浅粉红的洋芋花,对着那些在花丛中飞来飞去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那些站在洋芋地边上骄傲的杨树和馒头一样的圆疙瘩柳树,对着那些长在地埂上的青草,对着那些在草丛里叫唤个不停的蚂蚱,对着那些偷偷钻进洋芋地里扯秧开出的喇叭花……反正对着她眼睛里能够看到的一切,她都有说不完的话。
——洋芋花花哎,你们啥时候开败呀?你们顶梢上结出的果果除了绿色还会有其他的颜色吗?
——小蜜蜂呀,你们整天飞来飞去的,你们的家在哪里呀,你们晚上睡觉的地方有绵绵的荞麦皮枕头么?
——蝴蝶呀,你们身上的花点点是谁给你们染上去的,是你们的妈妈呀还是爹爹?你们整天和鲜花在一起,你们身上也一定是香喷喷的吧?
——白杨树呀,你的个子咋那么高呀,比爹爹都要高呀,你们长那么高是不是想长到天上去把天戳个大窟窿呀?
——圆疙瘩柳树呀,你们爬在地上把腰都爬弯了,啥时候你才能像白杨树一样把身子直起来呵?
——青草青草多无边,牛儿羊儿满圈圈。
——小蚂蚱,吱吱吱叫,蹦蹦跳嘻嘻笑。
——喇叭花儿开,凉帽戴起来……
花花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出来。但她一句也说不出来,她只能在肚子里一个人说。自己对自己说,自己说给自己听。
秋天头上,是花花最高兴的时候。成熟的夏粮一收掉,就开始挖洋芋了。又粗又胖的土塄上,爹爹一锨下去,一嘟噜胖墩墩的新洋芋就带着香气从湿土里抖落出来。花花扑上去,一颗一颗从根须上揪下来,先捧到鼻子底下闻一闻,再把洋芋和一脸蛋的笑举起来,朝爹爹晃一晃。爹爹的笑也挂在脸上,虽然被一层灰尘和汗水挡住了一些,但花花是能够看到的。爹爹一笑,脸就和圆洋芋一样了。爹爹高兴,花花就干得更起劲了。她拨拉掉洋芋上的湿土,把它们在地上一颗一颗小心地码好。一垅两垅挖过去,洋芋就码得跟座小山似的了。
小山堆得差不多的时候,爹爹就不挖了。
头茬子洋芋出地,村子里必然会在某个时刻飘起新洋芋的香气。这香气最先从花花家的厨房门里溢出来,挤满院子后,又一股一股往房顶上涌。涌着涌着,房顶就给涌满了,一阵风过来,香气就丝丝缕缕往村街上飘。如果是没有风的时候,村街也常常被这香气塞实了。如果谁不小心开了街门,香气会迎面扑上去,与他撞个满怀。当年下来的头茬子洋芋,进了锅,热气一上来,香味就十分撩人。等大锅里咕嘟咕嘟响上一阵,整条村街,便被新洋芋的香气淹没了。这时候第一个走到街上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张开鼻孔,贪婪地吸几声,然后说,嗯,花花家的头茬子洋芋出地啦!接着另外的人就走了出来,同样张大了鼻孔。
最先闻到这些香气耐不住性子跑出街门来的,都是些刚刚长了腿腿子的娃娃。这个年岁的娃娃,对这样的香气最是敏感。他们急忙出了自家院门跑到街上,一边眼睛咕噜咕噜转着,一边根据香气的浓淡分辨着方向。
到了花花家门口,鼻子闻着扑面而来的洋芋香,眼睛盯着花花家敞开的街门。左徘徊,右徘徊,不觉间一根手指就伸到嘴里嘬了起来,不听话的口水,也流成了明晃晃的一条线。
当一大团香气跑过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那是洋芋出锅了。白白胖胖的洋芋被一只大盆子端出来,花花家门前的那片儿空地上就热闹起来了。路过的大人和围过来的娃娃,热洋芋人手一颗。娃娃们只顾吃,吃了这一个,还要寻思下一个。大人们吃得小心,一边吃,一边还要慨叹。那时候,全村最甜的笑就盛开的花花的圆脸上。
爹爹说,下来了,今年的洋芋下来了,尝个鲜,大家先尝个鲜。
爹爹说话的时候,花花也许已经又端出来一盆子。
洋芋是个宝,灾年度饥荒,丰年翻着花样摆在桌子上。有谁家能离了洋芋呢?离了洋芋的日子,注定是少滋没味的。
爹爹更知道,在花花没了娘的那些日子,石榔头的娘,铁蛋的娘,还有东家三姨,西家四婶子,都将自己的乳头塞到花花嘴里过。花花身上的穿戴,某一道口子,某一个窟窿,未必就都是他一个大男人的笨手连缀起来的。一个村里活人,他多一口你少一把的事情,是无从计较的。想一想这些,现如今的一锅洋芋又算得了什么啊!毕竟花花大了呀。
毕竟花花是一年一年地大了呀!
爹爹觉得,洋芋与自己,与花花,与村人,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情份。
花花渐渐大了,地上的活儿,她都能搭上手了。爹爹的洋芋,也就越种越多了。
先前的时候吧,一年也就是个一亩半亩的,后来两亩三亩也挡不住了。
花花家的洋芋,大多是要卖掉的。
挖满一车,爹爹就要拉出去卖。早先是毛驴拉着的架子车。架子车小,车厢里装上一些,上面还得码上五六个蛇皮袋子。架子车一次拉不了多少东西,车子小是一方面,毛驴不是骡马那样的大牲口,力气也有限。一架子车洋芋拉出去,有时候转不了一个村就卖完了,还得来拉第二趟。本村的人家,知道这对父女的不易,看见花花家的洋芋出地了,没有种洋芋的就走过来说,今年的洋芋,给我留下一袋子呵。爹爹就笑呵呵地说,行哩,没有问题。即便就是自己家里种了洋芋的,走到花花家的洋芋地边,看见了忙碌的这一对父女,也要故意呆呆发上一愣,然后不好意思地对花花的爹爹说,我的洋芋不好,今年,洋芋给我留上一袋子吧。这倒不是说他真的没有把洋芋种得和花花家的一样好。花花家的洋芋么,要下一袋子么!
爹爹笑呵呵地说,行哩,没有一点点问题。
爹爹是想碎毛毛攒出个大钱哩!
后来,爹爹就不用毛驴架子车了。那年卖完最后一架子车洋芋之后,爹爹揣着钱去了趟城里。傍晚的时候,突突突开回了一台小四轮。小四轮头是红的,车斗子是草绿色的,看上去一身亮油油的颜色。往后这些年,花花家的洋芋种得多了,到秋天,都是爹爹开着新四轮拉着花花到城里卖掉的。
城里人可喜欢花花家的洋芋了。他们说花花家的洋芋吃起来沙沙的,有股阳光的味道。花花就觉
得很奇怪,她怎么就从来没在自家的洋芋中吃到过阳光的味道呢?
一次,花花拿着刚刚出锅的热洋芋在太阳底下吃。她吃一口洋芋,细细嚼一阵,然后张开嘴,对着明晃晃的阳光咬一口,叭嗒叭嗒再嚼。花花想把洋芋里的阳光味道分离出来,也想把阳光的味道掺进洋芋里面去。花花一次又一次专注地反复着,爹爹看到了,就呵呵呵地笑着说,花花哎,你在做啥呀,你是想把太阳也一起吃进肚子里去哩吗?
花花蓦地羞红了脸,转身一头扎进了爹爹怀里。
她把爹爹搂得紧紧的。
那时候,阳光在她纤巧的后背上照耀着,温暖像水一样在她心里淌个不停。
后来学校的秃头老师调到别的学校去了,也终于不再单身了。听说娶的媳妇也是个教书的女老师。花花想,秃头老师把人家柳大夫的圆屁股都已经拍过了,为啥没有娶柳大夫当老婆呢!拍都拍了呀,一个女人的屁股是那么容易给人拍的么?你不是说过偷看女生洗澡的行为是可耻的么。即使是远远地看,也是不道德的,也是可耻的。看都不能看,你拍就能拍了?你这个秃头老师呀!后来村保健站的那个柳大夫,说是嫁给了乡卫生院年过半百的老院长。花花想,一个被男人拍过屁股的女人,恐怕也只能嫁个半搭子老汉了。
秋天卖洋芋的时候,花花总是快乐的。她的快乐并不来自那一张张花花绿绿的钱,她觉得它们只不过是一张纸所代表的一种纸的形式罢了。当新下来的洋芋小山一样堆在地上的时候,她的快乐把心都装满了。装不下的时候,就从嘴角里溢出来。但当那些洋芋变成一摞钱的时候,她便由不得地感到一种失落。
那么多的洋芋呵,它们却变成了一把纸……
花花毕竟是大了呀。
花花娘,是生花花的时候大出血死的。那可是惊心动魄的一天一夜啊,血像水一样从妈妈的身体里不停地流出来,据说有好大一盆子呢。最终花花是给生出来了,娘却只看了花花一眼就再没上来一口气。当然,还有人说娘是生花花活活累死的。不管啥样的说法,爹爹都不那样认为,因为在她去世的那个瞬间,他从她脸上看到了惨白中涌出的大片的玫瑰红。她的眉眼是那样平和,像睡着了一样。因此爹爹认为别人的说法都是不对的,她在离去的时候,已经拥有了无限的幸福。花花娘临终前的这种平和,给了爹爹往后的生活许多说不清的启示。
光靠人家娃娃的奶头不行呵!爹爹从很远的地方牵回一只奶羊来,开始了与花花两个人的生活。
花花和别的孩子一样,会吃,也会笑。
花花和别的孩子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花花两岁了,还不开口说话。
转眼三岁过去,都要四岁了,花花还是不吐话。
——丫头三岁多了不说话,怕是有啥麻达哩。
有人悄悄给爹爹说了。
——出去看看吧。
这样的话,本来是不好意思说的,但还是说了。
说了,爹爹就急了。爹爹心里也早就寻思哩,好好的一个娃,咋快四岁了还不吐口哩?就抱着花花去了一些地方。十里八乡,城里,都去了。弄来各种各样的方子叫花花吃。那些东西,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花花一律吃了。
都吃了,不会说话的花花,还是说不出一个囫囵字。
先天的?后天的?说不清楚。
爹爹在阳洼洼里锁着眉头抽闷烟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对不住自己的女人,眼泪便一疙瘩一疙瘩往下滚。花花的小手就伸过来,把它们全都抹掉了……
多好的娃呀——
爹爹寻思上了学或许就好些哩。
上学的几年里,花花却从没写出过一个正经字。
那一年爹爹发了狠,秋天里弄完了洋芋,领着花花进了省城。爹爹把好几年攒下的钱全都揣上了。不是说科学已经相当发达了吗?爹爹不相信科学叫花花开不了口,更不信科学叫花花起不了变化。
大医院毕竟是大医院呵,这个拍呀那个照的,一路上顺顺当当就下来了。医生拿着几张片子看完,头就慢慢摇上了。爹爹不甘心,他咋能甘心哩么!医院就安排了几个专家一起看片子,他一张你一张轮着看,然后再把脑袋挤成一堆一起看。看完了,那个戴眼镜的老主任给爹爹说,钱就不要白花了,有钱了,叫娃娃穿好点吃好点就是了。那时候爹爹一屁股跌在了椅子里,心里全都是失望。满满一眼眶眼泪,就有几颗滚出来了。花花不让爹爹流眼泪,赶紧伸手将它们拭掉了。
那个老主任开导爹爹说,科学是个好东西,但科学也改变不了所有的东西呀。
就是花花伸出手来一拭的那个瞬间,把跌倒的爹爹又扶起来了——这么好的娃,她明明不傻嘛!
从省城里回来了,村人们不用问,也早知道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或许这样的结局爹爹也是早就知道的,只是他觉得,有一丝缝隙,就应该让光亮照进来。再或者,就把这道缝隙完全合上。从省城回来的花花,除了多了几套新衣裳,花花还是花花。
说什么呢?村人们又能说什么呢?说老天不公?说造物弄人?唉……人世间谁又是活得容易的!
毕竟花花会侍弄洋芋了。
毕竟会侍弄洋芋的花花已经大了。
爹爹觉得花花与洋芋注定要绑到一起的时候,是花花渐渐大了的时候。洋芋毕竟不像其他庄稼,不管旱年涝年,它是只要埋进地里就能收上的东西。春天种上一盆子,秋里就能收上一麻袋。洋芋在窑里放好了,一直能吃到第二年的新洋芋下来。两茬子洋芋接续上,人就不会饿着了。
毕竟花花会侍弄洋芋了。
洋芋秧子顶梢上的花儿,一年一年粉白粉白地开着。
……
洋芋芽芽出土了。
洋芋倒出毛叶子来了。
洋芋开始扯秧了。
……
时间像风一样吹过,爹爹的头发,一根一根白了。
花花长大了。
(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