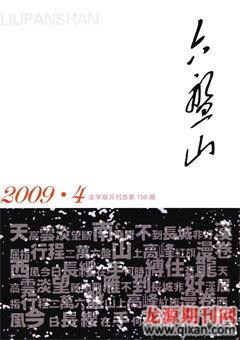好大一棵树
王秀玲
庞龙脸黑,胡子茬密密麻麻,像扎满红眼勾勾刺的枣树洼,个子大,体重,压得他那辆南方125在队里突突突响个没完,没少招村里妇女的谩骂指责。他头年腊月被选当上支队长,一开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就刮进了村子。村支书下了一个死命令:三月十二日前必须将村里那几座山洼,几片沟坡栽上树!几个支队长掐指一算,离三月十二日只剩下一个多月,要栽树的面积大着呢,这重要的不是栽树,而是挖树坑,年刚一过罢村里男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留守在家的大多是妇女,老人和孩子,这个任务不好完。
庞龙回家吃了两碗面,就骑上他那辆像病牛一样的摩托车进了自己管辖的自然村。挨家挨户将暖炕上的女人连拉带拽,又哄又骗,即讲情理又摆政策:这不是给我庞龙栽,是给咱们的子孙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咱们一到夏天被太阳晒得没处躲就是咱祖宗栽树太少。再说了,如果这次咱村的栽树任务完不成过不了关这春天各项优惠项目就到不了咱手,咱懒得狗都不想理,谁帮咱?
每早天麻麻亮,庞龙就穿暖和带上干粮和水,拿着尖头铁锹领一帮子妇女,从山顶往下挖树坑,一排一排一圈一圈,庞龙和县上派下来的技术员带头干。
这帮女人这时将调戏男人的本领都使出来用在庞龙和那个瘦技术员身上。或许不大熟悉,技术员常常只是在一旁听庞队长和她们谝闲传,听得认真专注。而向来以“牙客”为名的庞龙这会儿有了用武之地。干活累了,肚子饿了,他俩就盘腿坐在地上和她们一起吃干粮,还用柴棍子当筷子抢吃她们带的咸菜。其实庞龙挺爱和这些女人一起干活,有劲。女人们嘻嘻哈哈的谈笑中可捞的油水大着呢,当然是针对庞龙这样的男人。一两个男人在众多女人面前和一两个女人在众多男人面前的感觉是一样的,既有做为异性特征的骄傲,又有种寡不敌众的胆怯。这些女人在这高山野地里野得很,不信你试试,她们会像一窝蜂一样拥上来,扒衣服的扒衣服,脱鞋的脱鞋,拽胳膊的拽胳膊,压腿的压腿还大声叫喊:他婶子,咱们今天把他们也撂倒一回。然后哈哈大笑,笑声会在这空旷野地里、山沟里传出很远。
庞龙和技术员、村民早上麻乎乎,中午热乎乎,晚上黑乎乎的整整干了一个多月,总算把山桃、柠条等栽进了他们挖的树坑。
三月十二日到了,长城村村委会大院里人头攒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挤挤攮攮。站着看的,依在墙根抽旱烟的,扎成一堆说闲话的,拿着针线活的,你问我,我问你,不知道今天村里要开什么会,还摆出了罩红布的桌子,村口还挂着“欢迎区市县各级领导来我村调研开发”的横幅。“开发什么呀?”“不知道,我们长城塬地这么广这么平,这几年收成又好,开发哪?从哪开发……”
支书室里走出好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依次在红布桌后面坐了,面孔都很陌生,又带些许喜悦。南角边边上的村支书今天红光满面,看起来很高兴。他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西服下白色的衬衣领子将他的脸衬得红光光的,一条红方格子领带将他的脖子和衣服紧紧地系在一起,使人看起来有些不大舒服。村民中有几位年轻的媳妇在悄声地议论:你们看,支书今天很帅!还兴奋!也傻。哎,你们看他脸红的,又不是让他脱裤子上炕?啊?你见他上炕的样子了?哼,把他美的。女人在一起最热衷的就是议论她们熟悉的男人。她们看着这位平时松松散散,和和气气的大哥这会儿的模样着实开心。他一会儿将领带松松,觉着不对劲,又紧紧,过了一会儿还是不舒服又松松,他的两只手在脖颈处摸索个没完。他站起来大声喊:“静一静,大家别嚷了,今天是植树节。市领导来我村检查我们栽树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和我们商量一下如何开发建设长城塬”。村支书很会来事,他用“商量”这个词缓冲了领导和村民之间的距离。“下面我们请区领导说一下有关具体情况”。啪啪,村支书带头拍手村民们参差不齐、稀稀落落的掌声响了一会。红布桌后一位年约四五十岁,体型微胖,中等身材,穿西装打领带的干部站起来,把头发向后撩了撩,清清嗓子:“乡亲们,我今天代表市政府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自治区财政局要拨大量资金开发建设长城塬:1,重建村部大院;2,重建集贸市场,把这一排土坯营业房推倒重建砖瓦房;3,推土平地,把地平整成水平地;4,引水上塬。这是个大工程,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不懈的努力,更需要我们村民积极配合,把我们的村子建设成新型农村,我们要做新型农民,这点我个人认为我们能做好。”……后来还有好多人站起来讲话,庞龙再没听下去,他等着村支书给他分配具体的工作。
长城塬下属好几个自然村,长城塬地域辽阔,土地平坦,人口众多。每年麦收时节,大片大片的麦子黄澄澄金灿灿,夏风吹过麦浪一波一波,割麦的村民就成了浪头的冲浪者,脚底灵活,翻冲自如,汗水从额头滚下来,将灿烂的笑容冲洗得如同夏天早晨的朝阳热烈清新。战国秦长城从塬上穿过,那长城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风蚀,人过马踏已经成了矮小的土丘,但是在山峦沟壑中断断续续,蜿蜒起伏伸向远方。长城塬就像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伸展四肢腹在地表,稀落的树木是老人稀疏的毛发,秦长城就是老农流淌着历史文化脉搏的脊梁。每逢集市来这里交易的四面八方的农商吵吵嚷嚷做完一天的生意,收走村民的鸡鸭、牛羊等农副产品,带来村民需要的衣服鞋帽,药材副食,水果蔬菜。白马庙里的钟声叮叮当当,香火缭绕,给村民信念道德精神的寄托。庙院里一棵百年老柏树苍劲挺拔,树杆粗裂,枝叶茂盛。村民去庙里烧香拜佛会靠着它坐坐,扯扯家常,抽抽旱烟,老柏树像百岁老人,抚摸着前来乘凉的人。
“崔亮,崔亮!”崔亮回过头来见队长叫自己。“庞队长?”“崔亮,刚才支书和领导讲的话你都听见了吧,领导所讲的那些事要同时进行。”“同时进行?”“对,同时动工,平地的平地,先把这一排土房推倒,建营业房的建营业房,建村部的建村部,修学校的修学校,推地的推地。”“那咱们的劳力够吗?”“够,我们已经开过会了,支书让我们队长负责把各队的外出人员叫回来给咱自己干,平地是机子推,农贸市场,村部,学校,庙院包给我们村在外打工的那几支建筑队,他们可以给城里人盖高楼,就能把咱们的集贸市场建好。崔亮,你老哥这里空洞洞的,”说着庞龙用手指指了一下他那四四方方的大脑袋。“不管支书给我哪项工作,我需要有人帮我。你人实在,心眼好,文化水平高,你帮我把咱村建设好了,你就干队长。”“庞队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咋个干法不是为咱村搞建设,你分这么清干什么!”“不是,村子建好了,水引上塬,咱这地就不能再种小麦了,党和政府会派专人培养一批有技术的人来带动我村发展。”
三月十二日晚,各级领导走后,支书召集村委班子连夜开会分了工。
庞龙领到了平地这份差事。“可不好平啊庞队长,现在三月中旬,春田刚种上,可麦子长势好,不见苗子不心疼,地好平,小麦不好拆呀!”庞龙大喜过望后才听出支书话里的端儿,原来得拆小麦,要知道,在以世代耕种为生的农民心里,那庄稼比命都金贵,要拆小麦比拆他们的房屋祖坟都难。
第二天天没亮,庞龙就跑到地头了。站在地埂
上放眼望去,一片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望不到边,一眨眼的功夫就是一层金灿灿的麦粒呀。庞龙蹲下来,伸手抚摸着麦苗。麦苗在早晨新鲜的空气里噌噌长着,绿得泼了油一样,麦子长势这么好,庞龙心口却堵了半截猪屎样难受。他骑上摩托车直闯村部大院,他知道,支书昨夜又留村了,一两点开完会他回不了家,这会儿兴许还在被窝里躺着。今天把他从被窝里拖出来拉上地头,让他看看,四月了,这麦子长成什么样子了。庞龙这样想时已经到了村部大院,一把推开支书门,却看见那张单人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压根就没人睡过。“还钻老婆裤裆了?”庞龙骑上车往支书家追。经过麦田,他突然看见地埂上有个熟悉的背影。他走过去,支书依旧蹲在地埂上,抽着烟不吭声,眼睛一眨不眨的望着麦苗发呆。烟火烧到他手指了他才扔了,顺着烟头落下的地方庞龙看见一堆烟头横七竖八躺在支书脚前。庞龙也蹲下来,自己从支书烟盒里抽了一根烟点上,很认真地抽完,试探地问:“不行等麦子收了?”“你以为我不想啊,这麦子去年就不让咱种,咱都偷偷种了,自治区的文案里这可是一片待垦的荒地!”支书忽地站起来,“推,你带上崔亮把道理讲明白,不明白的偷着推,不行咱就动派出所!”支书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最好别动派出所,伤脸,伤情,伤政府的心。”
庞龙骑着摩托车驮着崔亮挨家挨户做工作。年轻的都签字同意推掉已经拔节的麦苗,年老的和男人不在家的女人就不好说。年老的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就知道一个道理,拆毁青苗是违法的,人肠子要用粮食灌,万一要推顺便把我也埋了。”“表叔,历年拆毁粮食是违法的,这次是为咱以后的庄稼更茁壮,收成更好……”老人脸一扯不再理会庞龙。妇女更难缠:“推小麦可以,你庞队长的炕上能搁下我这床被子,就推!”“能,十床都能……”庞龙高兴的忙应承,“你是叫驴啊?”庞龙被泼了一盆洗脚水样不敢呼吸。
虽说五月了,可夜晚的庄稼地里寒气逼人,庞龙和崔亮裹着棉大衣来来回回丈量土地,他俩的腿肚子像怀了崽的母山羊,又酸又痛。
白天的村部大院热闹极了,找村干部汇报农贸市场建设进展的,商量学校咋个修法的,上级领导抽查工作的,大多数是来找村干部评理的。妇女哭着说一觉醒来麦子变黄土的,有的说拆房损伤自家东西的,更有的是撒泼打滚连哭带嚎要村干部赔偿损失的……
庞龙拽着崔亮白天骑车在几辆推土机工作的地里来回奔跑,还得和阻拦在地头的村民磨嘴皮,他们磕头作揖:“别犟了,我庞龙比你们犟,可还被推掉了十多亩麦子,地整平了水引上塬,一年的收成就把咱的这点损失补回来了,这是政府看中了咱长城塬,咱长城塬有开发的价值。农贸市场要建设成县城那样有规模的市场,每逢集市各方农商来咱这交易带动我们经济发展,地整平水引上塬,我们就种蔬菜,水果等农业特产,要实行村村通公路,家家有出路。要在公路、水渠边上栽松柏,垂柳。雕塑白马像,文化戏台年年唱大戏,广场年年开农民运动会,物资交流会,让白马庙红火起来,让长城塬清秀起来,让村民精神起来……”庞龙扇动着双唇一遍一遍向村民勾勒长城塬未来的蓝图。
晚上,他还得陪推土机师傅偷偷推那些想不通的村民的麦子。五月中旬了,没推倒的麦子已经怀胎抽穗,今年雨水好,月月有雨,把个好收成见天往村民面前摆,庞龙和支书等村干部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农贸市场动工了,戏台设计好了,村委大院拆了,塑白马的工匠请来了,唯独这地平得艰难,支书和庞龙寸步不离地跟着推土机。
晚上十二点刚过,支书和庞龙领着司机来到两块连在一起的麦地,麦子在初夏的夜露里正拔节抽穗。支书闻着麦子的清香,吸溜着鼻子一挥手,推土机轰隆隆响了。没推出二十米远,支书听见推土机突然闷罐子样突突响了几下憋死了,司机狼样吼“想死啊!”支书和庞龙跑过去一看,一位老人站在推土机前,支书借灯光一看是麦生的父亲赵老爷子,老汉钉子钉在地里样站着,支书上去一把抱住老人哀求道:“老表叔啊,你这是要干啥,您老八十好几的人了,有个万一我咋向麦生交待……”“交待个逑,我几十岁的人了,和这麦子一起埋了值。我知道你支书能成,为了当好你的官,把咱长城塬几千口子人的口粮往土里埋。我没话说,倒下一塬麦子和我这把老骨头,树起一个好支书也值!”赵老汉颤动着双腿,眼睛喷着火。“扑通”,村支书双膝跪倒在赵老爷面前:“表叔,实在要埋,就把我埋了,如果把我埋了,这地能推平也是对党和政府为咱长城塬的期望有个交待,要么,这么大个塬让我弄成这副模样,我咋对得起这几千口子人的眼睛和政府交给我的任务?”说着支书泪眼矇眬地在初夏的月夜里环视东一片西一片的麦子和高高低低坑洼不平的黄土。赵老汉也望着面目全非的平塬老泪纵横:“娃。不是表叔犯浑,你就不能等咱把这把麦子收了。”“表叔哇,我想啊,可争取这个项目难,这一等不等给别人了吗!我是咱村民选举的村支书,我得对得起那份心。”“娃,起来吧,表叔心口子疼,再过一个月可是家家户户大丰收,村人也见你难,你看你这头发鸟都可以垒窝了。”赵老汉抚摸着支书的头发。
“娃,地整平了,市场,学校,戏台,庙都建设好了,可水上塬的事我看哄瓜娃娃哩?水往低处流,咱这可是高原!”“表叔,这水要用电抽,您就等水上塬吧。”“叔等着。”
其实,长城塬就是一棵大树,好大一棵树。树根扎进土里,吸收大地给它的营养,它的根系一天天庞大健壮,它就站地更稳。那条公路就是树身,田间小路村路是树杆,一块一块的田地是枝叶,村民从家到地里,从地里到家忙碌的就像一群在树间生活作息的鸟,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房子窑洞就是这群鸟的窝,秦长城就是流淌在树身里跳动的脉搏。突然有一天,春光明媚的一天,大地发现这棵树树身粗了,树杆壮了,可枝叶并不怎么茂盛青翠,枝叶不茂盛那群鸟就生活的不殷实,这棵树就削弱了它存在的意义,这大地是有实力的,拥抱一切的,世间万物都是她的孩子,她的胸怀是宽阔的,暖和的,她要挤出乳汁喂养这棵树,好让她茁壮成长,枝繁叶茂,搭起凉棚,好让那群鸟夏天太阳晒不着,冬天寒霜冻不着,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世代繁衍。
一块块平整的田地终于展现在村人面前,村部基本完工,农贸市场初现规模,戏台剩下些细活,白马雕塑就建在村子的东方,三匹白马已在庄稼地上空扬蹄奔驰。村干部和村民仍旧抢修水渠,打地埂。已进农历八月了,这地一封冻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七八月正逢多雨季节,早上修好的水渠说不定晚上一场雨就冲垮了,为了赶时间也防水渠被冲毁,村干部带领村民轮流连夜坚守在水渠前方,修水渠拍地埂。庞龙上眼皮打下眼皮,手中的铁锹开始荡秋千,他还是坚持着,他一停下来就都停下了。当发现干活的人少多了,他往水渠中一看,很多人躺在土渠边上抽旱烟谝闲传,还有的打起了呼噜。说闲话的听起来这会儿挺思念暖炕上的老婆孩子。庞龙蹲下来也参与了他们的话题:“庞队长,你家他婶子细皮嫩肉的,你那木锉一样的胡子茬她能受得
了吗?”一个年轻的村民斜躺在锹把上问庞龙。庞龙虽然很疲惫,可一说起自己的女人来他比谁都精神。他女人个子矮,模样一般,就是白,脸白,手白,脖子白,脚腕子白,哪都白,娘胎出来时啥色几十年还啥色,把个庞龙美的见了别的女人都斜着眼睛看。“他表叔,你不知道啊!哪晚你到我家看看……”说着他嘿嘿笑了,好像这位兄弟已经趴在他家窗户上看过了,他不但不恼还有些得意。借一根烟的功夫,这十几个已婚男人将彼此老婆的长相,喜好,特征都一一温习了一遍。
庞龙站起来,抽出压在屁股下的铁锹,招呼大家:“起来干活,咱赶天亮把这段土渠修好,那几条地埂拍了,天明了再回家睡觉,反正白天咱都不上工。”“你属猫的,没瞌睡,我们可熬不了,啊啊,我现在就想睡觉。”一个叫玉良的村民打着哈欠。“庞队长,你不知道玉良女人天一亮就上地拍地埂了,玉良回家也就剩个暖被窝,嘿嘿,他不发牢骚谁发牢骚”。另一个村民伸着懒腰扎了个舒服的姿势还斜着眼睛看着庞龙,庞龙无奈地说:“我明早给赵队长替你们老婆请个假,你们好好暖去。”“哎,干吧,他妈的支书这会儿爬在老婆身边做美梦呢。”还有个村民阴阳怪气地边说边起身子。“嗖!”庞龙将尖头锹猛地扎进渠沿的土里,锹把晃动了一下并没倒:“滚,谁想老婆了回去睡去,一群熊东西,支书正躺在医院里呢……”说着庞龙一屁股蹲在地上孩子般哇哇哭了。
第二天传回消息,支书得了肝病……
四月初八,白马庙一年一度的庙会热闹极了,整个长城塬像烧开了的锅沸腾了。在这个吉祥安宁的日子,村民放下手中的农活,从四面八方赶来,观大戏的,做生意的,参加农民运动会的,来白马庙上香的,兴高采烈,吵吵嚷嚷,叽叽喳喳,真像一群生活在一棵树里的鸟。
庞龙靠在白马庙院里的那棵老柏树上,抽着烟,笑嘻嘻的和已经完全康复的村支书欣赏着脱胎换骨的长城塬。庞龙说:“支书,白马像咋建在整个村部的东方?”“那里本来就有个土丘,推地时打算一起推掉的,可当时十几辆推土机推到那全停下了,只听机子响却不动,后来赵队长说那儿可能就是白马的地盘。你知道,赵队长一直操持着这座庙的营生,白马像的地址就依了他,没想到这白马像建在那还真建对了,那种姿势,美,庞队长,咱要的就是这种精神。”支书正美美地望着不远处的白马像,眼睛里是整个长城塬秀美如画的庄园。
拾级而上,四方护栏里套着四方护栏还套着四方护栏,三层而上的四方护栏里一个四方台柱全用大理石砌成,四面雕着楷书文字,讲述白马庙的来历和长城塬悠久的历史文化。四方台柱顶是一座独峰,一匹白色公马两前蹄腾空而起,像冲锋的战士猛然间将马喝住。马首嘶天鸣月,前蹄欲勾白云,后腿蹬陆,阳物在两腿间雄性昂扬,公马在蓝天白云下奔驰,而两匹白色的母马很温顺地在公马腹下姿态各异。
庞龙美滋滋地昂头望着老柏树,老柏树又多了几个年轮,树杆粗了,树皮上一道道地,裂着很多口子,叶子更茂盛了,几只鸟雀在树间跳来跳去,倾听着树下来庙里上香人的许愿声,敲打的钟声。脚下村委会大院,学校,集市的吵嚷声和戏台上欢快的秦腔声在长城塬的上空飘扬。庞龙美滋滋地自言自语:好大一棵树!
(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