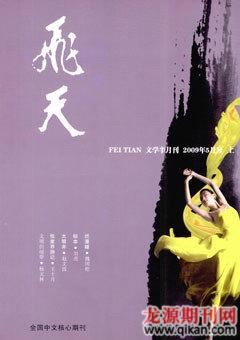大眼井
赵文波
几个年轻力壮的爷们,光着膀子,哗啦哗啦折腾了半天,才把得财从井里捞上来,紧接着一锨又一锨的土下去了。人死了,井也死了!只剩下光秃秃的井桩和没了柳罐的辘轳。
有花看着长脱脱躺在地上脸色青紫的得财,没有泪水,没有哭声也没有表情。大伯哥得旺却嚎得悲天恸地,捶胸顿足,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兄弟呀,你本来就够窝囊的了,大哥不该埋汰你呀,几捆破草咋就能要了你的命呢!你的命难道没几捆草值钱?
得旺昨晚心里总觉得不踏实,烦人的知了的鸣叫也让这夜格外地聒噪。老蛤蟆头烟叶的点点星火像是夜的眼睛,浓重的旱烟昧氤氲得满屋都是,媳妇桂兰用胳膊肘拐了他一下,咋啦,像烙饼似的,让不让人家睡了?得旺一翻身披了件上衣下了地。干啥去?睡不着,到地里溜溜。得旺到下屋取下挂在墙上的镰刀和着半夜的几声狗叫出了门。
夏夜的草地有些滑脚,露水打湿了半个裤腿凉哇哇的。在一片包米地旁,得旺听到一阵庄稼棵身体碰撞身体的沙沙声,他以为是风吹包米叶子,待这声音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停止脚步,立起耳朵,庄稼人听得出,这是收镰时刀吃猛草的噗噗声,而这声音就出自隔着玉米地东面的谷地里。
正是谷子抽穗的时节,茎嫩味美,又有刚结的谷穗,营养好,那些爱小的庄稼人常常趁着夜晚偷割谷草喂马。马不吃夜草不肥,每年的这个季节都有庄稼遭祸害。前天得旺家的谷地有一条垄被人偷割了两米多长,足足有一大捆。
今天是十五,满月。这大标月亮地的还有人敢偷割谷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得旺操着镰刀闪出玉米地。从弓着腰的高度上看,偷割谷子的这个家伙是个瘦高个儿,他割谷子的动作迅猛,像在飞,好像那些谷子们是他的仇敌,一溜未成年谷子被撂倒在地上。得旺举着手中的镰刀飞奔着冲向这个割谷子的家伙,可这家伙割得认真,竟然没发现后面有人。当得旺冲到这个人身后停住脚的时候,这家伙仍然像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镰刀。举着镰刀的得旺却怎么也下不了手,因为这个偷割谷子的男人是他的弟弟得财。
得旺呼呼地喘着粗气:得财,你疯了?得财似乎没听到得旺的叫喊。得财,你这是干什么?那刀仍然疯狂地飞舞,一片片谷子不情愿地横躺在垄台上。气急了的得旺一脚踹向得财的屁股,得财一个趔趄扎倒在地。得财慢慢地站起身,神情木然地看着得旺。你这个混蛋,你这个窝囊废、熊蛋包,连老婆都看不住的手,不敢和外人斗,倒祸害起你哥来了,你真有种!听了得旺的话,得财浑身打了个激灵,仿佛才回过神来,他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狼一般地嗥了起来,引得屯子里一连串狗吠声,让人感到疹得慌。
得财家在榆树屯算是有钱户了,说有钱至多也就三五千块钱,在得财他爹钟老算枕头底下枕着,那些由五块十块摞在一起的钱挂满了油泥味。钟老算很喜欢也很习惯别人给他取的这个外号,在他眼里这个外号充满了褒义。他本名叫钟厚仁,这钟厚仁虽然谈不上忠厚,但也说不上奸诈,只是这人心眼小,一分钱摔成八瓣花的主儿,自己爱喝烧酒却不买,专去那些抬了他家款的人家去喝,人家也不敢说他,因为年年都有求于他,尽管拿了利息,可是得罪了他来年不抬给你咋办?得财娘气管不好,平时钟老算只给买点镇痛药顶着,从不找大夫看,后来发展到肺心病,人死的时候脸肿胀得像个大紫萝卜,临咽气前,得财娘充满怨气地说,钱比你爹还亲,记住了别遭报应,到老了鸡鸭都离你远远的不搭理你。
按得财娘的话来了,得财都三十多岁了还没能讨上个老婆,当然得财讨不上老婆的主要原因是人长得丑。他的脸比常人长大约一倍,长就长吧,要是五官分配得合理也不至于太丑,可是得财的鼻子、眼睛、嘴都挤兑到脸的上半部分,下面拖着一个长长大下巴,像个肉尾巴,妇女们如果头一次看到得财能吓晕过去。得财的模样让自己很自卑,在人前总是显得蔫了巴唧,言语木讷,性格中多了几分软弱。得财不敢和人交流,却喜欢养马,他养种马,靠马维持生计;也喜欢骑马,他的马术高超,一米八的大高个儿站在飞奔着的马身上稳如泰山。
钟老算这么能算计就是没算准得财娶不上媳妇,老大得旺早就娶了老婆生了娃,就这老二得财让他绞尽脑汁也算不出究竟该咋办!前后屯谁家姑娘多大,甚至有多少寡妇他都知道个清清楚楚,可是那有啥用,得财长得丑,言语又木讷,别说外人相不中,自己这个当爹的看着都别楞。有些人向钟老算借钱,只要先说给得财做媒人,钟老算就麻溜把钱从枕头底下掏出来借给人家,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真正给得财介绍对象的。钟老算想来想去,想到得财妈临死时候说的话,就到坟前烧纸对得财娘叨咕说,以后要改掉小心眼算计人的毛病,谁再抬钱的时候利息少要点。
最近钟老算有很大变化,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主动帮忙,也不到他抬给钱的人家去喝便宜酒了,屯子人都说,钟老算像光长叶不开花的那种叫老来变的植物。真的是老来变了。
一天,天刚擦黑,吃过晚饭的钟老算倒背着手,到当街上溜达消化消化食。这人一上了年纪消化就出了问题,晚饭都不敢吃饱了,他叼着老太爷留下的那个熏得发黑的老烟斗,倒翘的山羊胡子下面飘出袅袅青烟。顺着一阵辘轳的吱扭吱扭不情愿的转动声,钟老算看到屯中间那眼大眼井旁,一个身材窈窕妇女站在井沿旁吃力地打水。谁家的妇女还来打水,这大老爷们干啥去了?钟老算走到近前才知道是王家闺女有花,待有花打上一桶水歇气的工夫,钟老算才上前接过辘轳把,把有花推到一边,你爹干啥去了,让你这小丫头来打水?井眼这么大,你气力小拗不过井把闪到井里咋办!我爹到后屯借钱去了,我娘的肺病加重了。钟老算没和有花搭话,他把打上来的水装进水桶,然后从有花手中接过扁担挑起水。有花默默地跟着来到家里,钟老算把水倒进外屋水缸后,一迈腿进了里屋。有花娘半跪在炕头儿上,手拄着一个装满秕谷的枕头,眼泡肿得能滴下水来,看到钟老算来了,拉风匣似的嗓子里冒出嘶哑的声音:“他钟大咋来了?”
“我看有花一个人挑水就过来看看。”钟老算拿出烟斗装上老蛤蟆头旱烟,掏出火柴刚要点火,看到有花娘气喘的样子,又把烟斗插进烟袋里。
“嗨!这人呀,要是活到我这个分上,就没啥意思了,不如嘎嘣死了省得连累好人。这借钱治病有啥用,早晚还不得死,欠那些饥荒还不都留给孩子了!”有花眼里噙着泪水,轻轻地给娘捶背。
“他婶,你咋能这么想啊,家里没有女人还是家吗?谁像我,一个老跑腿领着一个小跑腿,到现在我都后悔没给得财娘好好治病。有病不能上火,等有花爹回来告诉他,有啥难事吱一声,我先回了。”
“有花,快送送你钟大。”
有花把钟老算送到门口,钟老算回头说,天黑了不要出来了。他看了一眼有花,这姑娘长得多捋挂,白白净净的。可就是命不好,托生在这样一个穷家里。还说人家命不好呢,命不好长得好,早晚都能找个好人家过上好日子。得财呢,虽然家里不穷,可人长得石砢碜,有钱娶不上媳妇。
钟老算早早地倒在火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觉,
一斗接一斗地抽着老旱烟,弄得满屋都是烟气。得财说,呛死人了,不让人家睡了?钟老算狠狠地瞪了一眼得财,他起身划根火柴点着蜡,看看马蹄表,才九点。他一骨碌爬起来,拿起剪子挑开枕头,从里面拿出五百块钱揣到怀里下了地。爹,你干啥去?死去!钟老算没好气地说。
钟老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敞亮过,从上次借给有花家五百块钱后,他隔三差五就到有花家陪有花爹唠嗑。有花娘的病一到冬天就加重,现在钟老算已经借给有花家三千多块了。有花他爹对钟老算这样做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样一个铁公鸡,现在竟然主动拔出这么多毛来,让有花爹心里多少有点发毛,他说,我家穷,借你的钱一时半会还不上。钟老算也看出了有花爹的心思,解释说,得财他娘和有花娘一样的病,当初如果好好治疗也不至于过世那么早,他不想看着有花过早地没有娘。说得有花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
腊月,有花娘的病情加重,半夜里咳了血,有花爹要张罗后事。钟老算劝有花爹把有花娘送到县城医院治疗,有花爹摇摇头:人都这样啦还咋治?再说都借你家那么多钱,再不能麻烦你了。有花娘闭上眼睛挺死,有花悲伤得抽了过去,她要爹把娘留住。钟老算从枕头里掏出最后三千块钱,又向得财要钱。得财没好气地说:借出去的钱等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的钱还留着说媳妇用呢!钟老算气得山羊胡子直抖,骂得财是混账东西,狗屁不懂,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给你说媳妇。得财撅着嘴说,钱都给别人了,拿啥说媳妇?钟老算甩手一脖撸子抽在得财的大下巴上,得财转身从炕席底下拽出靠配马积攒的两千块钱,啪地摔给钟老算一扭身跑了出去。
治病治不了命。有花娘到底没过去年,在有花悲天恸地的哭声中人土为安,扔下一老一小和欠钟家的八千元饥荒。
钟老算去有花家的次数更勤了,他和有花爹俨然成了知己:他没了老婆,他也没了老婆,他老婆扔下没娶妻的儿子走了,他老婆扔下一个没出嫁的丫头去了。他觉得欠他很多钱和感情,他觉得理所应该。钟老算没事的时候和有花爹喝两盅,钟老算总叨咕说:“我把给得财娶媳妇的钱都借给你们治病了。我就后悔当初没有给得财他娘好好治病,弄得现在连个说话的伴都没了,得财那小子长得丑说不上媳妇,钱搁那也是闲着,想帮你救活有花她娘,可钱到这时候不顶用!”钟老算最近说话总带着一句口头语儿:“我把得财娶媳妇的钱都借给你们治病了。”而这句口头语只对有花和她爹说。每开口必带上这句话,不管和下边的话有没有联系。有花爹知道钟老算心里想的是啥,他想,你钟老算真是老谋深算啊!时间久了,有花也听出钟老算的话是啥味。“大,欠您家的钱我一定还上,你对我家的情我永远忘不了,我会向孝敬我爹一样孝敬您老的。”钟老算借着酒劲装糊涂:“大叔不叫你孝敬,大叔家就缺个儿媳妇。”
一天,钟老算又来到有花家,这回他没带酒,而是肚子里事先装满了酒来的。他嘴里喷着酒气,说完了那句口头语后才说正题:“今天得财相媳妇去了。”
“好啊,成了没?”有花爹有点兴奋。
“成啥啊!人家嫌咱没钱啊,我把得财娶媳妇的钱都借给你们治病了。”这回他又把这句口头语安在了后面,这更让人吃不消。
这天晚上有花爹对有花说:“有花,你看你钟大家咋样?”
有花知道爹下面还有话:“挺好啊,我家欠人家情太重了!”
有花爹叹了口气:“就是这人情太重了,压得你爹喘不过来气啊!”
有花没接茬,她知道爹还有话要说。“我看你钟大家的得财人挺实在,虽然长相不大好,岁数大一些,但家庭好,到这样的人家能享福。”
有花瞪大了眼睛:“是不是要把我顶债啊?”有花爹被有花的话噎住了。“爹,实话告诉你吧,我心里的人是水生,他对我好。”有花说。
嗨!谁叫你爹没能耐呢!有花爹长叹一声。
自打有花和爹说了心里人是水生后,就公开了和水生的关系,水生也基本上天天长在有花家,帮助有花干一些家里的活计。
钟老算来到有花家要账说给得财说媳妇,言语中透露出逼有花嫁给得财的意思。
这天晚上,有花爹拿出一瓶敌敌畏打开瓶就要喝,被闻到药味的有花拦住。有花爹老泪纵横地说,孩子呀,没钱咋整,我后悔当初不该给你娘治那个病,我死了,钟老算的账就没有了。有花抱着爹嚎啕大哭,她跪在她爹面前说:“爹,我认命了,我嫁给得财!”
“孩子,爹知道强扭的瓜苦哇!爹不能坑你啊!”
“爹不是坑我,是我自愿的,其实到钟家也不一定遭罪,人家条件好。”
当天晚上,有花去了水生家。水生是个穷光棍,除了嘴勤以外其余的都懒,一间破土房都快住倒了也不修缮一下。有花进屋,水生正倒在炕上吸旱烟,看有花来了便一把抱住有花要亲热,有花一把推开水生,看有花有点不高兴,水生才放手。“我来说正经事。”
水生摸不准有花来他家啥意思:“说吧。”
“你要是给我家八千块彩礼,我立刻嫁给你。”
“我家没钱!”水生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
“没有,我就嫁给得财。”有花一转身跑了出去。等有花出了大门的时候,屋里传出了狼一般的嗥叫声。泪水打湿了有花的衣襟。这泪里面有爱。也有恨,她恨水生家里穷,恨水生没有骨气,如果水生敢叫硬即使没钱她也会选择他,她对水生是爱恨交加,而对钟家则由原来的感激变成了恨。
有花要嫁给得财了!屯里人从寒冬议论到春暖,都说得财这小子有艳福,也有的说,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得财到现在才明白爹的神机妙算,尽管他知道这样做有点损,可一个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马上要成为自己的老婆了,他还是禁不住打心眼往外都冒甜水。
明个儿就是结婚的日子了,得财家今天送来了新衣服。有花躺在北屋炕上,春日里的微风从后墙小窗户吹拂过来,有花不敢想象和得财在一起的日子。“有花、有花,你睡了吗?”一个熟悉的声音飘了过来,有花赶紧爬起来,嘘了一声,然后一把把水生拽了进来,她扑在水生的身上,身体一耸一耸的却不敢发出声来。水生抱住有花无所顾忌地抚摸着,一阵撕裂的痛夹杂着说不出的从没有过的快感涌遍有花的全身。
结婚这天,得财披红戴花,骑着他的那匹高大的种马迎的亲,后面跟着四挂大马车。俗话说,好饭不怕晚。细皮嫩肉的有花小他十五岁,得财这个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
得财的婚礼是榆树屯最排场最热闹的婚礼,迎亲的队伍吹吹打打在屯子里绕了两圈。当队伍路过屯中间那眼老井时,从井边的榆树上传来一阵只有死了人才吹的丧调。水生坐在一个树杈上眼睛里冒出了火。嘀嘀嗒嗒的曲调充满了哀怨。得旺看到眼前的一幕,气得直翻白眼仁,他冲上去要和水生拼命。被得财拦住:“大哥,今天办喜事咱不惹事,兄弟讨到老婆不容易。得财感觉对水生有一种亏欠,如果不是爹的老谋深算,这媳妇可不是你得财的,得财总有一种棒打鸳鸯的感觉。
洞房花烛夜,有花没让得财上她的炕,她说三天后才能和得财睡在一起,她的下身疼得很厉害,
从昨晚一直疼到现在。人高马大的得财显得很乖巧,他怕自己的样子吓着有花,他知道和有花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他有足够的耐心等,三十几年他都等了,还怕这一哆嗦?有花不敢正眼看得财,她知道这个男人长相丑,一个屯子住着,以前离老远瞧过,从来没在跟前儿看过。有花不敢看,但却控制不住好奇心。她眯着眼看得财直挺挺地坐在硬板凳上,拖着个长丢丢的像尾巴一样的大下巴,眼睛微闭。头往下猛丁一耷拉,把他自己吓一跳,睁开眼睛晃晃头,再闭上眼睛,一会头又猛丁往下一耷拉。又吓了一跳。有花看着得财的憨态,在心里偷着扑哧笑了。你上炕睡吧。男人不知所措地“嗯”了一声。你睡炕梢。嗯。男人应了声,一脸的羞赧,抱了一床被和衣倒了上去。有花背靠着西墙,头蒙着被,偷眼看这个男人。男人将头埋在被里,有花能听到男人的呼吸,她知道男人心里在想啥。这男人是个老实人。
天刚抹黑,钟老算就蹲在窗台下吧嗒吧嗒地咂着老烟袋,他是来听屋里有啥动静的,他怕听到女人的挣扎和叫喊声。钟老算在窗台下蹲了大半夜,青蛙的鸣叫声反而使这农家小院显得格外的寂静,也不知道是失望还是什么别的感觉,但不管怎么说,得财娶上了媳妇,老儿子娶媳妇大事完毕了。躺在上屋炕上的钟老算才感觉身心疲乏,很快就进入梦乡。老伴回来看他说:人不能忒奸了,奸过头了,就会遭报应的,你钟老算就是太能算计了,你就不怕遭报应?钟老算被老伴的话惊了一身冷汗,一觉醒来就病了。
新婚夜过后,一大早,有花就开始忙活做饭了。她把白米饭端到钟老算跟前,钟老算颤巍巍地接过来,老泪纵横。得财今天显得很高兴,尽管昨夜他没和有花行夫妻之事,但他应该高兴,因为从目前的表现来看,有花没有对他和他的家表示反感,当然也没表现出一丝的热情。
第二天夜里,和新婚夜一样,第三天夜里和第二天夜里一样。有花能听到得财身板撞炕墙的声音,得财捂上耳朵都能听到有花的心跳声,闭着眼睛也能看到有花的眼睛睁得明亮亮的。
得财盼望第四天马上到来,有花说三天后他才能碰她。盼来白天盼晚上,吃过晚饭,天刚抹黑,得财就脱光衣服躺在炕上。新婚,他头一回脱衣服睡觉,他浑身火烧火燎的,三十多岁了,还没品尝过女人的滋味呢!过头的兴奋让得财周身都汗淋淋的。有花今晚也不知道咋地了,好像有很多事情都没做完,一会捅咕捅咕这,一会捅咕捅咕那儿,得财支棱着耳朵,听有花上炕没有。待得财将进入睡眠状态时,他才听到有花噗地吹灭蜡烛,掀开被子钻被窝的窸窣声,但很快就归于平静了。得财慢慢掀开被角,看到有花的头缩在被子里。得财从湿漉漉的被窝里探出身子,爬向有花。他颤抖着手慢慢揭开蒙在有花头上的被子,一张对他来说有着极强诱惑力的白白净净的脸露了出来,他急促的呼吸吹动了她的秀发。而有花的面部表情像一潭平静的湖水,好像一个风丝都不曾刮过,她那紧闭着的双眼像是一堵墙,堵截着得财那燃烧着的欲望。
在以后的几天乃至于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得财的欲望之火被那潭平静的湖水浇灭了。时间久了他们也习惯于这样无性的婚姻,除了这无性婚姻有点不正常外,其他事情都一切照常。有花每天早早地起来做饭,照顾病倒在炕上的公公钟老算,有时候还和有财一起下地干点农活。尽管有花也下地,可得财从不让有花做活,他舍不得有花那细皮嫩肉的小手做粗糙的庄稼活。这天,得财牵着他那匹心爱的种马,带着有花到谷地里拔大草。得财将马拴在地头的一棵杨树上,拔了一抱水稗草让有花给马送去。有花将草扔给马后,便欣赏起马吃草的样子。这马是钟家生钱的道儿,得财像供祖宗一样供着这匹马。有花用手帮马梳理毛发,这马也习惯于人们这样的照顾,悠闲地打着响鼻。这世界就是不说理,这种马配了母马,母马的主人还得给种马家钱,可是人就不行了,要是哪家男人强搞了谁家的女人,不仅钱上要遭罪,还可能进笆篱子。有花由这马想到了她和得财,她一看到得财的大下巴就会不自然地想到水生,一想到水生,她就想和得财离婚,可是她欠人家钱啊!有花发誓要多挣钱,赚到八千块钱后她就和得财离婚。
正当有花胡思乱想的当儿,一匹枣红马颠颠地向得财家的种马跑了过来,正在吃草的种马一声长嘶,身体竖了起来,身底下的阳物膨胀起来,拴在树上的缰绳挣断了。两匹马挤在一起头挨着头,身体相互碰撞着,样子很是亲密。得财家的种马发出一种异样的声音,它将两只前蹄搭在枣红马的背上。有花被眼前的场景羞红了脸,她转身欲走却与得财撞了个满怀,得财那两只火辣辣的眼睛似乎能喷出火来,没容她回过神,便一把把她抱在怀里,一片一米多高的还未抽穗的谷子倒了一片。有花用两排坚硬的牙齿咬着得财宽大的下巴,一股咸滋滋的液体流进了她的嘴里。
这大堤要是决了口子,洪水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得财与有花有了夫妻之实之后,得财突然来了爆发力,当天晚上又行使了一个男人抑或是雄性的威力。既然成了人家的老婆,就应该尽老婆的义务。尽管有花不喜欢这个男人,但她知道眼前的这个大下巴男人心眼并不坏。可她还是不喜欢他,她喜欢的是那个能说会道的水生,她在和得财行夫妻之事的时候,心里想着的是水生,这样心气就顺多了。当得财充分行使一个丈夫的权力,把那一摊孕育生命的液体全部注入有花身体的同时,他爹钟老算在另一铺炕上成了漏气的皮球。
钟老算死了,钟家的家境好,得财为钟老算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当钟家儿孙披麻戴孝的队伍路过屯子中间的那眼老井旁时,还是在井旁的那棵老榆树上,还是那个在得财婚礼上吹丧调的人,今天却吹了喜调。悲伤中的得财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冲上去要与他拼命。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只喊了一声“得财”,便叫停了他的冲动。
腊月的最后一天,有花生了个闺女,取名叫腊梅。
腊梅的出生像是给得财打了一针兴奋剂,虽然言语还是那样木讷,但行动更殷勤了,那些他该做和不该做的他都做了,粗大的手掌竟然洗起了尿布。再遇到水生的时候也没有仇恨和亏欠感了。有花是为他生过孩子的女人,他干嘛觉得亏欠人家的呢?水生再看得财时眼睛也不喷火了,反而主动与得财家靠近乎。没事的时候水生就牵着那匹老骒马。往得财家门口的老榆树上一拴,帮得财家干些零活,还能混顿烧酒喝。着水生现在这德性,得财在心里有些瞧不起他,在有花面前也自然多了一些自信,你水生除了嘴巴会说,模样比我强一点,剩下的啥都不行,庄稼把式靠嘴巴和模样过不了日子。
水生见得财对他没有丝毫的防范,花花肠子就逐渐冒出来了。趁得财不在家,水生问有花腊梅是不是他的,有花说,你想得美。水生说这娃长得一点都不像得财,鼻子眼睛倒像他。有花头一扭不再理他。水生突然袭击抱起有花要亲热,有花坚决反抗。有花说,你是一个穷光蛋,没资格睡女人,有能耐自己花钱娶一个。水生说,他只想娶有花。有花说,那你咋不娶我?有花用眼睛把水生盯跑了,水生受不了有花那样的眼神。水生走后,有花趴在炕上嚎啕
大哭。得财回来看有花眼睛红肿,问咋啦,有花说想她娘。
水生把他家的老骒马卖了,几天后又在牛马市场买了一匹马,过几天又把马卖了。水生成了牛马贩子。
有花养了十几只小鹅,她每天都要到地里给鹅挖苣荚菜。在一片菜棠里,有花将篮子放在一边,用短把刀专挑那些个头大、叶面宽的苣葜菜挖。这苣荚菜的生命力就是旺盛,每片地都至少铲三遍,可是没过几天,这些调皮的小家伙就会从黝黑的土地里冒出嫩芽。小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有花娘就带着有花到山上挖苣荬菜吃。有花边挖菜边忆起陈年旧事来。不知不觉篮子快满了,有花用手使劲压了压,把菜压实,想再多装一些菜。当有花再次把刀伸向一棵茎叶肥大的苣荬菜时,一只粗大的脚将刀和菜同时踩在了脚下,深草没棵的庄稼地,突然冒出一只大男人的脚,有花一个仰八叉倒在地上,心扑腾腾地狂跳起来。水生俯下身欲扶起有花,有花一看是水生,一使劲将水生推了个仰面朝天,你个死鬼,吓死人了。
水生将一沓钱递到有花面前,说,我有钱了。有花看看水生,又看看水生手里的钱,眼圈一红,说,现在有钱有啥用,要是你早先就有钱,要是你早先像现在这样有出息!水生的脸腾地红了,像个熟透了的樱桃。他近乎嚎叫着说,要不是钟老算那个老家伙,你早就是我的人了,告诉你,你迟早还是我的人,我早晚也会把你算计到我手里。有花嘴角向下一撇,想得美。其实有花说这话时心里甜滋滋的,她盼天盼地就盼水生有一天能发达起来,可是她偏要和他水生别个劲。见有花还是有点瞧不起他,水生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有花见水生这样,坐起身拍拍身上的土,挎上篮子要走,但还没容她起身,水生的身体就死死地压在有花身上。你是我的人,我是第一个要你身子的人,我要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在水生颤抖的声音和强有力的律动中,有花在甜蜜的挣扎中流下了甜蜜的泪水。这样的事情先后又发生了几次,每次水生都扔给有花一沓钱,有花也毫不客气地揣在怀里。她把水生给她的钱缝在枕头里,她打算等攒够八千块钱后,就把钱还给得财。
榆树屯的人都不大理解,先前那个庄稼不庄稼、买卖不买卖的水生,那个奸懒馋滑、二溜八蛋的家伙居然发达了。的确,和屯子里那些日子过得挺紧巴的庄稼人比,水生是发达了。现在的水生整天满面红光,精气神十足,加上原本就不错的长相,这人就显得更加精神了。水生的发达和马有关,和得财不同的是,得财靠配马营生,他水生靠贩马生活。不过他有时候也能用得着得财,因为他贩的马用得着得财家的种马。这小子脑瓜活泛,他贩的马开始还是一匹,在家养一段时间,再到市场上卖的时候就可以顶两个卖了,因为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呢,这怀上驹的马自然就值钱了。
水生发达了,得财心里就不舒坦,尤其是水生牵着骒马到他家找种马时有花瞅水生的眼神,他更不愿意看水生抱着腊梅又亲又咬,还一个劲地叫闺女的样子。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一声不响地在旁边干活,只是手劲比平常重,动静比平时大,可水生这小子倒耍起了赖,叫闺女叫得更加响亮了,好像故意与他得财做对似的。
也不知道水生手法咋那么高,不管多老的马,到他手用不了多久都能让马发情。后来才听说,水生也不知道是给马打了一种什么药,可能是春药吧,只要马一打上药就能发情,只要发了情,怀上驹,这马就增值了,水生就靠这发达的。得财打心眼里瞧不上水生的这歪点子,正经人不会干这歪歪事。
这天,水生又牵来一匹青灰色的马。这马牙口不老,水生咋呼着说,这匹马怀上驹以后保证能卖上好价。那匹马一见得财家种马,主动凑上前去。得财心里骂道,和你家主人一样不是啥好东西,骚货!见到这样主动进攻的马,得财家的马今天倒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虽然两只前蹄搭在青灰马的背上,身上的阳物却耷了个弯。得财心里骂道,熊蛋包!他走近两匹马中间伸手要帮助他家的种马,得财手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那匹青灰马一声尖叫,一个蹶子尥上了天,得财腾空的身体还没落到地下,青灰马便一溜烟地跑没影了。
人们在慌乱中把得财抬上马车,得财的身下淌了一摊血。
有花抱着腊梅吓傻了眼,等人们走了以后她才回过神来。这事说出就出了!发情的母马一般都很温顺,今天的马咋这么烈性呢!得财咋样了,不会死吧?有花盼望着大伯哥得旺和水生他们快些从县里传回信来。
得财醒来的时候,手术已经做完了。他下身的两个蛋蛋被摘除了,与其说是医生摘除的,不如说是马摘除的。得财知道自己两个宝贝蛋蛋被摘除后,眼珠子通红,瞪着一旁的水生,眼里充满了仇恨。如果不是给你配马能出这么大的事?水生耷拉着脑袋不敢看得财,好像得财的两个蛋蛋是他水生踢飞的。
一个男人一旦失去了男性功能,那将是一个雄性的最大悲哀和耻辱。得财对大哥得旺和水生说,他的事不能告诉屯里任何人。一个月后,得财出院了,到家的时候,有花都不敢认了,一个膀大腰圆的大男人,瘦了一大圈,颧骨高高的,本来就很长的下巴显得更长了。
得财被马踢的事经了官。其实说经官和私了不差模样。因为,这官是村长于得水。于村长眨巴着眼睛,端着架,问得财,水生配马收费不?得财说,收费。村长说,既然收费,这收费和义务就是不一样。你想啊,你家的马,怎么说呢,你家的马配了人家的马是收费的,就应该尽收费的义务,水生就没啥责任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水生是没责任了,可是他家的马踢了你,他家的马有责任,这马又是水生家的,这又和水生有点关系,所以水生又逃不掉干系。村长眨巴着眼睛看看得财又看看水生。我看这样吧,这事要全呼在得财身上,得财也挺冤的,要是全呼在水生身上,水生也怪冤的,你既然收了人家的费用,人家责任就小一些,你们花的七千元药费,我看得财承担四千块,水生承担三千块。村长说完眨巴着眼睛,左看看得财,右看看水生,又转过身看看村里其他两个支委。支委黄柱说,我看中。得财觉得村长处理得很公平。就答应说,行。水生说,要承担全部责任,一切费用他一个人包了。他回家取了七千块钱,放到得财家炕上。得财从里面抽出四千块,把多余的啪的一下摔在水生怀里。得财颤抖着声音说,我的损失钱赔不了。
得财被马踢了以后,水生感觉好像亏欠得财什么似的。得财家的大事小情他都要尽力帮忙,自然也就成了得财家的常客,尽管水生知道得财打心里往外反感他。有花也觉得纳闷儿,自打得财从医院回来之后,那方面很强烈的得财,再没和她有过那事。她从得财阴沉沉的脸色上看出点门道儿,得财的身体定是出了点问题。当水生再一次把一沓钱塞到她手里时,她才知道得财的那个东西彻底作废了。
得财不说,有花便装作不知道,只不过她和水生的亲热次数更勤了,她把和得财做的次数都给了水生。有花攒的钱已经超过八千块了,可有花一时不知道怎么还给得财。
有花和水生的事露陷了。当她和水生光着屁股在谷地里翻江倒海地尽情折腾的时候,被屯子里几个挖苣荬菜的妇女看到了。这几个妇女又偏偏都是
长舌妇,也不知道是昨传的,人们都说得财那东西被马踢废了。有几个好事的男人问得财是不是真的废了。得财叫来得旺和水生,质问是谁传出去的,把得旺和水生都说懵了。
一天,得财早起喂马,看到他家的木栅栏上挂着几支露了底儿的鞋。得财摘下几个破鞋头,正在做早饭的有花看到问得财,拿那几个又脏又破的鞋头干啥?得财脸色铁青地回答,别人给咱家挂的!
有人提醒得财,没事的时候常到谷地里瞧瞧,别让外人把自己家的谷子偷了。得财觉得这些人都是话中有话,他把这些话和那些破鞋头联系起来,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破鞋头和他家谷地有啥联系。不过得财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这破鞋还是这谷地都一定和水生有联系。
得财的脾气变得暴躁起来,有花知道得财的脾气为啥这样,都是那几只破鞋闹的。一个男人一旦失去那方面功能,又被人戴上绿帽子,那是很窝囊的事,所以有花也不敢惹得财。有花越是躲躲闪闪,得财心里就越憋屈,也就越肯定有花和水生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越是自卑的男人,心思就越细密。得财整天琢磨有花和水生的关系,他甚至联系到女儿腊梅,没想到这一联系还真的联系出了问题。他算起了账,他和有花是前年农历四月结的婚,到十二月生了腊梅,从表面上看,外人是看不出什么破绽的,可再算他接近两个月没沾有花的边,这样算时间就对不上号了,腊梅提前出世近两个月,这说明有花在和他结婚前就有事了。得财抱着女儿腊梅,他越看这孩子越不像他,这鼻子眼睛哪儿都能在水生脸上找到印痕。得财对着女儿自言自语,你是谁的,你究竟是谁的?有花看得财这个样子,她不敢和得财吵架,她知道一切都要露陷了,她有花本来就有问题,她没有资格和人家吵架。得财斜着眼睛看有花,他真想狠狠地揍有花一顿,从他摘下那几个破鞋那时候起,他就想暴打她一顿,可是他对这个女人真的下不了手。得财恨自己是窝囊废。
有花感觉得财变化很大,前几天看她的时候眼睛里还充满凶光,现在他的眼睛里好像是空的,除了喝酒,再就是倒头大睡,再不就是一个劲地干活,一刻也不歇息。这让有花很担心,担心会生出别的事端来。有花告诉水生,得财这阵子有点不正常,要他少到家里来,水生蹭了一下鼻子,说,他已经成了太监,怎么能和正常人比。有花用眼睛横了一眼水生,水生一缩脖不言语了。其实有花在心里感觉真有点对不起得财,得财除了长得丑点,人家不欠她有花啥,虽然自己是被他老爹算计到他家的,可与人家得财有啥关系!
水生这几天也用眼睛瞄着得财,他发现得财除了在家喝大酒外就是到外面干活,酒喝得大,活干得也狠,好像要吃掉谁似的,让人觉得这活干得有点疹得慌。这天,水生趁得财到外面遛马的空溜进得财家,看有花正做晚饭,水生从后面一把抱住有花。有花说,孩子在屋里呢,有点正形。水生说,我们都有一个闺女了,我还想要个小子。有花瞪着眼睛说,瞎说啥,上哪儿给你要小子去?水生说,有地方要啊,到你家谷地里去要啊!水生还接着要往下说的时候,他看见有花脸上的光线一暗,有花的表情也被这暗光定格了。水生一回头,见高大的得财堵在门口,水生张着大嘴矗在了那儿,直到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才醒过神,一溜烟地逃了出去。得财凶狠的目光中还带有些许的嘲笑意味,他死死地盯着水生远去的背影。待他转过身,举起手臂要砸向有花的时候,看到乖巧的女儿腊梅正在惊恐地看着他,他一把将腊梅紧紧地抱在怀里。
有花今天显得格外听话,一声不响的,得财让她烫壶酒,她便烫了一壶酒,还加了两个菜,然后坐在一旁看着得财喝酒,直到看得眼皮有些发硬。得财发话:“睡觉。”她便听话地给腊梅脱了衣服钻进被窝,不过她的眼睛还是偷偷地瞄着得财,他不知道得财今天会有啥举动。得财喝完最后一滴酒后,啪地将酒壶摔了个粉粹,吓得有花打了个哆嗦。腊梅也瞪着大眼睛看着得财,她也觉得她爸爸今天的样子很吓人。有花眼看着得财披了件上衣出了屋,她不敢阻拦。
十五的月亮格外地明亮,得财瘦长的人影在夜色的笼罩下显得很孤单。他手里握着一把镰刀,慢慢行走到田间小径上,露水打湿了裤角,却没有丝毫的感觉。当那片在夜风中轻轻摇曳的谷子进入得财视线的时候,得财好像受了刺激,他浑身的热血沸腾了。他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挥舞着镰刀冲向谷地,一片刚刚抽穗的谷子被他撂倒在脚下。
当气急了的得旺一脚将他踹倒在地,他才知道大哥误会他了!他的心是苦的,因为这苦闷无法向亲人表达,他觉得心里憋屈。得旺的一顿臭骂,将他的苦闷推到极点,却无处排解,最终,一阵疹人的嚎啕将他送到屯中的那眼老井旁。
榆树屯原来有五眼老井,得财死了以后就剩下最后一眼了。
人不嫌其他动物脏,却嗝应相同属性的人。这老井里不管是掉进鸡,还是掉进鸭,也不管鸡鸭是有意,还是无心,淘净了照样可以洗衣做饭;可是掉进人就不一样了,也不管是瞎子掉井,还是睁眼跳井,这井的命也跟着人的命一起走了。八
屯子里的人都说得财是被鬼抓走的,因为得财死的那天是七月十五,鬼节。
得财出殡那天,水生吹了丧调,这次他吹对了调。不过先前吹反调的时候,他的心情则和现在截然相反,今天虽然吹的是丧调,可他心里吹的却是喜调。得旺喷火似的眼睛恨不得将水生烧死,媳妇桂兰说起话来指桑骂槐,句句带刺。
得财死了,有花感到心里空落落的,有花现在才感受到,得财这个男人虽然不言不语的,却给她一种安全感。水生以为得财死了,他的机会就多了,没想到却遭到有花的抵触,有花义正辞严地告诫水生,在戴重孝期间别想碰她的身子。水生说,要娶她做老婆,有花说,要想娶她做老婆得等她三年。碰了一鼻子灰的水生心里不服气,得财活着的时候,他想要她,只要有机会她就会把身子给他,现在倒好,机会多了,她却不给了,难道他一个活人还干不过一个死人?
这天晚上,水生喝了半壶老烧之后,趁着夜色摸到有花家,他在有花家窗户下蹲坑,等有花哄睡腊梅脱衣关灯后,他摸着黑脱得只剩下个裤头,悄悄地爬到了有花的炕上。还没等他钻进有花的被窝,就听一个女人大声叫喊,快捉奸啊,有人养汉了!一听那破盆子似的声音就知道是得旺媳妇桂兰的喊声。水生来不急穿衣服想夺门而出,却被手拿棒子的得旺封住了门。喀嚓灯亮了,光着身子的水生惊恐地站在屋地上。坐在炕上的有花被眼前的一幕吓懵了,得旺手起棒落把水生打晕在地,地上淌了一摊血。得旺已经瞄水生半个月了,今天可逮住一个机会,他哪会错过,他早就想收拾这小子一顿,为死去的弟弟出口气。
屯里的人喜欢热闹,半个屯的人都挤在有花家的小院里,有人报告村长,说得财家出了人命。村长老于一边穿衣服一边叨唠,这女人一跑骚非出事不可。村长让人拿凉水把水生激醒,从外屋拎来衣服让水生穿上,别光着身子现眼。水生耷拉着脑袋坐在长条凳子上。有花怀里抱着腊梅,满眼泪花地看着村长。村长眨巴眨巴眼睛,昨啦,冤枉啦?身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