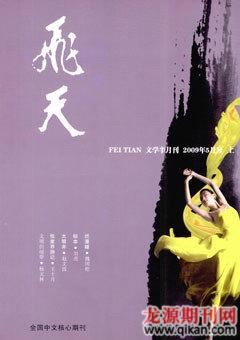农民啊农民
宗满德
现在农村有三难:看病难、养老难、上学难。村主任李育俊这样说。
村主任李育俊还是个村医。
我们农民基本上是小病养大,大病等死,没着。在我的卫生所来看的都是头疼脑热,都是村子里的人。一年能卖出去一万块钱的药,平均每天有三个病人,一年大概一千人(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病人要欠账,蛇蜕皮,年年看,年年要。如果不欠账,没有人会来看病,卫生所肯定要关门的。我行医二十多年了,有一些药钱永远都要不上,也没有打算要。明知道要不回,就算是积善成德,干一些善亭吧。正常情况下,村子里每年都要死掉二十来个人。这几年人口不净增,死亡与出生、婚嫁持平。村里的杨吉泉,五十六岁,患胃溃疡,没有钱治疗,在家里蹲着挨痛,死掉了。“五保户”张登祖,六十七岁,患肺心病,没办法,一次次地买安眠药,凑多了,全喝下去,睡在弟弟的热炕上,再也没有醒过来。汉永武,六十二岁,患慢性病,经常疼,没有医治,死掉了。许多老人都这样耽搁掉了。一个“老病”的理由就把一个活人推到死路上去了。活人一场啊,农民的命真是太苦了。许多老人长期患病,叫我去看一看。子女们只让看一看,不说买药的话,只问这个“老病”怎么办哩。我也只好忍着心痛说。这个“老病”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慢慢在家里养着,走着看呗。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天天遇着的都是这样的一些人。年轻人身强体壮,小病一抗就过去了,耽误致死的少。月子娃耽误掉的多。穷讲究,没有满月不能出门。有病了,就在家里烧香磕头地折腾。叫我去看,常常都是奄奄一息,没治了。妇女生孩子也有耽误掉的。农民都不去医院生,就在自己家里生。生得顺利,大人、小孩都平安。生得不顺利,不是要大人的命,就是丢小孩,还有大人小孩都保不住的。这主要是缺钱。去不了医院。生了病,住不起医院,吃不起药,这是农民最伤心的事。
困难户把维中,与哑巴弟弟两个人过活。五十多岁了。那天说,我大半辈子没有吃过药,今年腰腿疼得很,快要命了。就去村卫生所买了些治疼药,花掉了五块钱,心疼得了不得。我这一年给卫生所帮了五块钱啊。五块钱,真不够一些人吸一根香烟,不够城里的孩子吃一口零食,不够一些人打一次电话说几句闲话,而一个农民竟把它看得比五十多年的生命还珍贵。这是何等的哀痛啊!
王国龙。三十四岁。光棍。张秀,其母,六十岁。母子相依为命。我走进这个家的时候,母子俩正在抹眼泪。
张秀说,我耕种五亩水地。种小麦两亩,收一千四百斤;蚕豆两亩,卖五百多块钱。还有一亩没有平整,不能耕种。养猪一头,鸡六只。这五间房子是他舅帮着盖起来的。国龙三四年前患病,慢慢地不能下地干活,守在家里。在省城的一家大医院检查,说是脊髓病交,治疗花掉了六千块。病情有了好转,医生说还得交六千块作押金,继续治疗,就有希望治好。没办法只得出了院,吃些中药维持。不知道还有没有办法再去住院治疗。唉,真是难死人了。如果我上吊,有人给这么多的钱。我巴不得上吊哩。这钱不是树上的叶子。说摘就能摘下来。预备着把这房子卖掉,再把猪和鸡卖掉,看能不能把娃的病治好。这娃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把年纪了,还怎么过呢?要是娃前头走了,我就跟在后头呢,还有啥办法呢?亲戚庄邻的钱,都借遍了。至今一分都没有还上,娃的病不见一点好转。再张口去借,连人家的脸都不敢看哪。信用社已贷过一次款,没有还上。人家天天催着叫还上哩,现在连信用社的门前都不敢去呀。这里张家的放贷,虽是一分的利息,也不给我们这样的人家借一分钱。明摆着,你拿啥东西还账呢?我这命,咋这么苦啊。娃他爹死得早,也是没有钱的祸害。有钱医一医,或许就不那么年轻地早早死了。过啥日子呢?眼看着连命都保不住了。老天也没有长个眼睛看一看,把我这把老骨头收走,换个我娃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不行吗?
张秀声泪俱下。王国龙躺在土炕上,望着天花板,不说一句话,眼眶里噙满了泪花,闪闪的,闪闪的,终于止不住滚下来,顺着两颊往下流,泪痕像两条蠕动的腿,扭曲着苦难的影子。
时间正是中午。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一个大姑娘,赤身裸体,披头散发,脸色惨白,眼光呆滞,神情像冬天的铁一样冰冷。其时正站在一间低矮的草房里。这屋子窗户洞开,木门紧锁。土炕上连一根草都没有,也如这姑娘,赤裸而冰凉。据说,这姑娘从小就患了病,没有得到有效的医治,后来神经失常,渐渐地没有了人样的。
老支书说,这些人把人间的罪受完了,正积攒着阳光,预备着到阴间去把黑暗照亮。窃取人间的光把阴间的黑暗照亮,这句话像一把锐利的锥子刺破了正午的阳光。
最大的麻烦是生病。老支书王生荣摸着自己的腿子说。
我这腿和腰疼了好多年了,现在坐下去站不起来,站起来坐不下去,没有办法,眼看着要命呢。医生说可以治疗,要么住院,要么吃一些中药,也能奏效。哪来的钱住院吃药呢?就这样挨着吧,活过一天算一天,一甲子的人了,够本哩。吃不起药,疼得起病哩。庄稼人就这么活着。没病就是干活,有病躺不倒还得干活,躺倒了再说。小病挨着,大病抗着,实在抗争不过去了,找村医看一看。村医说这病闹大了,才想些办法去大一些的医院诊断。往往是没进医院门就知道自己不行了。病到晚期,像秋霜打过的树叶子,熬不了几个日子。村子里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们浑身都是病。常常是自己觉着啥地方疼,就去卫生所随便买些药片片子吃。不逼急了,没有人去县医院检查。就是去了,也不肯按医生的要求查,还怕查出大病来。偶尔有送医下乡的来了,人们光去检查都不买药,说:“唉,我就这个病。”
人口学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村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比例将达到百分之十四至十七点七。在农村,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八十,但是收入来源和生活料理依靠老人自己的比例分别超过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八十。现在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一般是四口之家,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弱化,外出打工者、迁移者大多数又是青壮年。
李育俊说,现在最大的忧愁是养老。全村三百六十户一千六百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八十多人。村里的老年人,只要还能劳动,都是自己种田,自己养活自己。俗话说,养儿防老。可现在年轻人都跑到城市里打工挣钱去了,留下老人,给他们种粮食吃,还要替他们带孩子。老人们都是庄稼地里的铁汉,儿女们的长工。到了哪一天真的干不动了,躺倒了,就回老家,永远地养老去了啊。老人老了,儿子接续;儿子老了,孙子接续,走的都是一条路径。现在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民帮助很大,但大病还是得不起,大多数的农民患者“小病磨,大病拖”。生老病死是人一生中最基本的生活风险,衣食住行是人必不可少的生活需要。农民本就是公民,也应当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养老、医疗、生活等方面的帮助和待遇。可现在城乡二元
差别很大。乡村的天更蓝,乡村的水更绿,但我们在脚下的土地上却写不出一个大写的人字。我们农民咬着牙关,挥汗如雨。我们农民患上了贫血病,哮喘,乏力。我们农民是老百姓,是黎民,多么希望成为堂堂正正的国民,能够站起来走路,能够横着站立。我们多么希望自己说话的声音能够传扬出去,能够有人听得见,不要叫城市里大街上的声浪淹没掉。我们多么希望自己首先是个人,是个活着是为了更好地活着的人。我们多么希望自己合法的土地、自己的正当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我们农民当了几千年的牛马,做了几千年的子民,现在的第一需要是想做一个会说话、会走路、会活着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农民病倒,这个社会就会抽搐。为着全社会的健康成长,不能让我们农民病倒!
农民现在最大的负担是娶媳妇。李育俊说。
孩子长大了,首先要盖新房子。我的九间房子是2004年盖起来的,当时花了六万多块。去年装修买家具又花了两万块,一共是八万多块钱。这几间房子把我多少年的辛苦都搭进去了。要是遇上今年这个物价,光盖房子就得八万块钱呢。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要盖这样的九间房子得打凑二十年啊。给儿子娶媳妇花了三万多块钱,还算是便宜的。送干礼七千块,买“三金”(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花了一万块,买衣服花了七千块,平时跑来跑去花掉了六千块。现在一般都要送“三金一拖”,就是外加一辆拖拉机。我送的算是少的呀。办婚礼招待亲戚朋友花了一万四千块,收礼钱也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字,掼了个平跤。人情嘛,有来有往。主要是买肉、买菜、买烟酒。烟是三块五毛钱的兰州烟,酒是一瓶子十五块钱。我开过二十年的车,儿子开了八年的车,都是给老板们跑运输,挣了些钱,凑下来就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现在手里连一分钱都没有了。农村的各种人情费也不少。礼钱是硬的,少不得。俗话说,人情不是债,便把锅来卖。娶儿嫁女,结婚一般都是三十到五十块,贺寿也是这样。娃娃满月,小孩子百天剃头,学生毕业,盖新房、建新门,买拖拉机、摩托车,这些事都要去祝贺,一般都在二三十块上。过年了,走走亲戚,礼品也是不能少的。这几年来,人们越来越讲究排场了,人情也越来越重了,人情消费越来越高了。过去主要是“红白事”,现在又添了生日、满月、升学、修房、开业、结干亲,名目多得很。每户每年人情费起码上千元。往往拿彩礼的厚薄和办喜事的排场来看女方的身价,评判男方的贫富,拿客人的多少来衡量家庭的社会地位。村里的人们过一个事情,都要讲究这个。
“每学期的学费就像父母的紧箍咒。”这句话是一个叫李长彩的中学生说的。另一个叫张正强的中学生说:“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家里卖掉了唯一值钱的一头耕牛。有多少次家里都是把买农药的钱拿出来让我去上学的。高三第二学期实在没有办法,家里卖掉了准备过年的猪。自从我和弟弟开始上学,家里过年就没有杀过一头猪的。”
傍晚,我一路打听着走进老丁家。
院子里长着一棵杏树,一人多高,杏子已经摘光了。树下用砖头搭了一个鸡窝。北面是六间低矮的土坯房,老丁说是1982年盖的。东面是五间虎包头的堂屋,没有粉刷,也没有门窗,用塑料封起来,还没有使用。老丁说是2000年亲戚们帮助盖起来的。坐在院子里的一个小木凳上,我和老丁聊家常。老丁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始终噙着泪花。
我是1956年生的,老婆小我一岁,是个壮劳力。两个儿子,老大叫丁文元,老二叫丁文旦。争气得很,今年都考上了大学,一个是兰州理工大学,一个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按理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可我高兴不起来,这几天背着两个孩子淌眼泪。是我这个当爹的没有本事,还是命运不济呢?两个儿子入学就得16000元,我怎么也搭凑不齐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亲戚朋友借遍了,给政府该张的口也张了,使尽浑身解数,才凑了11700元。眼看着报到日期就到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在1983年得了坐骨神经病,又是腰椎间盘突出,什么重活都干不成。住过一次医院。22天就将就着出院了。老病没好又添新病,这几年高血压病折磨得简直活不下去。现在就这么在家里养着,干不成体力活,挣不上钱,每天还要吃降压药和丹参片。我是电工,这活我也能干,可人家看我病兮兮的,谁也不要我干的。自己干,又没有设备,干瞪眼没办法。一年挣不上几个钱,脚下的窟窿越来越大。家里全靠老婆子硬撑着。去年她在附近建筑工地上干活,架杆塌下来差一点砸死,现在是脑震荡后遗症,也干不成重活了。哎,包工头撒手不管了,一盒脑震宁30元,就吃一个星期,买不起啊,不吃又不行,头疼得要命。她的药主要是娘家的亲戚给买的。去年,外父跑到学校去叫小儿子停学打工哩,差一点断送了儿子的前程。这过的是啥日子,说不成啊。
家里一年得搅6000元钱。两个儿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就得5000元。在学校他俩老吃的是从家里带去的饼子,一天上一次灶,大概花两块钱吧。回到家里自己动手,大的做饭,小的烧火。两个儿子从上初中开始就没有做过新衣服,穿的都是校服和亲戚们送的一些旧衣服。现在要上大学了,给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总共花了150元。初中三年,没有骑过自行车,十里路,他俩走来走去。到县城上高中就坐班车。星期天轮流回家取馍。新华书店是他们的第二课堂,买不起书,每周星期天都跑去看哪。
家里种6.5亩地,细算起来没有多少收入。1.6亩小麦收了1200斤,还不够一家人的口粮呢。0.8亩玉米收了800斤,添补着吃。0.3亩高粱能扎100把笤帚,估计能卖150元。2.5亩胡麻收了800斤,能卖1000多元,这就是拿到手里的钱了。1.3亩地浇不上水,荒了。丁文旦要去报到,杀了两只鸡,买了三块钱的波菜、蘑菇和粉条,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火锅,算是送行吧。还有一只公鸡,等丁文元要走的时候再杀,留下四只母鸡还要下蛋哩。艰难得很哪,比如长征,现在正过草地。想一想艰难的日子怎么过去哩,半夜里做梦都爬坡呢。谁要我的这五间房子,我就卖掉渡难关。往后的日子不敢想啊。
老丁噙在眼里的泪花打转儿,始终没有掉下来。
村主任李育俊说,学生供不起。初中在附近的乡中学上,孩子们都能毕业。高中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去上,一学期各种费用得三千块,就没有办法了。全村现有高中生八名,只有一个女生。主要是缺钱。手中有钱。心里不慌,谁不想把自己的孩子供成个大学生呀。我们这个村从恢复高考以来,考出去六个大学生,二十六个中专生,现在一年比一年少了,都是钱惹的祸。都想念,都想供;都念不起,都供不起。咋办呢?靠出卖苦力,农民越来越穷了,农村越来越凋敝了。俗话说,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人误人呢,究竟是什么恶果?这个责任谁来负,这个损失谁来补呢?看着自己的孩子被耽误而心
是改种百合亏了血本;再种板兰根长成了蒿子一样的草,拔出来扔了;今年又种了党参,不知能不能长成。长成了,能卖成钱卖不成呢?去年种的柴胡卖不出去,干柴一样,一捆一捆地扔着。这地不种不成,种了又亏本,光种小麦连地都养不活。这几年折腾来折腾去,也不知道种啥好。种了半辈子地,越种越不会种了。这庄稼汉咋当?种不成地就到城里找活干。没有啥手艺,卖力气,出苦力,干些粗活笨活。哪里盖好了新楼,就往哪里跑。住新楼的人都讲究装修,我把沙子、水泥、石头背上去,把垃圾背下来,投入的是力气,收回的是现钱。本钱就是力气。不怕苦,不怕流汗,一年也能收入五六千块钱。这七八年下来,我干的就是这苦力活。三个娃上学逼人哩。大姑娘上了一年高中就不愿意念了,我在心里头说谢天谢地。不供是我的责任,不念是她的问题。十七八岁的娃娃,啥道理都懂哩。两个娃还上高中,一年下来也得五六千块,不出来挣点钱能行吗?还好,大姑娘也在城里头打工,一年也能帮凑一些,这日子也能过得去哩。我文化浅薄,只念了个小学。兄弟姐妹六个,就老大念成了,现在当老师,日子过得滋润得很哩。老汉们供不起,我也没办法。我给娃们说,宁肯牛挣死,也不叫车翻掉。我下狠劲供他们上学,念不成也就不落抱怨了。现在这社会,念不好书尽受笨苦,还怕受不进去哩。这几年城里的变化可大了,新楼一栋一栋地盖起来了,马路也越修越宽了。我一年四季跟着新楼走,把这么大的城市都走熟了。可城里的行情变化也快,钱贵了。三年前一天挣个百八十块,松活着哩。这两三年挣钱不容易,筋都压断哩。以前背一袋水泥上楼给五块,现在连三块都不给。一天要挣百八十块,上下不放空,七八层楼要跑上七八十趟哩。遇上高温天气,汗都淌干哩。我们这号人,看起来瘦得很,素质好,一年四季不生个病,只要有活干就行。感冒头疼不算个病,干一天活,出几身臭汗,就好了。给城里人说不相信,还说是拿生命做赌注,胡整哩。庄稼人得不起病。去年老伴阑尾炎做手术,就一个星期的时间,花掉了我两千多块钱,你知道我要在这七八层楼上跑上跑下得多少天吗?心疼啊,没有办法。我们这号人吃的住的穿的,跟城里人根本没法比。一天下来连吃带住十块钱。四个人租住一间房,每月租金八十块,摊到人头上也就是每天七毛钱。吃什么?早上两碗开水,几个馒头,有时吃几根油条,中午一碗牛肉面,晚上一碗四块钱的炒面片。夏天口爱渴,吃个西瓜。喝个啤酒,一天加上两块钱。冬天电褥子取暖,一晚上用一度电五毛钱。天太热了,早起早干。午后的太阳毒得很,晒得人淌油哩。楼上楼下背一天的东西,晚上睡倒在干板床上,热汗渗进骨头里去了,腰腿生疼生疼。眼皮子都被汗水泡得板结了,瞌睡醒了,眼睛睁不开。冬天的活还是好干些。天冷地冻寒气重,少出些汗身子骨也松泛些。穿什么?买一件新衣要七八十块钱,得过七八个年哩。干活穿的衣服,东家给啥穿啥,穿烂了扔掉。七八年了,没有买过新衣服,也没有必要买。穿着不讲究,不露肉不现眼丢丑就行了。几年下来,总觉得外头跑比守在家里种地划算,不偷不抢干些出力气的活,供娃娃们上学,买些化肥种地增些收入,家里有几个零钱花,过个平淡日子。一年下来呆在家里的日子累起来也没有两个月。春天回去几天。种个地。夏天收麦子打碾犁地加起来一个月,过年回去蹲上七八天就出山。一年里照不到几个影子,老伴也埋怨。欠人家的钱得想办法还,这是常理。欠家里人的情没办法还,跟谁说去,成苦往肚子里咽。吃饭要紧,娃念书要紧,这才是人生的大事。守在家里没有钱花的日子更难受。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心里空得很,像悬在半天上,根本没有家的感觉。那些男青年换女朋友就像换工作一样。女孩子们干不动重活粗活,都往歌厅酒吧里去揽活,干着一些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有的连自己的贞洁都当钱卖了,还落下一身病。
小曾姑娘,今年刚三十岁,在省城打工。家里有五口人。
母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姐姐是个裁缝,妹妹正在上初中。我初中毕业后,跟着村里的一群姑娘南下深圳。在一家机械厂做工,干了半年,觉得钱不是好挣的。回家后,跟着姐姐学裁缝,又是半年,也没有干到底。去年和村里的一些姑娘结伴来到城里,在歌厅打工。一家歌厅一家歌厅地跑,跑了十几家,都干十几天或一个月。在这家歌厅干了三个多月。干这个活的,都是白天睡觉,夜里上班。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多开始,十二点以后大概就能够下班了。出台,客人每次付一百元,四六分成,我们得大头,老板得小头。不出台一点收入也没有。住房自己租,吃饭自己管。啥叫平台,其实呀就是陪客人聊天、喝酒、唱歌、跳舞。其他都好办,就是喝酒很麻烦,很讨厌,很痛苦的。不喝不行,客人不高兴,老板找麻烦数落,或者干脆一句话就得走人。天天喝呀,啤酒。红酒,白酒。喝醉了就睡呗。反正日子就这么过着。上这班,大家都这样。这个歌厅,平常上班的有二十多个姑娘。来歌厅里唱歌跳舞的,大多数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单看一看他们的穿着就知道。面子上正经得很,其实都俗得很哪。喝上几杯酒。什么都丢掉了。有时候想一想,痛苦得很呐,怎么在这种地方上班?天底下受苦遭罪的总是乡下人。太阳哪辈子能照到我们的头上?我们盼望着像城里的姑娘那样上班,那样挣工资。这该是多么好的一桩事啊!
我们跑到城市里来打工的,是特殊的农民,特殊的群体。旧城在我们的血汗与泪水中消失,新城市里我们是居无定所的游魂。我们睁大眼睛看着花花绿绿的世界,没人哭,也流不出一滴眼泪。我们在心里呻吟,哀鸣。在闪烁的霓虹灯下,在繁忙的车流和嘈杂的人流中,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呼叫、呐喊。
有资料显示,2007年全国农民工达到2.26亿。农民打工已由当初少量外出谋生演变为经济发展新模式,并且正在成为改变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角色。有人这样算账,一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是25000元,而他充其量才拿走8000元,剩余的都留给了城市。如果一个城市一年有100万农民工务工,它从农民工身上拿走了多少?这是一个令人产生诸多感叹的数字!二十多年前的东莞,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人口不过百万。如今,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国际制造业基地,仅外来农民工就超过六百万人。当地官员不无感慨地说:“没有民工,东莞的现代化建设不可想象。”农民工既是城里入,又是乡下人。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带着农村的文化价值,又不得不面对与之对立的城市文化。作为农民工,进城后想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得最大地融入城市,实现由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社会文化心理适应过程。由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农民工根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找到归宿。绝大多数农民工也没有打算以后留在城市生活。歧视与偏见常常使他们感到无比地失落,他们的闲暇时间无聊乏味,业
余生活主要是聊天、打牌、喝酒、看电视。大多数人的文化支出是零,文化生活基本上是空白。城市好像一个双面人,既热情地接纳着农民工,又冷漠地拒绝着农民工。农民工的处境就像用一支筷子吃饭。饭菜或许很丰盛很香,手中仅有的一支筷子却很难将可口的饭菜送进口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都要上涨百分之十。对于不计算成本、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农村仍有超过一亿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打工者的低工资使进城农民无法支付定居成本,绝大多数仍然是流动的劳动力。打工是一座桥,农民工在两头晃荡。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民对子女受教育的预期越来越差,最终直接影响农民子女的成长和素质。现行的收入再分配体制没有为农民及其子女提供与城市居民公平竞争的一个平等起点。农村在丰富、廉价的剩余劳动力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廉价的土地。国内外工商金融资本以低廉的成本获取农村土地资源,转而变为非农用地之后,获取超额利润,直接侵害农民利益。农村信贷政策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地区的产值基本上一直占取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河山,但获取的银行金融支持却始终没有超过七分之一。相反,农村信用社的大量资金却流入城市,农民很难从信用社得到贷款。现在农村金融网点的大量减少,使农民无端地增加了获得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民间借贷的活跃又使农民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最为严重的是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使农民继续受到歧视性非国民待遇,使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进一步下降。农村地方政府巨大的支出压力,事权大而财权小的农村财政分配机制,所有的大盖帽都向农民伸手。凡此种种,都像一条绳索绑在农民身上,都把有形无形的手,伸进农民的腰包。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制度。像一堵又一堵高墙,堵在农民的眼前;像一道又一道紧闭的门,立在农民的脚下。农民出卖土地,出租力气,希望能够转换身份,转变角色,带来幸福,但往往成为“无产者”,像失掉了根的草木,随水漂流,成为城市的“打工者”。既失掉了“农民”,又变不成“居民”,一大批精神上价值上已经与土地与村落割断联系、又注定在城市找不到职业与位置的现代流民,正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路上打工,为自己,为乡村,为城市;在城乡之间徘徊,身也犹疑,心也犹疑。
黑夜的尽头是白天,白天完了又是黑夜。农民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黑夜里点亮了灯,煤油灯,柴火灯,电灯;白天里闪烁着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厚重的土地,反衬着浓重的阴影。光阴正好,路正长。农民前行的步履坚实而沉重,充满坚毅和永恒的力。
“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走?”土地,农业,农村,农民,这是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面临的世纪大课题。怎样破解这道难题,正决定着农村发展的大趋势和社会的基本走向。
农民啊,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