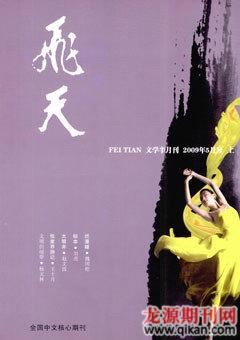坐街
张金彤
早上八点半,胡世荣就到世纪商厦大门左侧的一处空地上坐街。这个时候,街上除过上班族以外,基本没有什么闲人,他只能胳肢窝里夹着喇叭,坐在一只马扎上袖着手望着匆匆忙忙的上班族发呆。面前放着一只有几处豁口的破瓷碗,旁边放着一只纯净水瓶子。瓶子里装着他从自来水管里接的水,看起来并不怎么纯净,甚至有点混浊。从表面上看,老胡正在发呆,眼睛盯着东大街的远处望着,好长时间都不转动一下身子和头。其实,他是在等一个人,一个女人。
老胡在这里至少可以说坐了十年的街。这十年中,他天天基本上进行的都是一个程序,一个动作,一个过程,他八点半准时到达。他并没有手表或者手机之类可供参照的东西,他完全凭自己的感觉,他的感觉可以说基本上准确。他曾经证实过他的感觉,因为大街上的喇叭,是不会有丝毫误差的,他从他的住处往商厦走,大约需要十分钟,他来到这里,放下小马扎。小马扎是活动的,能撑开合住,放下之后,他要用手仔细地检查一下,看是否稳当,要是放下不稳当,他坐上去就会摔个背摔子,这样的话,可不得了。然后他又从一只布袋里取出那只破碗,端端正正地放在面前。碗和他坐的位置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远了,会影响行人,太近了他往起一站,可能会把破碗踩碎,只有适当的距离才能恰到好处。接着他又从布口袋里取出那只装着自来水的瓶子放在他的右侧,他只能放在右侧,因为放在右侧,渴了的时候用右手比较顺手,这是他十年来摸索出来的经验。接着他就把那只喇叭夹在胳肢窝里,袖着手发呆。发呆的时候,他不看西面街,也不看北面街和南面街,而是看东大街。按理说,他坐的位置坐北向南,看南面街是顺理成章的,而他却偏偏要向东看,向东看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头扭过去这样就显得有些别扭,时间长了,还会造成脖颈疼。可他偏偏要向东看,因为他只能往东看,只有往东看,他心里才舒服,才有盼头,不然,他宁肯不看。
老胡的穿着说起来有点特别,他穿的不是常人的衣服。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身和尚穿的衣服,灰不沓沓的长袍,让他本来就瘦小的身材显得更加单薄。和尚服好似全国都是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式样,像旧社会人的打扮。他本来头上就没有头发,完全秃了顶,根本不用剃就是个和尚头,再加上他脸白净细嫩,尽管已经快七十岁的人了,还显得十分的年轻。一年四季不论吹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他都在大街上坐街,可他总是那么的细皮嫩肉,这让那些天天都在美容院做护理的女人叹羡不已,唉哟哟,天哪,你瞧你瞧,老胡这脸怎么那么白净细嫩哎。他那双用来拿喇叭和压喇叭眼的手,也是一样的白净细嫩,而且像弹钢琴的女人的手指一样的纤细修长,这让一些过路的女人更是自惭形秽,自叹不如。老胡吹喇叭的时候,他那纤细修长的手指一下一上一下一上像蜻蜓点水般的有味道,常常惹来一群女子观看。她们不是在听老胡吹什么曲子,她们是在欣赏老胡灵活而又纤细秀美的手指,至于老胡曲子吹得是否好听,是否动人,她们根本不在乎,甚至有些不耐烦。欣赏他手指的女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往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手藏起来,不是袖着,就是伸进衣服口袋里不敢往出取。欣赏的时候,不论是大眼睛还是小眼睛,一律都闪动着亮光,让老胡觉着面前好似有梦幻般的感觉。这亮光刺得他都不敢睁眼睛,只能眯着缝,看起来好似睡着的样子。
老胡会吹很多曲子,他吹的全是一些老曲牌,什么《雁落沙滩》、《凤凰三点头》、《祭灵》等等,他吹得如泣如诉,激情豪迈,委婉动听,粗犷中含有似水柔情,柔情中透出雄浑和动人心魄的气势,一时似万马奔腾,江河咆哮,一时似流水潺潺,雨打芭蕉,一时如痴如梦,呢呢喃喃似燕子衔泥,一阵让人心旷神怡,激情燃烧,一阵让人如梦似幻,一阵让人泪如雨飞,心如寒冬……大街上过往的人驻足聆听。啊啊!这么好听。老胡是靠坐在大街上吹喇叭收取过路人的一点赞助,或一毛或一块,或五块或十块,其实过路人放在他碗里的最多的是一块。他曾经仔细观察过给他碗里放钱的各种人,最后得出一个准确无误的结论,给他五元十元,甚至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的人,往往是一些穷人,经济条件和穿戴打扮上他就可以看出个大概。还有给钱时的动作和脸上的表情。有钱的人基本上都是肠肥脑满,大腹便便,身上无处不体现着名牌,鞋是名牌,裤子是名牌,上衣是名牌,手表是名牌,手机也是名牌。比如鞋,他们一般穿的都是世界名牌或中国名牌:安朗、波派、必飞、格瑞特、尹丹姗、康奈、哈森、华罗、七品芝麻之类的,就这鞋里面还分休闲和运动鞋、皮鞋、凉鞋等等。比如衣服,他们一般都穿的是佐丹奴、班尼路、波司登、华伦天奴、阿迪达斯、香奈儿什么的;国内的有雅戈儿、虎豹、庄吉、九牧王等等。春夏秋冬,休闲西装、羽绒服等按季节都不相同。还有那手表,光名字都难叫死了,拗口得说不来,你比如劳力士、爱彼、法拉利、摩丸陀、格雷汉、欧米茄、萧邦、香奈儿,全是一些外国名牌,那玩艺儿,你不要看它是戴在手腕上的,价钱大得不得了,少说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说出来一般老百姓肯定吓一跳,不惊吓得你吐舌头才怪。再说那皮带,老胡常听人说,看一个成功的男人的品味,不是看你穿什么吃什么,而是看你三样东西,一样是手表,够不够档次,一样是你脚上的鞋,够不够名牌,再就是你腰里的皮带。他发现那些有钱人,腰里皮带是很有讲究的,他们这些人中用得最多的是梦特娇,天虎嘉恒。而且穿啥衣服用啥皮带,休闲裤用啥品牌,西裤用啥品牌,牛仔裤用啥品牌,穿长袖衬衣用啥品牌,穿短袖衬衣用啥品牌,打什么领带,应该用啥品牌的皮带,这里头都有很多的学问和讲究。这些皮带的价格也不菲,少至几百元,多则上千元、上万元也有的是,关键看你处在一个什么层面上。有钱男人用的手机也有很多讲究,一般都是摩托罗拉、三星和诺基亚什么的,杂牌子他们基本不拿。他们这类人吃的烟基本上都是高档烟,软中华、精品芙蓉王,还有黄鹤楼什么的,光冬虫夏草一盒就六百块,你想想没钱能吃得起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都不敢想。
老胡刚才说了一大堆,这说的是有钱的男人。有钱的女人则更不同了。她们一个个几乎都是珠光宝气,雍容华贵,一身的香气,昂着头,挺着胸,高贵得不得了。她们身上也都是一些名牌,什么皮尔卡丹呀、哥弟呀、爱玛斯呀,还有圣·保罗、梦特娇。光身上的香气把人都能薰得闭气。一些年轻的女人穿低胸内衣。露出胸脯不说,连乳房也露出了半截,让男人们一看就想入非非。这情景,谁说他不想才怪哩。可那些上了年龄的女人,四十岁或者五十岁的女人也穿低胸内衣,本来她们那乳房就瘪了,硬是用乳罩把它勒起来,里面填着填充物,老远你看鼓鼓的两个肉包,其实是假的,连露出来半边的乳房都失去了弹性。一些年轻女人,喜欢穿低腰裤子,肚脐眼露在外边,让人猛一看会发出惊讶声,唉哟,你的裤子掉了!有些上了年龄的女人也穿低腰裤子,让人看了有些东施效颦的嫌疑,你这何苦哩,年龄
不饶人啊!鸭子再打扮是扁扁脚,你再化妆,再美容,再修饰都不可能和人家妙龄少女们比。首先你脸上的肌肉是松弛的,色泽是暗淡的,皱纹是明显的,特别是你一笑或者一怒,就一下子露出庐山真面目。你说你有啥办法,这是没办法的呀,你就是有多少钱,也没办法呀。
老胡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些有钱人路过他的面前时,听见或者看见他的喇叭响,首先是牙一咬,嘴一咧,在口袋里摸索半天,掏出五毛钱或者一块钱,看都不看地扔在他面前的破碗里,显得极其的不情愿,不耐烦,手向钱碗的方向伸着,头却转向一边,走过去了,脸上的肌肉还没有松弛下来,总是绷得紧紧的,五官几乎都凑到了一块。老胡认真地观察过,也认真地思考过他们这种无奈的动作,无奈的表情。他们纯粹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他们的脑子里是这样反应的:讨厌,就会知道这样要钱!给还是不给,脑子起码有几秒钟的选择,最后通常都是作出给的选择,不给,说明他们太没有同情心和良知,给嘛,他们认为钱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钱重要了。作为一个有钱人,应该有点风度,有点绅士味道,所以他们就大大方方地给了,可给过之后心里还隐隐作痛,涌上一丝酸楚,他妈妈的,要不是这小子讨要,我会平白无故地掏腰包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老胡还发现,这些富人们你看他们平时嬉皮笑脸,打打闹闹,可在他的面前会装得一本正经,表情严肃,他给一块两块钱,俨然是上帝下凡在拯救普天之下的受苦受难者,俨然是菩萨显灵普度众生,俨然是救世主,他们普遍认为这一块、两块钱对于你老胡来说可以买四个或八个馒头。你如果有病,比如感冒了,可以用一块钱卖两片感冒胶囊。多么仁慈啊,多么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呀,简直可以和雷锋相提并论,真是伟大而平凡,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这不在于给多少,而在于给还是不给。你能说你给的太少了,太寒碜、太小气、太皮薄了,太啬吝了?千万不能,如果这样认为,你就大错而特错了。
对于富人的这些伎俩,十年来,老胡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而对那些穷人,他也是了如指掌。这些穷人们,他们几乎都是一个样子,不论穿着呀、态度呀、神情呀,他们一般穿的都很随便,随便到不能再随便的地步,都是市面上流行的,西装是化纤的,七八十块钱一身,茄克也是化纤的,五六十块钱一件,皮鞋也是仿皮的,顶多不超过五十块,就是手表和手机也是最廉价的,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特色。还有那些从农村进城打工的,你一看他的穿着你就知道,他们是打工的,不是在基建工地看搅拌机,就是抱砖和水泥什么的,里面穿着一件低领线衣,外面穿着像牛嚼了一样皱皱巴巴的西服。里面穿着一件衬衣,外面还会套上一件衬衣,脖子上两个领,怎么看都不顺眼。手里拿着一个过时的旧手机,还用链子拴在裤带上,充其量能值五六十块钱,还用透明的塑料套子把手机完全的套了起来。一块钱或者两块钱的低价烟,常常要装在二三十块钱的空盒里,吃的时候,烟屁股把手指都烧疼了,还舍不得扔掉,一直吸到过滤嘴的焦糊味才依依不舍地扔掉。扔烟头的时候,即使面前有烟灰缸,他们也不愿意往进扔,而是要扔到地上,非要用脚踩几下不可。虽说脚上穿着皮鞋,却没有穿袜子,皮鞋上也被污垢染得认不出是什么颜色。他们还时常把皮鞋脱下来在地上磕,试图倒出装在里面的沙子或者小石子,通常他们是在感觉脚硌的时候,一般是不会这样的。他们还习惯口袋里装手绢,吃完饭或者感冒了擦清鼻涕用。他们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一股恶臭让人掩鼻,可他们并不在意,他们还是大大方方,毫不犹豫地使用,或擦鼻涕或擦苹果或擦桔子,或者是铺在地上衬屁股。本来他们的裤子并不怎么干净,他们还是要习惯性地用并不怎么干净的手绢衬屁股。他们的手是黑的,脖子是黑的,脚面是黑的,凡是露在外面的部位全都是黑的,这黑并不是皮肤的本色,而是上面沾满了污垢,厚厚的一层。这污垢本来可以用清水洗掉的,可他们太忙,也太累,没时间洗还是不习惯洗,反正这又不影响干活。偶然到卡厅里去一次,小姐照样的笑脸,照样的把你抱得很紧,狗狗蛋蛋的叫。亲亲哥哥的喊。你再看他们那手,指甲长,指甲缝里装满黑色的污垢不说,手整个都变形了。年轻人不要紧的,年龄大的人的手,由于常年干活,变得比粗树皮还粗糙。手上全成了硬茧,很硬很硬,硬得连指头都弯不回去,伸出来的形状像个蒲篮一样,翻过去就像个耙地的铁耙。多数从山区来的打工者,不刷牙,牙变得黄黄的,发出的口臭让人掩鼻。可他们经过老胡处则毫不犹豫,连思考一下或者是皱一下眉都不,慷慨大方地随便给那只破碗里扔五块十块的钱,然后又匆匆离开。他们给钱的神情显得相当的和颜悦色,相当的充满同情和爱怜,相当的从容不迫,好似选民在投票一样,投下了自己的尊严,投下了自己的一片爱心和奉献,投下了一个人的良心。动物都有怜惜同类之心,何况人乎?你看看,他们多么的有情有义,多么的宽怀大度。他们囊中羞涩,只有少量的人民币。他们是打工者呵。
老胡虽然在路过的人们予以赐舍时看起来眼睛眯缝着,其实他用眼睛的缝隙对各色人都观察得了如指掌,烂熟于心,观察得细致入微,滴水不漏,观察得细微到不漏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连一句话里的发言轻重,抑扬顿挫,他都能用心体味出一种情绪来,体验出些许的真假和善恶,些许的人情世故。遇到这些情况,老胡自有他的招数,自有他的标准,他有他的一套理论和行动方案。那些大腹便便,视钱如命的富人路过,他给他们吹祭灵。祭灵是什么曲子?祭灵是纪念死者的音乐,低沉悲哀凄惨,他把这悲凄的音符送给他们,起码让其听见心里生出几分哀痛和悲伤。因为他们的行动不值得喜庆,那些没钱人或者打工者路过,他给他们吹《大拜年》,吹《百风朝阳》,吹《凤凰三点头》。这些是什么曲子?是一些喜庆的音符,一喜庆就会给他们传达吉祥如意、喜气洋洋的祝福。他们为生活奔波得累了、苦了,心里有太多的不愉快,听到他这些祝福喜庆的音符,阴霾的心情会为之一振,一切污泥浊气会扫之一光,心理上会得到极大的安慰。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你不仁,我就不义;你义我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连神仙都认这理。
老胡坐街和街上其他讨要的人不一样,你比如缺胳臂少腿的,瞎子聋子哑巴他们为了生存,睡在街上或者坐在街上,面前放一张纸,纸上写着本人因为什么成为残疾,请过路的好心人给一点救命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云云。老胡四肢健全,智力正常,家里四世同堂,儿孙绕膝,啥也不缺,啥都有。那老胡为什么还要坐街?老胡自有他的说法,他说,一辈子啥都不会弄,就学个吹喇叭,老了,家里啥也不缺,坐在街上挣几个钱,捐到福利院去,给那些没儿没女的老人和没爸没妈的娃们弄几个油盐酱醋钱,再说坐在街上还能看人看世事,一举双得,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层意思,老胡没有说出来,老胡十年前死了老婆,一个人呆在家里闷得慌,连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不如坐在街上热闹,说不定还
能碰到个知热知冷的女人。这一层意思,他没说。他没说大家心里都似镜一样,有些话,何必要说那么清,有时候,话说清楚了,反倒没啥意思。
老胡最近碰见了一个女人。老胡碰见的这个女人是个驼背,脊背上像扣了一只锅,一只做饭用的铁锅,这只锅让这个女人一米六八的个子就显得有些低,走起路来只能弯着腰,头就有点抬不起来,走起路来也就不那么利索,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挪,远看好似一个什么东西在移动,近看像鸭子和鹅一样摇摆着走,连背上的驼背也一动一动的跟着身子摇晃。她就是站直了,让人感觉她都好似弯着腰,一点挺直的味道都没有。驼背女人脸面长得很漂亮,眼睛也很大,像汪着两潭清水,清幽幽的透亮,五官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嘴是嘴,耳朵是耳朵,棱角很分明,让人看一眼就不会忘记。啊呀,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成为一个驼背呢?这驼背人多一半不是先天的,都是后天造成的,譬如跌了,摔了,压了,把脊椎弄断了或者弄突出了,就长成了驼背了。像骆驼背上的驼峰冒出个肉疙瘩。老胡见到驼背女人的第一次是在老远处,于是他就想,这驼背女人除过这驼背不好看外,肯定还有很多的不方便处,你比如她睡觉,肯定不能仰面躺着,这样躺着的话,肯定头和腿都在空处,头不能挨地,后半身子也不能挨地,所以她必须侧身躺着,顶多这边压着了,翻个身那面躺着。这驼背女人干活也有困难。背东西,她就不行,驼背上再背个袋子什么的,肯定背不成。挑水她更不成,水担说是放在肩膀上。其实是在驼峰上,会压得她走不成路。生娃她肯定不成,本来后面就有一个驼峰,前面再挺个大肚子,这怎么成?除非她是坐着怀娃,那样子,上厕所都有困难,坐不下去,坐下去又起不来,还要人侍候,这更麻烦了。
老胡第一次见到驼背女人是在东大街的广场上。老胡坐街位置的东面不到二百米有一个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天天早上都是人流如云。三个一扎,五个一堆,甚至十几个、二十几个人聚在一起或唱歌,或跳舞,或打羽毛球、踢毽子,或跳绳,大多数是一些老年人。说是健身,其实多数在娱乐,娱乐与健身融为一体。就在广场东面一棵大槐树下,有一个女人在跳绳,而且还是一个驼背女人,她所处的位置离老胡最近,一转头就可以看到,而且看得特清楚,除非有大雾或者是下雨下雪,有些模糊,但还是能看见的。驼背女人本来就不怎么健全,属于残疾人,按理来说,做不了这个动作,做这动作的人必须是健全人,而且是年轻力壮的人,中老年人一般不做这个运动。可驼背女人却在跳绳,她用的绳是学校上体育课用的那种,绳是花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绳两头有一个黄颜色的木手柄。驼背女人双手握着手柄,并不急着先跳,而是把绳在空中舞几下,再舞几下,然后往空中一舞,绳在空中划个半弧,半个弧的直径刚到她的脚时,她奋力往起一跳。绳从她跳起来的空隙抡过去,又上升到她的头顶,然后又到脚面。到脚面的时候,她又一跳。跳绳的动作主要在跳,跳是用脚跳,脚要离开地面,脚跳的时候,全身都要动。驼背女人身上有个驼峰,往起跳时很费劲,要用足全身的力气才能跳起来。而且跳起来之后,驼峰跟着跳起来。另外是舞绳。舞绳对跳绳来说也很关键,要舞得不快不慢恰到好处。如果慢了,脚离开了地面绳还没有来;如果舞得快了,绳来了脚还没有离开地面。可驼背女人掌握得很好,每次都是同速度,一丝一毫都不差。不过,她跳绳比健全的人慢,好大一会才跳一回,老远处让人看见好似一团什么东西在跳动,被早晨的霞光映照得火红火红的,像一只风火轮在滚动着,跳跃着……
老胡每天早上八点半一到,一坐下来,他的必修课,就是欣赏这带着红光的图画。他一看见这带着红光的图画,心里就热乎乎的,生出一些异样的感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他爱看这驼背女人跳绳。他觉着驼背女人不是在跳绳,而是跳芭蕾舞、跳迪斯科、跳探戈、在蹦迪,像月宫里的嫦娥在舞袖。依这驼背女人本身的条件。是不能做这一运动的,可她为什么要偏偏这样做呢?这里面肯定有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故事肯定动人心弦,催人泪下,是什么故事呢?老胡足足思考了一月,得出一个猜想和假设,肯定是驼背女人在上幼儿园或者上小学的时候,在体育课上跳绳,一不小心摔倒了,结果造成了脊椎骨折,成为驼背。她从小喜欢跳绳,她认为只有跳绳这一运动,才能让她感到愉快和欢乐,现在成驼背,就是从她摔倒的那一天,改写了她一生的命运,使她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失去了人生许多美好的向往,也失去了她喜欢跳绳的这一爱好。因此,她下定决心,每天早晨迎着东方升起的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太阳把红彤彤的光芒洒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因残疾而灰暗的心理会顿时充满阳光,她的脸上也是一片阳光灿烂,她手中的绳把灿烂的阳光抡得成为光团,成为火球,成为她生命中跳动的火焰。只有在此时此刻她才感到无比的幸福,无比的甜蜜,无比的快乐。
老胡想,一个人一旦失去他最最喜欢的东西,一定会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要寻找回来,这是肯定的,驼背女人就是这样。他喜欢看驼背女人跳绳,这就好似高山流水,找到了知音。哪一天,要是驼背女人不来跳绳,他就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好似失去了什么,失落的心里如沙漠般的空寂,连一棵树一根草也没有,让他一整天都魂不守舍,心不在焉。他常常为自己这种感觉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啦?驼背女人和他素昧平生,没有任何瓜葛,他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情绪来?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让老胡与驼背女人有了初识。大约是九点半的时辰,大街上已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了,老胡自觉眼前闪出一道红光,他一抬头,广场上跳绳的驼背女人站在了他的面前。驼背女人因为刚刚跳完绳,满面红光,汗水还挂在她的刘海上,在阳光里闪烁着晶莹剔透的光亮,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急促。她和老胡有如下的一段对话。
驼背女人说:“你为什么一直看我跳绳?”
老胡说:“没有啊!”
驼背女人说:“你说谎,你已经看了我两年了。”
老胡无语。
驼背女人说:“你嘲笑我?”
老胡说:“不是啊!”
驼背女人说:“那你为什么一直要看我跳绳?我跳了两年了,再没有哪个人像你这样看过我。”
老胡说:“你跳得很好看。”
驼背女人说:“真的?”
老胡说:“真的。”
驼背女人说:“我爱跳绳,我从小就爱跳绳。”
老胡说:“你跳得很好。”
驼背女人说:“是吗?”
老胡说:“是的,你跳得很优美。”
驼背女人说:“你是第一个看我跳绳的人,又是第一个赞美我的人。”
老胡说:“是吗?”
驼背女人说:“是的,我应该感谢你。”
老胡说:“为什么?”
驼背女人说:“因为只有你赞美我。以后我每天给你赞助一块钱。”
老胡说:“不不不。”
驼背女人说:“你嫌少?”
老胡说:“不是。”
驼背女人说:“那为什么不要?街上路过的人都给你赞助,我为什么不能?我没有多少钱,我只能每
天给你一块,算是感谢费吧。”
驼背女人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很认真地放在了老胡面前的碗里,向着老胡阳光灿烂地笑着。
老胡说:“那我给你吹一支曲子。”老胡说着就为驼背女人吹了一首《兰花花》。
街道已是人山人海,今天好像过什么节日。一条条横幅流光溢彩,一杆杆红旗迎风飘扬,一声声锣鼓声声入耳,一队队秧歌千姿百态。老胡那苍凉、雄浑的喇叭声也夹杂其中。不过他不是为什么节日助兴,他是在为驼背女人吹的。老胡吹着,驼背女人用心地听着。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老胡吹完了曲子,驼背女人说,她叫雒红梅,今年刚三十岁,未婚,一个人生活,享受城市低保,每月一百六十块钱,可以维持生活,主要工作是搞刺绣和做香包。刺绣和香包一年还可以收入万把元,这些钱她都捐给了山区贫困学生,特别是残疾孩子。她说她是小学文化程度,上幼儿园的时候,因跳绳摔成了驼背,后来父母双双出了车祸,就剩下她一个人生活。她说她现在不但搞刺绣做香包,还写小说,她准备以张海迪为榜样写一本有关残疾人的长篇小说,小说的题目就叫《跳绳》,都已经写了有十万字了,她打算写三十万字。驼背女人还给老胡说,有时间,我给你讲我小说里的故事,主人公叫佟红梅,和我一个名字,只是姓不同。老胡被驼背女人的话说得有些感动,心里头掀起一层一层的波澜,一层一层的涟漪,这波澜和涟漪开始很少,后来慢慢地扩大着,扩大着,像水库湖面上的水纹一样,一波一波的扩大漫延着,波澜和涟漪的中心还打着旋涡,溅起了无数朵浪花,飞溅到岸上,岸上的花花草草挂上了水珠,很亮很亮的,很好看。
驼背女人说完很快地离开,她说她家里还有许多活要干。老胡望着驼背女人远去的身影,心里头有些怅然若失,望着大街上的行人发呆。
一日,天下着大雨,老胡本来不想去坐街,可他想看一下驼背女人这两天是否来过,他就去到了街上。刚坐下来,他就拿眼睛朝东大街上瞅,文化广场空无一人,秋雨如注,天和地混沌一片,雨幕像挂了一道竹门帘,把远处遮得隐隐约约的让人看不清楚。什么东西都显得模模糊糊,街上行人也是寥寥无几。老胡有些失望。一失望心里就生出无限惆怅和寥寂,看什么都不顺眼。老胡心里责怪老天爷,迟不下雨,早不下雨,偏偏在早晨下雨。下雨你就下雨吧,不会下个小雨,而要下大雨,大雨滂沱,一泻如注。下得天地混为一体,街上行人稀少,广场空无人烟,老天爷怎么会成这样呢?这样的不近人情,不识时务,这样的不偏不倚,无声无息的就下起雨来了。啊啊,天若有情天亦老,我怎么会埋怨起天来了呢?天毕竟是天,人毕竟是人啊!
老胡这样胡思乱想着,突然看见广场的雨幕中有一个黑点在晃动,在跳跃,雨一大看不清,雨一小看得很清,时隐时现,隐隐约约,朦朦胧胧,若有若无,让人捉摸不定,看不清楚。老胡心里涌上一股暖流,是驼背女人,肯定是驼背女人,她一定是在跳绳。在过去的日子,老胡曾看见过驼背女人在大风里、细雨里坚持跳绳。呵呵,她终于来了,她真的来了,她到底来了。天上的雨越下越大,老胡的心里却照进一片阳光,透亮透亮的一片艳阳天,他站起来朝着文化广场方向大声地喊:“雒——红——梅一—雒——红——梅!”
老胡的声音很快消失在雨中,哗哗的雨声很快淹没了他的喊叫声。他顾不得拿伞,也顾不得给身上披件塑料布,他夹着喇叭在雨地里向文化广场跑去,他一边跑一边雒红梅雒红梅地喊,一口气跑到了广场的大槐树下,拿起喇叭朝着驼背女人吹,这回他没吹《兰花花》,也没有吹《百凤朝阳》、《梅花三点头》,他吹的是《黄土高坡》。
吱里呜啦吱里啦
吱啦呜里吱里啦
呜啦里
驼背女人穿着一身运动衣,被秋雨淋成了落汤鸡,身上脸上和眉毛上,全都挂满了雨珠儿。五彩花绳抡起来把雨粒给摔得粉碎,摔成了朵朵小小的雨花,随着五彩绳在空中飞舞。五彩绳就像一道天上的彩虹在上来下去地跳动,随着彩绳的跳动,驼背女人也在有节奏地跳动。老胡雄浑、激越的喇叭声似战鼓、似号角在为她助阵,为她呐喊,喇叭声把雨幕搅动成一块块碎片在半空中飘落,和五彩绳遥相呼应,互助互动。老胡吹着吹着,兴之所至。放下喇叭跟着驼背女人一起跳,驼背女人跳一下,他跳一下。他虽然没有五彩绳,但他还是照样挥舞着双臂。他模仿着驼背女人的动作,模仿得极其相似,一男一女与天地雨幕完全溶为一体。
“吱”的一声,老胡放在地上的喇叭呜里呜啦的吹开了,吹的还是那首《黄土高坡》: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老胡和驼背女人随着喇叭里传递出来的音符在一跳一跳的动着。雨还在哗哗地下着,雨柱更稠密了,下得更猛了,他俩跳得更精彩,更欢快了。大概是跳累了吧,老胡突然停下来喊:“唉呀。这喇叭昨会自动的响呢?”老胡发出了惊呼,驼背女人也发出了惊呼,两人一齐发出了惊呼。就在两人一齐发出惊呼时,喇叭声戛然而止,老胡跑上前拿起喇叭去看,由于吹得久了,喇叭头还散着余热。妈妈的,这就怪了,这小子还真的成神成鬼了啊!
驼背女人说:“你听见了?”
老胡说:“听见了。你呢?”
驼背女人说:“我也听见了。”
老胡和驼背女人一齐感到惊讶。过了好大一会,驼背女人说:“其实它并没有响,你的心在吹,心吹和嘴吹不一样,不但自己能听见,别人也能听见。”
老胡感到茫然。
转眼到了冬天,北方的小城一片萧条气象,树叶落了,树枝成了光秃秃的样子,松柏冬青之类的常绿树被风沙漫成了黄色,风把树叶和塑料袋吹卷在半天空,像一只只气球在飘飞着,人们身上都捂上了厚厚的冬衣,脸上捂着大大的口罩,头上戴着帽子或用围巾包着,只露出两只眼睛扑哗扑哗的闪动着。老胡还是天天早上出来,到晚上太阳落山都一直坐在大街上,他那如泣如诉的喇叭声伴着呜呜的北风在飘。驼背女人跳绳的时候,他还是吹奏那首《黄土高坡》。驼背女人跳完绳走的时候,还是一次不误的要给老胡面前的碗里放一块钱。这一块钱有时是硬币,多一半都是纸币。驼背女人把一块钱放到老胡的碗里时,会朝老胡笑一下,老胡也会朝驼背女人笑一下,然后驼背女人走开,老胡从碗里拣出驼背女人扔下的那一张钱,拿在手心里慢慢的熨平熨展,然后装在他贴身的上衣口袋里。老胡曾经仔细地数过,驼背女人已经给他碗里扔下了一千零一块钱,这一千零一块钱,就说明驼背女人已经在这广场上跳了两年零七十三天绳,而且风雨无阻。老胡决定把这一千元存到银行去,他不给山区小学捐助,也不留给自己花,他要到某一天,到底是哪一天,他也说不清楚,反正总有这么一天,他要把驼背女人捐的钱原原本本地还给她。她不容易啊!她一个残疾人,能每天捐一块钱着实不容易。再或者给驼背女人买一件什么东西送去,他自己绝对是不能支取这些钱的。老胡决定每凑足一千元就存到银行去。想到存钱的事,他灵机一动,为何不存在驼
背女人的名下呢?对,就存在雒红梅名下,这存折自己保存着。
就在老胡作出这决定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他第一次发现驼背女人破天荒的没有到文化广场跳绳,他从一开始坐下来,一直望到九点半,还是没有看见驼背女人的半点身影。望得他双眼发昏,脖颈疼痛无比,心里空空落落的不行。老胡算是一个农村的文化人,他爷他爸当了一辈子教师,有很多书,他全读了,因此上说来,他是读了许多书的人,可以说博学多闻。他想起了《庄子·知北游》中一句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而过邻。”这句话的意思后来被人们幻化成一句成语“白驹过隙”,比喻时光过得极快之意,再直白一些说就是人生匆匆,不过一瞬而已,生命中的分分秒秒,时时日日,月月年年,到头来也无非就是无数个瞬间的总和罢了。至于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个美好的瞬间抑或疼痛的瞬间,似乎没有人认真地统计过,这样的瞬间需要的是沉淀,就像河底的沙、流水一样一去不返,沉淀下来的,便是沙,是记忆,也是生命中的每一个难忘的瞬间。老胡确信,2005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瞬间。这一天早晨他看见驼背女人在早晨的霞光里跳绳的那一瞬间,像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上,永远都抹不去。
一个人心里欣赏和留恋的东西,就像陈年的佳酿,随着年代的久远,时间的推移,这陈年佳酿会越来越香,越来越气味浓烈。老胡对驼背女人跳绳的欣赏和赞美,让他心里生出无限的绵绵情意,这情意似酒似蜜似六月熟透的杏子和十月的桂花一样时时刻刻都发散着醉人的清香,这种感觉支撑着他人生的航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意啊,既非男女之间的恋情,又非朋友之间的友情,更非亲情,反正,他看见驼背女人和驼背女人跳绳,心里就会生出一种别样的情感来,这情感让他心里无比的愉悦和舒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老胡决定去找驼背女人,驼背女人曾经告诉过他,她住的地方在箭道巷123号。于是老胡就把他坐街吹喇叭的行头寄放在他旁边的钉鞋处,走街串巷地去找那个箭道巷。他从来不知道箭道巷,也没有去过箭道巷,他问了好多人,也都不知道有个箭道巷。足足找了一天,这让他很失望,也很焦急。这个驼背女人到底怎么啦,是病了还是外出了,再或者是嫁人了?这些都不可能,驼背女人说她身体特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连一次感冒都不得呢,怎么会病了呢?这不可能,外出更不可能!她这么一个驼背女人走起路不大方便,外出会有更多不方便的。嫁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她谈恋爱,没人给她介绍对象,就是嫁人也没有这么快。那么,驼背女人到底怎么啦?是不是还有这么几种可能:早上她往回家走的时候,一辆汽车撞了她,把她撞成了骨折,住进了医院,有可能那汽车司机还逃逸现场,是街上的行人把她送进了医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驼背女人正在街上行走,一青年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而过,青年伸手摘走了她耳朵上的耳环,并将她拉倒在地,驼峰正好着地,她受了伤。还有一种可能,驼背女人晚上出去办事,不小心掉进了下水道检查井。检查井的盖子经常被人偷走,有许多人晚上掉下了检查井受伤。无论怎样,只有找到驼背女人,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可是他怎么都找不到那个箭道巷,问谁都不知道。最后他问了一位老年人,这位老年人少说也在八十岁以上,头发胡子全白了,走路战战兢兢的,好处是脑子还算灵活,记忆力也好。这老人告诉他,是有箭道巷这么一个地方,那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现在那个地方是陵园,里面全是公墓,埋死人呀,现在不叫箭道巷,叫幸福乐园,你怎么会连幸福乐园都不知道呢?老胡听罢惊了一身汗,老人的话也让他一头雾水,那里现在是陵园,埋死人的地方,这句话让老胡心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时他的心狂跳不止,血压升高,出气的声音都粗起来。莫非他经常见到的这位驼背女人是一个鬼魂?
老胡心里尽管疑惑不解,但他还是要到那个四十年前叫箭道巷子现在叫幸福乐园的地方探个究竟。早晨太阳刚冒花花的时候,他就从租住地出发。他先到文化广场,直到九点钟,还不见驼背女人出现,他才决定离开,向幸福乐园出发。幸福乐园并不远,不过四五站的路程,他不坐公共汽车而是步行。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来到了幸福乐园。陵园一片寂静,估计掉一根针都能听见响声,偶然传来几声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有。老胡装作去上坟的样子,一个陵墓一个陵墓地转着看。每个陵墓都有石碑,石碑上写着亡人的姓名,有些还有照片。看起来,经常有人到这里光顾,一些陵墓上放着花圈,或者鲜花,陵墓上还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和烟酒之类的东西,也有烧过纸的灰烬,微风一吹,像一只只黑蝴蝶满天飘飞。这情景还真有点另一个世界的味道。老胡身上的皮肤紧了一下,刹时间汗毛都立了起来。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个陵墓,墓碑上写着“雒红梅之墓”五个大字,老胡有些不太相信,这怎么可能呢?他揉了揉眼睛,刚才他以为眼睛花了,没有看清楚,他又一次仔细地去看,没错,就是“雒红梅之墓”五个字,一个字也不错。啊呀呀,这可怎么得了?真的撞见鬼了,这个驼背女人原来是一个鬼魂!老胡硬着头皮再仔细看墓碑上的年月日,竟然是三年前的日期。唉哟我的妈哟,怎么会成这样呢!老胡从幸福乐园逃了出来。
从墓地上回来,老胡病了,连续几天发高烧,迷迷糊糊的,老说胡话。水米不进,人显得很虚弱,房东老太一天几次进来,还给他请来医生开了药。但是老胡还是不见好转,他的面前老闪动着驼背女人跳绳的身影。忽高忽低,时隐时现,若有若无,隐隐约约的让人捉摸不透。这天晚上,老胡还梦见了驼背女人,和他还说了一席话。
老胡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驼背女人说:“我是雒红梅啊!”
老胡说:“你不是人,你是鬼?”
驼背女人哈哈大笑,“啊呀,老胡哟,我怎么会不是人,而是鬼呢?”
老胡说:“陵园里那个雒红梅不就是你吗?”
驼背女人又笑了说:“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三年前是有一个和我名字相同的女人死于车祸,埋在幸福乐园里,可她不是我,这个雒红梅是剧团的一名演员,演小生的,《周仁回府》唱得特好,可惜她被汽车碾了。我这个雒红梅,怎么能跟人家比呀?再说我是驼背,人家可漂亮啊。”
老胡说:“那这几天怎么不见你到广场上跳绳?”
驼背女人突然双手掩面哭了起来。
驼背女人这一哭,老胡就醒了,梦也完了。
第二天早上,老胡自觉他的病彻底的好了,他决定今天继续去坐街。八点半刚到,他就准时地一分钟不差地坐在马扎上,把头转过去朝广场上望。驼背女人来了,她正在跳绳,抡转起来的五彩绳把早晨的霞光摔得粉碎,摔碎的霞光似天女散花似的在半空中飘飞,忽一下,忽一下,驼背女人随着五彩绳跳上来落下去地运动。老胡奋不顾身地冲过上班族的人流,一口气跑到文化广场大槐树底下,大喊了一声:“雒红梅,你这几天干啥去了,不见你来跳绳?”
驼背女人停下来,向着老胡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有一星期没来广场跳绳,欠你七块钱的赞
助。”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七块钱往老胡手里塞,老胡躲避着,退却着,驼背女人跟着向前毛,咚一声老胡撞在了老槐树上了。老胡是头先碰上去的,接着身子再撞上去,头不是脸和额头,而是后脑勺。这一碰,一下就把老胡碰了个仰面朝天,后脑勺也擦破了皮,往出流血,吓得驼背女人连忙用卫生纸按在老胡的头上止血,一边掏出手机拨了120。不到十分钟,一辆120救护车呼啸而来。
老胡住了七天医院,病愈后又重新坐街。驼背女人又照常每天早上到文化广场去跳绳,跳绳结束回家时照常到老胡这里来,给老胡面前的碗里放一块钱。一切都归于正常,正常得似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又从西边落下去,一点都没有含糊。但是老胡心里老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这个驼背女人为啥说她住在箭道巷123号呢?这个箭道巷明明已经有四十年不复存在了,而原先是箭道巷子123号的地方,恰恰现在就是幸福乐园,陵园又恰恰有一个墓碑上写着“雒红梅之墓”,世界上的事情竟然有这么巧合的吗?有几次,他想向驼背女人问个究竟,可总是没有机会。一天,北风吹,雪花飘。天气很冷,大街上行人稀少,驼背女人跳完绳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他的身旁,照例给他面前的碗里扔了一块钱。之后,驼背女人开了口,向他要水喝,她说她今早不知怎么了,老感到口渴,渴得舌头都端扎在嘴里。他把他的水瓶递过去,驼背女人拧开瓶盖,咕咚咚,咕咚咚,一口气就把一瓶水全喝了下去,然后用手抹着嘴,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老胡觉着机会来了,开口说道:“你不是说你住在箭道巷123号吗,那里怎么是陵园?”驼背女人一听,哈哈大笑,说她不是住在箭道巷123号,而是箭杆巷123号。老胡一听恍然大悟,啊呀!这一字之差,竟然弄出这么大的误差,我险些把这驼背女人当成了鬼魂,啊呀!这真是张冠李戴了。啊呀!天哪!
驼背女人今天正式向老胡发出邀请,让他到她箭杆巷、也叫箭杆胡同的123号去做客。另外驼背女人还给老胡说,让老胡买一个手机,这样有什么事也便于联系。老胡嘴里没有说啥,心里算是接受了,他向驼背女人说:“你先回去,等下午我一定登门拜访!”驼背女人很快地走了。
驼背女人回家了,老胡继续坐在街上吹喇叭。街上行人很多,十年的坐街经历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不抬头看行人的脸,这样他觉着有些仰人鼻息看人脸色的味道。他也不看人的衣着打扮,刚开始的时候,他不但看人的脸,还看衣着打扮。后来他就不看了,他专看人的脚。这街上的行人脚上穿的鞋可以说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但是总体上可以归为这么几大类:休闲鞋、运动鞋、游泳鞋、皮鞋、布鞋、凉鞋,光休闲鞋、凉鞋什么的也有好几种好几大类。老胡从人的脚上可以判断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可以判断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还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是干部、工人还是打工的、生意人等。他做过详尽的观察和调查,一般干部之类的穿的鞋,基本上是皮鞋,怪模怪样的休闲鞋之类的他们根本不穿。他们一般都穿的奥康或康奈等国内名牌,再贵一些的国外名牌,他们一般穿不起,能穿起的也不敢穿。而那些自由职业者,一般都穿的休闲鞋,样子怪怪的,穿在脚上很臃肿的那种。一些生意人,如今的打扮都尽量靠近干部,靠近那些当科长、当处长的干部。科长处长一律的白衬衣红领带,西装革履,一些生意人也一律的白衬衣红领带,西装革履。科长处长们大腹便便,生意人也是大腹便便,他们二者穿的鞋基本上是一样的,正统的黑皮鞋或棕色、白色的。他们不会随便穿怪模怪样的休闲鞋什么的。还有时下的女人们。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特别是那些八○后九○后的女青年,一律的穿裤露肚脐眼,穿衬衣露乳房,穿鞋也是休闲式旅游式的运动鞋,鞋跟高的足有五六寸,把姑娘们白嫩的大腿映衬得修修长长。老胡闲下来的时候,就低着头瞅过往行人的脚、行人穿的鞋和袜子,自己测试自己,看猜对了还是猜错了。有几次他抬起头证明,基本上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准确。老胡常常因自己的猜想准确而自豪和欣慰。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老胡决定今天登门拜访驼背女人。为什么要登门拜访驼背女人,他说不清,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自己想去,于是他就把他的行头又寄存到钉鞋的跟前,步行着向箭杆胡同走去。箭杆胡同其实离他这里不远,也就是四五站路,他估计有半个小时足够了。
老胡很快就进入箭杆胡同。说是箭杆胡同,也真像箭杆一般的窄小,只能容两个人并行。汽车、三轮车和摩托车根本就过不去。老胡一边走,一边看着门牌号。他找到了箭杆胡同122号,就是找不见123号,连124号他都找见了。他问人,人们只是摇摇头,说不知道。他把122号和124号的门牌找见的事都报上去,被问的人说,可能从来就没有123号这个门牌号。听了此话,老胡干脆不找门牌号了,找人吧。他如此这般地把驼背女人形容了一番,被他问的人还是一头雾水,说箭杆胡同从来就没有一个叫雒红梅的女人,也根本就没有过什么驼背的女人。这里虽然住着一些穷人,可个个都非常的健壮和健全,连一个聋子哑巴都没有,怎么会有什么驼背女人?好人一生平安,胡同里的男男女女基本上都是好人。顶多有那么一两个偷情的女人,还是因为男人外出打工,常年不在身边,再剩下的全是好人哟,我建议你还是到其他地方找去吧,或许你记错了地名。
老胡一听,心想怎么可能呢?上一次记错了一个字,让他找来找去找到了幸福乐园,这一次说不定找到的地方是火葬场。他这样思谋着离开了箭杆胡同。是继续找,还是回去呢?
老胡心里想,等明天早上问了驼背女人再说。这次无论如何要问个九九归一,不能再麻痹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