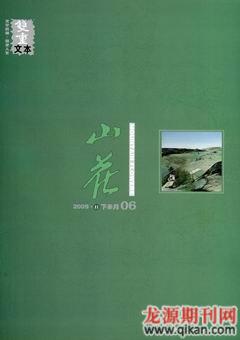形式与主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博尔赫斯曾在中国引起极大影响,这种影响现在看来似乎有所衰落,但实际上仍有一代代的青年热衷于阅读博尔赫斯,欣赏博尔赫斯,甚至是模仿借鉴博尔赫斯。随着博尔赫斯全集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读者们也有机会全面地阅读博尔赫斯了。在博尔赫斯众多的小说中,有多篇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和探讨,其中《永生》篇也日渐引起重视。下面本文就《永生》篇中多层叙述者的设置,以及被多次内部颠覆的情节进行分析,并梳理出作品的主题。
这篇小说的内容相当晦涩,一部分原因是多层次作者的设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作者屡次对自己已经完成的叙述进行反思、颠覆、评论。关于多层次作者的设置,是通过委托发现别人书稿并予以转载的形式完成的,这种手法在中外文学创作史上都不鲜见,关键是这些作者对已完成的叙述屡次进行的反思颠覆,令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都要花费一番心思才能理顺,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正与博尔赫斯一起,实现了文本的复数化,或者说增殖:当我们以为阅读的是一篇游历冒险小说的时候,很快发现自己错了,这实质是一篇关于永生的哲理小说;但这也不是正确答案,其实文本最终表达的是博尔赫斯一而贯之的一种重要观点:个别事物代表着类,个体与个体之间并无区别:个体在一个顿悟的时刻认同所有的人或者某一个特定的人。他对这个问题的猜想可以达到这样的极致:“如果埃德加·爱伦·坡的命运、海盗们的命运、犹大的命运和我的读者的命运私下里都是同一命运——唯一可能的命运——,那么宇宙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了。”既然所有人的历史和命可能运合而为一,那么所有的叙说也不过是彼此的重复罢了,正如《永生》篇的最后一句话:“语句,被取代和支离破碎的语句,别人的语句,是时间和世纪留下的可怜的施舍。”此即本篇小说的最终主题,本文下面将予以分析论证。
上文已经说过,本文是伪托他人手稿进行转载的,而转载的内容又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故,本文的作者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作者,自然是现实中的博尔赫斯本人,他虚构了下面的两个作者:第二层次的作者是伪托发现书稿的人,他假说,土耳其古董商约瑟夫·卡塔菲勒斯卖给某公主一部蒲柏译六卷本《伊利亚特》,在最后一卷中附有一份手稿,不明出处,于是进行了全文转载。这第二层次的作者是什么身份文章并未透露,他不仅伪托转载了手稿,而且还对自己伪托转载写就的小说进行了辩护,即文章最后的“1950年后记”。这个后记并不是真实的,来自论敌的攻击也不是真实的,仍然是博尔赫斯的虚构,是归属于第二层次作者的叙述:第三个层次的作者,即是书稿的作者了,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自传性故事,大致内容如下:“我”,罗马军团之一的执政官马可·弗拉米尼奥·鲁福,在战场上建功无望,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决定出发寻找永生之河和永生之城。最终我喝了永生河的水,也参观了现存的永生城,这座永生城像是“戏谑的模仿或者老城的反面”,风格相当混乱、荒唐,像但丁笔下的地狱,又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总之是很不愉快的经验。还遇到了一个古怪的,看起来没有思想、语言,也没有情感和欲望的永生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天降大雨,使那些彻底忘记了肉体和物质的永生者从纯粹思维的快感中暂时回到了现实世界,我才知道这个永生者是荷马。和荷马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出于对永生的厌倦,我决定出发寻找另一条河,来消除永生。我用了两千多年的时光来喝世上每一条河的水。这期间到过世界各地,从事过各种职业,最终找到了那条河,又恢复了死的自由。
至此故事看似已经结束了,除了其中有很多关于永生的哲学思辨之外,看起来就是一个奇幻的游历冒险故事。但此时小说用波澜不惊的一个省略号,就开始了对这部分情节的反思与颠覆:“……一年之后,我重新检查了这些底稿。”这里的“我”从上述情节中的一个人物,纵身跃出文本,回头审查自己的叙述,这也是博尔赫斯惯用的技巧之一,使得文本陡然生出层次。对于尚未习惯博尔赫斯的读者来说,就觉得惊奇讶异:作为叙述中的一个人物,是如何跳跃出来,凌驾于已有叙述进行指点评价的呢?但对于熟悉博尔赫斯的读者来说,这就不是多大的障碍:博尔赫斯在散文《吉诃德的部分魔术》中提到一种令他吃惊的艺术手法,即《唐吉诃德》的人物竟公然在作品中谈论《唐吉诃德》一书;《罗摩衍那》中的两位年轻人读书识字用的教材竟然是《罗摩衍那》;《一千零一夜》中王后的故事有一个就是她讲故事的故事;还有《哈姆雷特》的戏中戏手法……其实这些都可与博尔赫斯的“阿莱夫”相提并论——在他的短篇小说《阿莱夫》中,他虚构世上有一个小球,能展现所有空间和时间里的景象,但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小球,它就必须是也能展现自身的,于是造成了不断后退的效果,类似两面镜子对照,将会形成无穷尽的彼此的镜像。博尔赫斯本人正是这种手法的熟练运用者。
第三层作者对已有叙述反思的结果是:“我叙说的故事看来不真实,原因在于故事里混杂了两个不同的人的事情。”为了表明这种令人不满的结果,手稿作者列举了种种问题和破绽,以证明“我”,鲁福的记忆,实际上混合了本该属于荷马的声音:由于阅读过荷马史诗,与荷马进行过交谈,并同处于永生人的处境,使这份经历和记忆中,混合了两个人的共同因素:“我”所说的一些话,实质是荷马可能会说的;对“我”寻找解除永生之河的两千年中所经历事件的简述,也特别突出了一些具有荷马气质的事件:在13世纪誊写水手辛伯达的故事,及1714年在阿伯丁订购了蒲柏翻译的六卷本《伊利亚特》。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件事放在鲁福身上是平淡无奇的,但若换成荷马就成为:“稀罕的是荷马在13世纪誊写另一个尤利西斯,也就是辛伯达的历险记,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在一个北方王国看到用一种不开化--的文字写他的《伊利亚特》。”在荷马看来,辛伯达是另一个尤利西斯,英译本《伊利亚特》不过是用一种不开化的文字对原文进行重写。记忆因为混合了鲁福与荷马两个人的因素,已经让读者纠缠不清,但实际上那个土耳其收藏家也掺杂其中:全篇的“后记”中认同了手稿的作者就是卡塔菲勒斯,那个土耳其收藏家,另外订购蒲柏的六卷本《伊利亚特》,最后把它转送给某公主也是一条线索,证明了手稿作者就是他,也即曾经的鲁福,他最终的结局是找到了解除永生的河,在“回伊兹密尔途中身死,葬在伊俄斯岛”。这与文本中多次提到的一种观念是一致的:“谁都不成其为谁,一个永生的人能成为所有的人。正如科尔纳里奥·阿格里巴那样,我是神,是英雄,是哲学家,是魔鬼,是世界,换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什么都不是。”
上面是第三层作者叙说的故事以及对自我叙述进行的颠覆,下面进入小说的最后部分——“1950年后记”。后记,一般被认为是真正的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情况进行的真实的述说,因此具有极大的伪装性,但是鉴于博尔赫斯常用看似真实的后记、书评之类进行虚构,我们细辨之下就能发觉,这部分仍然是博尔赫斯的虚构,应该归属到第二个层次的作者,是他假托小说发表后遭到指摘而对自己的创作进行的辩护。这部分在为读者的解读打开了一扇大门的同时,又设置了一层障碍:“前文发表后引起一些评论,其中最奇怪但并非最谦和的是一篇用《圣经》典故题名为《百色衣》的文章(曼彻斯特,1948),出自内厄姆·科尔多韦罗博士执拗无比之笔。”这篇评论文章的大体内容,是指摘这篇小说插入或化用了很多别人的篇章文字。《百色衣》的作者“根据这些插入,或者剽窃,推论说整篇文章都是伪撰”,第二层次的作者则认为这篇评论的指摘“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认为,“语句,被取代和支离破碎的语句,别人的语句,是时间和世纪留下的可怜的施舍。”这与他对“永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永生是可能的,则个体之间并无确定区别,连记忆和个性也可以混合;进行叙述的语言和文字说到底,也不过是彼此重复罢了,这正是博尔赫斯一贯的认识之一,也是本文的真正主题。
两层作者都对自己的叙述进行了颠覆和超越,使得作品的层次感很强,也是本文的魅力之一。而创造这一切的,是第一层次作者,现实中的博尔赫斯。我们不得不一次次惊叹,博尔赫斯向我们展示出的小说写作的手法之花样,变化之无穷。但是除了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令人赞叹,博尔赫斯这位一贯强调形式的小说家其实在文本中流露了自己长期思考的结果之一,也即本文是有着鲜明的主题的:无论是人的记忆和个性,还是人的语言与文字,都有可能是彼此重复,互相重叠,而不是我们一贯认为的彼此明显区别。对于这种观点,博尔赫斯在散文中多次提到,而且在其多篇小说中都有涉及,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一个问题。
作者简介:
陈为艳(1980-),女,山东日照人,文学硕士,讲师,工作单位: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研究方向英语文学的叙事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