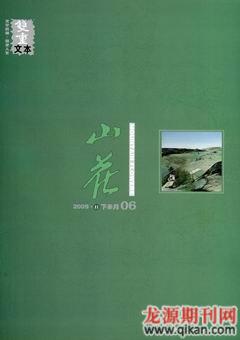云在深处
一
他(但丁)在漆黑一片的丛林里不知所措,那里的梦何等深沉。
——博尔赫斯
但丁显然对自己的梦着了迷。那一次次深陷其中的困惑吸引着他造就了伟大的《神曲》。现实与梦境的区别最好的阐释就是幻想力。我曾数次渴望将现实中的城市化作梦境,因为它缺乏最起码的戏剧性,即使我依然在这片“丛林”里不知所措。幻想深处的但丁用一部鸿篇巨制将现实赋予神性,而我们仅能可悲地编造着城市的诗意。我想,我不理解城市,或者说不想理解。
比起这座熙熙攘攘的北方城市,人渺小得可怜,一声呼哨回到山谷一样杳无音迹。
这种情况下,我习惯耸耸肩头斜跨的公文包,聊以自慰地想:也许自己正获益于这种渺小,才得以像一粒沙尘在风的指缝中自由穿梭。我不斥这种相较下的渺小,这也许是这世上最绵长的存在方式和最难以瓦解的生命单位。我回忆起毕业前夕的那些日子,自己像一只找不到蜜源的蜜蜂慌不择路,在一片质疑与嘲讽声中求存。然而,迷茫下的内心斗争竟无意中被一个陌生人的来电和解——我由此有了生平第一份工作。冥冥中,似乎越深入细部的事物往往容易被人遗忘,正如我们容易遗忘沉在逼仄口袋里的一枚硬币。有时缺了它,我们甚至不能搭乘那开往春天的列车。
旁观抑或身置,滚烫的纷繁复杂在细微体察的淡定中渐渐冷却,化为一块坚硬厚重的金属,闪耀着一道狭长的冷光。我更愿它是越来越多细微生命攒成的结石,在一个隐秘的时节,由我操刀,将它从城市的心腹中取出,暴露这变异的生命形态。
某个寒冷的雨夜,我衣着单薄,瑟缩行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冷气直逼内心,我以弓形的姿态躲避着迎面咆哮的车辆和淫威的狂风。行至一个十字路口,停下,哈气。右手边的一个乞丐不由得令我乜斜。这个身影藏在角落里蜷缩着,形态忽缩忽胀,活像一只守株待兔的洋底生物。这无意中也瞥见了自己的投影——被雨水侵浸着的其蜷缩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这个乞丐,唯一的区别在于我的站立,而他横躺着。这个发现洞穿了我多年生活的本质,它像朵蘑菇一样怀着极大的焦虑在这个幽暗的雨夜悄无声息地顶出来,而我却不敢采摘。
蠕动然后翻身,再蠕动,他把自己的身体盘成一个井状,求雨。我想他真的是枯竭的一口井,映不出天空中的一片云彩,穿堂而过的只有风声和自己的呻吟。
童年梦里的一个断章,永远尘封在记忆深处,似乎没有密码就难以启动——我的身体陷进一片野地中,野地是皑皑的云。它们卑微地低身俯就,在我的胸口簇拥,似乎我一低头就可以喝到它们。云啊,云啊。云在深处。我丢失了辨别方向的能力,周围轻得危机四伏。我害怕脚下的路也是这般铺设,无助的生命渺小如草芥,以至于醒来后,我急于查看自己的胸口,竟惊异地发现几根纤弱的卷曲的胸毛正向我昂首挺胸,它们软弱得几乎看不到脚跟。直到多年后的今天,它们已团成了一撮灌木丛,像大朵的云了。现在,我每天双脚一着地,就开始感恩这种踏实的渺小和博大,一种源自内心的敬畏油然而生。正如2004年的秋末,我失落地住在一条铁路附近,每当途经,有火车迎面开来,内心的轰鸣就与铁轨的呼啸对峙。随着冲击力的逼近,脚下的大地也开始战栗,共振如触电般贯穿全身,内心坚持的壁垒层层剥落。我下意识捂住双耳阻止它对肉体深处的入侵。这种真实的感受,让我对生命深处的灵魂产生怀疑,意志的单薄,凸显人的弱小。而你需要强大自己的心灵。
我确实爱做梦并对此永远充满好奇。对于梦是什么,圣奥古斯丁早有启示:“你们不问我,我是知道的。如果你们问我,我就不知道了。”其实,梦有时是现实的神性,它经常让你的内心变得瞬间强大,里面充满了二氧化碳。一旦梦里的事物同现实接轨,便将我拖拽到幻像的湖中。在白天它为我的奋斗构筑了一道敦实的理想之墙,那令我诚惶诚恐的理想主义得以继续负重在我的肩上。我曾做过这样一个梦。简洁场景里的两个道具:一根细长的针和一座巍峨的山。梦里,这根针的针尖就能擎起整座山。这场景定格了许久,以至于我清醒后的反应就是去厕所哇哇大吐。我觉得不可思议,但那个镜头如此逼真,令我对一根针肃然起敬。继而,联想到自己也像这根针一样,不履行引线缝衣的义务,逆行于世,何其壮哉!后来,我果真几次叛逆了自己的道路,大易其道地走到了现在,虽茕孑独立,却也充实自在。
——城市里,总有这样一类人的影像出入于世俗生活的罅隙,艰难地维系着生存,他们是这座城市上空的“皮影”,既取悦于城市,也取悦于自己。更多时候,他们隐藏于城市深处,自我救赎。
二
……克鲁斯提醒朋友看一眼身后的村庄,就只见两行热泪在朋友脸上滚落。
——[阿根廷]卡列戈
这条常走的路突然停电了。
我感到路上行走的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呢?此刻他们看不清彼此的脸,甚或猜不透暗夜深处的秘密,都低着头,沉默不语,“世界仿佛进入深沉的宁静”。我准备吃碗面,饥肠辘辘的胃惯于在夜里不停地抒情。为难的是,这叽里咕噜的声音很容易就打破黑暗,将其他人引向惊恐的边缘。
其实,走夜路恰恰是最令我兴奋的。它掩饰了我白天的疲惫和暗伤,这样一个场合轻易让我走进身边同为受伤的人。我想一个火星就能擦燃魅影,在明灭间,你善于发现一些内部的事情——走几步就能遇见一对正在互相倾诉的对象。而大白天,他们裹紧了衣裳,用细得像线一样的眼光做急促的交流。显然,在夜里,他们可以正大光明了。
一条路的伸展,在黑咕隆咚的夜里越描越黑,抽象如一幅混乱的涂鸦,我可能就是其中一个荒唐的表情。我走得极慢,生怕撞见某个角落里荒唐的隐私。莫名地想起无数次走夜路的场景来。遭遇那些场景有偶然的、必然的,被迫的、自愿的,可往往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些时间的流转大都曲折,在一个个拐点面前常常自认为是假象的尽头,其实那不过是“有着裂纹的真实”。这像极了天空里的星系,巴掌大小的若隐若现的星座背后,却隐藏了宇宙的运动轨迹。
我想到了邂逅。这个没有预设的时间和空间竟是如此变化无常,也构成了我们奇谲生命中丰富的资源。某一日,我因口渴而偶遇一家书报亭的店主,顺便和她攀谈起来。不期得知她竟是一个异常叛逆的人,如今却整日安然蜗居于如此小的店面中,并以此为乐。她也曾皈依文学,受其熏陶而欲罢不能,终日写作,可是较少见诸报端。后来,终于为生活所累,而选择放弃。其实,她这样的人委实不少,像西绪福斯的宿命,将文学的巨石搬上搬下耗尽一生。而现在她心中又不忍,于是有了这个书报亭。她拿出几期文学杂志,杂志崭新如初,被一个塑料套包着。她说,现在不写了,但每每看到了这类刊物,还是不自觉地订购,读后就封存起来,心里也留个幻想。我听着心酸。至今,她同文学的交流仅限于此,宛如一江之隔。我能想象到她当年痴迷的状态,能想象到同自己内心抽象的交流,她为梦想而忽视周遭的一切,最终沦为一位悲情的自我推销员。我相信在她的内心不止一次像克鲁斯的朋友一样留下两行热忱而无奈
的眼泪。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与任何偏好事物的过从都要保持一份理性的激情,要把握力度。就像一堆燃柴,既不可急功近利烧得过旺,随风肆虐,失去方向,又不可疏于添柴,不闻不问,最后落得奄奄一息。
我将始终保持清醒而警惕的预见。
最近的一个体会:成长中的时间一直处于解构中。你可以细分一天中的每个时段,发现它们正以极快的速度离我们远去。我对时间的敏感甚于对自己身体体察出病症的敏感,这仿佛先于意识,先于每天的经验。我几乎每个夜晚都要醒来两次以提高自己生物钟的警觉性,那种不安的心理仿佛做错什么事情,搅扰得你心神不宁,其实你只是担心第二天上班迟到而已。每天的事情似乎正按照某个剧本的剧情发展,你获得的一切心情正悄无声息地关在你的脑海里,不知道哪一天堆积成山会当成垃圾一样排空,然后你继续敝帚自珍地收集。上述这些仅仅是我对一天生活的真实记录,它许多次隐藏在我的疏忽、麻痹中。我把它看成是希望的负担,时间久了,就会变成生硬的疼痛。
我每天都重新审视自己所在的城市,因为它对我依然陌生。唯一不陌生的就是这里的空气质量很差,每天都需要洗头。有时我会产生错觉,害怕自己会患上洁癖,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在这里生活工作的很多人内心都有着厚厚的一层污垢。他们衣着光鲜地行走在城市里,为的只是填满自己空虚的内心,在精神深处他们无疑在挣扎着,沦陷着。
解构一词对我或许并不陌生,因为它往往隐含了另一个词:重组。是的,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概念。你每一天都在分裂,重生。你不会觉察到这个规律,但它左右着你的思维和态度。解构中的你是复杂的,你需要条分缕析地辨清周围的真伪和杂简。前一分钟的理解和顿悟很可能被下一秒钟的自己嘲笑,而你显然盲目地自以为是了,你陷入这世界上最难以挣脱的网,那是夏洛特善意的礼物,而此时的你正为成长而烦恼。
正如“荣誉与金钱不会走进同一个口袋”(西班牙谚语),生命里的重组也绝不会是解构之后的延伸。
每天我7:30准时在公交车站等候,那是辆老实巴交的班车,总是误点拖延。等车的人们不耐烦地在内心咒骂着,他们脸上升腾起群青的色调。而我则在遥望等候一个陌生人。上车后不久的时段里我在寻找他,那个每天早上都与我不期而遇的男人。后来我时常沉思这幅画面,这个陌生城市里唯一的安慰竟来自一个陌生男子,而你仅仅总与他在早上相遇而已。我见到他会善意地投去友好的目光,并渴望得到他的回礼。即使他总是沉默得像尊雕像,我也依然愿意以一个雕塑家的一厢情愿结束这又是一个神奇的早晨。
总有巧合结束的那一天。我却并没有失落的感受,我惊讶于自己的承受力,要知道,我是个多么敏感的人啊!我默默地挤上车,又默默地下了车,时间存我的身上平静地流淌,我只记得那一天,它像阳光一样平常,有点黏,我内心的缓慢,充满阒静。是夜失眠,我体味着改变,体味着生活里的元素在一点一滴地重组。
我时常期冀自己的来生成为一片云。这既满足了我儿时想要飞起来的愿望,又给了我莫火的生存空间。我不会孤零零地飘来飘去,我会分解自己的身体来享受集体的待遇,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云有意识、无意识地分解,最后总会凑到一起的,能想象得到,它们最后因为拥挤,而遮蔽了太阳,最后化成了雷雨又重返地面,那时候我在哪里?
天空深处的云,因悬浮而渴望重量,因孤独而渴望雷同,因失落而渴望照耀,所以它们容易聚集,遮天蔽日,也为世间带来了盲目和躁动。
作者简介:
付大伟(1985-),生于山东淄博,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擅绘画,喜阅读,业余写作。提倡用平静的言语为思想结庐,为心灵安营扎寨。曾为刊物创作过手绘插图。有过短暂画室教学经历。现为天津一本家居类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