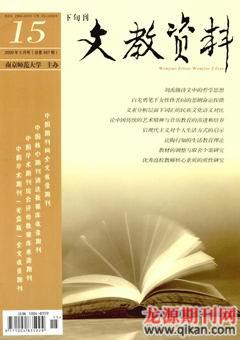道术将裂,天下何为
梁 波
摘要: 本文论述了《庄子·天下》之天下视域中的道术与方术,认为无论《天下》之身家背景如何,它的存在性都体现了古人曾经拥有的那种致力于在全局观照内解决问题的卓越思路。
关键词: 《庄子·天下》 道术 方术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
一
今本《庄子》,存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按照多年来的传统,大部分学人皆以内七篇为钻研庄子之最要,而外篇、杂篇,则多被归于后人之伪篡;并且,针对《庄子》中的篇章,尤其是外篇与杂篇的辨伪,似乎自宋代便渐趋成风了。故而,作为《庄子》之最末的《天下》,关于其著作权归属的争论,在今日依旧是《庄子·天下》研究中的大问题之一,也是任何人在探讨《天下》时不可回避、且不得不首要交代的问题。
概而言之,一方面,由于古人有序列于著述最末的传统,则很多人皆以《天下》为《庄子》之自作,并不同程度地认同《天下》“以上三十二篇,多支离蔓衍之辞,而此篇独为庄语,则欲以窥庄子之真,尤于此不可不潜心玩索也”的观点,如:
故此篇乃本经之末序,序其著书之本旨也……(释性通《南华发覆》)
一部大书之后,作此洋洋大篇以为收尾,如《史记》之有《自叙》一般,溯古道之渊源,推末流之散失……(宣颖《南华经解·天下》)
《天下》篇,《庄子》后序也。历叙古今道术渊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终篇之意。(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天下》)
一部《南华》妙旨,既以寓言、重言、卮言标出立言之意,复著此洋洋大篇,归结全书,如太史公《自叙》之例。(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天下》)
另一方面,由于《天下》所秉持的观念较老子五千言与庄子内七篇都过于泛化,也有相当不少人,如林云铭、吴世尚等,就曾大力怀疑过《天下》为后人之作:
此篇……虽以关尹、老庄,概顶一曲之士来,语意却犹轩轾。其叙庄周一段,不与关老同一道术,则庄子另是一种学问可知……庄叟断无毁人自誉至此,是订《庄》者所作无疑。(林云铭《庄子因·天下》)
此篇自昔皆以为庄子所自作……漆园之南华既成,其高足为之疏通义类而就正于蒙雯……(吴世尚《庄子解·天下·总论》)
而中国现当代的学人,典型的如胡适先生,便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断言“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更多的人们,也都在不同程度地持着《天下》或为庄子后学所作、或出自儒家的观点①。
二
其实,无论学界持有哪一种观点,私以为,大体上都折射出了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庄子·天下》作为研究先
秦的学术史料的价值是否可取、在多大程度上可取;其二,《庄子·天下》的基本价值取向如何、是自圆老庄之学还是实取孔孟之道。而我们说,学人们之所以普遍地关注《天下》之作者何人,恐怕也是以为这第二点——何人之何种价值取向的证实,决定了、至少是相当地影响了第一点——即《天下》是否堪为“周末之学案”②的判断结果。
不过,这里的问题是,所谓“学案”,或者说“诸子概况”这类综述简括性文字,除却《庄子·天下》,尚有《荀子》之《非十二子》、《韩非子》之《显学》、《淮南子》之《要略》、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班固之《诸子略》……其皆不出《天下》之左右,尤其《天下》、《非十二子》、《显学》几篇,其先后序列,基本处于难以厘清的状态。③
可见,无论是标榜《天下》之为“学术史”的地位,还是争论《天下》所代表的学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过处于“假定”的状态,而唯一能够确定的,不过是其存世所反映的一种诸子思想渐趋融合的社会文化事实。在这个意义上,私以为,无论《天下》系何人作于何时,很可能只是一笔文献考古中的“糊涂账”,而《天下》的辨伪也并非是一个多么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毕竟,我们说,在一个思想流派纷杂的时代里,很难有什么思想是能够绝对自给自足的;并且,处在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一群具有政治人生关怀的“士”,能够注意到相类似的命题,也并不是一件必然要分门别类贴标签的事情。
举个例子来说,早年很多学人们借著名的“内圣外王”来质疑《天下》的观念,而这一点,又在后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中被逐渐证实并非儒家所独有——
静无定生,圣也……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故不以物惑……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管子·戒》)
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
内圣者,精神之原也,莫贵焉,故靡不抑制焉……圣道神方,要之极也;帝制神化,治之期也……圣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终始焉。(《鹃冠子·泰录》)④
因而,相对于《天下》究竟何人作于何时何地而言,一个似乎更需要被理解的问题应该是:当《天下》以“天下”名篇时,这个“天下”体现出的,究竟是那个特殊而具体的文化语境的什么非常特征。今天,基本的认同是诸子所拥有的强烈的“天下意识”。而这种意识,我们说,一方面,树立起了诸子强大的现实关照与内心关怀,明确了诸子于乱世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放大了诸子高耸的超越实在感,卓然自立于“世”上而不愧为“士”的人格。
在这一理解之上,也许我们可以试图去感受一下为何陆德明会视“天下”为一个介入文本结构中的主题——即在《天下》之“天下”中也许有一个更本质的内容——这一论断有几分确指相当难说,但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
三
刘凤苞在《南华雪心编·天下·总论》中,给《庄子·天下》戴了一顶很不小的帽子,刘氏云:
笔意雄奇磊落,恣肆纵横,而词旨要归于醇正。……通篇大气盘旋,精心结撰,胸襟眼界,直据万峰之巅,视百家之分门别派,随声逐影者,真不啻蚊虻之过太空也……
《天下》确实有很多惊叹之处,首先要提及的便是开篇的一连串三个问题:
天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但是,这里突出的重点,私以为,既不是圣之何由生,不是王之何以成,又不是道术者在与不在的问题,而是一种隐隐渗透出的、极为浓烈的“观照精神”——很像是一种将个体投射于广阔视域后所自然形成的问题意识。
为什么这样说呢?私以为,在“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之中,所谓“天下”,正是引发这种广泛性思考的“视域”,而这些复杂问题的症结汇聚于一点,又恰恰是道术或者说道术与方术相互纠结的问题。
我们知道,“方术”这里所指,并非单纯的方技与术数,而是概括性地作为了其时百家争鸣、各执一端的语境描述与特定产物。“天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即诸子百家以其方术为道术而不自知的心态写照——所谓的“诸子百家各道其所道之道”,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得不引起广泛注意和深入思考的时代现实:各种方术都将自己视为道术,针对着道术不停聒噪地言说,却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涉及道术本身。但是,更为纠结的,也许还不仅仅是这种政治上的无奈。须知,单纯的对于治方术者而言,其方术自是道术,而其所谓的“道术”,根本上却是“方术”——这其实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悖论。
我们说,既然“所谓道术者……无乎不在”,那么,就至少有两个问题不正自明:其一,道术未必不在方术之中——即道术通过方术来呈现自身;其二,道术不当随时变、事变——即无所谓古今之分。那么,显而易见的,《天下》讲“古之所谓道术者”,是点明了方术与道术之间,确实有一个“所谓”的问题。所以,一句“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的感叹,在这个意义上,虽是对时代文化现状的不满,但更彻底揭示出了一种认识结构上的“无意识封闭”。而这种“东西”,倘若能够从逻辑上被意识到,其实根本无所谓失望什么的情绪。
钟泰有一段关于道术与方术相互关联的分析,且借来一观:
全者谓之道术,分者谓之方术,故道术无乎不在,乃至瓦甓尿溺皆不在道外。若方术,则下文所谓天下之人各自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者。既有方所,即不免拘执,始则各为其所欲,终则以其有为不可加。其有者,其所得也。所得者一偏,而执偏以为全,是以自满,以为无所复加也。此一语已道尽各家之病……若学虽一偏,而知止于其分,去声不自满溢,即方术亦何尝与道术相背哉!(钟泰《庄子发微·天下第三十三》)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钟泰给出了一个“方术亦何尝与道术相背”的结论——这是一句颇为震撼的论断——它鲜明地揭示出了一种可能性:虽然,从方术的层面去理解道术会导致道术的裂变,但是,只要守住“学虽一偏,而知止于其分,去声不自满溢”——即不满于仅仅堕落为一端之方术的信念,有限的方术就将会走向无限的道术。
在这个意义上,《天下》所给出的,倒像是一个很深刻、也很哲学的“学术政治处方”——既然任何方术都包含着或通往、或远离道术的两种可能,则问题就完全不必再纠结于方术的灭除与否,而应该致力于如何从方术中开出通往道术的最大可能。当然,这是个人浅见。但是,倘若顺延此一思路,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道术与方术之辨”是《天下》的主题吗?
四
公平地说,“道术与方术”,无疑可以作为《天下》研究中一个独立的问题领域,并且它确实也就是——大量的研究论文都可以佐证。但私以为,如果没有另一个关键的词——“天下”,这个问题将彻底面临釜底抽薪的危机。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围绕“天下”、在“天下”这样一个时空广阔的视域之内,这个问题才能够成为一个问题,继而被注意到,从被展开、被探讨,乃至被解决。因而,我们可以认定的是,对于《天下》,“道术与方术”是一个进入“天下”的基点;对于“道术与方术”,则是一个承载前者的“整体”。
这个问题要怎么说呢?一个大概的逻辑是:“天下”作为一个已经日趋成型的整体,它的最终开放,要通过道术而不是方术才能够完成;而方术,可以通向不能够脱离方术的道术,却又必须不沉迷于方术的状态;而这种方术的“自我克制”,又只有当处于开放的天下状态中才能够做到。所以,说得不客气一点,在《天下》中,也许正是“天下”,规定、并限制了对道术内涵的思考角度与对现实境遇的处理方向。
也正是本着这样的一种“天下”思路,个人才不能够、或者说不愿意将《庄子·天下》一定归入老庄、道家后学、儒家这样貌似具体的标签领域中去。个人的看法是,无论《天下》之身家背景如何,它的存世,都体现了古人曾经拥有的那种致力于在全局观照内解决问题的卓越思路。不论是否可行、能否实施,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值得珍惜的动机。
注释:
①侯外庐认为,《天下篇》乃庄子后学所著(《中国思想通史》卷一,309页);冯友兰认为,《天下篇》比较晚出……他的观点是庄子这一派的观点(《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353页);范崇高以为,天下篇乃儒家者流所伪托,而又尊道家,不相薄也。(《文学丛刊第一卷,1929年1月号》;任继愈认为,《天下篇》既不是庄子或庄子学派的著作,也不是道家著作,它是在道家术语的掩盖下,全阐述儒家的观点(《中国哲学史论》;334页)……
②此处借顾实语,原文系“《庄子·天下》篇者,庄子书之叙篇,而周末人之学案也。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着书之本旨,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之概要也。”(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序》)
③关于将《天下》作为学术史料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仅列一例聊供参照:“《天下》篇是《南华》之序。或云庄子自作,或云非庄子自作,兹不详考。惟序晚周学术之源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与此篇有同等之价值。”(胡朴安《庄子章义·天下》)
④《鹃冠子》一书是一部先秦古籍,唐兰、李学勤诸先生将汉墓帛书与《鹤冠子》相比较,认为它和《经法》都是战国时期著作,而且属于同一学派。唐兰、李学勤先生的有关论文分别刊于《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淮阴师专学报》增刊《活页文史丛刊》第1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