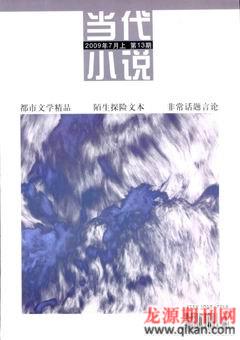结缘
张洪兴
一
“收旧家具了——!
收旧家具了——!”
韦福泉推着自行车,在前边吆喝,郝岚山蹬着三轮车,跟在后边,还不时地晃荡着前闸,铁闸不断地敲打着车的大梁,发出“啪啪啪、啪啪啪”的响声。
太阳落山了,村里静静的,风儿小刀子似的划在人的脸上,有些麻疼。
“妈的,怎么一个人也没有!”韦福泉心里想着,又吆喝起来。“收旧家具了——,收旧家具了——。”郝岚山也“啪啪啪、啪啪啪”的晃起前闸来。
“局长,咱们回去吧,连个人影儿也没有!”韦福泉一只手骑着车,另一只手放在嘴边哈了哈。“妈的,这么冷?!”他回头看了看郝岚山说。
“再等等,说不定能碰上个卖主哩!”郝岚山劝道。
韦福泉是县农业局的办公室主任,他说的局长就是郝岚山。十年前,有一天晚上,郝岚山做了一个梦,梦见许许多多的废铜烂铁、瓶瓶罐罐把他埋了起来,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坐在床边,怎么也睡不着了。第二天,他闷闷不乐,冥思苦想了整整一天,也解不开那梦是啥意思。下班的时候,便到了路对面的起名公司解梦。起名公司的老陈是他的老熟人,就说:“做梦都是反着的,那些废铜烂铁、瓶瓶罐罐都是宝贝呀,是古董!”从那以后,他莫名其妙地爱上了收藏。起初,他买来一些关于收藏的书,什么《收藏大观》、《古家具鉴赏》、《古瓷鉴赏》、《古玉鉴赏》等等,不断地看,不断地琢磨,慢慢地,手就痒了起来,学着去逛文物市场。十几年下来,虽然也有走眼的时候,但还是淘到了不少的好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收藏瘾越来越大,每到周末,总是常到古玩街上走走看看,还时不时地叫上韦福泉到乡下去。为了尽量和村民们拉近乎,每到乡下,两人总是先把车放到镇上的商场前,租上辆自行车、三轮车就开始走街串巷了。
今天是周六,早上,郝岚山起床后感觉脖子有些疼,脑袋左右一晃,更是疼痛难忍,原本不想下乡,可偏偏这时候韦福泉又打来了电话:“局长,今天去不去呀?”经韦主任这么一问,他的瘾又上来了,说:“去,要去!”这次,两个人来到了这个远离城市的龙山镇。他们照旧是先把车放到了镇上的商场前面,在车里换上旧衣服,租了自行车和三轮车,便下了村。一天转悠下来,也没有淘到什么好东西,只收到了五六十年代的几盏灯笼。眼看着天就黑了,韦福泉有些泄气了。
二
“他娘的,还真能飞!”随着骂声,有一户人家的大门突然“吱呀”一声开了,跑出一个头发斑白的老者,差点撞在郝岚山的三轮车上,他趔趔趄趄地站住,稳了稳神,没有和郝岚山打腔,又往前跑去。接着又从门里跑出一个穿黄底子红袄的姑娘,后面又跟出一个腰有些弯的老太婆,小脚碎步,跌跌撞撞地边跑边喊,“抓红嘴鸭,抓红嘴鸭!”随着老太太的喊声,不少家的大门“呼啦”一声开了,跑出十几个中年人、小伙子也跟着往前跑去。
“走,跟过去看看!”郝岚山说着,加快了骑车的速度,一会儿,这位老者和穿红袄的姑娘、老太太来到了一棵大榆树下,大伙儿也跟了上来,接着,郝岚山和韦福泉也骑车过来了。
“他娘的,这鸭子变天鹅了,飞得那么远、那么高?”老头站在树下,望着榆树杈上一动也不动的红嘴鸭说着,急得直跳脚。
老大爷名字叫杨晓东,穿红袄的姑娘叫杨红梅,是杨晓东的独生女。还是春天的时候,杨晓东在村东的水库旁捡到了这只受伤的红嘴鸭,他就把它放在鸭群里一块儿养着。谁知,这鸭与别的鸭相比,确有不同凡响之处,不光下的蛋是红皮的,个头又大,下的又多,而且还特别护家,家里来了生人,它往往从后面猛地咬住裤脚,死劲地拖着你,特别惹人喜爱。终有一天,县动物园里一名工作人员听说了,专门来看,发现确是一只不同寻常的鸭,就想买下,放在动物园里,最后的价钱竟出到八百元。刚才,杨晓东把鸭单独放到了一笼子里,准备第二天给动物园送去。谁知,红嘴鸭懂事似的,就在他关笼子的刹那间,野鸭跑了出来,又一翅膀飞到了屋顶上。杨晓东找来一根长竹竿,想把它赶下来,谁知,它却又一翅膀飞到上百米远的榆树上。
这时,榆树下,来帮忙的老乡,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用石头把它打下来吧!”
“不行!”
“就是上去,我们也够不着呀!”
“太阳要落山了,天黑了,还不知道它飞到哪里呢!”
“嗨,它要跑了,我的学费可怎么办呀!”杨红梅有些担心地说。
“大爷,我爬上去够吧!”这时,韦福泉突然说。
“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杨晓东突然一愣,说。
这时,大家才发现,这一圈人中突然多了两个陌生人,人们用疑惑的眼光看着郝岚山和韦福泉: “怎么突然来了两个外乡人,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收旧家具的!”郝岚山很善意地笑笑说。
“你能够着?可别伤着它!”杨晓东打量了一下韦福泉说。
“放心!”韦福泉说着,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放,来到树下,只见他双手抱树,双脚斜蹬树干,如同猴子上树似的爬上了树。
韦福泉是中医世家,从小又喜欢武术,还当过侦察兵,上树爬高是小菜一碟。大家眼看着韦福泉上去了,站在一个树杈上,却怎么也够不着那红嘴鸭。再往上,树枝太细,又有危险,想到树下有那么多眼睛看着他,天又快黑了,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便又往上攀了一个树杈,这时,树枝猛地晃动了一下,他的身子也随树枝晃着。“小心,小心!”下面的人们咋呼起来,这时,红嘴鸭显然也觉察到了韦福泉,突然扑棱一声,又飞了。
人们追着红嘴鸭,不断地跑着,最后红嘴鸭落在了一根电线杆子的最顶端,一下子坐在了上面,而这根电线杆子就在杨晓东的屋后。看到这样子,真把杨晓东一家人急坏了,大伙也是直挠头,没有办法。电线杆子又细又高,而且又有危险,天又快黑了,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韦福泉和郝岚山也赶到了。
“杨大爷,我可以把它打下来!”韦福泉说。
“打下来,打死了怎么办?”
“顶多打断一根腿!”
“不行,断了腿动物园就不要了,我下学期的学费怎么办?!”杨红梅说。
“要不打,天黑了,还不知道它飞到哪里去呢!”老太太说。
“你能确定打不死?”杨晓东又重复道。
“不会的,顶多打断一条腿!”郝岚山帮腔说。
“嗨,好吧!”杨晓东说着摇了摇头。
见到杨晓东应允了,韦福泉不慌不忙,从地上拣起块石头,在手里搓了一搓,吹了吹,突然他身子一歪,胳膊一甩,石头便嗖的一声出了手,可是,石头偏着飞走了。“嗨!”韦福泉又弯腰捡起块石头,又是一扔,“砰!”正好打在电线杆上。
“你能行吧?”杨晓东看到韦福泉两次都没打中,有些担心地说。
“没问题,嗨!今天怎么打不准了?!”韦福泉心里想着,嘴上没有说什么。又捡起了块瓦片,他用手指捻了捻说:“放心!”说着,他弯一弯腰,胳膊一甩,瓦片斜着飞了出去。接着,只听那红嘴鸭“呱呱”叫了一声,便一下子摔了下来,正好摔到了杨晓东的家里。“坏了,是不是被打死了!”杨晓东想着,第一个跑到了家里,一下子抱起了躺在地上的红嘴鸭,只见那鸭把头贴在杨晓东的胸上,眼里流出两滴清清的泪水。还好,只是一根鸭腿断了。这时,乡里乡亲们也来到了杨晓东的天井里。
“嗨,你不愿去动物园就算了,何必乱飞呢!”杨晓东心疼地说。
“爸,腿断了,我的学费怎么办?”杨红梅说着,一副要哭的样子。
“闺女,你放心,鸭不能卖了,咱们就把那张旧床卖了,怎么也得给你凑够!”接着,他又说:“大伙请回吧,谢谢啦,谢谢啦!”
大伙儿一个个走了,只有韦福泉和郝岚山没有动。直到这时,杨晓东才猛然想起应该感谢这两位陌生人:“小兄弟,多亏了你,多亏了你呀!”他又看看郝岚山说:“多亏了你们俩,谢谢!谢谢!”
“大爷,不谢,还是把它的一条腿打断了!”韦福泉说。
“那怕啥,养好了还可以卖!”杨晓东说:“里屋坐,喝口水!”
“不坐了,天要黑了——!”郝岚山说。
“哎,你们不是收旧家具吗?我这里有张旧床,你们看看吧!”杨晓东说。
三
杨晓东领着郝岚山和韦福泉来到天井东面的厨房里。一进厨房,一股陈芝麻烂谷子味扑鼻而来,郝岚山忙用手在鼻子旁左右扇了扇,心想:啥味,真难闻!这时,他看到厨房的靠墙处,果然有一张旧床,床上放满了锅碗瓢盆、米袋子、破砖头等。一会儿,杨晓东把这些东西都搬了下来,露出了那张旧床。郝岚山发现这旧床做工考究,床边进行了精心的雕琢,床头的雕琢更是精细,郝岚山围着床转了一圈,突然眼里放出一阵蓝光,恰巧,这蓝光又让杨大爷看到了: “他娘的,是人还是鬼呀,眼里怎么放蓝光呀!”
在郝岚山眼显蓝光的同时,他的脸上,腮上,眉毛、鼻子、头发上立时绽满了笑,傻瓜都看得出来,这笑是从每个细胞里冒出来的,从心底里冒出来的。郝岚山从三轮车上拿出个小锤子轻轻地敲着床,一会儿趴在床沿听听,一会儿又闻一闻,用他的话来说这叫望闻听切。这些年来,他在古董收藏中渐渐总结出了自己拿手的办法,即通过看成色、嗅气味、听声音、把器脉来分辨考察真假,这些土办法也许对别人不一定适用,对他来说还是很有用的,走眼的时候很少。经过这简单的几个动作,郝岚山已经知道了这床的年代和价值,他已经判断出这是晚清时期的一张床,特别让他兴奋的是床头下面的一根横板,竟是用海南黄花梨木做的。
“老大爷,这床挺好的,你怎么不用啊?”郝岚山心里纳闷:挺好的床,老大爷不用,还放到了厨房里了?为了不打眼,他想弄个究竟。
“不瞒你说,这张床是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时分的,当时,我分了我们村的地主王三同家的这张床,从来也没在上面睡过觉。当时想,他娘的,地主家的床,咱贫下中农还在上面睡什么觉呀,不能让地主劣绅的坏习气弄脏了咱!所以,床一分来,就把它扔在这儿了!”杨晓东介绍说。
“哦,是这样!”
“大爷,你要多少钱?”
这时,杨晓东突然想起了刚才郝岚山眼里的那道蓝光,想:“看来这家伙是相中了这破床!这张床在咱眼里不值钱,在他那里也许就不一样了!”想到这里,他用探听的口气说:“这床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你看着给吧!”
“啊呀呀,大爷,您的床,还是您先说个价吧!”
“给七百块吧,把我闺女的学费凑齐就行!”杨晓东憨厚地笑笑。
“啊,七百?”郝岚山听了心里咯噔一声,还没等郝岚山说话,杨晓东的女儿杨红梅跑过来: “爸!”说着,把杨晓东拉到了北屋里,她把胳膊一甩,脚一跺: “爸,哪有你那么实在的,一点儿幌也不要,人家现在做买卖都是拦腰砍五,你倒好!”杨红梅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
杨晓东明白了女儿的意思,从屋里出来,走到郝岚山的面前,嘿嘿一笑说: “郝同志,对不起,刚才我少说了个零!”
“啊!”郝岚山轻轻地叫了一声,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杨晓东,心想:“这老家伙怎么变得这么快呀!”
“老大爷,是贵了点,太高了,我们恐怕承受不起呀!”郝岚山有些为难地说,但他心里却在想:“七千也不多!”
就在这时,韦福泉走过来,在郝岚山的耳边咕哝了几句。郝岚山拉着韦福泉走到门楼里,韦福泉说:“郝局长,扶贫办来电话,统计我们包村帮扶贫困户的数字,要今天下午上报。”
“报什么数字,都周末了,下周一再说!”郝岚山说。
“好吧,那我告诉那边!”韦福泉答应着,走出家门,打电话去了。
这边杨晓东一看郝岚山和韦福泉在那里嘀咕什么,以为说的是这床的事,他心里担心,害怕郝岚山不要他的那张床了,急得在天井里直转圈,等到郝岚山回来,他笑嘻嘻地迎上去说:“怎么样,商量好了吧?”
“嗨,要了也是生火的材料,贵了点!”郝岚山微微一笑说。
“哎,郝同志,可不能那么说,生火和生火不一样。烧煤有时呛得你喘不过气来,烧这些老木头,有时候却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就拿我冬天作烧饼来说,烧煤做的烧饼和烧木头做的烧饼味道大不一样,烧木头做的烧饼多好吃?!烧煤做的烧饼都没人要!”
“是呀,大爷,我家老母亲也这么说。”郝岚山停了停又说:“不过也太贵了,说句实话,我顶多出到四千块!”
“唉,郝同志,不瞒你说,要不是今年秋粮绝了产,我也不会卖这破床来给孩子筹学费。别看这床破,可分量有,要把它劈了,烧一冬没问题!”
“不瞒你说,大爷,我那老母亲有哮喘病,一遇煤烟,咳嗽起来就躺不下了。这不,特意寻些老木头,给老人烤火。可不就寻到这里来了!”郝岚山顺着杨晓东的话说了几句假话。话一转,又说“嗨,大爷,看你也不容易,孩子上学又要用钱,这样吧,再给你六百,也是个吉利数。卖,我就买了;不卖,我们就走了。”郝岚山笑笑说。
“嗨,让你捡了便宜!孩子上学急用,要不,我才不卖呢!”杨晓东紧紧握着郝岚山的手说。
“不过,天要黑了,这床我们今天拉不了。现在我给你三百块钱的订金,这事就算定下来了,明天早上,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郝岚山说着,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三百块钱,递给了杨晓东。
“好,好吧!”杨晓东满口应道。
四
第二天,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雪,满地皆白。郝岚山和韦福泉弄了辆大头车,压着雪路,来到了村里。由于来得早,村里人大都没有起来。一到杨晓东的家门口,就听见院子里传来“啪啪啪”劈木头的声音。韦福泉轻轻地敲着门,敲了一阵子,没有动静,韦福泉便使劲地敲起来。
“哎。来了!”这时传来了杨晓东应答声。接着,开了门,郝岚山和韦福泉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堆满了半院子刚劈的木头。
“您早,杨大爷,劈了这么多木头?!”
“是呀,是呀,我这一夜未睡,把那张破床劈了,省得你们回去再麻烦!”杨晓东说着,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嗨,农村人,不差力!”
“啊——”郝岚山和韦福泉一下子惊呆了,同时坐到了雪地里。
“起来吧,起来吧,不用感谢!你们俩买了我的破床,我女儿后三年的学费都有了,我出点力没什么,不差力,不差力!不用说一晚上不睡,就是三晚上不睡也没什么——”杨晓东仍沉浸在兴奋之中,嘴里不断地说着,可就在他用手去拉郝岚山的时候,他才猛然意识到,郝岚山和韦福泉的表情是那样的异样!
“你们俩怎么啦?”杨晓东问
“杨大爷,我们不买了!”郝岚山扑打扑打身上的雪,站起来说。
杨晓东一下子噎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突然说:“你们城里人怎么说话不算话,说买怎么又不买了?”杨晓东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爷,我们买的是床,不是这些散木头!”韦福泉气得结结巴巴地说。
“那破床和这些木头不一样吗?我是看到你们城里人娇气,费了一晚上,才给你们劈好,现在却不要了,还讲理不讲理?!”杨晓东和郝岚山、韦福泉吵起来。
“大爷,不是不讲理,我们买的是床,不是这些散木块呀!”郝岚山说。
“嗨,不都一样吗,不都是弄回去生火吗?”
“不一样,我们买的是床,床值那些钱,您劈成了木块,就不值那些钱了,我们走了!”
郝岚山、韦福泉嘴里叹着气,无可奈何地走出了杨晓东的家门,来到大头车旁。“愚昧!”韦福泉说着,跳上了车,钥匙一拧,轰隆隆发动了汽车,郝岚山上得车来,叹了声气:“嗨,真倒霉,走吧!”
汽车的尾部拉出一溜青烟,缓缓起动了,接着刷刷地跑了起来。突然,郝岚山的耳朵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爸爸,爸,你醒醒,你醒醒……”“她爸,她爸……”
“停下,回去!”郝岚山说。
“怎么啦?”韦福泉问。
“你听,出事啦,回去!”郝岚山阴沉着脸说。
韦福泉停下来,细心地听了听:“我怎么什么也没听到!”
“笨熊,我听到了,快回!”郝岚山命令似的。
“好的。”韦福泉倒着车,飞快地后退,一会儿就来到了杨晓东的大门前,“爸,你醒醒,你醒醒……”果然院子里传来哭声。郝岚山、韦福泉连忙跑进院子,一看杨晓东直挺挺地躺在院子里,韦福泉连忙蹲下,把手指往杨晓东的鼻子上放了放, “怎么没有气了?”他立即趴下,把嘴放到杨大爷的嘴上,进行人工呼吸。
杨大爷苏醒了,韦福泉累得一下子躺倒在地上。他喘了几口粗气,坐起来,试着把杨晓东扶了起来,坐在地上。“我这是怎么啦?”杨晓东努力回想着刚才的情景,疑惑地望着郝岚山和韦福泉:“你们不是走了吗?”
“爸爸,你醒了,醒了!”杨红梅破涕为笑,鼻子一酸: “爸,大不了咱不上学了,你要好好的呀!”
“杨大爷,对不起,刚才我们是和你闹着玩的,谢谢你把床劈成了木块,我们省了老鼻子劲了,这是钱,你收下吧!”郝岚山说着,把早已准备好的四千三百块钱塞到了杨晓东的手里。
“呱呱呱!”突然,刚才还在墙根的那只红嘴鸭扑棱一下子飞到了杨晓东的怀里,嘴巴放在杨晓东的胸前,眼里又流下两滴清泪。
“都是你惹得祸!”杨晓东拍拍鸭的翅膀说,这时,红嘴鸭突然衔起了那一沓子钱,扑梭一下又飞到了屋顶。
“大爷,我给你打下来吧!”韦福泉一看急了,怕那只鸭再飞远了,盯着屋顶的鸭说。
“不用,它的腿断了,飞不远了,自己会下来的。”杨晓东说着,朝屋顶望了望,喊道:“快下来!”这时,他环顾了一下院子里那些木块说:“郝同志,钱我不能要,你们买的是床,不是这些散木块!”这时,屋顶上那只红嘴鸭懂事似的扑棱一下,飞了下来。“呱呱!”它嘴一张,钱正好掉到了郝岚山的怀里。
“不,大爷,我们要的就是这些木块,是呀!”郝岚山说着,又把钱往杨晓东手里一塞,拉起韦福泉开始往车上搬那些木块。
一会儿,木块装上了车。郝岚山和韦福泉走出杨晓东的家门,韦福泉跳上车,轰隆隆发动了汽车,汽车尾部突突突地冒出一股青烟,驶出了村子,路上留下了清晰的车辙。杨晓东和老伴、杨红梅站在大门口不断地喊着:“再见,谢谢,再见……!”
韦福泉开着车,用余光瞟了郝岚山一眼,见他眼睛微眯,面无表情,似睡非睡的,心说:“嗨,这办的是啥事呀!”突然想起:“周一要往扶贫办报包贫困户数量的那个电话。这两年,郝局长已经包了三个贫困孩子上学了,嗨!这个就自己包了吧!”想到这里,便说:“局长,要不,杨红梅上学的费用我包了吧!”
“什么?”郝岚山瞪了韦福泉一眼,说道:“毛病!就你能?”说着,郝岚山又眯上了眼睛。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