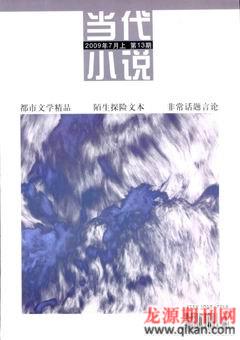老乡兰兰
宋传恩
一
刚子告诉我,兰兰是我的老乡。
刚子是老家刘宝财的儿子。他到这个城市来打工,求我给他找一份工作。我离开乡下十多年,结婚时,回过老家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我的家离这个城市一千多里路,中间要倒几次车,到了镇上,还要坐三轮跑十几里的山路,才能到家。回一次家,用陶琴的话说,像做一场噩梦。
刚子再一次到我家时,已不像一年前,一说话脸就红,怯怯地。他在门口换上拖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脸的疲惫。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我问他。
哎呀!他苦笑着,找了整整一天。
我问,又没工作了?
不是。刚子摇摇头,没工作倒好说,要出人命了!这回你得帮我找个人,不然,她爹要攮死我!
他很着急,不知他说得是谁。
兰兰!咱庄上长得最俊的,比婶子还……他知道说漏了嘴,看了妻子陶琴一眼,嘿嘿一笑,她爹叫杨老三,卖羊肉的,也给牲口看病。
你把他闺女拐跑了?
哎呀,不是,她跟我出来打工。这几个月家里给她联系不上,硬说我把她卖了。他已看出我的不乐,在这个几百万人的城市里找人,无疑是大海捞针。刚子不住地搓着手,有些难为情,说,我从早干到晚,哪有空找她。你给评评理,给我有啥关系,带她出来打工这不是好意吗。前天俺媳妇打电话来,杨老三拿着刀子堵着俺的门骂了一天。
对兰兰我没一点印象,她爹杨老三,住在我们庄的西头,公鸭嗓子,吆喝起来声音像破锣。刚子啰啰嗦嗦说了很长时间,我终于理清了头绪。刚子说兰兰长得漂亮,这有可能。说来也怪,我们庄上的女孩子个个都水灵灵的。沙河门前过,美女满山坡。说得就是我们庄子,这在全省都有名气。我们庄子南面是一条沙河,终年水清如碧。庄子后面是山,山不高,却树木葱郁。也许是这山河的灵秀气滋润了村中的女子,使她们个个面好如花。
兰兰高考第一年没考上,又复习一年,又没考上,上大学的路堵了,只有在家帮着爹娘收拾地里的活。有时,她把爹买来的羊赶到山坡上,绳长长的,拴在树上,随它们啃去,自己坐在那里发呆。
一天,杨老三正在剥羊,他嘴里噙着刀子,左手扯着羊皮,右手握拳贴着羊皮一捅,三两下便把羊皮退下。他要给羊开膛,叫兰兰帮着扯羊腿,兰兰给她爹说,我想出去打工。
不去!杨老三头也没抬,说,你走了,沙河南的地谁种?
我不管。
我说不去就不去,你敢去我砸断你的腿!
砸断我的腿也去!兰兰说着一甩手,转身朝屋里走。杨老三头一扬,手一抖,刀扎在案板上,簌簌地抖动。
兰兰坐在床沿上,朝窗外呆呆地望着。早春时节,那山是黄的,树高高低低,树枝交织在一起,比她的心还乱。兰兰坐一会儿,便去找刚子,打工的事是刚子说的,他还在村头贴了一个告示,谁愿出外打工找他报名。村里人说,他是镇上公司的联络员,联系到人会有他的提成。兰兰觉得刚子是个能人,去年两口子到新疆拾棉花挣了万把块。刚子正在修理他的压水井,见兰兰打听打工的事,他放下手中的活,问,你爹同意?
我的事,我当家。
刚子笑了,这次去唐州。镇上服务公司联络好了,每人600块钱,包括车费、路上吃饭,一车送到。刚子看看她,你要想去,快报名,后天一早就走。
咱庄上还有人去吗?兰兰问。
有,我去,还有保民。
没女的?
没有。刚子低声对她说,你去劝劝二香,出门有个伴。说好了给我回个话,好给你们报名。
兰兰去找二香,她娘说她点化肥去了。兰兰走过桥头便看见了二香,她先在麦垅里刨好坑,把化肥撒在坑里,用脚一驱土踩实了。听见兰兰喊她,她看她一眼,仍干自己的活,等兰兰走近了,埋怨道,你又不帮我干活,喊我干啥!兰兰一拉她,说,咱出去打工吧?刚子正招人哪。二香的眼一下亮了,你愿意去!兰兰说,去唐州的,刚子说后天一早就走!
二香收拾着化肥袋子,你去我就去!她和兰兰走到地头,说,我去问问他,要不一块儿去。兰兰知道二香去年订的婚,他要不去哪?兰兰问。他不去我也去!
吃晚饭时,兰兰看了爹一眼,说,我要出去打工。杨老三一敲碗,脸板着,你不懂,外面乱得很。家里不富裕,好歹能吃饱,过两年,找个婆家走了,你愿上天俺也不管。她娘还想说什么,一看她爹那脸色,便闭了嘴。
二香来找兰兰,兰兰连忙迎出去,给她一递眼色。你爹不叫去?二香问。
他不叫去,我也得去,我才不在家憋着。
二香低声说,你要去,我就去!你不去,我也不去。兰兰一推她,我咋不去呢,走,咱这就去找刚子。
天还没明,兰兰和二香爬上村头的三轮车,车子是刚子头天定好的。除了兰兰家,每家都有人来送,人们便知道她是偷着走的。兰兰不住地看着村里,爹要是知道了,窜出来,真会打断她的腿。三轮车离开了村头,她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到了镇上,交了钱,刚子把她们带到一个客车上,车内都是年轻人,有许多人兰兰都认识,她显得非常兴奋,坐在她身旁的二香却一声不吭。兰兰一碰她,咋的,是想家,还是想他?
谁也不想!说着,两眼已满是泪水。
受二香的感染,兰兰心里也酸酸的。这次一走,不知啥时再见到娘。她知道,这次不走,下次还要走的。索性到外面打几年工,自己养活自己,给爹娘减轻点负担。她理解爹娘的心,宁愿在家养着她,也不想叫她到外面打工。她在村里憋够了,日子一天天熬得她心焦。她知道,就是出外打工,早晚还是要回到这个村子,像二香一样,找个男人嫁了,在家种一辈子地。她心里又不甘,但又想不出别的出路。这样想着,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二香一看她,两人抱在一起,抽抽搭搭哭起来。
二
刚子告诉我,打工的地方是韩国人开的皮包厂,其实就是个小作坊。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干了一个星期,二香挺不住了。晚上下班,二香往床上一躺,把衣服盖在脸上,失声痛哭。兰兰坐在她身旁,一个劲地劝她。二香哭一阵,坐起来说,咱走吧,累死人,我不想干了!兰兰倒不怕累,就是那难闻的胶味,熏得她头疼,每天都不想吃饭。自己和二香还不一样,是偷着跑出来的,这样回去,给爹娘没法交代,邻居也笑话。
发工资的日子,宿舍内一片笑声。虽觉得700元的工资不能抵补平时的付出,她们仍很满足。兰兰拿着钱在手里点来点去,她问二香,咱给家里寄多少钱?最好咱俩寄一样多。二香说,我先买个手机,来时,在家就说好了。兰兰犹豫了一阵,我给家寄500,叫家里先安电话,下月再买手机。
星期天的晚上,到了约定的时间,兰兰要通了村长家的电话,她爹正等在电话旁,还没等兰兰说话,她爹告诉她,不要向家寄钱,叫她先买个手机,他明天就去请人安电话。兰兰说,爹,我偷跑出来,你不会生气吧?她爹说,不生气!出门在外,要多个心眼。她第一次听爹的话这样柔软,心一热,眼也湿了。
不到两个月,刚子离开了这个厂,准确地说,他是被开除的。他告诉我,这与兰兰有关。根本不怨他,是他们欺负人!事隔半年,刚子说起这事,还耿耿于怀。兰兰长得漂亮,便有人关注她。特别是门口的几个保安,一看见兰兰,便嬉皮笑脸地套近乎。一天,兰兰上班,那位姓张的保安看看她的出入证,便抓住她的手。兰兰手一甩,随口骂道,不要脸!张保安故意歪头看着她,你怎么骂人?说着便抓住兰兰的胳膊,不让她走。刚子就在兰兰的后边,看不惯,冲过去,问,怎么,大白天还耍流氓?张保安看见刚子出头,放过兰兰,一把抓住刚子,厉声问,你说谁耍流氓!他身后的几个保安见状,也过来抓住刚子要往屋里推。刚子高声喊,他们耍流氓,还不叫别人说话!当时正是上班时间,门口聚满了人,平时就对保安的作为看不惯,便跟着起哄,和刚子同一个镇子的工人便挤过来拉住刚子。一个保安刚举起警棍要打,帽子便被人打飞。此时老板赶到,喝令保安住手,叫工人先去上班。事后,这个厂开除了两个人,一个是张保安,一个是刚子。
同宿舍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二香回家结婚,兰兰特别感到孤单。晚上,又有两个女孩子要走,兰兰要送她们,她们拦住她不要声张。兰兰说,你们工资也不要了。一个女孩说,还领工资,厂里知道你不在这里上班,连行李也拿不出去。
刚子打来电话,劝她离开皮包厂。现在他在包装厂上班,工资多拿200多块。兰兰有些心动,她打电话问其他的工友,她们也都找到工作,兰兰决定离开。她犹豫很久,她不能像其他女孩偷偷摸摸地走,她要领了工资再走,自己辛苦挣得钱,不能白扔了。下午上班,她找到领班,对他说,我爹叫我回去上学,请你把我的工资给我。
领班惊讶地上下打量着她,什么,你要工资?
兰兰点点头,还差半个月的工资没给。
领班轻轻地摇着头,似乎对眼前的事感到不可思议,他淡淡一笑,工资给不给不是我说了算,你去找老板。
老板是个韩国人,50多岁。兰兰想,那老板看着很和蔼,应该不会太刻薄。真找老板要钱,她还是有点紧张。如果去找,有可能要回来半个月的工资,不找,一分钱也拿不到。兰兰硬着头皮,走进老板的办公室。老板看到她,一愣,背靠着座椅,静静地看着她,问,有什么事吗?
兰兰站在那里,轻轻地说,我想回家,我爹叫我回去上学,还差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要开会,你在门口等着。老板说。
兰兰站在门口等着,站一会儿看看会议室。从下午1点站到4点,会议室还是没有动静。过往的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她从没站过这么长时间,腿疼得几乎站不住,她觉得自己的腿要断了。兰兰想,我就在这里站着,我要等你出来,我一定要回我的工资。兰兰一直站在那里,快5点时,老板终于出来了,老板看了兰兰一眼,还没等兰兰说话,他拿着文件夹又进去了。兰兰在心里骂了一句,没办法,还得等。等就等!那是我的钱,我又没偷没抢,我的血汗钱,我绝不放弃!兰兰站在那里,心想你认为你厉害,可是我比你更厉害,我就不信要不回自己的钱。坚持!她给自己鼓着劲。快7点的时候,一群人走出会议室,她看到了老板,走到他面前。
老板说,工资可以给你,不过要3个月之后再过来拿!
为什么?
公司规定啊!
公司的规定不都是你说了算吗?
可是这个规定是以前就定下来了!
兰兰看到了希望,她已经看到老板有了妥协。只要努力,今天一定会拿到工资。兰兰说,我现在回去上学,怎么可能有时间再过来拿啊?
我现在要去吃晚饭,你3个月之后再来吧!老板说完就走了。
兰兰气得泪水在眼眶里转,刚才还觉得能拿到工资,站了那么长时间,现在还是拿不到。兰兰横下一条心,不管那么多了,我今天一定要拿到钱!你去吃饭,我就在餐厅门口等你!我不怕,我已经等了5个小时,不在乎这几分钟,我就等,我就不信我拿不到属于我的东西,我光明正大,我理直气壮!她在给自己打气。
兰兰站在餐厅门口,看着老板在那里吃饭,她也好饿,心想要到钱可以去吃饭了!她坚信,老板一定会把钱给她的。老板吃过饭出来餐厅,兰兰便跑过去。老板看看她,皱了皱眉头,不知在想什么,然后不耐烦地摇摇头,喊道,李处长,你把她的工资结了。
兰兰回到宿舍,工友们把她围在中间,没等她说完,便高呼她天才。
三
我打断刚子的话,这个城市几百万人,去哪里去找?再说,我和她走对面也不知是她。
刚子有些不好意思,连连说是,我知道,她爹寄来照片,我给你送来!我问刚子有多长时间没见过兰兰。他告诉我,快半年了。兰兰离开皮包厂,到一家酒楼刷盘子,再后来是听说在歌舞厅打工,以后便联系不上了。
兰兰去的酒楼叫唐州酒楼,在这个城市,酒楼的规模算是中等。一个月后兰兰离开酒楼,离开的原因不是待遇低,而是因为领班小梅。兰兰对小梅的第一感觉是时尚,酒楼的员工统一服装,穿在身上却不相同。小梅身材高挑,特别是她头上缠一块蓝底白花头巾,别有风韵。经理身材干瘦,眼球突出,面无表情,手里不停地揉搓着一块玉。兰兰想,都说和气生财,经理这脸面,会不会影响生意?经理告诉她月工资800元,兰兰没有思索就答应了。她已经奔波了一个星期,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小梅把她交给一个女工,兰兰喊她张姐。张姐上下打量她,连说,叫你刷碗真亏了!兰兰被她看得不好意思,笑了。她跟着张姐,穿过厨房,走进洗刷间。兰兰首先闻到酸臭的味道,室内光线昏黄,地上湿漉漉的,张姐叫她小心点,她已经摔过多次。兰兰看她走路的姿势,也变得小心翼翼。她看到池子前面并排八个竹筐,里面摞满了盘子、碗筷,知道这就是她们工作的场所。听你口音,你哪里人?张姐问。玉山!兰兰话刚一出口,张姐高兴地拉住她的手,咱是老乡呢!怪不得你长得好,那是个出美女的地方。也许是老乡的原因,张姐格外热情,她递给她两个套袖,并告诉她洗刷盘子的窍门。张姐说,小心点,打了盘子要赔钱的,头一个月我就赔了80块。
对洗刷盘子,兰兰并没把这活看得多重,在家,她整天帮爹娘洗碗刷锅。一上午下来,她上身的衣服全部湿透,不断有汗珠顺发梢滴下,两个胳膊又酸又疼。她才知道酒楼老板的精明,稍有松懈,工作就无法完成。她们把盘子洗刷干净,在消毒柜中消过毒后,再按类分好,码在厨房的平台上。
兰兰和张姐、小梅住在一个房间,刚才三个人还在说笑,张姐往那一躺,鼾声便起。真是头猪!小梅骂道。兰兰看看她,没有说话,心想,你不干活,你咋知道她累!她刚翻了两页杂志,眼皮便急切地合在一起,她心想,小梅也要骂我是猪了,她睡着了。
没过两个星期,兰兰觉得蹊跷,她多次看见小梅快天明时,从外面回来,什么时候出去的,她不知道。后来,她留心一下,小梅的手机一响,她便悄悄下床,溜出门去。难道她男朋友在这个酒楼里?兰兰自己问自己。
一天,张姐和兰兰洗刷完毕,坐在宿舍里休息,兰兰说出心中的疑惑,张姐一笑,哎!地球人都知道,她和老板有一腿。她原先就是刷盘子的,现在工资比咱俩的都多。
我的天,兰兰吃惊地叫一声,半天没有说话。她怎么能这样!兰兰说。
张姐摇摇头,现在的女孩子,都解放了。
他老婆知道了能饶她?兰兰问。老板的老婆经常来,兰兰见过她,在酒楼里派头十足,说话嗓门很高,从没见过她的笑脸。
早晚得出事。怨谁,她自找的!张姐说。
兰兰想到那个鼓着眼球的老板,一阵恶心。
夜晚,兰兰刚刚躺下,听到小梅的手机响,她装作睡着。不一会儿,小梅悄悄溜出去。
又出去了!张姐在那边低声说,那个龟孙老板劲怪大来。
兰兰见张姐还没睡,一下坐起来,说,小梅真傻!年轻轻的,这算啥呢!她躺下来,再也睡不着。在这个酒楼里,她对小梅印象不错,她知道小梅看不起张姐,但对她好,小梅常买水果和她分尝,还会送她一些化妆品,她床头那个别致的挎包就是小梅给的。正因为小梅对自己好,装作瞎子心中有愧,兰兰觉得应该劝劝小梅,赶紧回头,不然,年轻轻的会毁在老板手里。
等了几天,兰兰终于等到机会,张姐有事出去,兰兰把门关上,坐在小梅身边。你这是干啥,坐这么近?小梅说。
有事,真的,我有事!兰兰说。
小梅看了她一眼,说吧,我听着哪。
兰兰说,你年轻轻的,跟那个龟孙伙在一起干啥!
小梅一愣,迷惑地看着她,问,谁?
你还装,都知道,老板!
小梅脸一红,叹了一口气,说,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只能看结果,不要管手段。她看着兰兰,你也会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说我?兰兰问。
对!
兰兰脸一板,我能像你,我看见那个龟孙就烦!他敢动我一指头,我给他拼了!
小梅脸涨得像块红布,眉毛一挑,你变着法骂我,她一指兰兰,你觉得你是谁?我告诉你,有钱的才是爷!你要有钱,你干这活?你要真有钱,他们会舔你的屁股!小梅甩门而去,兰兰呆呆地坐在那里。
看着你怪透亮,你真傻!张姐听兰兰一说,不住地埋怨她。她要是给老板说了,有你的好果子吃!
兰兰有些后悔,怪自己多嘴。但她不相信小梅会告诉老板。
一天上午,兰兰刚换好衣服,正要去干活,张姐跑过来,告诉她,可能要出事,老板叫你!
兰兰心里一惊,惴惴不安地走进经理室,老板死死盯住她,不停地揉着手中的玉,突然说,以后,你要管好你的臭嘴!你愿意干就干,不干就滚!兰兰哭着跑出经理室。
四
下午,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杨老三快要急疯了,他非要上唐州找他闺女,叫我帮帮他的忙。我不知该如何向父亲解释,这不是乡下,站在村头喊一声,村里人都听得见,就是吃个饭,端个碗也能串几个人家。这是几百万人的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尚无能为力,杨老三来,又去哪里找人。最好的方法是在电视上插播寻人启事,一个星期的费用也在万元以上,杨家能否承受。
刚子带来的消息更叫我坐卧不安。他送来了兰兰的三张照片,糟糕的是他带来的那张报纸,公安部门在城西的一座桥下发现一个女尸,用刚子的话说,很像兰兰。
我看着文中的照片,女尸横陈在桥下的草丛中,右脚的鞋已不知去向,只能看到女尸的半个脸,我问刚子,你能确定?
刚子左右看着照片,说,很像。他指着文章,年龄20岁左右,身高1米66。兰兰就是1米66,这上衣也像她的。
看着报纸,我不知如何说好。
刚子问,上面要求提供线索,要不要告诉杨老三?
又不能确定,告诉他干什么,告诉他等于杀了他!
几天来,我一直为此事烦恼,就是在上班中也难以摆脱此事的阴影。兰兰的照片我已看了多遍,三张都是与别人的合影。她长得是漂亮,像电影明星林志玲。妻子陶琴理解我的心思,她审视着照片,说,女孩子长得越漂亮越容易出事。要不,我叫同事都看看,有没有啥线索。
下午,父亲又打来电话,如通过电视台找人,杨家愿拿钱,砸锅卖铁都干!再不,大伙给他家凑钱。我答应着,几次想把报纸上的事告诉他,话到了嘴头又咽回去。
陶琴下班回家,见我不在,便打电话给我,同事说了,在哪个歌舞厅见过这个女孩子。
陶琴的提示非常重要,我看着照片面熟,觉得她像林志玲,没有想到和她相聚过。我确实见过兰兰,是在舞厅。我在一个公司里任副总,负责客户的吃住娱乐,常和宾馆、饭店,娱乐行业打交道。
在哪个舞厅?我一时想不起来。在这个城市,大小舞厅几百家,上好的也有几十多家。
金三角舞厅!我在辅导儿子数学时突然想到的。我反复看着照片,兰兰就是那位满面通红怯生生的女孩子。那天,陪客人用餐后,应客人的要求到了金三角舞厅。刚在一个包房内坐下,服务小姐送上饮料、水果。客人的手伸向服务小姐的腰间。再摸,我骂你!服务小姐羞得满面通红,怯生生站在一边,她身材高挑,容颜甚好,极像电影演员林志玲。我经常出入娱乐场所,这样的事情,第一次碰到。客人一进包房,大多服务小姐迫不及待地扑进客人怀中。好在客人并没有生气,而是怪模怪样地学着,再摸,我骂你。客人们开心地笑着。那个晚上,再没有看到那女孩子,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金三角舞厅是本市设施豪华、服务功能最为齐全的娱乐场所。集舞厅、歌厅、迪厅、健身房、酒吧、茶馆、咖啡厅、网吧、餐饮、住宿为一体。金三角舞厅的位置极好,它既摆脱了城市的喧嚣,又拥有城市交通的便利。处在二环路的交叉路口,有十几路的公交车在这里停靠。它的南边是风景秀丽的云河。一到夜晚,水光,灯光相映成趣,与金三角变幻多端的霓虹灯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知道,在这个地方,经营这样的舞厅,其背景绝非一般。我刚走进迪厅,一位小姐走过来,问,你要卡座还是选包房?
我摇摇头,坐在靠墙的茶座。舞厅里已是人山人海,摇滚乐震耳欲聋,在霓虹灯下,几百人疯狂地扭动着自己的屁股,拼命地甩着头。音乐声、说话声、嘈杂声混在一起,让人感觉整个舞厅里热浪翻滚。借助跳动,交错的蓝光、红光,我搜索着兰兰的身影。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音乐声,一个浓妆艳抹的小姐扭动身体走过来。先生,请我跳个舞吗?
我想休息一会儿!
我陪你聊天。说着坐在我身旁。我知道舞厅的规则,从兜内抽出20元钱塞在她手里。
谢谢,亲爱的!小姐站起,扭向另外的茶座。
我在坐台小姐里面没有看到兰兰,起身走向二楼舞厅,可能她在那里。
这舞厅的装饰格调很有异域风情的味道,显得典雅大气。舞厅分为黄、黑两个区域。在黄区活动的多是中老年人,舞曲悠扬、轻缓。黑区活动的人,老中青都有,每当慢四的舞曲响起,舞厅的灯光会逐渐暗下来,直到暗到不能再暗的程度。我多次看到,当黑区的灯光亮起来,一对对男女还没有从粘乎乎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仍激情地拥抱在一起。
要包房吗?我刚坐下,一位小姐不知从哪里窜过来,我只好朝她挥挥手。
要不要吃快餐?小姐用手一指左边十多位花枝招展的小姐。
送杯饮料!我说。
小姐送来一杯饮料和一碟小吃。我示意她坐在身旁。你陪舞多少钱?
20元!
那位呢?我已经看到兰兰,她双肩袒露,正和一位中年人在跳舞。
找她陪跳得40元。
为什么?
她是这里的1号,春风第一枝。
我笑了,春风第一枝,名字叫得好!
舞曲再一次响起,我走进舞池。来,春风第一枝。她刚坐下,便被我拉起。
还认识我吗?
认识。
说谎,说说我是谁?
你是?你是武二郎的大哥;萨达姆的表弟;拉登的小舅子;阳痿的爸爸……说着她笑起来。我一拉她的手,她夸张地叫着。
你变了。我说,去年在包厢里,你还骂动手动脚的客人。
兰兰一扫我的脸,若有所思,悠的一甩头,莞尔一笑,我那时特傻,是吗?
为什么?
老板娘骂我,姐妹们也骂我,我也骂她们,后来想开了,人也就是这回事!
我看着她,极力想找出照片中的兰兰。她胖了,也变了!她已没有以往的质朴和羞怯,一口普通话很纯正。看她的状态,目前混得还不错。我不想深究她走向这条路的原因,我对来这里的初衷产生了动摇。
我要带你走!
她斜视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走不走?
不走。
我叫你走,你就得走!
干什么,这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她向右一努嘴,我早已看到角落的那几个男人。
明天我再来,没等她回答,我匆匆离开舞厅。
五
走出舞厅,心中非常失望。对兰兰的沦落,我没有想到。许多进城打工的女孩,对生活道路的多种选择,我能理解。兰兰是我的老乡,心中便觉得痛。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我犹豫不决。通常,舞厅的背景较为复杂,常有一些说不清的关系,甚至会有黑道势力的参与。领走兰兰肯定有风险,后果也许不堪设想。
陶琴有些担心,她说,如果兰兰是舞厅的摇钱树,会看得更紧。你带走她,他们迟早会找到你!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事。如果我袖手旁观,无法面对家乡的父老。其实,也不能怕,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恶势力和政府斗,是鸡蛋碰石头。尽管我自己安慰自己,对可能出现的后果仍迟疑不定。
最后,我决定帮助兰兰,她肯定是被胁迫的!如果她是自愿,随她去,她被胁迫,我坚决把她带出来。如不能带出,就打电话报警,交给警察解决。
吃过晚饭,我直接打的到金三角舞厅。到了二楼,舞池里舞影浮动,整个舞厅没有兰兰的身影。我陪你跳舞吧?
一个小姐问。
叫1号过来,我说。
不一会儿兰兰从一个雕花玻璃门中走过来。噢!春风第一枝,好难请呦。
她淡然一笑,拉住我的手走入舞池,我立即被笼罩在香气之中。她身材高挑匀称,浑身洋溢着一种成熟的美。我问,我能带你出去吗?
她笑着没有说话。
真的!我说。
她一笑,点点头。何必出去,这里有包房,楼上有宾馆。
多少钱?
每小时600元。
不是300元吗?
那是白天。
白天几点上班?
下午三点。
明天三点我准时来接你!
她犹豫了一阵,问,安全吗?
放心,绝对安全。
第二天下午,我把兰兰接到春城宾馆。这宾馆距离金三角舞厅不到800米,对面是长途汽车站,常有客人在宾馆里作短暂休息。宾馆的隔壁就是辖区派出所。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是我选择春城宾馆的原因。
她戴着墨镜,穿一身白色休闲服,更显得风骚撩人,她一进客房,便匆匆脱去上衣。
我问,男人找你都是要干那事吗?
这还用问吗?除非他是性无能,要么是他没钱。男人没一个好货,当然也包括你!她说着笑起来。
男人并不全是这样。
装什么假。
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从来看不起这些人,只要有钱,老的少的,瞎的瘸的,什么人都能折腾。我的老乡下作到这种地步,我感到恶心。
我拿出三张照片叫她看,她仔细看着,一脸惊恐,连忙穿上上衣;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安慰她,别怕,我不会伤害你。我是受人之托,想帮你离开金三角舞厅。
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一愣,这样说,你心甘情愿在这里干?
是的,又没谁胁迫我,只要想走,我随时就能走。走了干啥?你不知道我们那地方,山区,穷得想买件衣服只有卖粮食。我学习不行,就是学习好也上不起大学。我也打过工,累死个人,一年也剩不下几个钱。在这里我一星期的收入比家里一年的收入都多。
你应该和家里保持联系,你父亲担心你叫别人卖了!
兰兰哎了一声,你不知道,烦死人。我一再给他说,我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给我打电话。上了班,不准接电话,这是规矩,白天我要休息。你越不接,他越打。现在,他要上这个城市看我在哪里上班,真烦人。
我劝她,你还是离开这个城市,不然,会毁了你的一生。
兰兰摇摇头,不,现在我看透了,有钱的是老爷,没钱的是龟孙,我吃得青春饭,靠得色相。靠的是自己的身体,比当官贪污受贿好得多。我不会干多久,三四年,弄个几十万,租间门面卖服装,正正经经的过日子!
真是这样想的?
不这样想,又能咋想。你说我又能干啥,打工一天十几个小时,累死个人,也就几百块钱。我也干过保姆,那个男主人坏得很,女主人只要不在家,他就骚扰我。我不从,有一天,他说我偷了他的钱,还打了我两巴掌,什么东西!
我没有想到,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人会用这种方式。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说好。
兰兰脱去外衣,笑笑,谢谢你,我觉得这个社会,好人都死绝了。还真有好人,我会给爹联系。来吧,300元付了,不吃白不吃,过一小时,又得掏300元。
心里话,此时,我没有一点欲望和激情,你走吧,我说。
怎么?她笑了,我不能白花你的钱,来,我帮你。
我推开她的手,真的,让我休息一会儿,你走吧。
她一愣,朝我一笑,然后默默地走了。
我盯着天花板,突然感到茫然。在公司,自认为不管处理什么业务,出入何种场合,应对什么局面,都应付自如,游刃有余。现在却感到自己的浅薄,社会如此复杂,自己远没有把它看透。
手机响起,是陶琴,你在哪里?
我连忙坐起,在街上,正准备回家。
你没事吧?陶琴问。
没事!
你爸爸又打来电话,问兰兰的事。
我应了一声,好久没有说话,对父亲,我又能说些什么?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