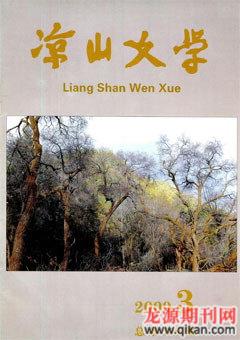冬天里的人
丰里布
天气奇冷,加上有病在身,总被一种无法排遣的忧郁折磨着、苦恼着,因无处发泄使脾气变得比天气还恶劣。家人一早就忙各自的活去了,只我一人在家里面对着阴冷,面对着药罐,面对着不死不活,只好病怏怏地探头看看天色后,百无聊奈地出门去了。
“万物肃杀的冬天也该是这样的了。”我望着阴沉沉的天,一边想一边走。其实我走不到哪里去,只不过是习惯性地来到屋后那小土包上,仿佛免得窒息一般,想在那里透上几口气。
我无可奈何地坐下来,环视周遭,这时的树木全都褪尽了颜色,在呼呼的北风中光秃秃地瑟缩着,好像是盛怒的匕司面前站立着的部下。大地在阴霾的天空下显得萧索而颓唐,山头的林子上白朴朴满眼都是冰凌子,看着冰凌子,冷森森地仿佛直扎进人的心头,我简真害怕再看下去。
那边尔古阿妈拄着拐棍正一瘸一拐地走来,她一身褴褛,蓬头垢面,似乎才从恶梦中醒来,又像是刚被人从病榻上拖起来。“阿呀天——阿妈天”,她一边小声地哼哼着,一边艰难地挪动着脚步,嘴里似乎还在自言自语。她的呻吟中病痛、恼怒、怨恨交织在一起,使她更显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听出来了,她的孙儿早上出牧时又忘了她的那头老牛,还关在栏里,她是着急呢。虽然牛是预备着她老倒的那天杀给前来吊丧的人吃的,但她的牛还不是儿孙的牛,儿孙的事由他们自己去吧,管他们把牛关禁闭也好,杀了吃也好,自个儿管自个儿吧。已病到这个份上,谁还管他什么牛不牛的。我想。
我不禁在心里暗暗嘀咕起来:这老人今天只怕要倒在这刺骨的寒风中了。
其实尔古阿妈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不堪一击,她见我站在这头,便把呻吟忍了些回去,但最终还是没能全部忍住,仍有一两声时不时地冒出来。我说:“大姑,我瞅着你脸色实在不好,是不是病情又加重了?”她忍住哼哼,深吸一口气,然后徐徐吐出,许久才缓过气来似地说:“其实我的病是好了,只是这气堵在心口总是提不上来,心头就在想,看‘阿呀啊呀地哼上两句怎么样,一哼哼,果然好受一些,也就这么一路哼哼着不是?病其实早好了的”“病早好了”,是一句她对别人问候时的口头禅,不管好不好都这么说。我想,哪怕弥留之际她也会这么回答的。为此,一些不理解她的人还有些不高兴:人家真心实意问候她,她却不掏真心话。我知道她是怕惊动邻里,让人家这样那样地为她破费,她知道她的儿孙是还不了别人的厚情的。
我知道她没好,她也清楚自己没好。但她怕人家没听清似地连连说她好了。之后开始絮絮叨叨抱怨她的孙子,而且恨恨地说:“说不定是他妈挑唆的!”我听了暗暗想:婆媳问自古就如此。于是,她的一些遭遇便零零星星地浮现在我的跟前。
记得那一天,已是三月天了,可是依然春寒料峭,尔古阿妈愁眉苦脸地蜷缩在一棵树下,怀里抱着四儿家的小不点儿。她一身嶙峋筋骨如树根,头顶一卜的树枝上垂挂着一根将断不断的枯枝,犹如遭了雷击。她紧紧地搂着孩子与因了人畜的经常磨蹭而裸露在外的老树根融为一体,似乎只有树根还有些许暖意,除此而外到处都让她身心俱寒。
确实,几天来让她悲愁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的说打工在外的小儿子被老板打伤了;有的说因老板拒付工钱,小儿子把老板打死了;还有的说……惊恐,忧虑,愤怒,悲伤交织在一起的她几乎成为疯子。早上为此又与儿媳闹得个不愉快,想到这里尔古阿妈不由得“儿啊——儿啊”地放声嚎啕起来,周遭的人们听到这悲怆的丧腔惊呆了:“莫非……”她怀里的孩子被她吓醒,见奶奶这副怪模样,也惊拉拉大哭大叫起来。尔古阿妈愁烦地搡了搡孩子说:“你就不能安安静静地睡会儿么?”说完抹了把泪想伸伸被孩子压得酸麻的双腿,孩子的哭声却更加尖锐,直冲着树冠弥漫开去。而对小孩不屈不挠的哭声尔古阿妈无计可施,只好任凭她哭死哭活。自言自语地说:“小的时候都是这么千辛万苦经佑大的,可你养他们的身子,他们却养他们的胆,养大后就不由娘了。这犟东西只怕也是与她父母一样的德行。”
其实尔古阿妈与儿媳的不和是在老伴去世之后才开始的,大儿媳妇见丈夫的病总不见好,天天寻医问药都不见效。苏尼毕摩都说是一件外来的四脚家具冲撞了他,把家中凡外来的四脚家具全送走才行,无奈之下,就依着苏尼毕摩的指点行事,而苏尼毕摩所说的外来的四脚家具只有母亲送给他们的一个老木柜。儿子儿媳没和她通气就悄悄地把被烟熏得黢黑的古旧柜子背到她家屋后,不明真象的尔古阿妈只当是儿子儿媳不稀罕。她有些酸楚地把柜子背回家,准备修补一下再用。等她打听明白时,她火冒三丈地骂起来:“本来就是一家人,哪有什么冲撞不冲撞,再说我们这些老人死了,成鬼也是你们儿孙的鬼,成神也是你们儿孙的神,不在你们儿孙中来往,还能到哪里去?不图魂魄有个来往处,养育儿孙有个屁用!居然还没死,还没成鬼成神就嫌弃起我来了?”
儿媳也很委屈:“还不是为了求你儿子安康,除此而外还能有其它什么用意?为你儿子的平安你不乐意,我才不知道你安什么心?”双方为此各不相让,并心生芥蒂。从此婆媳俩相互没好话。
最让她烦恼的是二媳妇老生女儿,现在已是第五胎了,想起这事她不由得更愁烦。抱怨二媳妇不争气的同时,她更恨起管计划生育的:“这些该死的,吃饱了没事干,人家生人家的孩子,关他们什么事,又不让他们喂养。她望着一窝孙女整天吵吵嚷嚷哭哭啼啼,尤其是最小的一个一哭就没个完,她抱起孩子喝道:“再哭!再哭就把你丢了!那么多女儿,丢个女儿稀奇么?”二媳妇听了,心中自然不高兴,恨不得捂住耳朵,便气呼呼一把从她怀里拽过孩子后,把背对着婆婆。其实孩子生下来时,苦苦盼个男孩的二儿媳见又是个女儿,便不想要,于是放到一边没给她喂奶。“尔古阿妈见了,她不忍心一条小生命就这样丢了,便把奄奄一息的孩子捡起来,贴着肉焐在怀里喂点白糖水把她给救活了。她不想再管儿孙们的事,可遇上了总是忍不住要说上一两句,冲突也就由此不断发生。她的几个儿媳都在众人面前说:“她觉得都是我们几个当儿媳的不好,自有比我们好的幺儿媳妇要娶回来,到时候走着瞧!”小儿子还没有娶上媳妇,这确实也是她尔古阿妈犯愁的事。
在日夜焦虑渴盼中,小儿子终于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了,尔古阿妈的脸上这才有了笑容,那以后,人群中经常响起她开怀大笑的声音。有一天,她似乎特别开心,她说等哪一天我也攒上两块钱,去吃它一顿馆子。众人听了轰然大笑,这老太太怎么突然间想到要吃馆子了?众人笑过之后都说:“两块钱只怕吃不起馆子呢。”见人们笑,她以为说错了,便涨红着脸,也跟着讪笑,之后辩解说:“我不哄你们哪,昨天我看见木呷惹从馆子里买了些饭来吃,上面豆腐、肉片、粉丝、青菜什么都有,说是才两块钱呢!我是说从来没吃过馆子,等哪天有两块钱,我也去吃个稀奇,以前总以为那些馆子是干部才能进进出出的,原来还是很便宜的。”
人们又一阵哄堂大笑时,她也开怀大笑起来,她好像为自已不切实际的穷开心而笑。在她看来,吃馆子不管怎么说,总是件值得骄傲的事。其实大家都知道,她所谓的吃馆子也不过是两块钱的盒饭而已。也难怪在乡下就是每年尝新都会引起老人无尽的感慨,说:“不觉间又吃上新洋芋了”,“不觉间又吃上新荞了”,“一日不死,可吃三餐;一年不死,能穿三件,说得就是这个意思了。”没吃过馆子的人觉得能上一回馆子是一种幸福。上馆子对于尔古阿妈来说是一个奢望,一个梦想。一头是两块钱,一头是饭馆,这中间不论有多长,毕竟是个距离。
尔古阿妈不是没见过两块钱,她所有的钱都为小儿子娶媳妇积攒着。有一次她向我借钱,我问她:“大姑你想借钱买点什么?”她见我发问便有些犹豫,好像在作选择:是扯谎,还是说实话哩。最后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也没啥用,只是我现在身上有八十块钱,想借卜二十块凑个整数,因为八十块钱终究是个零钱,很容易被花掉的。一百元钱就是整数,不易拆散的。”我周围的人们吃吃笑道:“可人家那二十块钱也终究是要还的呢。”她说:“是要还的,可二十块钱是个零钱,容易还。”她的几个儿媳也许觉得婆婆有意让她们难堪,都阴着脸不说话。而她说完后也显得很局促,似乎后悔说出的话,因为她伸手从我手中接钱时,好象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接了,笑着说:“顾不得羞愧了。”当然这是几年前的事了。
尔古阿妈是否已经有了两块闲钱?她是不是已经吃了馆子?我不知道。但不知为什么,自从有了那个奢望之后,她又有了一瓶灭杀庄稼害虫的毒药。她不藏着掖着,反而有了安慰一般,笑着问左右:“只一瓶能喝得死人吗?”似乎有些担心剂量不够。人们不搭腔,只瞅着她暗想:这个尔古阿妈怎么啦?是不是哪根神经不对头!又觉着有些好笑。住人们的笑声中尔古阿妈正色道:“人老了,一时又死不了,病痛的滋味难得忍呢。一旦病痛就把药喝了倒下去,也不用孩子们经佑,多省事啊。”她总是害怕活得太久,说:“我好害怕再活上十年八年的,这可怎么好呀?”人们说:那不更好吗?现在形势这么好,这样的幸福日子正是活不够的时候呢。她说:“活久了没意思,她的几个儿媳在私底下相互使眼色窃笑,几个儿子也没把她的话当真不说,还不以为然地说:“石头要滚挡不住,人有心要死劝不住。想死的人尽管死,想活的人尽情活呗,有什么法子。”人们觉得不可思议:她想吃馆子。可怎么突然又有了服毒的念头?人们纳闷:大约……就是……可是……但从儿子到儿媳,从儿媳到孙子,都没有觉出老太太的反常情绪。但那瓶毒药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近年来不知为什么,害虫特别多,所有的庄稼都得喷洒药物才有望收成,否则,甭想有什么收成。尔古阿妈看着人们纷纷给庄稼喷洒农药,便心焦起来,一个劲儿地催促儿子:“你快去买药给庄稼喷洒呢,不然,你就等着挨饿吧”她一边催,一边又抱怨起来:“我活这么大把年纪了,从来就没给荞子上过什么药的,如今这荞也奇了怪了。”
有一天,她到我家借喷雾器,她说:我给自己准备了一瓶毒药,可儿子们没钱买农药,今儿只得先让给儿子们拿去给庄稼喷洒。再不喷药,今年恐怕就没收成了。妻子一边把喷雾器递给她,一边说:“尔古阿妈你千万别老是想不开,老年人应该善始善终,往儿孙们脸上添光彩才是,你千万别往他们脸上抹黑。你又不是老鼠,怎么老念着那瓶毒药呢。”说着我们一起大笑,她抹着笑出的泪说:“我活得不如老鼠自在啊。只是眼看就要到口的庄稼不能不管了。否则,我……唉,没法,也只好等有钱时再买一瓶就是了。”说完急匆匆走了。
不知不觉间天上飘飘洒洒地扬起了雪花,看着身边不住哼哼的尔古阿妈,我忘记了自已的病痛愁烦,因为尔古阿妈惦念的两块钱、馆子、毒药、庄稼让我有些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