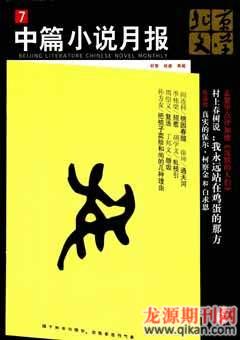真实的“保尔·柯察金”/还你一个真实的白求恩/路翎:作为战士的悲剧
王国华
真实的“保尔·柯察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一书在我国曾是风行一时的“红色经典”。年轻时,我曾不止一遍地读它,并为书中许多动人情节和名言警句感动。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在这本书里讲的完全是自己的生平”,“书中对真实性所抱的态度是严肃的”。
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出生于穷苦家庭,后入团入党,参加红军,在战场上受重伤;复员后参加过“契卡”工作,担任地区共青团的领导……他一生经历过3次爱情:初恋情人冬妮娅,后来成了“酸臭的”阔太太;第二次和丽达的友情因偶然误会而中断;瘫痪后和“忠诚的同志”达娅度过最后年月。
外甥女的回忆
2006年11月26日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载了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写的《重铸的生平》,记述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的一次采访。加林娜的妈妈叶卡捷琳娜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他晚年病中的“护理保姆”,女儿从妈妈那里了解到舅舅的情况。
根据加林娜的回忆:
——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阿历克赛·伊万诺维奇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被授予两枚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十字勋章。妈妈奥尔加·奥西波夫娜出生于一个捷克林业局主任的家庭,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会讲6种语言,而且写过诗……(尼古拉)根本谈不上是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柳博芙·鲍利谢维奇(冬妮娅原型)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谦虚的女性”。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思想进步,十月革命后“拥护苏维埃政权,当了一名教师,丈夫遭到了镇压,再也没有嫁人”。她很珍惜和“保尔”的一段感情,“保尔”去世后,曾专程看望加林娜一家。
——“忠诚的同志(妻子达娅)在结婚后没过几年就离开了他”,后来“嫁给了他(即尼古拉)的亲哥哥德米特里”。
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加林娜下面的几段话:
——“不久前从档案材料中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受过法庭的审判。在内战年代,他曾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也反对‘肃反运动”。
——“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尼古拉)在朋友面前经常承认说:‘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他的朋友阿纳托里承认说:“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
加林娜没有说明,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什么场合下“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的。人们分析说:“保尔”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的额部中了子弹,险些丢掉性命,在战场上,他是不可能“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的,只能是战场外的其他场合。那是什么样的场合?
1918年9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公布《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以恐怖方法来保障后方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必须采用将阶级敌人送往集中营,实行隔离的方法,来防止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侵害;必须将所有与白卫组织、阴谋和叛乱活动有关的人予以枪决。”根据这一《决议》,1917~1918年有100万人被处决。
加林娜说:“朋友们知道舅舅的性格:他绝对不可能容忍镇压。人们在夜间把舅舅的许多好朋友、那些在战斗中经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给抓走了。”
编辑要求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初稿“完全写自己的生平”,几次投稿被退回来,最后投到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编辑部发现其中许多素材有用,于是派人与他合作。“人们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传记‘做了修订,把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变成了偶像、‘一个人和革命者的典型”,《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如是说。
奥斯特洛夫斯基答应按照编辑的“铅笔批注”“将书根本重写”。他在一封信里坦诚地写道:“现在我前面有两种障碍:第一是疲倦;第二还有许多事情,总起来可以叫做‘经济危机,因此我这次才不得不让步,并且同意按照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要求修改以后再出书。”
加林娜举了一个例子:“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钢铁》的最初版本时,真实地反映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妻子达娅中途分离的关系。但是考虑到党的书报检查,迫使他删掉了这一切。在一个‘理想的英雄那里,妻子也应该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忠诚的同志。”
为此,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我的创作经过》一文中特别声明:“这是小说,不是传记,这不是共青团员奥斯特洛夫斯基传”。
“余光”未灭
1991年,苏联解体,文坛“解冻”,《钢铁》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了批判。人们认为,这本书歪曲了历史,违反了“生活真实”。从大的方面来说,《钢铁》所描写的1915~1932年这段时期,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各族人民经受着剧烈社会动荡的年代,接连不断的国内或对外战争,党内多次的斗争和清洗,给人民和党带来了巨大灾难。《钢铁》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只有简单、倾向性的叙述,缺乏客观、全景式的描写;特别是充满困惑、阴谋、痛苦和悲剧性的党内斗争,成了左派幼稚病者和斯大林路线拥护者高唱凯歌、节节胜利的过程,这些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却被回避开了。更重要的是,《钢铁》把当年为了实现乌克兰独立而战、乌克兰的民族英雄西蒙·彼得留拉描写成为无恶不作的“匪帮”,这是今天的乌克兰人民难以接受的。
在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钢铁》被定位为一部有严重错误的作品而被广大读者冷落。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一响亮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可在遥远的东方,他的“知音”依然存在。鲁迅先生说过一段话:“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
今天,中国50多岁以上的人看“保尔”,可能是在找寻年轻时的激情,或是重温某种理想;可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言,保尔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打动他们心灵的,可能是其成长过程中的苦难酸辛、那些青涩动人的爱情故事,或者仅是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摘编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 盛禹九 文
还你一个真实的白求恩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英雄。对于许多来自中国的移民或者留学生来说,能到白求恩故居去参观,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即使年轻的一代并没有经历背诵“老三篇”的年代,但是他们的父辈,却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
那是一个青春躁动、一个需要英雄、一个只有一种精神选择的年代。
白求恩故居坐落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著名的旅游区姆斯柯卡。白求恩于1890年3月3日出生在格雷文赫斯特镇一座普通的民居。这里距多伦多约200公里,是安河著名的林业区,人口约26000人。
光临白求恩故居的大多是中国人,且多选择在秋季,因为秋天的姆斯柯卡,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树叶尽显华彩。无论你是泛舟湖上,还是走在林间小径,游人无不陶醉在秋天的韵味中,这是加拿大一年中最美丽的日子。
白求恩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母亲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在白求恩故居,我们看见一张极普通的儿童睡床,相信这就是白求恩睡过的小床。
孩提时的白求恩喜欢生物,追求科学探索,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多伦多大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年轻的白求恩当过餐厅服务员、消防员、报社记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轮船上的锅炉工和礼拜天学校的教师。在一张老照片前,一位年轻的女孩指着叉腰站在一群伐木工人中间的白求恩对她男朋友说:“你看,白求恩原来也是labor(劳工)……”话音刚落,大厅里顿时漾起温馨的笑声。
1923年,白求恩通过了非常严格的考试,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临床研究生。此时他遇见了比他小11岁的苏格兰姑娘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从性格上看,白求恩与弗朗西丝两人的个性并不相容。白求恩性格豪爽,喜欢喝酒,参加各种形式的聚会,生活上不拘小节。更重要的,是他追求冒险的精神。这些都是个性恬静、内向而羞怯的弗朗西丝所难以接受的。但是,爱情总是热烈而盲目的。在白求恩的眼里,弗朗西丝不但是他感情所系,而且成为他素描作品的主角。
1923年8月13日,弗朗西丝不顾家人的反对,与白求恩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先后到了巴黎、柏林、维也纳等欧洲著名城市游览,这是白求恩与弗朗西丝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一年后,白求恩完成学业,他携带弗朗西丝离开英国到美国底特律正式挂牌行医。由于当时医生奇缺,白求恩从早忙到晚,夜里还常常出急诊,自然冷落了弗朗西丝。加上白求恩是个眼睛里只有工作的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拿出时间来调整他与弗朗西丝的关系,而内向的弗朗西丝则对这种冷漠的夫妻生活充满苦闷。
1926年夏天,白求恩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他们的婚姻关系因此而走到了断裂的边缘。据彭志良的《白求恩的婚姻》一文介绍,白求恩其时将弗朗西丝叫到身边,他望着妻子焦急的面孔十分内疚:“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谈谈,我不知道医生对你说了些什么,不过我快要死了,而你才25岁,前面还有整整的一生。我要你跟我离婚,走你自己的路。”年轻的弗朗西丝对此表示反对,她说她在此时不能离开他,“不管我们中间发生什么,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跟你在一起。”而白求恩决意要离婚,他说:“这样没有什么意义。我决不再浪费你的生命。除非你同意跟我离婚,否则我决不到疗养院去治疗。”
至今我们无法探究白求恩当年迫使弗朗西丝与他离婚的真正原因。据白求恩故居所提供的短片介绍,此时的白求恩生活相当放荡,他酗酒、抽烟,晚上参加各种舞会,生活相当没有节制。他大概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但绝对还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甚至放弃了争取生存的斗争。在他的画作里,他预言他将会早逝。这些信息可以为我们勾画出一个真实的白求恩: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此时他正陷入人生的最低潮,他连生命都可以放弃,何况爱情呢?
白求恩与弗朗西丝终于离婚了。在特鲁多疗养院,他收到了法院寄来的离婚判决书,他与弗朗西丝这段爱情故事画上了句号。此刻他能做的,就是与疾病进行搏斗。当时他听到有一种“人工气胸”的方法有可能治好肺结核,这是一种把气打入病肺空洞的危险手术,在治疗上存在着相当的危险,但他立即要求医生给他做手术。富于冒险精神的白求恩,此番与死神赌了一把,结果他幸运地赢了,而且因此掌握了运用“人工气胸”治疗肺结核的技术,当时全世界懂得这种技术的专家只有13位。
1928年初,病愈后的白求恩回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成为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加拿大胸外科开拓者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的第一助手,其间他发明和改进了12种医疗手术器械,还发表了14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的创见和学术成果得到业内同行的公认和尊敬。
随着身体的逐渐康复,白求恩对弗朗西丝的思念愈发强烈。他曾多次给弗朗西丝写信,倾吐自己无法抑制的思念。在白求恩的真诚打动下,1929年秋,远居苏格兰的弗朗西丝再次回到白求恩的身旁,他们在蒙特利尔复婚了。
1934年,白求恩接受了新的职位,在魁北克省的圣心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此时他已是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这是白求恩在学术上最鼎盛的时候。这个对工作有着一股子疯劲的男人,又回到忽略弗朗西丝的故态,他们的婚姻再次走进死胡同。
据说有一天下午,弗朗西丝回家后看见白求恩正盘腿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个骷髅模型,当她强压着内心的不快打开冰箱准备做饭时,却看见白求恩从医院带回来准备作研究用的一条人的肠子,她被吓得大叫一声,积在心中的火气一下子爆发出来。
由于生活志趣的不同,白求恩与弗朗西丝这段婚姻终于在1933年3月再次画上句号,所不同的,这次是弗朗西丝提出来的。
说句公道话,白求恩是个具有相当情趣的人。他不但是医生,还是作家、画家,曾经在蒙特利尔开设了一个儿童绘画班。在中国期间,他还创作小说。他喜欢旅游,他是个懂得感情的人。他对弗朗西丝有着很深很具情调的爱,曾信誓旦旦地对弗朗西丝许诺过:“我一生不可以给你富贵荣华,但我一定不可以让你这一生过得贫乏无味。”
什么是白求恩所认为的“不贫乏无味”呢?是冒险,是满世界跑,是为贫苦人争权利——这就是白求恩的性格,也是弗朗西丝无法理解和难以接受的。相信这才是他与弗朗西丝这段两起两落的情感最终落幕的根本原因。加上白求恩是个很主观武断、脾气也相当大的人,譬如说,在中国,当他听到有人要“照顾”他留在后方延安时,他曾气愤地将圈椅从窗户扔出屋外,这足以显示他性格的独特性。白求恩为了能到前线去做手术,甚至将自己化装成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唯一所忽略的,是他的大鼻子和蓝眼睛,再怎么化装,也无法变成中国人。
白求恩来自草根阶层,他对平民百姓的医疗状况相当关注。在蒙特利尔,他领导着一个小组,专为穷人的孩子医病。20世纪30年代初,加拿大低收入阶层生活相当艰难,面对饥饿和贫穷,白求恩提出由国家负起公共医疗责任、建立一个为公民服务的健康保障体系的改革设想,这个设想应该就是今天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模式。
1935年,白求恩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机会到苏联访问,这使他有机会看到苏联全民医疗体系的成功,这是他的梦想。他认为加拿大这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保障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必需的医疗服务的系统,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法西斯在德、意支持下进攻共和国政权,白求恩参加医疗队前往马德里,他在那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从西班牙回来后,他在加拿大各大城市讲演募捐,这时候他看到了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国爆发全民抗战的消息鼓舞了他,他向美国共产党募集了5000美元,购买了一批珍贵的医疗器具,于1938年1月到达中国。
白求恩逝世于1939年11月12日,之前他在摩天岭抗日前线为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幸受伤感染,到了11月10日,高烧达40摄氏度的白求恩病情恶化。白求恩逝世时年仅49岁,与毛泽东所说的“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说法有些出入。
在红色革命的年代,白求恩是全中国人民仅有的几个偶像之一,《纪念白求恩》被作为“老三篇”之一而成为天天读的范文。如今俱往矣,当我们历尽沧桑站在白求恩故居前,我们宁愿相信白求恩是人,而不是神。
选自杨文、裴小敏主编《被历史忽略的历史》王伟 文
路翎:作为战士的悲剧
我想把汪曾祺和路翎二人做一个对比。其实,汪曾祺和路翎并没多少可比性,他们的性格、阅历、境界大相径庭。之所以把他们拉在一起,是因二人在浩劫之后的巨大命运反差。两个作家,同为江苏人,年龄相若;以文为生,起步都很早。1940年代,路翎的文名怕还要高过汪曾祺。同其他绝大多数作家一样,在1949年至1976年,两人几乎处于封笔状态(汪曾祺的状况稍好一些)。 1980年代初,两人重新提笔写作。汪曾祺频出佳作,大器晚成,暴得大名;路翎却雄风不再,戮力而为之后,亦不免雷声大,雨点小,没几篇可拿得出手,让人不由得扼腕叹息,为之遗憾。如果说汪曾祺的劫后余生是新生,路翎的劫后余生则是继续消亡之路。两人再次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征途,可谓机会均等,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路翎,男,1922年生,原名徐嗣兴,江苏南京人。16岁时开始给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投稿,得到胡风的赏识。他先后创作了抗日小说《要塞退出之后》,反映矿工生活的小说《家》《祖父的职业》《何绍德被捕了》《卸煤台下》。1942年,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让他一举成名时,年仅20岁。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胡风屡次作文介绍路翎,对其倍加提携。1945年7月,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出版之际,胡风郑重宣布:“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
路翎的作品在40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有青年给路翎写信说:“路翎先生,你底火辣辣的热情,你底充沛的生命力,你底精神世界的追求力、拥抱力,惊人地震撼了求进步的青年人的心。”
1949年以后,路翎先后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他激情满怀地写了“歌颂新时代”的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但是,他的作品遭到了猛烈批判。胡风越执着地挺他,以周扬为首的文坛当政者就越凶狠地批他。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直至1955年胡风被钦点为“反革命分子”,路翎作为胡风多年至交,自然首当其冲被列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遭到抄家和逮捕。在监狱里被关了10年,1965年才保释出狱。出狱后,路翎写了39封上诉信,“恶毒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久又被收监。在此期间,他被当成精神病患者送入医院接受电疗,大脑严重损伤。直至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接到消息时,他正在扫大街。
这以后,路翎重回文坛,被邀参加各种文坛盛会。他勤奋笔耕,写诗写小说,但除了偶尔几首小诗见报外,长篇小说没有一部出版。当年的少年才子落了个江郎才尽的凄惨下场。
相比之下,汪曾祺却要幸运得多。汪曾祺,1920年生,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中文系教授沈从文的热心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50年调回北京,任《说说唱唱》杂志编辑,偏安一隅,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举动。1958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1962年调北京市京剧团任编剧。“文革”期间被江青点名参与样板戏《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其小说《大淖记事》《受戒》《异秉》等恬淡清新,多次获奖。他还潜心画画,研究美食,为人潇洒清通,颇具六朝风骨,人称“最后一个士大夫”。
路翎晚年写了很多东西,但看到其子徐绍羽列举他晚年的长篇小说名录却不能不让人尴尬。“1987年,父亲65岁的时候写作反映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长篇小说《江南春雨》;1988年写作表现针织厂建设题材的长篇小说《陈勤英夫人》;1991年写反映待业青年与当代青年的建设精神的长篇小说《早年的欢乐》;逝世前他一直在写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计190万字。但这些鸿篇巨制的文字都是无法出版的文字。”(《闲话》第4辑第10页,青岛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可以看出,作者紧跟形势,乃至图解政策的意图是很强的。这样的结果,诚然与二十多年的迫害有关,他囿于特殊语境下的特殊思维方式而无法摆脱。汪曾祺在“文革”期间,环境要宽松得多,有一种延续下来的自由惯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1980年代新的境况下,路翎的被迫害使得他可以轻装上阵,汪曾祺在“文革”中的“得势”却让他要背负一定的历史包袱。这样一来,双方算扯平了。如果追根溯源,打量一下他们40年代的写作,就会发现两人在劫后的写作依然延续了起步时的路数,轨迹并没被打断,更没有改弦更张。
从《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到后来的《江南春雨》《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你都可以看到居高临下、宏大叙事的态势。不是说宏大叙事不好,而是路翎一出道就被“使命感”困扰了。他出道时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无论站在哪一方,只要立场坚定,就能获得关注,对立阵营越打压,在本阵营获得的鲜花和掌声就越多,这甚至与作品本身质量关系都不大。以后,社会进入一元语境,获得了当政者的认可,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作家们以之为写作的捷径与准则。胡风、路翎们尽管与曾经的“主流话语”发生冲突,但他们要取悦当政者的心态并没有变。在跟“主流话语”叫板的过程中,自己更是深陷当政者的思维语境,无法自拔。汪曾祺则不然。有人这样分析汪曾祺的成功之道:“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从汪曾祺1943年出版的《邂逅集》,到1963年出版儿童小说集《羊舍的夜晚》,再到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论文集《晚翠文谈》等,莫不如此。他的关注人性、以人为本,一以贯之。与胡风、路翎们的高度关注政局、形势区别甚大。
一元话语时代,当政者的话语体系和草根的话语体系必然对立。只是在高压状态下,不见草根发声,只听得到当政者的声音,似乎他们代表了全体;形势一旦发生松动,两者分野成为大势所趋,作家要想取悦一方,就很难再取悦另一方,谁也别想里外通吃。而路翎,自始至终就没离开过出道时的语境,最终被大舞台所淘汰。这就是路翎作为战士的悲剧。
汪曾祺的成功则是纯文本的胜利,与他相似的还有同样大器晚成的张中行。这并非以暂时成败论英雄,而是因为,无论怎么讲,文学还是有自己的一定之规,有自己特殊的存在形式。
选自《湘声报》2008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