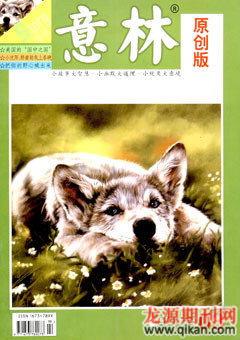“赵括为将”谁之过
邓忠强
赵括为将,全军覆没的故事,说的是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不仅赵国主将赵括被箭射杀,而且还搭上了45万士兵的性命。后世以之为戒,教训是深刻的,赵括成了“纸上谈兵”的典型,常为人们所诟病。然而,重读《资治通鉴·周纪》,又让我觉得任用赵括的赵孝成王也同样难辞其咎。他本不该把一个只知夸事其谈却毫无实战经验的人放在重要岗位上,可他却偏听偏信,拜赵括为上将军。
原来,驻守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抵挡秦军进攻的是沙场老将廉颇。廉颇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他认为秦军远道而来,粮草供给不便,必难持久,于是命令赵军“坚壁不出”,不管秦军如何挑战叫骂也不出来应战。双方对峙了四个月。秦军久攻不下,进退两难。可赵王却求胜心切,屡屡责备廉颇胆怯不战。这时,秦国丞相范雎使了一计,他暗中“使人行(行贿)千金于赵”。赵王身边的人被收买后,就在赵王面前散布輿论说:“廉将军年纪大了,哪儿还敢跟秦国打呢?要是让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秦国就害怕啦!”秦国施行这一“反问计”,要害在于除掉廉颇,好让赵国换上他们容易对付的赵括。果然。赵王轻信左右的议论,更加深了对廉颇的不满,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
丞相蔺相如这时抱病在家。听到这个消息,就急忙面见赵王说:“赵括虽是名将赵奢的儿子,可惜他只会死读他父亲遗留下来的书本,不会随机应变(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大王怎能因为他有虚名就加以重用呢?”可是赵王的头脑如同胶柱鼓瑟,死抱着一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来识人用人。他重“名”轻“实”,也就不去考查赵括这个人是不是名副其实,反倒以为“将门出虎子”,赵括也一定会像赵奢一样带兵打仗,所以他很容易相信赵括的海口狂言,当然听不进蔺相如的意见。
就在赵括要动身的时候,赵括的母亲上书给赵王,请求赵王别派她儿子去。赵王把她召了来。问她什么理由。赵母说:“他父亲临终时再三嘱咐我说。‘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看做儿戏,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如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我们一家造了灾祸还在其次。只怕国家断送在他手里。所以,他父亲让我把‘括不可使这句话转告给大王,一定不能让他当大将啊……”
赵母还根据自己对儿子的观察,说了第二条理由。她说:“他父亲任将军时克己奉公,‘不问家事,凡是大王赏赐的财物,全都分给军中的文武官吏:可是他一旦为将,就将大王所赐的金银布匹拿回家里藏起来,而且还每天察看好房子好地,能买的就买下(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不在战事上运筹帷幄,反而一门心思忙于私利,怎么能当大将?”
显然,当时的赵括不光是纸上谈兵,而且贪婪之心已开始滋生、膨胀,无论是“才”还是“德”都不堪重任。因此,赵母再三劝阻,提醒赵王别以为赵括像他父亲。其实,他父子俩在心智品德上判若两人。这番话言词恳切,触及问题的根本所在。按说。“知子奠若父母”,赵母和赵奢两人对自己儿子的了解比蔺相如更直接更具体更深刻,也最有发言权,这总该使赵王翻然醒悟了吧,可赵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竟然说:“老太太,你不要再说了,我已决定啦!”
赵括的悲剧,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赵王用人的悲剧。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古代君主专制条件下虽然不可能实行民主的选贤任能机制,但赵王如果是一个智者,察人用人时不那么刚愎自用、主观独断,能够虚心纳谏,循名责实,也许就不会为华而不实者所惑,以致铸成大错。
——首届“赵王杯”全国小小说征文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