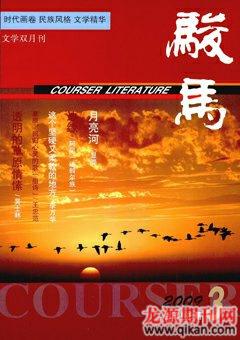一堵白色的墙(外两篇)
辛 杰
背对黄昏,隐没在霞光中的坡路一直通到那堵白色的墙边。
如果我站立在墙边,在日子重复着日子的单调声中,龟裂的泥墙,以一种独特的姿势极其清晰地吸收着我影子的重量,我就会听到,当午后的阳光使一切都安然入睡,那堵白色的墙便会像一名悠然而醒的老者,带着汹涌的潮汐的声音,一伸一缩,直挺挺地朝我走来,伴随着海鸟跌落浪尖的呻吟,以及海潮迎面扑来的温馨气息,都在诉说着同一个古老的故事。
我惊奇地环顾四周,没有大海和波涛的私语。这里是一座宁静的村庄的古庙遗留下的惟一一截残壁。在幽静清冷的松树林里,怀抱着所有梦想和希望。在一望无际的郁郁葱葱的绿色中,就连刺目的阳光的呼吸,都被松林的清香所占据。不过,刺目的阳光在激射着点点银光,像一颗又一颗星星冉冉升起在沉沉的海面,焕发着一种激情,使我再也不忍用那双粗糙的大手,去抚摸那圣洁的墙壁了。
啊!你会相信吗?这堵赤裸的墙壁,曾经波动着一个阔大而无比壮观的海洋吗?
我静静地注目观视——
微含着海藻气息的冷风,滑动在微微颤动的空气的表层,吹动着残冬那忽冷忽热的面庞。我知道,古松树的青翠正含着一首苦涩的歌,由远及近,渐弛渐缓,正隐约地向寒冬拉开战斗的序幕。
擦鞋者
黄昏降临了。
降临了的黄昏,拖着蹒跚的脚步像秋风中一片干枯的枫叶,随手被人抛弃一样。缓缓地、带着浓重的背影,笼罩着每一个人对生活做无休止的战斗后,令人陶醉的激情。一切开始变得生动起来,有梦的石头开出灿烂的花朵。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言谈和交往,都在黄昏的喘息中,不断沉沦。
可这时,我却在霞光穿透云层的血一般的苍穹下,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擦鞋老人。他肯定已许久无所事事,正埋头擦着自己的皮鞋。那双皮鞋破烂不堪,就像那位老人脸上的皱纹一样很难抹平、擦亮,变得年轻起来。他擦得是那么仔细,凝聚起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专心致志地擦着自己的皮鞋,就像在别无选择地为他人服务一样,从容、自信,一块皮革接着一块皮革。那双皮鞋终于在那条幽静的林荫道下,散射着熠熠光辉,令人惊叹!
我也应该去擦一擦自己的皮鞋,我毫不犹豫地向那位老人走去。老人擦起了皮鞋,动作轻柔而有力。他弯曲着背,用除尘的毛刷狠劲地清除我皮鞋上每一处微尘。这使脚跟、脚背和趾尖,都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和惬意。然后,他用那双干枯的大手,轻轻地、一点点地挤出指甲盖大小的鞋油,认真地、仔仔细细地、完完全全地涂抹到鞋面上,一直到脚踝的部位;对每一点鞋油他都小心翼翼,绝不会在鞋面的同一个地方涂抹两次。最后,他甚至将皮鞋举到眼前,就像欣赏一件完工的成熟的艺术品一样。随后,他非常有力而稳健地为我把鞋带打了一个结,用近乎庄严的动作紧了紧。当他驾驭着那两把鞋刷交替在鞋面上游走的时候,他的动作变成了一幅肖像,那件被鞋油弄黑的衬衣,也变得格外醒目。鞋刷的擦拭声,像一种绝美的、华丽的、令人激动的天籁之音,穿透秋风瑟瑟的黄昏,响彻大地。
而此时,林荫道旁那些嘈杂、嬉闹、欢乐的人群,却伴随着老人微颤的肩头,在轻轻地奏鸣着,如醉如痴地享受着一切;在我面前是老人晃来晃去,只剩下一圈白发的圆圆脑袋和积满灰尘的头发。每当我应该换脚的时候,老人便用一把好像是特意准备的小刷子有力而快捷地敲打着他的鞋箱。皮鞋从未像现在这样亮过,但他是以极小的动作幅度,很大地抖擞干净,然后滑过鞋的贴皮——只是在这里——他才长出一口气。于是,从皮面上,从皮革最狭窄的,第一次显露出来的条纹和裂痕中,便发出最后一道额外的闪光。此时,那位老人已完成了他的作品,并短促地敲击示意。
我像一个逃犯似的扔下钱,急促地逃离那条血色的林荫道。我不知道我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去看待那位老人,但我知道,命运之手已在那位老人的身上再次显示,毫无办法。从那时起,那双锃亮的皮鞋再也没有在我脚上穿过。
暮色中的朋友
走在秋天最后的一个日子里,我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远去。在暮色逐渐浓重的时候,他缓慢地像落叶一般地消逝在苍茫中。
秋风就那样随意地刮了起来。
我转过身来,回到那条通往郊区的道路。这是一条连接我和这个城市的惟一纽带,就在这条通往郊区的道路上,有我深恋的故乡。多年来,我总是在这个时候出来散步,这种独自享受的娱乐,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渐变得模糊,想甩也甩不脱。从城市到郊区,不仅仅是空间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有一份恬淡和乡思的心情。每当我踏上那条熟悉而陌生的乡村道路,我总有经历沧桑和幸福的感觉。
就在三天前,就在这条乡村道路旁的小酒馆里,我遇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旧友。我们热情地握手,彼此拍着肩膀坐了下来,随后斟满了酒,一饮而进。我没预料在这种与世不入,而近乎做作的地方会遇见他。听朋友们说,他如今已然腾达。正是在这个破旧的小酒馆里,我们谈起了分别后各自的生活。想不到当年彼此间的亲密,看来已被过去的时间所切断,留下的惟有空洞的记忆。在酒馆昏黄如烛的灯光下,他给我留下他的住址,说有空去喝酒。
就在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忽然想到了那位年轻的朋友。在一个暮色笼罩的黄昏,我骑上自行车,通过打听到达了他的住所。这是一片还没有改造的老城区,破败的房屋,横七竖八地胡乱停放的自行车,污秽的马路上,永远散发着黯然之光。树很少,成片成片的房子挤在一起,挤成一条窄窄的小马路。我轻轻地敲了门,朋友走了出来。在房檐浓重的阴影下,他的目光显得迷离。就在那时风刮了起来。我推开门时,发现空荡荡的房间里,除了几个高大的书架和一张单人床,还有孤独的写字台外,大概只有那把老式藤椅了。这把老式藤椅是一位大学同学送给他的;更早以前,朋友也许只有一个人坐在屋中,边读书边朗诵着叶赛宁的诗。现在它就安稳地平躺在那里。朋友向我提起这把椅子,那已是坠入遗忘之谷的往事了。我们喝着酒,想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酒毕,从朋友低矮的屋檐下走到铺满石板的小马路时,朋友的脸因过量的酒而显得苍白,一缕额发垂下来挡在眉前。朋友至今仍孑然一身,除了和书籍相伴之外,生活已经过早地在他的额际刻下一条条烙印。我握着他的手,拥着他的肩,狠劲地拍着他的后背。此时,夜幕已降临,没有路灯的小巷中月光尤为清冷。我踱出小巷转过头去,看到朋友依然倚在门口,脸上依稀还是对饮时那种恍惚不经的笑,我的心一阵痛楚,勉强朝他挥了挥手。
在我骑车离开老城区后,一阵难以抑制的晕眩使我停了下来。我握着冰凉的自行车把站在老城区的巷口。这时,我又看到了月光下的老城区,泛着难言的凄清之色。大概已是午夜时分,街上静悄悄的,只有我的背影显得格外沉重。这种感觉让我吃惊。无疑我想到了许多,并且无数次地在梦中见过,但我已无法回忆。
回到宿舍,我没有开灯就睡下了。
没有开灯的夜晚,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走进我的记忆,在我烈酒翻腾的脑海中,这种不真实感一次又一次浮上我的心头,让我心悸,让我悲哀。我的乡村已经不见,惟有朋友的脸在梦中反复升起又降落,犹如一个镜头的反复推进或拉开。刺鼻的白酒味夹杂着朋友失意的笑声,让我从梦中一次次惊醒。朋友们对我说起他已腾达,只不过是一个谣传而已。这个玩笑的恶劣程度,并不亚于朋友喝酒时那种孤单的姿势。
那么,谁开的这个玩笑呢?朋友们都不是恶意的人,我想不通。此后的几个月中,我在梦中反复看到朋友苍白的脸,猝然闪现又逐渐远去的情景。日常生活总是充满了无谓的繁琐细屑,我思忖着再一次去老城区,再一次看看我年轻的朋友,最好带上一瓶酒对斟,可我喟然而止。往事并不能帮人找回自己,相反它让人再次失去自己。
在我独自一人走向乡村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背影,在苍茫的暮色中,时隐时现在老城区的瓦房之中。暮色将他的轮廓逐渐消解在周围的事物之中。朋友的身影也越行越远,直至隐没在灰白的石板路和暮色里。就在秋夜的烛光里,我和一位来自草原的不善言谈的朋友,谈起了许多往事,流露出少有的深情与伤感。那天送别朋友之后,我看着那对蜡烛,一时感到无比的奇妙,就是那颗跃动的火苗,竟然改变了我们俩整整一个夜晚。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