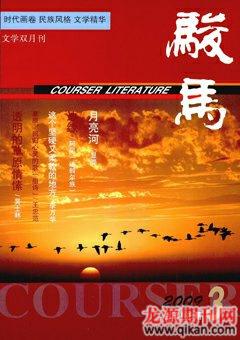捐款
闫耀明
当瘸子老五的事被人们传得像炊烟一样飘满巴村的每一个角落时,他正弯着灰毛虫般的弓腰给玉米撒化肥。茂密的玉米长成树林的模样,让老五在沉甸甸的感觉中看到欣喜正飞虫样地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发出余音袅袅的嗡嗡声。玉米林中热粥一般粘稠的空气使得老五那张核桃一样的瘦脸上分泌出无数颗汗珠,从容而缓慢地在他的脸上流,痒痒的感觉便一点儿一点儿地爬过他的脸颊,一直爬到他的心里。“该死的空气,要闷死人么?”他骂着。
钻出玉米地,迎头落在脸上的雨点儿先是让老五愣了一下,然后他的脸上就有一些笑容很生动地走过,像草地上觅食的漂亮鸟儿在一下一下地跳动。雨季终于来了。下吧,下足了化肥才使上劲儿呢!
往村子里走的时候老五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但他的心情就像这雨一样快活。走上用水泥预制板搭成的小桥时他差一点儿摔倒。因为水泥板搭得很不牢固,有人走动就一扭一扭的,腿脚不好的老五走起来就更加不顺畅。虽然河水很清很浅,老五还是吓了一跳。他跌跌撞撞地逃过小桥,进了村。
站在屋檐下,老五脱去了已经湿透的上衣,递给老伴,转身进屋,脱去了同样湿透的裤子。老伴看见赤身裸体的老五,就在他没有多少肉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哎哟,你这个缺德的老五,大白天的你咋扒得精光!”
门一响,麻村长拎着一把破雨伞走了进来。老五慌得像一只土蜂东撞一下西撞一下,却找不到可以遮羞的东西。麻村长不耐烦地摆了下手,说:“行啦行啦,又不是大姑娘来了,你慌啥?”
窗外的雨很从容地下着,雨滴飘到玻璃上,密密麻麻地抖着。
“我听宋大说,你在市里给希望工程捐了二百块钱?还上了电视新闻?”麻村长问。
老五说:“捐款这事有。我上县农电局要下了三千五百块钱工程款,在街上正遇到捐款的事,就捐了。但上没上电视我不知道,我没看新闻。”
老五的儿子组织了一个小施工队,在市里承揽一些小的工程干,效益还不错。
麻村长指点着老五的脑门,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老五你是不是疯了?那二百块钱咋说捐就捐了?”
老五这才注意地看麻村长的脸。一看他就吓了一跳。几十年了,他看惯了麻村长的脸,什么表情有事什么表情没事他一搭眼就能看出来。老五的心就开始慌,像窗玻璃上不停跳动的雨点儿。
“你个傻老五哇,你是聪明人咋办糊涂事?你没动动脑子,那二百块钱捐出去了能花在哪儿?落到咱杨树乡能有多少钱?落到咱巴村能有多少钱?毛儿都没有!咱村张寡妇家的孩子不是辍学了吗?正放着羊呢。村西边老曹家的曹二不是也不念了吗?你把那二百块钱花到咱巴村该有多好!”麻村长数落完,转身就走了。
上电视新闻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瘸子老五身上,多少有些令巴村人感到意外。所以,当靠跑运输发家的宋大说起这件事时,人们以为他在开玩笑。宋大急了,说:“我亲眼看见的,那个采访老五的是个漂亮的女记者,穿着粉红色的连衣裙。”
当晚上九点市电视台重播当天的新闻时,几乎每个巴村人都坐在电视机前,盯着荧光屏。
这天晚上,巴村人都很晚才入睡,大家都在议论老五捐款和上电视新闻这件事,老五成了人们嘴上出现最频繁的字眼儿。
雨依旧下得很有耐性,这种耐性是人类无法企及的。可此时的老五却没有什么耐性了,他坐在炕上如坐针毡,心里一绞一绞的怎么也平静不下来。麻村长那几句话、那不悦的表情,都让他火烧火燎地闹心。他原本良好的心情像雨中疾飞的紫燕一样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心里比眼前的铅灰色云层还要压抑。
窗外一阵汽车喇叭响,乡里的高书记和宣传委员小马走了进来。高书记经常下村,跟老五很熟。他一进门就说:“老五哇,看了电视我这个主管文教的副书记都觉得脸上有光啊!我代表杨树乡党委谢谢你呀!咱杨树乡的普九任务是全市最重的,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乡里的财力太有限,有些事情因为资金不足而办不了。下一步我们准备加大力度,动员全乡的力量,打一场普九攻坚战。你在市里捐款的事是一本活生生的教材,乡党委决定大力宣传你的事迹。”他指了指小马说,“小马是搞宣传的,负责把你的事迹宣传报道出去,让全乡人都来向你学习。”
接着小马拿出本子,对老五进行了采访,不仅谈了捐款的情况,而且重点挖掘了老五对捐资助教和致富不忘乡亲的思想认识。临走,高书记握着老五的手说:“虽然你在市里捐了款,上了电视,如果你有能力,还可以为本乡、本村的教育事业做更多的贡献。”
高书记的到来,像云层中射出的一缕阳光,在老五的心里照出了点点亮色。窗外的雨不再使他心烦意乱,他美滋滋地吩咐老伴儿炒两个菜,中午他要喝两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还上了电视,成为全乡人学习的榜样,他能不高兴吗?他的嘴上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小曲儿。
可哼着哼着他突然不哼了,他反复想眼前发生的事情,越吧嗒嘴越不是味儿。他想起麻村长说起孩子辍学的事;想起高书记说希望他为本乡本村教育事业做更多贡献的事,他的心里就忽悠一下。他感到这件事到现在远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麻村长认为自家的肥水流进了外人的田,他不会就此放手的,下一步说不定会打他手上的三千三百块钱的主意。他赶紧拿出三千块钱,装进上衣口袋里,说:“我去一趟乡信用社,把钱存上。”老伴儿说:“快中午了,你还去?明天再去吧!”老五坚决地说:“不行,现在的事情变化太快。”
老五披件破雨衣,刚刚走出门,差点儿撞在一个人的身上。是麻村长。
“急三火四地干啥去?”麻村长问。
老五的心里暗自叫着糟糕,嘴上却说:“没啥事。村长有事吗?”
麻村长嘿嘿地笑了两声,说:“你是不是去乡里?你是去把那三千多块钱存在信用社吧?”他用脚踢了踢地上的石子,“你想干啥我都猜得一清二楚。”
老五突然有了一种被麻村长轻蔑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是全乡学习的榜样,连高书记都来看自己,他能受这个气么?他就有些不高兴,问:“那么村长,我去信用社存钱,还需要向你这个村长请示吗?”
麻村长一愣,他第一次听到老五这样不客气地对他说话,几十年了这是头一次。他把脸沉下来说:“老五,你这是什么话?今天我来找你,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村那几个辍学孩子的上学问题。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商量?还不是因为你老五出了风头,上了电视?我这是高看你了。你别忘了,我看在你腿脚不好的份上,农业税等各种税费可都没有收你的。我提醒你,这件事老五你要办不好,可没什么好处。”说完,麻村长气哼哼地走了。
老五愣住了,呆呆地站着走不动路。
老五心里清楚,麻村长说的没错,这么多年了,老五从没交过各种负担费用,麻村长对他是很照顾的。他觉得这样跟麻村长对着干不太妥当。
可商量孩子辍学的事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商量?实际上就是来让我掏钱!这三千块钱必须马上存上,不能耽误!
老五再次披上破雨衣,抬腿就往外面走。门一响,张寡妇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她的儿子。
张寡妇苦着的脸像一只用水浸泡过的青萝卜:“五叔哇,我可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啦。这孩子都十岁了,还认不了几个字呢。五叔,你在市里捐了款,又采访又上电视的,名利都有了,啥也不缺了,你就伸把手,帮帮咱自己的孩子吧?”张寡妇说着,擦了擦眼角的泪。
老五勉强装出笑容来,说:“我儿子搞工程是挣了点儿钱,但那钱挣得不易呀。要说捐款,我原来没打算捐,但赶上了,我才捐的。其实上不上电视是无所谓的。”
“现在你是全乡学习的榜样了,能眼看着孩子一天天大了上不了学吗?”说着张寡妇拉过儿子,“快给五爷鞠躬。”小孩子走到老五面前,一边道谢一边一下连一下地鞠躬。
老五一看这架势,受不了了。孩子的道谢声针一样扎他的脸。“别,别这样。五爷给钱。”他从兜里摸出一张百元票,递给张寡妇,“让孩子上学吧。”
张寡妇千恩万谢地客气了一阵,走了。老五却气得不行。他知道张寡妇带孩子来是麻村长的主意,但老五不敢惹麻村长,说到底人家是村长,要免去各种税费麻村长一句话就行。目前看只要把钱存上,手上没了钱,再来他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爱咋咋地了。说走就走,老五又向外面走。可他刚到大门口,就被曹二和他爹曹大头给拦住了。
曹大头点头哈腰地冲老五笑:“五哥,忙哪?有点儿事想和你说说。”
老五装出极不耐烦的样子,说:“你没看我正忙着?等我回来的吧!”
曹大头拦住老五,说:“五哥,就说几句话不行吗?”
老五看着愁眉苦脸的曹大头,真是哭笑不得。他说:“是不是要钱?”
曹大头笑了笑:“兄弟也是没办法。我常年有病,成药罐子了,这孩子就没法上学了。你儿子这几年搞工程挣了钱,兄弟想来想去只好舍个脸来麻烦五哥了,看在这孩子的份儿上……”
老五说:“我儿子的工程队也是很难啊。现在水泥、红砖等建材的价格一涨再涨,户主还老是拖欠工程款迟迟不结算,我们也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你没见我的日子也是紧紧巴巴的?”
曹大头依旧笑:“五哥,咋说你也是个体大户,拔根汗毛也比我的腰粗。再说了,我就是有一点儿办法,也不会来向你张口哇!”
老五无可奈何地回到屋里,拿给了曹大头一百块钱。
此时老五已经没有精力去为曹大头生气了,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麻村长精心设计出来的,他很可能会按照这个办法继续搞下去。老五渐渐觉出自己的势单力薄,麻村长的计划像这讨厌的雨一样无法抗拒。
而此时时间已是下午三点了,乡信用社该进行账目清点了。今天老五是没法存上钱了。
老五胆战心惊地吃完饭,很怕谁再来敲他的门,不等天黑,就早早锁好大门,连电视都没看,闭灯睡觉。
第二天早晨,老五连饭都没吃,穿上雨衣就出了门。走过村头的小桥时,他看到河水涨满了许多,也浑浊了许多。他小心翼翼地走过桥,直奔乡里去。当老五一拐一拐地走到乡里时,见信用社的大门还没有开,心想今天这钱是存上了,就在门前等着。
雨依旧下得不紧不慢,细密的雨丝均匀地从天上落下来,在他的雨衣上走出一串清清脆脆的脚步声。信用社门前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有的与老五高声地打着招呼。老五的心又悬了起来,他是怕遇见巴村的人。信用社还不见有人来上班,他就向里面望,见一个白发老人正坐在值班室里,就喊了一声。
老人走出来,头上顶着一把圆扇子,说:“要存钱吗?你今天来不是白来吗?今天是星期六,信用社的人都休息。”
老五一听,心凉半截,心想这事情咋这么不顺呢?他站在那儿想是不是回家,蓦地想起今天是乡里的集日。“我说马路上咋那么多的人。”他自言自语着,用一只手捂着腰里的三千块钱,一拐一拐地向集市上走去。“回家?回家只能是被动地等着给人家拿钱,说不定今天麻村长又得派人上门要钱,现在的人为钱个个都能舍出个脸。我先到集市上去转一转,下午再回去。”他想。
集市上的人并没有因为雨季的来临而减少,相反,撑着各色雨伞到集上来转的人像蘑菇一样挤作一团,卖东西的和买东西的都在雨的冲洗之下变得鲜鲜亮亮。老五毫无目的地走着,他不想买什么,只想在此消磨时间。在卖水产品的摊床前,有卖活鱼的,他就停了下来,看新鲜。在一只很大的铁箱子里,一群鲤鱼正欢快地游着,买主看中了哪一条就给捞哪一条。正看着,一个买完鱼的人站起身,抬头看见了老五,就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这不是老五吗?赶集来啦?”
老五定睛一看,是高书记,忙笑着说:“随便转转。高书记买鱼呀?”
那鱼很大,在塑料袋里很不老实,蹦来蹦去的高书记都快拿不住了。老五蹲下来帮高书记把塑料袋系上口,鱼才安稳。高书记说:“昨天晚上我们开的班子会,统一了意见,决定树你这个典型。今天宣委小马就在乡里打印你的事迹材料呢,下一步发到各村,好好造造声势。老五哇,我得感谢你呀,在咱乡普九最关键的时刻出了你这么个典型,乡里的工作就好做了。这绝不仅仅是二百块钱的事情,它的意义大得很呀!”
听了高书记的话,老五心中一喜,说:“何止二百呀,昨天我就又拿出了二百块钱资助了巴村两个辍学的孩子。”
“是吗?”高书记眼睛一亮。
“高书记我能骗你吗?”老五说,“钱是我拿的,张寡妇和曹大头,一人一百。”
“好!”高书记挥下手,“咱的典型又有了新的事迹。我这就回家给小马打电话,让他把这件事加到材料里去。”说完,高书记就走了。
老五在集市上又转了一阵,觉得腿脚都有点儿乏了。他看看表,见快中午了,自己早上没吃饭,早就饿了,便在集市旁边找了一家小吃部,要了一碗面条,慢条斯理地吃。吃完了,集市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他这才没精打采地往回走。
第二天早上,老五在门前看雨。雨下得跟前几天一模一样,看不出一点儿区别。院子里已经积了一片雨水,老五就想,大概今年要发大水了,已经好几年没发过大水了。雨季到了,该是发大水的时候了。
这时麻村长喜喜地进了院,手里拿着一大叠材料。看见老五,就情不自禁地说:“老五哇,你看你看,乡里的材料发下来了。小马的水平真是不低,把你的事迹写得特别突出。”他把材料递给老五一份,“乡里要求各村组织学习,我先给你送来了,让你高兴高兴。”
老五心想:“高兴个屁,这是我花四百块钱换来的。”他接过材料,翻了翻,没吭声。
麻村长指点着材料,说:“你看看结尾处写得清清楚楚,乡党委专门立会研究做出的决定,号召全乡人向你学习。老五,你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啦!”
老五的心里满是不高兴,他把材料卷在手里,说:“啥人物不人物的,是人物了乡里也不给发奖金。我根本没当回事儿。”
麻村长指了指老五,说:“这样的事你不当回事儿还行?我想成个人物还没这个条件呢。”两个人走进屋里,麻村长说:“咱巴村出了你这个先进典型,完成普九任务咱也要走到全乡的前头。不过老五,我还得跟你说个事。昨天村小学校的刘校长找我了,说有七八个适龄儿童不能上学,家访了好几次也没有效果,家长都说条件太差。而上面的要求又不允许有一个学生辍学,事情就卡在这儿了。所以,我想你既然风光了上了电视,就帮人帮到底,把几个孩子的学杂费给解决一下吧。村上太穷,拿不出资金来,学生不上学又不行,我可是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老五坚决地说:“我已经前前后后拿出去四百块钱了,这回,我是说什么也不能再拿钱了。”
麻村长笑了一下:“老五哇,你咋就看不透这个关系呢?现在普九正在关键时刻,各村都有一个资金问题。咱巴村就这几个学生的学费问题解决不了,并不是要花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这个典型就更有说服力了。你的名气大了有多值钱你想过没有?以后村里、乡里有事情还能少了找你商量?农民税费的征收我不就更有借口为你免了吗?将来说不定当个人大代表或是政协委员啥的,结交的市里名人就更多了,这对你儿子在市里搞工程得有多少好处呀?这些账你咋不算算呢?”
老五闷闷地没有说话,他觉得麻村长说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正沉着头琢磨,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四个人。领头的是宋大,一进门就向老五道喜:“老五哇,恭喜你呀。”他指着身后的三个人说,“老五我给你介绍,这三位是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的领导,张会长、宋副会长、田秘书长。他们来是向你宣布一项任命。我是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他们就找到我,让我领着来了。”
张会长与老五握手,把一份文件递给他:“我们个体劳动者协会听宋大介绍了你的情况,特别是听说你为希望工程捐款的事之后,感到你是一位有责任感、思想觉悟比较高的个体业者。在与你们杨树乡党委沟通情况之后,我们开了会,研究了你的任职问题。最后大家取得一致意见,根据工作需要,决定任命你为市个体劳动者协会杨树乡分会的副会长。咱们个协是群团组织,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热心人来做工作,将全市的个体业户管理起来,为繁荣我市经济做出贡献。”
老五看了看文件,愣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副会长。
麻村长在一边拉了拉老五,说:“愣啥?快请市里领导坐呀。”
老五这才招呼几个人坐下。田秘书长从包里拿出一张表格,说:“这是任职呈报表,一式二份,你抽空填上,然后我们给你建档案。”
几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宋大一看表,说:“老五哇,快中午了,咱们请市里的领导去吃饭吧?”
老五看看表,才十点多钟,便在心里骂起来,该死的宋大,你也来凑热闹琢磨我手里的钱。他的脑子里乱糟糟的,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把他搞蒙了。他咬咬牙,说:“吃饭去。”几个人走出屋,宋大问:“咱上哪儿去吃?”
老五想,市里领导来了,既然招待了就招待好。他说:“上老金家饭店。上饭店吃显得热情。”
金家饭店在巴村村头公路边,生意一直不错。餐厅里有不少过路的客人正在吃饭,显得热气腾腾。老金给他们开了个雅间,打开电风扇,接下来就一个接一个地上菜,凉菜热菜摆了一桌子。
田秘书长有很好的酒量,喝得兴起,给一直推辞不喝的老五也倒了一杯。麻村长说:“老五你真的应该喝,全乡人都在向你学习,这可是个了不得的荣誉。今天市里的领导又来任命你做副会长,这叫双喜临门哪,不喝还行?”
大家一连干了三杯,老五就有点儿晕,头也疼得厉害,说啥也不喝了。几个人也就不再让他喝了。麻村长一边喝酒一边向市里领导介绍了老五在村里捐资助教的事迹。宋大在老五的肩上拍了拍:“从今天起,老五就是杨树乡分会的副会长了,今后我这个会员要在老五的领导下来开展工作了。一个村住着,我宋大是个明白人,以后副会长有什么事情,你就吩咐一声,由我去干。我有车,办起事情来方便。”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起身离座。老五说:“我去把账结了。”他是从内心往外不想说这句话。但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他想推也推不出去。麻村长打着饱嗝说:“今天老五应该请客。”
送走客人,老五在路边站了一会儿。雨已经下好几天了,丝毫看不出有停止的迹象,雨季的所有特点都可以很容易找到。老五的雨衣破了,有水流进他的脖子里,凉凉的,使他重重地打了个寒噤,忍不住想尿尿。
村子里的路很泥泞,老五的腿脚不好,加上他的头晕,还疼,走路就更加不顺畅。他想:“饭店做的饭菜应该不错的,但我咋就没有品出香味儿来呢?”这顿饭,花去他三百块钱。从衣兜里往外拿钱时,他的手都有些抖了。
此时老五思前想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捐完款接受记者采访是个天大的错误。“如果没人知道我捐款的事,能引出来这么多的麻烦?前后已经花进去七百块钱了,事情还没有完。麻村长不是说村上还有几个孩子的学费由我来负担吗?”那种后悔的感觉像一只毛毛虫令人生厌而又固执地在他的脊背上不停地爬来爬去。
其实老五不是那种一分钱捏出汗来的小气人,如果真是为资助孩子上学,他还是舍得花钱的。但现在的情形让他越来越感到这钱花得有些味道不对劲儿。
“唉——”走在雨季里的老五长长地叹了一声。
他像一只疲惫的鸟儿,走得没精打采,有人跟他高声打招呼也没有听见,他的耳朵里充满了雨落下来时让人烦躁的沙沙声。
老五身体一晃一晃地拐进了自家的大门。
然而抬起头来的老五立刻就愣住了,惊愕使他的身体像一根干枯的木桩,直直地呆立在那儿。
细雨中他家的院子里站满了人,有的举着没了颜色的雨伞;有的披着没了颜色的雨衣;有的头上戴着锯齿一样破旧的草帽;有的头顶着一件看不清颜色的旧衣服;有的人干脆什么也没有,静静地站在雨水中……
老五看到这是他十分熟悉的面孔,尽管在雨中这些面孔有些变形,但老五仍然能看得清他们。
“这……这是干什么?”
老五愣愣地看着众人,嘴里发出惊异的叫声。可他的声音一出口,就被雨淋湿了,变了声,听上去那么陌生。
转眼间从人群中挤出了一个男孩子,接着又挤出几个男孩子和女孩子,一群孩子跑出来,站在老五的面前。他们都是黑胳臂黑腿的小孩子,乌黑晶亮的眼睛眨着,看着莫名其妙的老五。
不等老五开口,小孩子们就开始恭恭敬敬地给老五鞠躬,同时发出清脆脆的一声喊:“五爷!”
老五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逃出院子的,有一刻他曾很怀疑地看了看自己不一样长的两条细腿,看过之后他的脸上滑过了一丝模模糊糊的笑容。他很迅速地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很害怕迎面遇到村里人,心里慌慌的仿佛自己做了贼一样。
急于离开人们视线的老五很快逃出了村子。当他抬起头来时,发现自己已经逃到了小桥的边缘。
河水似乎又涨满了一些,又浑浊了一些。但桥面上被雨水冲刷得十分洁净,像城里的大街。
他几步就站在了桥面上。他回头看了看,见身后没有人,便缓缓地蹲下来,开始一点一点地清理自己大脑中乱糟糟的思路。几天来发生的事情使老五第一次这样仔细、这样全神贯注地蹲在桥面上想事情,以至于洪水带着深沉有力的轰鸣声向他袭来时,他都没有听到。
(责任编辑 高颖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