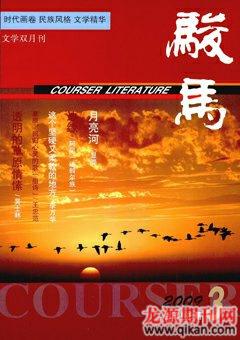这个坚硬又柔软的地方
李万华
七月的一天,我坐在青海湖北岸的大通山上,看云来云往。这是一个清朗明净的午后,舒卷在高海拔的云团,在蓝天的背景上,仿佛盛开的花朵,是牡丹抑或芍药。花瓣层叠、繁复,包裹朗朗清气。云在天上,一如鱼在水中。无端想起王昌龄的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想着诗里的云是另一种云,现在不曾见到。也许在冬季,它们出现,泼墨一般,向西,皴染河西走廊,如同滚滚雷声,直到那个陨落了的古楼兰。诗里的青海湖却依然在眼前。悬起的高地,丰富,蔚蓝,没有边际。湖上是岛,岛上是鸟,鹰的翅膀盛满阳光。湖中银鳞闪烁,湖畔水草碧绿。牛羊的影子如同帐篷般宁静。天地的呼吸强壮盛大。再无声息。七月的夏季风送来幽凉;送来似有还无的草的芬芳;送来牧人简短的说唱。而在云影流淌的天上,盛开另一面碧波荡漾的湖光。湖在天上地下,彼此相望。
环顾,明净的、再无庞杂班驳的时空交错。如同澄澈的精神个体,自由奔放。妄念消失,无挂无碍。自然的面孔宁静安详。坐着的人是尘上的一星花草,连同吃草的牛羊。
只是,在闭上眼睛的瞬间,人仿佛依旧坐在古人的诗里。彤云密布,雪山连绵,将士征战,黄沙弥漫,白骨遍野,衰草卷着哀叹。
仿佛苍凉沉郁的调子从没有变换,仿佛冬天从没跨过,仿佛征战依旧绵延,仿佛金甲依旧裹着黄沙,仿佛马蹄还在杂沓。多年前的一首诗,丰盈成一种持久坚强的植物,葳蕤在湖的四周,再无枯萎的想法。
然而总想解释诗歌的另一种可能,仿佛孩童手下绘出简单纯真的梦想。譬如云是大朵大朵的莲花,洁白,次第开放,一如眼前。譬如雪山,便是在七月份也有白雪覆盖一如华发滋生的雪山。譬如云朵遮住灿烂阳光,庞大云影移动在山腰暗了草色。譬如七月。譬如长风浩荡。譬如湖水泛着远古气象。譬如湖畔油菜花铺展金黄。
如此坐在诗歌的另一种可能里,是因为眼前展开着这种可能。想象这种可能其实在很久以前便已经存在。如同在衰败的季节想着季节曾经的繁茂,也如同在人的盛年不肯回忆前尘旧事。
不肯承认。
而实际上,一句诗酿造了一个文化时空,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记录在纸上的地理概念。置身其中,想改变,又不忍改变。于是在不见长云黯淡的时间,依然仿佛呼吸着寂寥和苍凉。走不出去的,永远的青海长云暗淡着雪山。
这是湟水河畔一个名叫柳湾的村子。高大青杨织着绿色云烟,沙枣花儿星星点点,湟水汤汤。红瓦砖墙的庄廓静穆无声。人们偶尔出没,脸上是强烈紫外线灼出的伤斑。空气干燥,风却带着远处冰雪的清凉。波斯菊盛开,清秀优雅。也有蜀葵,有大理菊,有庭院深处的丁香。它们的芬芳裹在太阳的光里,热烈又寂静。依旧是夏季的青藏高原,蓝天飘荡,白云悠闲,黄土路泛着耀眼白光。
没有牛马的足迹,也没有鸟儿轻捷的翅膀,只有风在树冠扫出沙沙的声响。
想着在3000年以前,那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及青铜时代的柳湾,也是这样静默的一个夏天,树木在阳光下葱郁茂盛,发散清芬,蜂蝶往来,翅膀带着轻盈。河水流淌。所有的氏族成员在首领的分工下忙着自己的事情。他们的头发一定浓密,四肢健壮,皮肤粗糙,他们的手背上一定有荆棘和动物牙齿的划痕。他们的交流简单纯真,神情专注。他们亲近黄土,尊崇临盆的女人。这样的一个午后,一定有一些工匠在明丽的光线下制作彩陶。他们选料,制坯,彩绘,然后烧制。他们技艺娴熟,心里装着万物,装着男女欢娱。他们把希望抟成模型,他们描绘,纹样、图案和符号是他们爽朗的表情。
很多年以后的阳光依旧耀眼,在柳湾,我面对一具人像彩陶壶长久沉默。一个身着紫红色衣服的女子坐在时光深处沉默不语,她的鼻梁高直,耳垂丰盈,她的手宽大厚实,双腿粗短,她的眉骨清秀,眼睛正眯成一条细缝。她的乳房,她的肚脐,她的生殖器裸露在外,带着夸张又童真的手法。她的周身绘着黑色的圆圈纹和蛙纹。她坐在斑斓中开口呼叫,她的肚腹高高隆起,那里一定有她的孩儿在踢着小腿小脚。
她的阵痛传过来,一阵紧似一阵,攥着时间,逼迫人心,我感到自己腹部在强烈痉挛。
但是死亡,死亡随后来到。
1700多座墓葬,长方形墓坑,叠在一起的尸骨,墓室口用来封门的木棍木板,木棺,残损的陶器和装饰品,消失了的呼吸,黯淡了的声音。最早的墓葬和最晚的墓葬相隔1000多年。2000多具尸骨。柳湾这一个氏族公共墓地,记载了死亡的多少类型,又记录了多少种悲痛。怎样的丧葬仪式曾经举行,怎样的权威曾被首领施展。站在柳湾的黄土上,再找不到确切的回答。柳湾先民早已远远地走过。
他们带走气息,带走温润。文明埋在地下,无声无息。他们一定不是现在柳湾人的先祖,但他们留下陶器和石制工具,留下谜一样的符号、纹样和图案,留下海贝,以及白骨。
他们还留下茁壮的日子,以及从无改变的高原夜色。
2007年夏,我从西宁出发,乘坐大巴前往贵德。“贵德的梨儿民和的瓜,名声大,亮过了黄铜的唢呐”。这是青海花儿里的贵德。去贵德看梨花在春天是件愉快的事情。夏天,梨花是谢了,念想里的梨花却依旧开着,这也是件愉快的事情。
终年与雾相伴的拉脊山,其实也是个频繁出现在花儿里的地方。在海拔3816米的拉脊山上,我看见倒伏的青稞,白色野花和黄色油菜花夹杂各半的油菜田,还有正在抽穗的燕麦。看见牦牛像黑色的甲虫爬在山腰,散落的羊群和散落的白色石头点缀着连绵的山峰。山阴是茂密松林,向阳的地方青草碧绿漠漠铺展。云雀的歌喉锦缎一般,雄鹰盘旋。山口有翻飞的五彩经幡。静谧,透着清凉。简单植被,悠闲牛羊,以及无处不在的豁然,这是典型的青海夏季。
翻山过去,绿色陡然减少。山凌厉起来,是丹霞地貌。路旁的山峰高大陡峭,刀削斧劈一般,造型奇特,是山的城堡、山的森林、山的人群。山体赭红,不着一星草木,风雨的痕迹深刻又新鲜如初。山下人家的庄廓墙泛着淡粉,阳光下看去,仿佛瓣瓣桃花飞落。
在山谷,看见黄河。
仿佛一块冰雪融成的湖泊,又仿佛一块温润的碧玉,独自生烟。宽广的、宁静的、清澈的黄河,在此处柔美、悠闲。风的翅膀掠过来,再掠过去,却总也掠不到黄河的微波上去。俯身下去,只见得河底枚枚卵石,纹路清晰。贴近耳朵,听不到丝毫纤细的声音。黄河仿佛是静止的。
简直不相信她就是黄河。那横贯下去的咆哮、怒吼,那挥之不去的浑浊、粗放,竟会来自如此细腻温婉的水面。
靠近黄河,蹲下来,伸手触摸水面。手底滑过的清幽,一如眼眶里涌动的冰凉。是一瞬间的感动,并长久持续。黄河在这里成为真正的母亲。她缓缓而过的身影,一如母亲抚摸儿女的手掌。
“天下黄河贵德清”。这是钱其琛副总理当年视察贵德时的题词。
站在黄河大桥上,眼前是青杨、芦苇、钓者、小儿。仿佛错步靠近多雨的南方湖岸,满眼的柔媚隐隐浮动。
而环顾四周,山刚水柔,和风温煦,瓜果飘香,人心沉静。严寒、粗糙、沉滞、广袤青海的另一面,我看见一方一如处子的大地,仿佛是静卧在地图上的那一只真正的兔子。
2001年11月14日,立冬刚刚过去,可可西里已是天寒地冻,呵气成冰。这一天,青海沱沱河帐房保护站负责人木玛扎西,正带领巡山队在西金乌兰湖一带开展反盗猎活动。盗猎分子的猖獗使藏羚羊的尸骨横陈在大地上,本已荒寒的土地现在越加显得凋敝。他们顶着风寒,艰难行走,追踪盗猎分子的足迹。天空一如往日,凝着脸,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这一天,他们曾看见大群野牦牛和藏野驴四处狂奔,似乎大难临头,这使他们忐忑不安,隐约感觉到将有什么不测。17点26分,他们突然听到一阵猛烈震耳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横贯而来,大地瞬间抖动起来,远处山峰如同旗帜飘摇,西金乌兰湖涌起层层巨浪,浪头高达2米左右,浪花拍向湖岸,溅起团团白雾。
地动山摇。昆仑山口西8.1级大地震就这样突然发生。
其实在这之前,种种迹象早已隐约出现。109国道沿线的电线杆上,往日傍晚常常会蹲满红隼,它们在那里私语,梳理羽毛,但在地震前的几天里,它们无影无踪;野牦牛往年初冬分布在保护区的数量不超过400头,但在地震前的一星期里,库赛湖以南、五道梁西北地区野牦牛大量密集,以至于形成上千头的牦牛群,巍巍可观;昔日温顺乖巧的藏原羚也一反常态,疯狂地四处乱窜。有人曾经在五道梁看见成群结队的藏羚、藏野驴和藏原羚争先恐后地沿青藏公路向东迁徙,情状惊恐烦躁,毫无秩序。
这一年,青藏铁路刚刚开始修建。地震发生时,工人们正冒着严寒铺铁轨。大地剧烈的颤动将工人们颠起来,抛出去,如同抛小小的弹丸。而刚刚铺好的铁轨平移出几米开外,职工的帐篷被撕成碎片。
天崩地裂的瞬间,万物的秩序散失殆尽。只有慌乱。
等慌乱停息,大地已经变了模样。
这是建国50年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
震后有人说,地震来时,人仿佛骑在疯牛背上,冰冻的大地筛糠一般抖动不已。地面瞬间张开口子,不断撕裂、拉长、变深。来不及逃跑的动物连同山石犹如食物,被大地之口吞没。仿佛噩梦,5分钟后,大地的容貌彻底改变。
如今,一切似乎已经过去,只是在人迹罕至的东昆仑山南缘的大地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长达430公里的地震形裂带宛如一条狰狞的刀痕,记录着大地曾经的暴虐和疯狂,再无法平复。一个黄昏,暮云飞渡,山口的风肆虐狂放,掠起人的衣衫如同经幡飘动。血色残阳里再难见悠然的羚羊。鸟儿的身形也没有踪影。站在昆仑山口西8.1级地震纪念碑前,想象这里曾经的情形。天翻地覆前的寂静仿佛只是一场模糊的梦。醒后已是亿万斯年。只有小山似的花岗岩纪念碑矗立在荒原上,它凝固的表情告诉我们,青藏高原正在摇篮里酣睡,你们画不出他以后的行为轨迹。
年轻的高原仿佛电影里的硬汉,给人以假象,它表面沧桑、荒凉,内里却血脉膨胀、热情涌动。
这是一个故事。故事总是虚妄,却带着真实的情感。说是一个老猎人背着杈子枪在路上,老远看见一只肥壮的藏羚羊。四目相对的瞬间,藏羚羊突然朝着老猎人跪下来,眼眶里流出晶莹的泪水。老猎人早已看惯了死亡,一枪射过去,藏羚羊倒下。藏羚羊倒下时依旧保持着跪姿,凝滞的眼睛里布满哀求。疑惑的老猎人剖开藏羚羊的腹腔,发现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死去的小藏羚羊。
应该说这只小藏羚羊是幸运的,它的幸运是它能够完整地蜷伏在母亲的子宫里死去,它尚未看见人类的残酷。而更多的藏羚羊,死后连具完整的尸骨都没有。
带着精灵的身材,雄性藏羚羊头上架着竖琴,音符一般奔跑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这优美的藏羚羊,闪电般划过高原的藏羚羊,温顺又时时惊怯的藏羚羊,数量只有5万多只的藏羚羊,它们的命运仿佛就是成为盗猎分子枪下的财宝。
一条收集来的数据。在中国境外,1公斤藏羚羊生绒价格可达1000~2000美元,一条用300~400克藏羚羊绒织成的沙图什围巾价格高达5000~30000美元。而一条可穿过指环的沙图什围巾包一只鸽子蛋,据说能孵出小鸽子来。
是什么样的谎言让那些贵妇们安然享受藏羚羊细致柔软的绒毛?说,藏羚羊在灌木丛里跑过,身上的绒毛脱下来,挂在树枝上,人们收集加工而成。
哄小孩儿一样的谎言。
这是真实的场景,依旧发生在无人的可可西里。正在繁殖期的藏羚羊成群结队地迁徙,雄性藏羚羊要护送雌性藏羚羊到更高寒的深山峡谷去生下它们的孩儿。途中遇到盗猎分子的扫射,甚至来不及哀鸣,一千多只藏羚羊在片刻间失去生命。它们的幼儿在它们的子宫里蠕动,它们的皮毛却已经剥下来。
尸横遍野的惨状。无辜的藏羚羊和更加无辜的幼儿。它们的血流出来,渗透草丛,染红湖泊。
保护它们的志愿者在艰苦奋战,盗猎团伙却乌鸦一般赶过来,扑进去。藏羚羊有着在高海拔植被稀疏地区生活的坚强品质,却始终逃脱不了人类的围追堵截。这个苦难的物种,或者已经失去了与人类共生存的信心,所以,它们在繁殖的时候要到更高寒的地方去,那里,它们的孩儿或许能得到片刻安宁。
我看到一张照片。一名志愿者蹲下来,他的眼睛里漾满幸福的泪水,一只小藏羚羊仰起脸来,他们相互凝视,他们的鼻头轻轻相触。仿佛在呢喃,在撒娇,在倾诉。小小的藏羚羊,它冰凉的鼻头,它尚未破坏的信任,它对家园的热爱,它的纯真透明。一遍遍看过去,手指反复触摸的,是小藏羚羊满含期盼的眼睛。
一个从青海玉树牧区出来的孩子见到路边的青杨,吃惊地叹道:怎么这么大的草啊!有一天,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网络里一位南方的朋友听。我讲故事的时候,内里已有着隐隐的痛。但是朋友并不理解这个故事里的伤悲,他说:孩子的想象力真丰富。我不责怪朋友的曲解,因为他并不了解一个没有树木的地方,而且是一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
这是个孕育了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广漠之地,是个面积26万多平方公里,却只居住着25万人的土地。这里是高山冰川,湖泊沼泽;是戈壁荒漠,是狂风大雪。这里的花无法用姹紫嫣红形容,这里的鸟无法用百鸟朝凤描述。植被以及人烟的稀缺,仿佛头顶上那一层薄薄的氧气。
在一个名叫新寨的村里,我站立,并长久沉默。
屹立(没有一个更确切的词来形容)在我面前的,是被誉为“世界第一石刻图书馆”的玛尼石堆,我甚至不想说它仅仅是一个石堆,它是玛尼石砌起来的城堡。石墙巍峨,寂静的石门洞开,旷野的风携着冰雪的清凉来去自如。神塔高耸,经幡彩布兀自拍打,发出啪啪的声响。偶尔走来的人,捧着玛尼石,前倾上身(那永远是一种虔诚的姿态),绕着玛尼堆转经,或者走进石门去,拿出青稞和柏枝,煨桑祭祀。青稞酒、糌粑、酥油和柏枝的味道混合起来,是一种奇异的芬芳,缭绕,并长久持续。
我看着他们把小小的玛尼石填到庞大的石堆间隙里去,看他们在玛尼堆前诵读经文,他们的虔诚使他们神思专一。我知道他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而来,他们有时会从远处将玛尼石驮运过来。刻着六字真言的玛尼石,刻着佛像的玛尼石,色彩斑斓的玛尼石,一层一层垒积,一圈一圈扩大,直达25亿颗之多。
站着,仿佛听到这25亿颗石头在窃窃私语。这些形状各异附着灵魂的石头,这些承载情感和希望的石头,伫立此处,凝然不动,这分明是六道轮回里芸芸众生的呼唤。
我同时听到沧桑老者的祈福之声。万物有灵,雪山、湖泊、牦牛、雄鹰,即便是一块小小的石头,也有着高贵的灵魂。他们守护万物,救赎众生。他们值得歌颂,值得崇拜。而自身的力量又是怎样的气势磅礴。600年的岁月,数亿人的搬运和雕刻。没有君王的命令,只凭着一颗虔诚的心。这是青藏高原之上的另一高度,擎起它的,是一个崇尚精神的民族。
2007年10月上旬,一场三十年未见的大雪突然从天空扑下来,一夜之间,天地容颜骤变。厚重的积雪压在茂盛的树冠上,仿佛残暴的大手,蛮横地撕裂树木的枝丫,露出树枝嫩白的筋骨,仿佛夭折了的幼儿的肌肤。翻过日月山,青海的整个牧区,来不及枯萎的草场,瞬间成为茫茫雪原。十月,正是牧民们准备丰收的季节。育了一夏的牛羊即将出栏,而辗转高山牧场的牲畜将回归冬季牧场。牧民们年复一年地迁徙,转场,不辞辛劳,如同保护生命一般保护着的牧场,现在,早已不见。
夜以继日,雪带着韧劲,持续落下来。宿雪未曾消融,新雪又在上面层层累加。雪原洪水一般蔓延,潮水一般涨高。雪的气势,凶猛、凌厉,潜藏横扫的刮毒心性。都来不及惊叹,雪原又变成冰原。坚硬的覆盖,如同天空弥漫的彤云。大地上再难见到草的踪迹。这是种未曾料想的慌乱。牲畜找不到吃食,牧民晒干的牛粪被冻结。气温急转直下,零下,严寒。
饥饿、冻伤。牛羊的目光日渐黯淡,瘦弱,然后死亡。死亡如同一场瘟疫。睁着的美丽眼睛,弯曲的膝盖,努力朝着冰层啃啮的牙齿,瘪下去的肚腹,冻伤溃烂的蹄腕,斑驳脱落的皮毛。死去的牛羊,一一横陈在雪原上,倒下的姿势,带着未曾明白的迷惘。
牧民的帐篷,散落,如同在大雪中飘零的孤舟。
在玉树称多县的一个小村里,我看见蹲在雪地上翻拣牛粪的老人。冻伤的手红肿溃烂,渗着血粒。寒风吹起碎雪,扑打在老人凌乱的发辫和紫红的脸颊上。十几厘米深的雪,淹没着老人的脚和腿。刨开的雪堆在老人身边,露着白牙。老人给我看收集在编织袋里的潮湿牛粪,说,只有这两袋了。只有两袋了,可严寒的冬天还没有真正到来。取暖、做饭,牧民全靠这些牛粪。老人的脸上没有惯常的宁静。
我所知道的,离这里不远的一所小学,在这个早上,我刚刚经过。为了省牛粪,教室里只在早上生了一次火,牛粪很快在炉子里化成灰烬。漫长一整天,孩子们不得不缩着身子在寒冷中上课。每隔十几分钟,老师就让孩子们到教室外面去晒太阳。可是,吝啬的太阳只在中午时分放射它的光芒。腮腺炎、肺炎、支气管炎,阴影碾过来,孩子们缺医少药。
路上,零散的牧民拦住过往车辆,希望有人能用低价买去他们手里的牛羊肉。他们不得不大量宰杀缺少食物的牛羊。这是他们对即将来到的死亡所做出的惟一反应。
诗词里的雪,歌谣里的雪,在这里,仿佛一群野兽,狰狞、凶残。
我听广播,知道牛羊出栏的补贴,一只羊20元,一头牛100元。这是多好的政策。我也看见救灾的粮食、衣物和煤。我还看见许多友善的眼睛凝望着这块雪原。可是,我依然无法忘记那个瑟缩在冰冷帐篷里的孩子,他的腿已经严重冻伤,再也无法奔跑。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