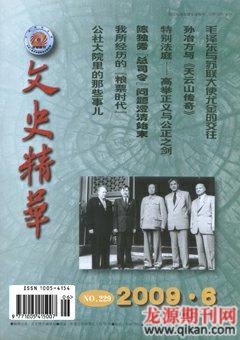孙冶方与《天云山传奇》
朱安平

作为第一部触及“反右斗争扩大化”题材的影片《天云山传奇》问世于1980年,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仅一年多,正是新时期的“早春二月”。它的出现引发了热烈的社会反响,也招致了不同评价的激烈交锋,甚至险遭“差点被枪毙”的厄运。一篇影响甚大的“申辩”文章,曾起了促成舆论转折的关键作用,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不顾身患绝症,在病榻上写就的《也评〈天云山传奇〉》。
并非“传奇”却惹是非
电影《天云山传奇》是根据著名作家鲁彦周同名中篇小说改编摄制的,原作酝酿写作于1978年底至1979年春,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其时,正在北京参与反映与“四人帮”斗争的农村题材电影剧本《柳暗花明》最后修改定稿工作的鲁彦周,亲身感受到社会处于巨大转折之际所特有的激荡热烈气氛。经过深入思考,他决心在国家形势和个人命运都处于历史交会点之时,写一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仅仅20多天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初稿。恰逢作家所在的安徽省筹办大型文学期刊,遂发表于1979年初出版的《清明》创刊号上,旋即又应上海电影制片厂邀约,亲自改编成电影剧本,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于1980年底拍成影片。
无论电影抑或据以改编的中篇小说,虽都名为“传奇”,其实本身皆无“奇”可言,均属十分严谨的现实主义之列。它所讲述的是一个在生活中并不罕见却充满悲欢离合的故事:50年代中期曾任天云山综合考察队政委的罗群,在反“右”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右派分子,恋人宋薇和他分手,并嫁给了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他的前任吴遥。而宋薇的同学、好友冯晴岚,则在罗群落难时与之结为夫妻。这对患难夫妻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仍孜孜不倦于科学研究达20余年。70年代末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之后,罗群的政治问题终于冲破重重阻力获得解决,而冯晴岚却在此时与世长辞。
对于熟悉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观众来说,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平常、太普通,但在当时拍成影片却阻力重重。谢晋曾经披露,因涉及以反右运动为背景,这在电影创作中从未有过,一开始就有风言风语:会不会在政治上太敏感、弄不好会违反政策等等,亲朋好友们也都劝谢晋不拍这个戏为妙。当看完外景回来,摄影师去领胶片、录音师去联系工作,有人仍在议论:“你们这个戏还拍呀?谢晋瞎起劲儿,你们没听到最近有新情况啦……”后来开赴九华山拍外景,还刮来过“反右题材搞不得”的风声,致使摄制组一直处于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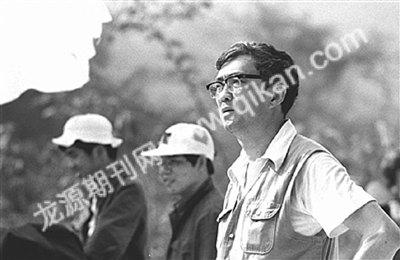
影片送审以及公映也都不很顺利。它首次“亮相”于1981年初由《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有来自全国的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100多人参加,被称为著名的“新侨会议”即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20年后的电影界又一次“反右”盛会。谢晋带着刚完成的《天云山传奇》与会,介绍说正在送审但“前途未卜”,因为有一种意见认为影片“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虽然放映后受到普遍赞扬促成审查“过关”,但公映后很快又有一些来自上层说法的流传,说有的领导认为这部影片把右派写成英雄,把干部写成坏人,并下令禁演了;又说有的领导反对这个片子,也不好说禁演,但规定了几条:不得参加世界电影节,不得出国展映;还有的领导指责影片中地委书记住的房子太豪华了,并说我们共产党员怎么把别人的未婚妻抢走呢?你可以描写他政治上的错误,不该在品质上丑化他,等等。这些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的不胫而走,很快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混乱,有的甚至采取措施禁演影片。在电影界最新设立、最具权威的由专家评奖的首届“金鸡奖”评选中,《天云山传奇》以一票之胜领先《巴山夜雨》,最后评委一致通过两片并列“故事片大奖”,《天云山传奇》排名在前,但上报后领导却作出决定,将《巴山夜雨》调到首位并毋庸讨论。
影响最为直接与广泛的,是报刊宣传由热变冷,从影片刚公映时的“一片叫好”,转为褒贬不一,甚至出现批评意见“一边倒”。《西藏日报》于1981年3月12日、4月2日和16日连续发表文章,反对者严厉指责该片“是一部倾向上存在严重问题的影片”,“是借用三中全会决定的为右派摘帽和改正错划右派的政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来丑化党的形象,美化乃至歌颂右派。”北京的《文艺报》很快对此作了公开报道,详加综述了肯定或基本上肯定、否定或基本上否定、艺术上肯定但政治上否定三种意见,随之又于1982年第4至8期专门设立栏目,开展了长达4个月的集中讨论,把有关该片的不同意见争论推向全国范围,以致外界形成非议四起、风声鹤唳的印象。
“路见不平”挺身而出

《天云山传奇》上映后的“褒贬悬殊、争论纷纷”,引起了著名经济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孙冶方的关注。据他在后来参与讨论撰写的文章中所述:“在我们机关集体购票观看《天云山》的那天,碰巧我有别的事,原来不想去看的。但是听到同志们告诉我:这是一部有争论的片子,有人认为是一部玷污党的形象的坏片子,不应该放映;有人却认为这是一部好片子,应该放映。我已经意识到这不只是对一部影片的艺术评论,而且是思想战线上的一场争论。于是我决定放下别的事,去看了《天云山》;看完之后,我情不自禁对一同看电影的同志说,这么一部宣传落实党的政策的好电影,怎么说是玷污了党的形象呢?”
促使孙冶方介入《文艺报》有关《天云山传奇》的集中讨论,是该刊开展讨论首篇刊出的署名袁康、晓文的《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评〈天云山传奇〉》,此文从根本上否定了影片《天云山传奇》,认为影片“歪曲了反右派斗争的真相,丑化了党的领导,在青年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是一部思想倾向和社会效果都不好的作品”。文中以“尽管这场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为由,指责“《天云山》却只是通过主人公罗群的不幸遭遇着意渲染了反右派争‘扩大化的一面,根本不去反映‘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一面,因而在不了解这段历史的青年观众中造成了反右派斗争完全搞错了的印象”,“《天云山》通过一系列画面所告诉的,却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政治概念:反右派斗争是‘百分之百的错误”。文中还认为影片所描写的主要反面人物吴遥“是损害党的形象”,主要塑造的正面人物罗群也是“不真实”的,“通过宋薇这个形象告诉观众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宋薇之所以‘永远失去了爱情而沦为‘上流交际工具的可悲处境,完全是由于听从党组织的意见。这难道不是‘毁坏党的形象吗?”文中承认“《天云山》的某些表现手法确实取得了成功的艺术效果。它对吴遥、宋薇、冯晴岚等人物的刻画是比较细腻的,避免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它在吴遥、宋薇与罗群、冯晴岚之间所作的强烈对比,确能调动一些年轻人的感情”,“但由于创作思想不健康,成功的艺术手法就更加深了不良的社会效果”。文中强调影片《天云山传奇》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

作为一位饱经风雨沧桑、受尽各种迫害和折磨的老革命家,孙冶方以特有的高度敏感意识到,这虽然是就一部影片具体人物命运和情节安排所作评价出现的分歧,实际争论的意义却涉及尖锐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政治范畴,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保持沉默。正如他后来在讨论文章开宗明义所说:“对于文艺(包括电影在内),我是门外汉;论理没有我插嘴的余地。再说,我自己分内的工作也没有做好,自已肩上的,好多必须完成的任务都还没有完成;我应该‘少管闲事,做好本职工作。但是我读了袁康、晓文二同志写的影评:《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评天云山传奇〉》之后,总觉得喉头有什么东西哽着,必须吐出来才好。何况袁康、晓文二同志认为《天云山传奇》是一部‘毁坏党的形象影片,而且认为《天云山》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思想在文艺上的反映。既然这已经不是文艺界“孤立的”问题,那末,一个文艺界圈子以外的人,过问一下‘毁坏党的形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应该不算是‘管闲事吧!”

孙冶方首先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光年打去电话,述说了自己的观点,并声明要写一篇评论文章。40余年前他们曾在上海一起从事过左翼文化和抗战救亡工作,有并肩战斗情谊,关系素来投契。接到当年曾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自己老领导孙冶方的电话,张光年先是满心的高兴,细听下去却不由感到为难:能有像孙冶方这样有革命经历,而又有深刻见解的人士出面伸张正义之言,对这部影片作出公正评价,对于身居《文艺报》主管部门领导岗位的他,当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可是考虑到孙冶方不久前被确诊为肝癌,又在忙于抢写“文革”7年牢狱之灾中打了85遍腹稿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犹豫片刻之后还是委婉相劝:“不要写了吧,你还是尽快把你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吧!”孙冶方没有接受老友的劝阻,坚决表示一定要先把这篇讨论文章写出来。张光年清楚孙冶方的“硬骨头”与“怪脾气”特点,只要认定是正义、正确的事,当先地冲上前去,从没有丝毫的犹豫迟疑,决不管代价后果如何。只好婉转地说:“既然坚持要写,那就写吧!但不要太劳神和费力,也不要着着急,慢慢地写,一天写它一点儿!”
就这样,孙冶方不顾已患绝症的衰弱,在病榻上用了8天时间写出了长达8000字的《也评〈天云山传奇〉》。张光年收到文章之后,深为其深刻的见解和缜密的表达所折服,很快便在《文艺报》1982年第6期以显著位置发表出来。孙冶方还特意将稿样寄给另一位老战友陈修良征询意见,称自己“‘路见不平管了一下‘闲事”。
“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文艺报》在刊载孙冶方这篇文章时,专门加了“编者按”:“本刊第四期发表袁康、晓文同志的《一部违反真实的影片——评〈天云山传奇〉》以来,受到了读者、观众和文艺界同志的广泛注意,许多同志寄来了稿件,积极参加讨论。这个事实又一次说明党的双百方针深入人心,对文艺问题展开平等的自由的同志式的讨论,对于提高读者、观众、作家、评论家的水平,推动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发展都是极为有益、不可缺少的。我们欢迎持有各种观点的同志畅所欲言,并继续发表各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讨论文章。”
孙冶方的《也评〈天云山传奇〉》,正是一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力作。文中旗帜鲜明地表示“《天云山》是部好电影”,它“是以为罗群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这个主题展开的。为此电影倒叙了罗群被打成右派的前前后后一段故事。从反右派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间经过‘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么几次大运动。如果说,吴遥这形象在反右派运动时不够典型,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太够典型的了”,“袁康、晓文二同志认为《天云山》的某些艺术表现手法的成功加深了不良的社会效果。我却认为相反,是加深了《天云山传奇》的良好政治效果。因为它的成功的表现手法,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会牢牢记住:今后我们再不能重犯‘把同志当敌人的错误了!”

他指出:“为什么我们和袁康、晓文同志以及同他们二位抱有类似观点的同志,对同一部电影会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呢?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自信心问题;二是对号入座问题。”并在文中结合对袁康、晓文观点的驳斥,分别作了深入阐述。他写道:“在袁康、晓文两位看来,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是很脆弱的,经过《天云山》的某些成功的艺术手法把反右派斗争‘严重的扩大化所造成的‘不幸后果,这样尖锐地暴露在群众面前,党的形象就被‘毁坏了。我们却不是这样想,一个有自信心的政党或是个人,对自己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犯错误,挖掘得越深,那么它或他的威信越高。”他又写道:“不论是经历过还是没有经历过反右派运动的,凡是看过《天云山》的人都可以‘对号入座。看你是如何对号入座罢了。‘反右派运动,我们都参加过的,运动是搞得过火了,然而我们是执行党的命令呀!难道我们就是吴遥吗?真是岂有此理!这是一种对号入座法。联系《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提高认识,不犯吴遥这样的错误——这是另一对号入座法。对于没有经历过反右派运动的青年一代,《天云山》是很好的一部政治教育片子。牢牢记住这段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搞这样的运动了。”
他在文中大声疾呼:“给《天云山》戴上‘毁坏党的形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大帽子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切记‘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历次运动教训,乱飞帽子、乱打棍子的做法不能再来了。”并语重心长地强调:“如果把建国以来32年党所经历的道路,说成是一条笔直笔直、百分之百正确、毫无弯曲的康庄大道,那么,非但不是事实,而且对于吸取教训、避免今后再走弯路毫无好处,只有害处!”
孙冶方的这篇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申辩”文章发表后,很快就在社会上广为传扬,文艺界反响更大。电影界前辈夏衍拍案叫好之际,立即致函孙冶方:“我认为这是评《天云山》的最公正、最有力(说明力)的佳作。”主持该片创作、拍摄并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上影厂厂长徐桑楚后来回顾说:“有些人,感情上很喜欢这部作品,但看到那些批评文章就不敢说话了;还有些人,本来观点并不明确,但看了孙老的文章,认为它有说服力,便也写文章支持和响应。所以孙老的文章,在舆论上形成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赞成影片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却越来越小。”
对于《天云山传奇》的主创人员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鼓舞与慰藉。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的当天,同是代表的鲁彦周和孙冶方,经王元化引见在人民大会堂相见。鲁彦周钦佩而深情地说:“孙老,您不知道您的这篇文章给我减轻多大的压力,因为您不是文艺界却是革命前辈和著名的经济学家,您的文章就特别有说服力。”孙冶方平静而诚挚地回答:“我从来是不跟文艺界打交道的,我这次出来是打抱不平的。你有勇气敢写,拍出这么一部好电影,对党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你是有贡献的,你不要感谢我,我们应该感谢你。作为作家,你就要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
1983年2月初,身在国际电影节上的谢晋闻听孙冶方病危的消息,匆匆打电话给孙老家属,请求赶回国内到医院作最后的探视。当谢晋从马尼拉飞回严寒中的北京,此时的孙冶芳已命若游丝。为了能见谢晋一面,他要求医生成倍加大输液剂量,以便在谢晋到来时保持头脑清醒。当谢晋来到他的床头,握住他那瘦骨嶙峋的双手时,孙冶方吃力地眨动着眼睛,声音颤抖地说出令谢晋刻骨铭心的话语:“历史不能再重演啊!”……这是孙冶方在生命的最后岁月留给文坛的一段佳话,也给《天云山传奇》风雨历程画上了圆满句号。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