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人说
网上有朋友说鄙人属没有什么才气,但人还算老实的那一类。又有说我老实得像个老农民,言外之意是虽日日耕作不息,但人难免糊里糊涂。搞艺术的,必然要有天份,有才气,而我没有才气还要硬来搞艺术,属于无自知之明。这其中有两点“错误”:一是我天资愚钝。这是父母的过错,我只能怨天叹地了;二是我竟然在书法篆刻中泡了50年,至今仍不思悔改,这便是我的错了。有人说我属于老实无才的那一类,我觉得其说对了一半,其实我是无才而“顽固”的那一族——撞了南墙心也不死,见了棺材也不肯落泪,是伟大领袖所说的“愿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那一类。于是尽管没才气,还是要顽固下去,誓将书法篆刻革命进行到底!
没才气的人有没才气的好处,愚者长悠悠,智者长戚戚。其一,有才者容易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老天爷第一我也是第一”;其二,有才气的人容易象小说里的周瑜、罗成一样使气斗狠。眼中的一切都不顺溜,一天到晚嘴里笔下都在骂骂咧咧。从王羲之骂到启功,从馆阁体骂到现代派,自己骂别人别人又回骂自己。骂中出名,骂中获利;其三,有才气者容易“艺高人胆大”。呵祖骂佛,离经叛道,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而不才又顽固如我者,一是不敢有傲气。每每三省吾身,自警自惕;二是无斗志。与人与物和谐善处,心静气平,知道敬畏古人、崇敬学问;三是没胆。知道想随心所欲必须不踰矩。所谓的老实人就是俗常所说的“傻”,然而傻有傻的快乐,傻有傻的福气,傻有傻的平安。傻是一种天份,傻是一种境界;积数十年生途与艺途之经验,一言之蔽之,曰:“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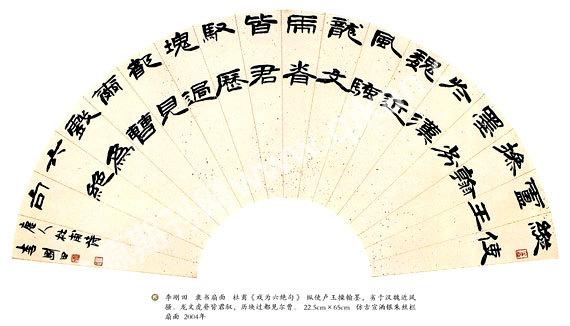
然而愚者也有蠢蠢欲动的时候。不才如我,有时看到战国、秦汉古印中那种浑然天成之妙,有时看到青年印人作品中的奇思妙构,我便怦然心动,便生出了“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邪念。这“邪念”一萌生便想改变招数。一说到变,首先得努力改变头脑中积淀已久的审美惯性,改变手下沿袭已久的刀笔模式。不久前。洪亮道兄写了一篇《李刚田丙戌书法变法》的文章,对我多加缪赞,认为我近期的篆书创作有了突破。所谓的突破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了古人、前人;二是突破了自己、过去。以此来对照我近期的篆书,突破仍不算大,只是觉得近来笔下比过去松活自由了许多。不像过去写得那么精谨矜持,但其中仍保持着对古人、对故我的延续性。
说到变法,洪亮兄认为:“所谓书法变法,其实是书法家在创作中审美观念的超越,是书法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方面的突破。而超越与突破是需要深厚的学养、功力和开阔的胸怀的等多方面的支持才能实现的。”首先应是观念的变化,随之带来了技法的变化。而变化需要胆识作支撑,有识无胆不敢变,有胆无识盲目变。只有有胆有识才能变化出新而合于道。宋元时期的文人提出了宗法汉式的篆刻理念,是对当时刻印艳俗、匠俗的拔乱反正,从此奠定了中国篆袤4艺术以汉印为典型样式的基本审美特征。后来在宗法汉式的理念之下,印越刻越模式化,路子越走越窄。到了清代中期,印人们提出了“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的理念。这是对宗法汉式理念的充实,或者说是对宗法汉式的一种反动,从此印坛开始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篆刻家的篆书风格成为其篆刻风格的有力支撑,印外的种种形式成为古代印式的重要补充。从邓石如开始至今200多年间,“宗法汉式”“印从书出”“印外求印”揉合一体的创作思想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近十几年的篆刻创作中,在年轻一代印人身上,创作理念又发生了变化。“印外求印”的方式被扩大,而“宗法汉式”“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在萎缩。在有些作者,有些状况下的创作中,“宗法汉式”“印从书出”的理念甚至被视为求变出新的障碍。随着创作理念的变化,作品的形式及创作的技法也开始打破了种种既往的程式,变得丰富而又无序,而一些所谓老派的印人还坚守在“宗法汉式”“印从书出”的理念中创作。印坛呈现出多元化的新局面。

篆刻,具有印章属性、书法属性、美术属性和工艺属性。所谓的创新与守旧,不过是此四种属性的此消彼长而已。我刻印之所以对自身难以有很大的突破,其实是我难以突破数十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创作理念的局限。篆刻的印章属性、书法属性成就了我的篆刻风格,也制约着我创作的想象空间。我对这两种属性所生发出的篆刻之美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于是我只好用加法,不愿弃旧从新,而取了“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创作态度。争取在守成中有突破,在突破中蕴含传承,把握“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度。我不愿使自己的作品走向美术化、工艺化,又不想株守在今天展览中使人看去有木讷感的汉人模式。我不愿失掉书法美在篆刻中的潜在作用,不但力求作品的可视性,而且要有可读性;不但要营造篆刻中建筑般的空间之美,而且要保持其中音乐般的时序之美。但我又不想仅仅是把书法的具体形质生硬地移植到印石上,而是用刀情石趣替代笔情墨趣,以刀法手段来替代毛笔挥运。一般来说,篆刻中的印章属性、书法属性较多地体现着传承性,而美术属性、工艺属性则较多地体现着表现力。但两者又不是绝对的,其中各种因素相互支撑又相互制约。欲求变出新,聚焦点在于形式。而形式的新变,往往有赖于在奇古的文字中汲取素材;有赖于新的工艺技巧;有赖于印面上重新安排红白对比的形式;有赖于在古代印章和当代美术中得到启示、激活灵感。传承性仍然是求新变的根基。出新求变不可能是完全割断传承来向壁独造。师造化与得心源二者不可缺一,就如吴冠中说是“风筝不断线”。
“欲变”到“能变”,再到“新变”,要得到时人的认可和历史的认可,谈何容易!塑造新我的首要任务是解脱旧我。塑造新我需要天赋,解脱旧我需要勇气。由于我的自恋自爱,解脱旧我不可能彻底;由于我属“老实人”一族,重塑新我也进入不了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境界。于是我之变只能如春柳之渐染,似残雪之悄融;只能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而无才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惊世骇俗。

欲变,还有一怕——怕画虎不成反类犬,怕“没才气”的评论依然如故。而那时“老实人”的称赞却没有了,变成了愚而诈的盗书蒋干,献图栾平之类的小丑。
噫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