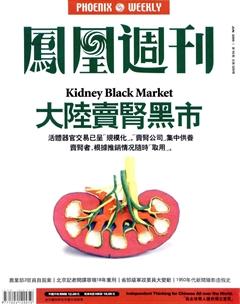活体移植:“不完美的方式”
谌彦辉
“活体移植是以鲜血、痛苦、健康甚至死亡为代价,它不是中国器官移植的方向,你去动用活人这个方向就是错误的。”陈忠华最终放弃了沉默,并上书卫生部表达了他对当前活体器官移植现状的忧虑。
陈忠华是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也是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委员,现为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他曾是中国活体移植手术最早的推动者,但如今,他不但拒绝做一例活体移植手术,还毫不留情地站出来直斥其诟病。“因为尝试之后,我最有仅利来批评它,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方式。”
“家庭自救”動因
2000年,陈忠华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而当时。英国的亲属活体移植刚刚起步,占整个器官移植手术量的10%~15%。为此,英国器官移植学会出台了一份活体器官移植指南试图规范这一新兴事物。
陈忠华将这份指南翻译成中文带回国,并在不同会议场合公开介绍。那时候,中国的活体器官移植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大部分医疗机构的活体移植手术率为零。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2001年,陈忠华到武汉同济医院担任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便开始推广活体移植,然而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因为当时死刑犯的器官源源不断,很多医生认为推广活体移植没有必要,而且活体移植手术风险大。
“我们冒着很大的风险,假如一个病人发生并发症怎么办,一个家庭又增加一个病人,谁来承担责任。”陈忠华说,“很多人质疑你的动机,甚至还有人想看你的笑话。”
但陈最初还是想借助活体增加一部分移植器官的来源。他说,死刑犯器官这一获取方式在世界上广受质疑,它总会有改变的一天,移植手术必须有更合适的器官来源。
陈忠华首先想到了家庭内自救,即从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开始实施活体移植。他们当时从爱心奉献的角度来推广举行多场科普宣传,并对手术进行电视直播,这使得活体移植纳入公众的视野。
后来,陈发现很多家庭因为血型不同而实施不了活体移植,于是,他又根据欧美经验推出一个多家庭互救方案,同时也是爱心奉献,这也是通常所说的交叉换肾,这个案例当时产生了轰动的效应。
陈先后提出了解决器官来源的两个策略——家庭内自救和多家庭互救,直接导致同济医院2007年上半年活体移植手术率上涨到30%。这样一个增长让很多等不到合适器官的绝望患者获救,并创造了_一个个生命奇迹。
据介绍,到2006年,活体移植占整个器官移植总量的比例提高到15%,到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50%以上。
假亲属的困扰
“每一例活体移植手术我们都非常小心谨慎。”陈忠华说,他们所做的100例活体移植,首先都要一一确认亲属关系。
病人登记住院,患者和供者一般都会进行知情同意。而时下一些移植中心却省略了这一重要环节。陈说,他在术前和患者,供者见面谈话,然后再各自单独谈一次。三次谈话中,他首先要确定供者是否确有捐献意愿,而且通过独立谈话确定供者的捐献意愿是主动的,而不是胁迫,其中也没有牵扯经济利益。
“其实我们也很困惑,作为一个推动者,希望他捐献成功,但是我们不能引诱他。”陈忠华说,每次谈话他都要进行两个多小时,更多的是把困难和风险告诉供者,很客观地向他陈述活体移植手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时候,很多家属就打了退堂鼓。
“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父母。”陈深有感触,正因为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们有激情去推动活体移植。
此外,他还观察这些亲属入院的亲情体现,是否亲属可更多地用直觉去观察。同时对其身份证认真核实,如果发现长相完全不同,关系又不亲密,他会亲自打电话过问,并到当地派出所核实。
陈清晰记得,2005年他曾遇到一份供体提供的身份证明,其中身份证发证日期居然和出生日期在同一天,这让他非常惊讶也深感后怕。
“为什么一个无关的人来捐肾。”陈忠华立刻警觉到这涉及非亲属,而非亲属活体移植背后可能牵扯其他利益,甚至还有可能被人操控。他忽然意识到:“这个口子开了,可能会带来更坏的结果。”
自2005年开始,假亲属似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至于其背后的交易,陈说,很多医生当时还不清楚,因为他们提供的身份证明已经超出了医院监管的范畴。“我们发现这个苗头后只能严格审查,宁可少做,也要每个亲自审杳。”
陈从中识破了多例假亲属,“但我并没有通过什么特别手段,只是看看文件资料,到病房走一圈,谈话聊天就跟病人说不要来了”。他认为医生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如果他认真的话”。
他还称,在亲属认定这一程序,相关人员完全可以把关。各地移植中心和医生有相当的能力去自律,但目前一些移植中心的医生却以身试法,甚至参与利益的分配,这使活体移植目前陷入危险的处境。
慎做活体移植
武汉有一个家庭,爸爸患有尿毒症,他有一对年轻漂亮的双胞胎女儿,十七八岁正是豆蔻年华。为挽救父亲的生命。两个女儿流着眼泪争着要捐肾。这一故事深深感动了陈忠华,也触动他对活体移植进行反思。
“当时我就觉得这一刀下不去,她们又年轻又漂亮,还是学生,如果今后她们的男朋友因此离开,那不是害人一辈子。”陈左思右想,最后拒绝了这对姐妹,也因此有了不再做活体移植的念头。“子代给亲代捐献,应该非常慎重,因为子代面临更长的生命之路和更多的社会挑战,这是我的原则。”
另外一个家庭的故事也震惊了陈忠华。他说,这个家庭的弟弟处于尿毒症期,而哥哥因为烧伤注射链霉素导致耳聋,脸上布满皱纹,长得又很矮小。他的父母决定要把残废哥哥的肾捐给弟弟,一家人都同意了,但陈忠华最终还是将他们拒之门外。“残疾人没法知情同意,他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群体,我们怎么忍心再割掉他一个肾脏,这违反伦理学的原则。”他说,弱势人群不能是捐献者。
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陈忠华开始意识到活体移植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他们在推广过程中恰恰忽视了它潜在的问题。
2006年,陈忠华个人决定停止活体移植手术。除非父母给子女捐献器官,惟有这种关系他还可以坚持做。即便是子女给父母捐献肝或肾,“我不但不做,还反对”。他说,年轻人面临更长的生命。时间、机遇的挑战,健康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尽管活体移植使很多病人减少了他们等待的时间,生命得以延续,但陈仍深感忧虑:这些单肾人日后活在世上,迟早会出问题。
陈忠华深感内疚,他推动活体移植技术成熟起来,而死刑犯器官来源正逐渐减少,活体移植很快变成了一个替代品。“大家都疯狂地来做这个事情,我现在连刹车都刹不住。”而他也抵挡不住活体移植中滋生的器官买卖,“这一块已经产生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根本停不住,他们希望赚更多的钱”。
“我现在只能约束自己不做活体移植了,但不能保证其他医生不做。”陈忠华说,他并不反对亲属活体移植,但对现在的活体移植,他希望能强烈限定一个要求,即供者完全自愿,而且还有能力保证他今后复查的医疗费用,“没有这个先决条件不能做”。他说,社会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机制保证供者的安全。特别是非亲属活体移植,社会还没有建立一套医疗保障制度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亲属活体移植至少还有家人能保护他们。
遗体捐献是正途
陈忠华放弃了活体移植,现在又开始他新的努力方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一切又从零开始。
他发现了更好的方式,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脑死亡器官捐献。2006年只有22位死者家属在陈忠华的努力下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2007年这个数字翻了一倍,2008年11月11日,捐献者达到100例。
陈忠华说,他们通过100多例脑死亡器官捐献者挽救了400多个人的生命,而这里面只有受益者,没有受伤害的供体,也没有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它没有伤害。”陈反复强调说,他更愿意推动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而不愿意再做活体移植。
通常,“医生讲究一个利益最大化,他对生命的理解,对伤害的理解,加上技术的含量,达到一个利益最大化,这才是他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就是盡量减少对健康人的伤害,尽量使捐献者,接受者健康得到保护,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医疗体制和医疗技术”。他说:“这很难,但现在我们找到了。”
陈认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它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只有利益没有伤害,这才是器官移植的真正出路。
而现在,一些医院的移植中心仍在鼓吹活体移植,可它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太大了。“如果活体移植是中国器官移植的方向,那简直是胡闹。”陈忠华说,伦理学十大原则之一——万不得已不得为之,即患者没有器官才去找亲属,最后的一个选择才动用活人。“可活人不是病人的器官库,目前放着大片的自然死亡人的器官不去利用,你去动用活人,这个方向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