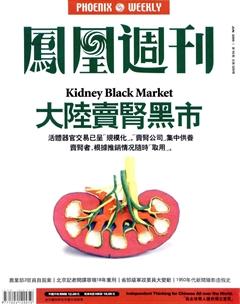大陆卖肾黑市
谌彦辉
4月13日早上8时许,23岁的龙启平被护士推进寂静的手术室,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脱光衣服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一言不发,神情略显紧张。他一边安慰自己摘掉一个肾脏还有另外一个在发挥作用,一边又害怕身上会留下一个缝合后的巨大伤口,而伤口内将有一个永远的“空洞”。
龙启平不敢继续想下去,脑中一片空白。这时,护士向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手术步骤,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强迫自己精神放松接受手术。

素昧平生的“亲属”
这一天,龙启平将要经历一次永生难忘的大手术,他决定摘掉一个肾“救”他素未谋面的“叔叔”。
身份证明显示“叔侄”俩住在西安市城郊的一个小村庄,但过去他们从不相识。最近,小龙和“叔叔”一家人在北京某总医院附近的一个小饭馆第一次见面,一顿饭的工夫,小龙答应他们一同前往北京武警总医院做“亲体”肾移植。
手术进行一个多小时后,小龙被推出手术室。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叔叔”家人并没有急切地凑过来问候,而是依然神情紧张地关注着手术室内。
小龙被推进了住院大楼6层一间大病房。两个小时后,小龙“叔叔”手术结束也被推了进来,和他正对床。
和小龙一样,在北京这家医院,几乎住满了来自各地前来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人。在这里,通常患者单独住一间病房,而供者大多挤在一间大病房里。最近医院床位紧张,一些患者和供者不得不临时住在一起。
3天后,小龙恢复了一点体力,他已经能下地走动了。面对病房外走廊宣传栏里诸多亲体肾移植的感人故事,他似乎有点不屑。他知道,在这个住满等待进行“亲体”。肾移植手术的病人的6楼,有不少和他一样与“親属”素不相识。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在来回地走动,每天只有医院的护工来照顾他。
一周后,龙启平出院,“叔叔”一家人没有过来送他,他们又成了之前的路人。
服务到病房的“咨询”
小龙无声无息地离开,让对面病房的患者家属、河北承德市70多岁的闫福民难以释怀。每天看着一对对关系冷漠的“亲体”进行移植手术,老闫很肯定地判断:“他们其实都不是亲人。”
老闫是3月初陪40岁的儿子闫大军到北京这家医院来看病的。10年前,闫大军患上了肾病,病情一直未见好转,前两年,肾炎转化为尿毒症。治疗只有两个方法,要么换肾,要么进行血液透析。
刚开始,闫大军一周做一次透析,现在发展到一周3次。每月高达6000元的透析费用让他们不堪重负。
医生建议闫福民做亲体肾移植,但考虑到膝下孙女年纪尚小未成年,而两个闺女也都年过半百,他害怕失去儿子,又担心连累一个闺女,尽管主治医生再三解释手术风险有多低,老闫始终拿不定主意,一家人踌躇无措。眼看着同时间进来的病人都相继做了手术,他又暗自着急。
老闫时常碰见一些患者家属在医院走廊的尽头私下议论找中介,“他们能帮患者找到合适的肾源”。闰福民半信半疑,他试着拨通了一个中介的电话。很快,一位叫蔡源的年轻小伙找上门来。
“他30出头,戴眼镜,高个子,隔三差五便深入病房挨个进行宣讲。”老闫说,蔡源自称为。肾病提供医疗咨询服务,为患者带来福音,并向病人们派发了很多张印有“肾友之光”的名片,随传随到。“我能帮你从社会上找一个和你血型、配型一样的人来捐肾,只要你肯出钱。”蔡源开门见山地说。
老闫仍一脸疑云:法律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据称,医院还会多方求证,并组织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审查。
蔡源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供体虽然不是亲属,但术前他们会给双方做一套假的亲属证明,这些假证明到时也不用担心被人识破。“所有的问题都由我们负责,凡是你们担心的地方,我都帮你们排除,一切由我来搞定,”蔡源再三向患者家属承诺,“你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就行了。”
3天后,蔡源果然帮闫福民找到了供体,双方在北京某总医院附近一处僻静的茶楼见面,寒暄几句,老闫当即“认亲”,并向他们提供儿子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他们回去迅速地帮供体做了假身份证和假户籍证明,还为双方做了一份假的亲属证明信。
河北省乐亭县中堡镇徐家店村25岁的徐东杰最近为同村的“叔叔”捐献了一颗肾脏,但徐家店派出所的户籍民警却称“查无此人”。青海省民和县隆治乡桥头村的李辉忠也为远在黑龙江宁安市的“舅舅”捐肾,然而桥头村村委会主任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毋庸置疑,他们都是在中介的“撮合”成为“亲属”的。
截止到2008年12月,仅这家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共完成亲体肾移植140余例。该院内部人士透露,95%的“亲体移植”都属于假亲属。
闫福民担心假亲属为了钱隐瞒自己的病史和遗传史。为排除有潜在疾病的供者,他陪供体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经过血型、基因、淋巴等数十项严密的化验比对,最后配型成功才让他松了一口气。第二周,老闫的儿子排上了手术日期。
“我们的速度就是15天让病人可以做手术。”蔡源自豪地说,患者从见供者到出院不会超过一个月。他最近一个50多岁的天津患者12天就出院了。蔡源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他称两年里已帮助上百个患者找到供体。
一些外国人也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找他,一些日本、韩国的患者开诚布公地表明要换取活体肾。“那些外国人开具的亲属证明更好过关了。”蔡说,一些沙特、科威特等中东国家的患者都带着活体肾源来到中国做“亲体移植”。

“供不应求”催生中介
像闫福民一样,安徽的周庆先也开始为儿子寻找活体肾源。他儿子去年底已在北京武警总医院做过肾移植,但当时换取的是一颗死刑犯的肾脏。
术后,老周的儿子很快产生排斥反应,医院只好把他刚换取的肾脏摘除。现在他们又要准备第二次肾移植。病房区还有一个7年前植入死刑犯肾脏的女患者,她也在等待一个新的肾源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据了解,中国目前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以及严格的法律手续,使得来自死刑犯捐献的器官越来越少,这就使一些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另谋他途”。
据统计,中国内地每年新增尿毒症患者达12万之多,其中大部分需要肾脏移植治疗,但由于器官来源不足,每年有5%在等待中失去生命。
截至2006年,中国已进行了1.1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但供求矛盾依然突出。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
与此同时,在全球面临供体普遍缺乏的现状下,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正渐渐成为当今世界器官移植的主流方向。目前,亲体移植占器官移植手术总量的50%。
“病人都等急了,他们到处去找亲属帮忙。”一位器官移植医生感叹说,可现在亲属间捐献肾脏的义举还太少,不是所有的亲人在需要的时候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所以,一些人在生命线上垂死挣扎的时候,他会想尽办法活命,“这给器官中介提供了机会”。
集中“供养”随时“取用”
正是因为需求市场的巨大,器官移植中介也日益兴盛,已形成严格的程序化,公司化模式。
譬如,前文提到的“捐肾”给“叔叔”的龙启平自称是西安市一个出租车司机,但他操着河北口音,而他掏出来的身份证一看就是假的。不过,在北京这家医院的大病房里,小龙和其他供者似乎很熟络,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小龙说,他们卖肾前其实就在一个“公司”呆着。
但小龙不愿意多谈他们“公司”的情况,只说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知道卖肾“赚钱很轻松,钱到手也快,而且割掉一个肾就和阑尾炎切除一样,对人没有太大的影响”,于是自己就来了。
“那些卖肾的小伙子好像都被人控制着,他们有组织。”闫福民说,尽管与供者接触的机会不多,但他还是对这些年轻人略表同情,他们大多来自山西、河南等地农村,平日从不多话,生怕说漏了嘴,每次被好奇的患者问到“为什么要卖掉一个肾脏”,他们都只说“缺钱”。
中介更忌讳患者家属向他们打听供体的来源,“这是一个敏感话题,问不得”。老闫说,尽管每个中介都信誓旦旦,向他们保证供体没问题,但不知供体出处,他们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我們现在有一个活体肾源库正等待患者。”蔡源说,他们今年成立了北京诚信源信息服务公司,自己是移植信息部的主管,公司在重庆、上海,天津,北京、长沙、杭州等地设立了联络处。据他介绍,只要拿到病人的配型(俗称DNA),他们就能从上千个供体里去找,“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24小时到位”。
确切地说,这些供体事先早已做过检查,他们等着患者来匹配。蔡称,届时供体的身高、体重等相关资料都会传真过来给患者过目。目前的行情不仅仅是患者来找供体,也有供体来找患者。
“它就是一个活体肾源库。”蔡源绘声绘色地形容,这种活体肾源库就像一个菜市场,找活体肾就像买黄瓜一样,到菜市场就能买到,而菜市场什么黄瓜都有。
相比以往那些在医院厕所门口张贴卖肾广告的个体,目前已然出现倒卖肾源的团伙组织。据了解,目前在河南郑州、吉林长春,陕西西安等市郊区村落中相继出现这种活体肾源库。这种倒卖活体肾的团伙就像传销一样,下线分布全国各大医院。他们用低廉的价格买。肾源,然后以双倍的价格出售给病人。一般直接联系病人的都是下线,由下线支付上线费用。
“供体平时都被他们供养着,有的供体被养了一两年,直到卖出他们的肾。”蔡源透露说,这些供体大多是二十三四岁左右的年轻人,多半是社会上一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青年。其中有一些是农村青年,他们因为贫困被中介忽悠过来卖肾,还有一些则是因为欠下高利贷,或者参与赌博还不起赌债而被逼卖肾。蔡称,这种倒卖肾的团伙也会设下陷阱以赌博、玩游戏机的形式让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参与,他们输钱之后无法还债,只好以器官相抵。
“他们很可能不择手段把供体弄到手,甚至是胁迫。”在北京这家医院开展中介“业务”的方小兰介绍,目前供养活体肾源的人有黑社会组织,也有患者、中介集团等,他们很清楚有多少中介在帮助供体联系患者,从不接陌生人的电话联系业务。“你要想找活体肾必须通过这些组织,否则你没办法把人带走。”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根据中介“流程”,在配型检查合格后,接下来就是讨价还价了。
闫福民在找到合适自己儿子的肾源后,蔡源开口向他索要20万元的供体费。
这令属于工薪阶层的闫福民大伤脑筋,据他了解,市场上的活体肾源15万元左右,加上手术费大约二三十万元。于是,老闫延迟了儿子一周的手术时间,与中介多次进行器官价格谈判。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承担的话,一次给够钱就什么都不管了。”蔡源称,供体价格也分“大包”和“小包”,“大包”包括供体费、住院费、检查费以及护工费等。除此之外,供体将来是否死亡,术后反应以及后遗症等,患者一律不管。大多数患者选择“大包”一次性了结,相比“小包”只多两三万元左右,而且不用担心供体术后出现其他症状不能及时康复的风险。
闫福民最终与中介敲定16万元的供体费。加上手术费,药费,住院费……闫福民总共花了26万元左右,包括为供体支付2万元治疗费,六七千元检查费,3万元左右的医生好处费。4月2日当天,在用现金一次性支付完毕后,闫福民的儿子终于被推进手术室。
虽然患者家属支付的价格不菲,但供体本人实际所得相对有限。
“供体拿到的其实很少,中间盘剥的太多。”蔡源说,做一例活体肾移植手术,供体本人一般只能得到3~5万元,而每一台手术顺利施行,医生也得到相当大的利益,中介给病人肾源,病人支付中介除了手术费的所有费用,中介还得支付医生“闭眼费”(手续上他们是亲属捐献),他们必须向医生上交一个固定的数目,大概3万元不等。蔡称自己只能得到1万元左右的手续费,大部分钱都交到上家,即控制供体的组织。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得到某种形式的回报。患者是最大的受益人,其次还有进行移植手术的医生、护士、医院还有制药公司。由于第三方的存在,卖肾者所得自然有限。
龙启平即表示并不清楚一个肾脏的“市场价格”,“他们给多少是多少”。他这次卖肾得了8万元,相对其他供体来说已是一个“高价”。由于不掌控价格谈判的主动权,也没有机会和患者家属讨价还价,小龙们只能任由“公司”宰割。那些靠卖肾偿还赌债的人甚至分文未得。
买通医院“伦理审查”
蔡源接触过的患者中有的较有身份地位,蔡源时常向病人炫耀,这些都是有权有钱的阶层,他们对自己也是充满感激的。
蔡源也一直宣称他们在行善积德。他说。现在被执行死刑的囚犯越来越少,如果禁止这些活体肾源,那病人只能活活等死。
然而他们做的“善事”却不被法律认可。依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三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条例规定,对买卖人体器官或者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活动的,由卫生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交易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医疗机构参与上述活动的,还应当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等。但是,“什么时候下狠心来整治这种状况,卫生部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一位委员说。
该委员认为,杜绝活体器官移植出现非法买卖,关键在亲属关系认定这一环节,相关人员完全可以把关。目前成立伦理委员会,在每个器官移植手术开展前进行严格审核,已经成为医疗机构开展器官移植的首要条件。
据了解,伦理委员会由临床医学专家,器官移植专家、律师和伦理学专家组成,三分之二以上专家同意,手术才能够批准实施。在讨论某一个器官移植手术时,本专业的移植医生,要回避讨论。伦理审查中最重要的文件是捐献者书面的知情同意书和自愿捐献书,公安或者公证机构还要出具捐献者和接受者之间亲属关系的证明。
然而卫生部关于伦理委员会的设置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各地移植中心的伦理委员会构成要求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北京武警总医院肾移植专家组主任刘航介绍说,伦理委员会现由药房、检验等各个相关科室的专家组成,同时武警总医院还专门聘请了律师来审查。但因为业务繁忙,不是所有专家每次都能出席伦理审查,每次大概有10來个专家参与评审,而移植专家不能列席。
“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假亲属。”刘航称,所有的病例都由伦理委员会来把关,医院同时保留存档经得起任何检验。但作为主管医生,他们平时并不负责把关,“我们也没法判断他们是否为亲属,我们只能相信他们提供的东西”。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与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负责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坦承:“器官买卖的现象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亲体移植中器官捐献者不是亲属,而这一现象在内地医院相继出现。”
沈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目前作为医学会伦理委员会的试点单位,院方还购置了第二代身份证验证机,但仍有假亲属蒙混过关,世界各地都发生过类似的现象,“这并不是中国的特色”。他说,杜绝这一现象不仅是医院的责任,还有待社会共同努力。
一位曾参与伦理审查的医生透露说:“中介现在越来越高明,他们什么文件都给你配齐了,我们也没辙。”他称,甄别真假已经超出医生的工作能力范围之外。更何况,一些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不严,“他们只是做一些象征性的审查”。
一些中介扬言伦理委员会已被他们买通了,一些医生甚至与他们合伙参与器官买卖。闫福民透露,在儿子手术前,医生到病房还特别关照教他们如何通过“伦理关”:“伦理委员会也只是简单地问我们是不是亲属,是否自愿捐献等问题。”老闫说,过关非常轻松。
“我们干这一行是‘民不告,官不究,”蔡源说,“大家都踩在线上走,不要越轨就相安无事了。”
不过沈中阳认为,绝对不会有伦理委员会成员从中受贿,任何一家医院的伦理委员会都不会协助这种器官倒卖,甚至受贿让假亲属过关。“我们医院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和中介勾结从中牟取私利。”不过他不能排除一些假亲属蒙混过关,背后暗藏器官买卖。
移植标准即将探讨
据透露,7月初,卫生部将在长沙召开中国第一次规范亲体移植标准的讨论会。届时,国内器官移植专家将讨论如何控制当前亲体移植存在的器官买卖现象,而有关亲体移植的基本标准目前由沈中阳起草。
沈称,标准制定出来后,即使不能完全控制住器官买卖,也至少能刹一刹这股歪风。
沈介绍,标准制定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第一是控制亲体移植的医院资质,即该医院首先必须是有能力的,做一个能好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保证供体的安全。沈中阳说:“我们现在关心的不仅是器官买卖,而且是供体安全的问题。”他认为,医院进行亲体移植必须是技术能力成熟,而且科学态度比较严谨,能够有效保证供体安全。
第二是怎样杜绝器官买卖,目前卫生部和医院没办法抓住器官中介,只能从内部管理控制这种现象发生。
第三是关于伦理委员会,沈中阳建议卫生部应该给伦理委员会相应的费用补偿,而不是让他们免费来进行伦理审查,伦理委员会一定要有一个政府开支。“让他们当作一件工作去做,必须给他们费用。”他说,现在有一些伦理委员会成员存在审查不严格的现象,伦理委员会成员构成适时也会作相应的探讨。
据悉,这次会议关于亲体移植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至少国务院法制办将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予以规范。
(文中患者、供者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