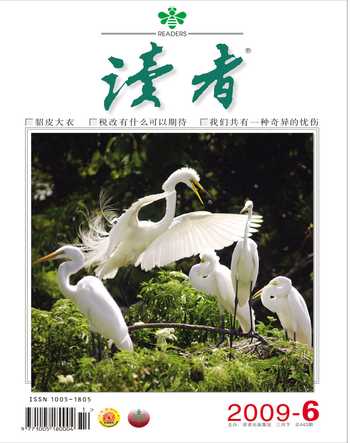只有疏狂一老身
熊召政
研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某一个人物,生在某一个时代是福气,头上顶着光环,到处受人尊敬;换到另一个时代,便成了天地难容的人物,不但吃尽人间苦头,弄得不好还会丢掉性命。杜甫说李白“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其意很明显,道的是李白不合时宜,世人都不喜欢他,必欲诛之而后快。其实,杜甫言过其实,李白生活在盛唐,当属社会的宠儿。他虽然受到流放夜郎的处分,也是在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之后。他参加了谋逆者反抗朝廷的军事举动,若碰上朱元璋或康熙一类的皇帝,十个脑袋都搬家了。把中国历朝历代做一个区分,则可以说:春秋战国养士,汉朝养武,唐朝养艺,宋朝养文,明清多养小人。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套用之,一个朝代也会使某种人得到特别的发展。照这个逻辑来推理,李贽生活在明代,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李贽写过不少“咏史”诗,其中有这样一首:
持钵来归不坐禅,遥闻高论却潸然。
如今男子知多少,尽道高官即是仙。
读这些诗句,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癯瘦削的老人,戴着斗笠骑在驴背上,看着满街的驷马高车,发出鄙夷的微笑。李贽为何有这等感情呢?这还得从明代的政局说起。李贽出生于嘉靖初年。嘉靖之前的正德年间,实乃明代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在正德皇帝之前,朝廷的清明虽不如开创初期,但大臣都还讲究操守。皇帝虽不能严于律己,却还能宽恕待人。正德皇帝十五岁登基,未谙世事,国家的操控权实际掌握在大太监刘瑾手中。胡闹几年之后,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虽经正直的大臣设计诛除了刘瑾这位“九千岁”,但正德皇帝并未汲取教训,依然胡闹。由于皇帝坏了坯子,他身边的小人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到他死时,因小人当道而形成的官场潜规则,早已变成了指导官员的“世间法”。继位的嘉靖皇帝不但不能扭转颓风,反而因为迷恋斋醮、猜疑多忌而助长了小人政治的发展。出生于嘉靖六年(1527年)的李贽,终其一生,都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度过。在他入仕为官的二十多年中,君是昏君,臣是庸臣。除却张居正柄国十年推行“万历新政”这一时期外,政坛上生气凋敝,乏善可陈。
政坛越是腐败,想当官的人也就越多,这几乎已成规律。因为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可以通过当官来获取非分的名利。按市场经济学的观点,官职永远属于短缺经济。这就导致卖官鬻爵的情形屡有发生。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官民的尖锐对立已使大明朝陷入深刻的危机。但是,俗世的享乐与眼前的利益促使明朝的士人放弃了忧患,官场因此变成了名利场。李贽是少数清醒的读书人之一,他讥笑那些把高官当神仙的人。既然官道龌龊,令他心寒齿冷,与官场的断绝便是无可替代的选择。在多年的道德探求之后,他终于发现了“菩萨道”的美妙,既可救心,亦可救世。于是,他自负地吟唱“欲见观音今汝是,莲花原属似花人”。
在古代,对皇帝的效忠被看做是一个读书人起码的道德要求。但是,李贽弃官绝俗皈依佛门,并以观音自居,在士大夫眼中,他便成了双重的叛逆者,既背叛了皇帝,也背叛了儒家。比之李白,李贽是真正的“世人皆欲杀”。他认为自己的灵魂只能安置在莲花宝座上,但在世人眼中,他只能待在万劫不复的地狱中。
中国是一个善于造神的国度,因为造神者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被造者。李贽看出这一点,十分痛心,在给友人耿定向的信中言道:“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对于造神者的批判,李贽一针见血。
李贽穷诸学问,关注当下。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他比李白更彻底,干脆认为自古本就无圣贤。这种思想脉络,可从禅宗慧能的偈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中寻找。佛家讲“众生即佛”“我心即佛”,是民本观念,而儒家的内圣外王,则是精英观念。李贽援佛批儒,在儒家盛行的中国,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研修学问,讲求经邦济世,即学问服务于国家、作用于社稷的功能。从观念上看,这一点是不错的。但由于儒家学说的局限,读书人入仕后,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往往与经邦济世的理想南辕北辙。究其因,乃是因为儒家把道德伦理作为建设社会秩序的基础。事实证明,离开法制,社会根本就没有秩序可言。这道理虽然简单,中国古代的儒生,却似乎难以懂得。李贽虽也是儒生,也入仕为官,但他并不把道德伦理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学问。他对古人与当世人的评价,其着眼点不在操守,而在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这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他对张居正与海瑞的断语。
李贽与张居正、海瑞是同时代人,都生于嘉靖初年,死于万历年间。客观地讲,这三个人,外加一个戚继光,应该是那一时代最负盛名的四大人物。张居正于1572年出任首辅(相当于宰相),辅佐十岁的神宗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是有明一代绝无仅有的中兴名臣、力挽狂澜的大改革家。他执政期间裁抑豪强,注重民生,后世称他为“权臣”“法家”,讪谤甚多。海瑞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抱着一死的决心给沉湎斋醮、荒怠政务的嘉靖皇帝上万言书,是有明一代最大的清官。张居正柄国,始终弃用海瑞,这一点曾引起当世士林的诟病。张居正死后,朱翊钧迅速对他进行残酷的清算,并重新起用海瑞。在史籍记载与后人的口碑中,张居正毁大于誉,而海瑞却是誉满天下。
作为他们同时代人的李贽,却没有随波逐流。他深情地赞誉张居正是“宰相之杰”,而评价海瑞为“万年青草”。在李贽看来,张居正是真正的经邦济世的伟大人物,而海瑞只是以人格取胜。生命如草可以万年长青,但绝不是振衰起隳的国家栋梁。
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来看,李贽心仪的政治人物,不仅仅只是会做道德文章,更应该有着为社稷求发展,为民生谋福祉的巨大的担当精神与行政才能。
道德与事功,清流与循吏,一般的读书人,都看重前者,而李贽赞赏的却是后者。
李贽既不能像张居正那样,以事功影响后世,也不能像海瑞那样,用道德影响士林,但他的叛逆与追求本真的精神,却是晚明时期思想界的一盏明灯。
数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人有两种:一种是石头,在任何激流中挺立;一种是咖啡,可以百分之百融于水。李贽当属于前者。他特立独行,蔑视世俗,因此当世难容。比起张居正与海瑞,他的处境更惨。皇皇一部《明史》,张居正、海瑞皆有列传,而他只在耿定向的条目中附上数语以示交代,可见皇室操纵的史家,对他这位狂人,连贬损几句的兴趣都没有。李贽晚年弃绝功名,对这种“世人皆欲杀”的处境,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
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
以七十五岁疏狂之身在狱中用剃刀自杀,表明了李贽与流俗抗争到底的决心。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明朝就以崇祯皇帝的上吊而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谢幕。比起崇祯来,李贽的悲剧似乎更能体现文化上的意义,因为他死的年代不仅是明朝最腐败的时期,更是思想上最为平庸的时期。
(吴顺国摘自中华书局《去明朝看风景》一书,黎 青图)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