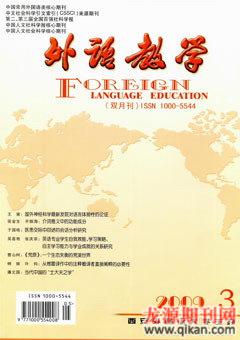胡适在翻译史中被边缘化现象的改写理论解析
摘要:本文依据改写理论,论证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对外国作品多种形式的改写——即广义的翻译一无论是自身的翻译研究价值,还是对目的语文化和文学的导向与影响都有着狭义翻译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胡适在译史中却处境尴尬。这种现象在译界有其普遍性,是翻译及翻译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文章深入分析了该现象所反映出的多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建议,旨在引起译界的重视。
关键词:改写理论;翻译史;胡适;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44(2009)03-0085-05
1,引言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在这一文化转型期,一向处于边缘位置的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系统的主流而处于中心位置。在这种状况下翻译与创作、译者或改写者与作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译者的主体性增强了,从语码转换者变为源信息的阐释、评论及改写者,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所需对源文信息量进行取舍,进行综述,形成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的局面。这一时期对外来文化的译介呈现出多种形式。特别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领袖人物各类形式的改写,直接介入并影响了时代文学思潮的走向,在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构建中国本土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方面起着狭义的翻译无可替代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胡适在这一时期的论著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个特点。他以创作形式撰写的论文、外国文学评论、仿作、文学史等都是在以不同的改写形式输入外国作品和思想(赵文静2006)。与传统的翻译所不同者,这些形式为译介者按照自己的翻译动机或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需要去塑造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形象提供了选择空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绝大多数普通读者了解外国作家与作品的渠道不是通过读原作或具体翻译作品而是通过文学评论,传记作品,文学史等形式的改写(赵文静2006:222-3)。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这些改写形式译介的外国作品,特别是出自像胡适这类有学术威望并拥有广泛读者群的学者有意识地改写,比狭义的翻译对于目的语社会应该会有更大的导向作用并能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研究这类形式上不明显的翻译对于翻译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胡适在运动初期以多种改写形式发表的一系列震撼知识界的文章无论是发动文学革命还是构建新文化,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演变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直接推动了当时新文化及新文学的发展。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我国,这种“形式上不明显的翻译”(k—revere 1982/2000:235)还没有真正成为译界的研究对象,对这类改写的研究仍然是个薄弱环节。例如,在对胡适进行的多方位的研究中,以他的改写方式作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胡适因此在翻译史上一直处境尴尬(见赵文静2006:1-18)。这无论对于该阶段翻译史的撰写还是对胡适本人的研究都无疑是个缺憾。本篇将从改写理论的视角对胡适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展开分析。
2,关于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是由翻译的文化操控学派关键人物之一,美籍比利时裔学者Andr6 Lefevere提出的翻译研究理论(1985,1992)。这一理论广泛吸收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等邻边学科的研究成果。受这些理论的影响,Lefevere将介于翻译与创作之间的文学形式: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评论、文学家传记、仿作、百科全书等——即无标示或标示含糊的翻译——统称为改写(rewriting),这些一向被传统译论视为与翻译无关的创作形式因此而进入翻译研究领域,成为合法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该理论还强调翻译研究应该将关注的焦点从单纯的文本转向复杂的语境(context),从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层面进而研究社会的诸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探讨翻译活动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的操控下产生、接受并起作用的。如果说纳入不同形式的改写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的研究范围,那么关注焦点的转换则为翻译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方法论。Lefevere也因此被视为当今翻译学的一位先驱。毫无疑问,改写理论是对翻译研究的一场革命,它打破了翻译研究必须与原文对应的框框,从而把译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研究平台。根据赵文静(2006),该理论可大致从“改写的形式”和“控制因素”两个方面加以概括,首先翻译研究的对象还应该注重那些“形式上不明显的翻译”。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应包括对原作思想和精华的总结、提炼,对原文作者和精神的评价以及对原作的模仿等。至于对改写作品的研究,该理论认为翻译从来不是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译者不是单纯的旁观者,引进外来思想绝不会原样照搬,而会根据本土的需要进行改写。Lefevere指出应该从接受环境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活动。相信凡是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接受环境中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操控下对原作品的思想,概念和文本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改写(见Lefevere 1992:1)。前者应该说是相对于狭义翻译形式的广义的翻译,而后者则是包括政治,社会及文化多种制约因素的广义的翻译研究。
3,从改写的视角看胡适对新文化建构的贡献
根据改写理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发表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改良刍议》、《论短篇小说》、外国文学评论《易卜生主义》、模仿易卜生创作的《终身大事》,以及后期的《白话文学史》等都属于对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不同程度的改写(见赵文静2006)。这类对西方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多种改写形式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新文化的建构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顾名思义,就是要用新思想,新价值观。新诗学观取代旧观念。在中国的历史上,“五四知识分子与传统彻底决裂的那种激进的态度,或许在世界知识分子运动史上也是无可比拟的”(Denton 1996b:114)。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受到如此严厉的质疑和批判。这种决裂使得这个刚刚推翻了封建帝制而处于历史转型期的国家文化中出现暂时的空白。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倡导者通过“形式上明显的翻译”和“形式上不明显的翻译”大量引进反映西方思想意识,价值观的文学理论及作品。使得通过各类改写所构成的翻译文学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极具代表性。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和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胡适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西方思想和文学的改写(见赵文静2006)。也就是说,胡适之所以成为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发表的一系列震撼学术界的文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胡适的名字在当时的知识界几乎无人不晓,为他后来成为学术史上的中心人物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胡适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学理论
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在他的同代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被胡适后来称之为“八不主义”)(1917)是公认的文学革命宣言书,它呼吁废除文言文,强调白话文在正式文体中的应用,由此掀开了新文学的篇章,改变了文学创作的形式和内容。然而这篇文章本身就是对Ezra Pound“一个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要”(1913)的模仿和改写(见赵文静2006:127-132)。他的《论短篇小说》(1918)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以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Galik 1986:10)。其中对短篇小说的定义——后来被中国文学界作为金科玉律反复引用——原本是对Clayton Hamilton(1908)所作定义的改写(同上:13)。他翻译的《短篇小说》和他的翻译与创作的混合诗集《尝试集》都是初版后不久就多次再版,后者还开创了白话写诗的新纪元。他为译介易h生发表的系列作品:评论文《易卜生主义》(1918)在中国读者中确立了易卜生的叛逆形象,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读者心目中的易卜生更多地是作为社会改革者而不是艺术家(胡适1919/1993:487)。他模仿易h生的《玩偶之家》而创作的独幕剧《终身大事》(1919)塑造了中国版的娜拉(赵文静2006:229-234)。上述作品对中国新文学在创作风格和内容上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剑华1996)。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翻译与改写确立了胡适最初的学术权威地位,使他拥有了话语权,赢得了专业人士的支持。他的作品因此成为“文化资本”(借用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的术语),对当时的文学翻译与创作有极大的导向作用。
然而,从笔者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来看,从翻译尤其是改写的视角来研究胡适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文学进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目前还不多见。因此胡适在翻译史研究中处境比较尴尬:凡翻译史都难免要提到胡适,也不得不对他的翻译及其影响书上一笔,但都不过是简单的一带而过(见陈玉刚1989;陈福康1992;王锦厚1996;郭延礼1998;谢天振等2004)。然而这显然不是上述撰写者的责任,对胡适的翻译改写没有或缺乏足够的研究文献直接影响到对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定位。笔者认为胡适研究的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反映出翻译研究领域在观念和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以便引起学术同仁的重视。
4,改写研究的薄弱环节反映出的问题
如上所述,对西方思想与文学的翻译和引进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而这一时期胡适的改写对移植西方文化起着主导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西方思想和文学理论的改写上。缺乏这个角度的研究,的确是胡适研究的一个缺憾。究其原因,是受翻译研究理念的局限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研究的操控所造成的。这恰恰也证明了改写理论中有关控制因素的论点。下面我们似乎至少可以从方法论,研究观念,学科的局限等三个方面来探讨。
4.1方法论的局限长期以来,传统上都把翻译只看作语码对应转换,只强调译文对原文的服从而忽略译者的自主性,即他的翻译愿景。翻译研究主要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为准则。不考虑时代,读者与译者所处的环境以及翻译作品对目的语社会文化的影响,不注意观察描述译者究竟是如何做的,不考虑具体转换过程所受到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只是规定应该怎样翻译,一味追求译文与原文之间的最近似的相等。任何增加或删略,都会使该翻译受到质疑。在这种研究方法限制下,诸如书评、模仿、文学史和文选等这类改写形式,尽管在引进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推动译人语文学和文化变迁上与狭义的翻译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有些情况下甚至比狭义翻译作用还大,仍被排斥在翻译研究的范围之外。
4.2研究观念的局限传统意识中固有重创作轻翻译的观念。认为翻译属于衍生物,低于创作,缺乏学术研究价值。翻译作品“不仅被认为是二手的,而且是二流的。因此不值得予以过多的关注”(Herrnans1985b:8,笔者译)。由于翻译受歧视,改写之类的作品地位自然就更低。有时还会被贬为抄袭或剽窃。例如胡适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不久,便被指责为剽窃(见Chow Tsetsung 1964:28)。这种观念使得人们在对著名学者的研究中,有意回避他们的改写,认为只有原创作品才能代表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能力。而承认他们的改写文献则是贬低其能力。以至于连一些学者本人也极力否认其作品的改写性质(见赵文静2006:127—132),因为他们也以所谓的“原创”为荣。具体到胡适,他的“创作”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的翻译,尽管他的一些所谓的“原创”实际上是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翻译与改写(同上),由于受上述传统的价值观影响,研究者宁愿将其作为创作而不归于翻译和改写来研究。事实上翻译与改写不仅仅在新文化运动这个特殊的文化转型期占主导地位,也在胡适该时期的成就与贡献上占据重要位置。胡适在这一时期提出的“输入学理”与“再造文明”的目标(胡适1919/1953)使得以他为首的文化革新派会根据需要引进外来理论,改写必然是其中很重要的方式,因而应该成为研究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通过读具体的外国作品来了解其内容的读者较少,他们对于外国作品及作者的印象多数来自外国文学评论,尤其是在读者心目中有权威的学者的评论。Gfieder有一段描述很形象地反映出胡适当时在学仁中的威望:在那一时期的精英群中,“他那受西方教育海归派闪亮的光环,他在北大的地位,他与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新青年》的关系使他成为这组为数虽不多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前卫派当然的领袖。毫无疑问,无论他发表什么论点,都会受到关注,受到重视,至少是在早期”(Gfieder 1970:78,笔者译)。也就是说,译者/改写者本人的学术威信和话语权力以及读者群对于他们的信任会使他们的作品对目的语社会产生特殊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的翻译与改写应该会比他同时代的职业翻译家的译品更具影响力,对树立原作的形象起着更大的作用。作为一项社会性极强的活动,翻译和改写与其接受环境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观、译者的话语权以及当时读者的期待等都有密切联系,这些都会相应的反映在胡适的译品与改写的接受与作用中。
4.3学科的局限学科的局限性形成另一个重要因素。从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来看,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者多为比较文化、比较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学者甚至哲学家,并至少精通双语(例如Baker,GentMer,Hermans,Lefevere,Venuti等均生活在其第二语言国家)。翻译研究在中国(包括港台)目前仍局限于大学教外语的教师之中。王向远(2001a)也谈到不同专业之间很封闭,同时像语言大师王力、吕叔湘、罗常培、钱钟书以及许国璋等兼有中外文学两方面的人才越来越少。翻译专业基本上是在语言层面上研究翻译的技法,而在大学中文系,翻译文学研究则难以展开。在他的《关于学术史编写原则的思考》一文中,樊俊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忽视翻译文学的现象,究其原因,是该领域的研究者受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两方面的知识所限。“对他们来说,产生这种‘忽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转引自王向远2001b:6)。就胡适的情况而言,绝大部分胡适研究者是中文、历史、哲学、政治等领域的学者,这就不难理解在翻译和改写研究方面的不足。
5,结论
翻译研究范围的扩大,包括多种改写形式,为重写我国翻译文学史、研究当代历史转型期的领袖人物及翻译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但是真正在观念上认可这些广义的翻译形式还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研究文献。应该指出,狭义的翻译中,毕竟有原作的存在,要顾及到专业人士的资质和声誉,译者还是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因此,所做的改写是有限度的。而在广义的翻译,即诸多的改写形式中,改写者有较大的自主权,对原作的阐释有整体操控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接受环境的需要去塑造原作或原作者的形象。应该注意到,近代大的社会变革都伴随着外来理论思潮的引入,而引导社会变革的领袖人物往往是新思想的译者或改写者。他们想要利用外来思想影响和改造本土文化的强烈动机决定了他们在改写过程中必定要按照自己的愿景对源文本进行过滤以便达到促进社会变革之目的。而他们特有的话语权以及他们的作品形成的文化资本使得他们的翻译与改写注定会比职业翻译家的译品拥有更大的市场,产生更大的导向。以胡适为例,他的评论文“易卜生主义”要比他参与翻译的《玩偶之家》在树立易卜生的形象上作用大得多。因此用改写理论中提出的诸多社会控制因素研究这些人物对外来思想理论的改写过程,研究这些翻译活动及其接受状况可以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学等方面的发展境况,勾勒出一幅比较清晰的社会变革图,这必将会对翻译史和理论研究有新的贡献。此外,翻译研究领域还需更加注重其跨学科性建设,培养和吸纳更多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以确保此类研究的切实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