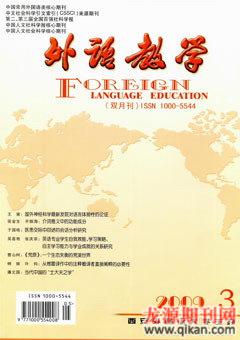伊莎贝尔.阿连德《幽灵之家》解读
刘雅虹
摘要:本文在文化批评的范畴内,以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为出发点,对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小说《幽灵之家》进行解读,旨在使读者认识拉美民族身份特征,关注社会关系,并把视角提升到整个拉美大陆的层面,揭示拉美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伊莎贝尔·阿连德;《幽灵之家》;文学;民族;拉丁美洲
中图分类号:1784,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44(2009)03-0078-05
1,引言
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处女作《幽灵之家》“出版后,很快引起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注意。小说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几种外语,在书市上十分走俏,成为读者争相传阅的畅销书,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它是‘二次大战后世界文坛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作者被誉为“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跻身于用塞万提斯的语言从事创作的最优秀作家的行列”,被誉为是继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拉丁美洲新一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本文旨在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
《幽灵之家》称得上一部鸿篇巨制,并非因其篇幅的长度,而是因为其中浓缩了智利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达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表现了土地改革、工人运动、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民选政府掌握政权、军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政府,对进步力量进行血腥镇压等种种社会问题,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不同人物在历史大变迁中的境遇,向读者展示了拉丁美洲各个社会阶层人物和城市、农村、地理、气候、历史、拉丁美洲生活的魔幻和现实的一面。小说以特鲁埃瓦·瓦列家族的兴衰变化为中心线索,讲述了三个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家长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是家中惟一的男性继承人。由于父亲的挥霍,家道日趋衰落。因此他从少年时代就不得不工作以贴补家用,养活卧病在床的母亲和由于照顾母亲而终身未嫁的姐姐。成年后他去北部开发金矿,发现了一条丰富的矿脉,发了横财,并振兴了家族古老的“三星庄园”,即故事的大半部分发生的地方。埃斯特万与他的第一个未婚妻罗莎的妹妹克拉拉·瓦列结婚,和她生了三个子女:女儿布兰卡,孪生兄弟海梅和尼古拉斯。布兰卡与庄园管家的儿子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生下了女儿阿尔芭。除了这几个特鲁埃瓦家族的人物,作者还塑造了其他人物形象,他们与特鲁埃瓦家族的人物互为补充,构成一幅丰富的人物画卷,表现了拉美广阔的社会现实。
2,文学与民族
艺术与文学可以复制民族想象。小说是想象的方法之一(另外一个是报纸)在现代化开始时出现的。以故事的时间结构为出发点,在想象的共同性方面,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可以表现民族身份特征(Anderson1993:46-49)。民族的集体经历通过演出、叙述和形象来表现,即用戏剧的形式表现民族固有的思想观念、民族经历和共同记忆(Subercaseaux 2007:15)。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历史时代的舞台化是文学作品的一个象征性装置。民族的共性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文学作品承担表现其民族共同想象的使命,民族的共同特点,共同经历通过文学作品得以再现。文学作品一般都间接地或用比喻的方式反映了真实的现实世界,否则,文学作品的部分或者全部就超出了读者的理解范围,其结果是不可理解(R0j0 2006:203)。
《幽灵之家》使读者进入到拉美民族的共同想象领域,关注社会关系,由社会各个阶层联系到不同种族,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作品中表现的民族意识、文化差异并逐步对其加以认同,并把视角提升到整个拉美大陆的层面,表现了拉美广阔的社会现实。
3,庄园——暴力征服的象征性空间
3.1“从属”文化
“幽灵之家”是私人住宅,是特鲁埃瓦家族在城里拥有的房产,是克拉拉·特鲁埃瓦“实践”“招魂术”,接待秘密会团的成员、保护穷艺术家的场所。“幽灵之家”像一辆巨大的车,一个收容所,满载被“幽灵之家”吸引的人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虽然小说的重要部分在城市展开,但庄园是贯穿全文的象征性空间。故事从始到终发生在特鲁埃瓦家族在南部拥有的“三星庄园”——和其他拉美国家相似的庄园,因为在智利,农村人多于城市人,传统多于现代,暴力超越理性——和拉美其他国家一样。“庄园”破译了拉美的身份特征——殖民时代的征服者实行的原始暴力在庄园得到延续,被庄园主对其家庭和雇农实施的暴力所替代。
Pedro Morande和Carlos Cousifio认为,关于拉美身份、民族身份的说法是定义拉美阶级和种族关系的文化母体,取代了以前的印欧混血人、私生子、天主教和庄园这些名词。为了理解拉美文化身份,找到20世纪前几十年里出现的寡头政治的共和国危机的根源,即为什么现代化在拉美难以推行,现代化的过程未能产生包含全部社会团体的新的混合文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社会学家Pedro Morande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对“现代化”进行了评论和阐述。Morande认为,在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强烈而虔诚的宗教意识,表现了“产生于18和19世纪的拉丁美洲的文化融合,基于两种文化——西班牙和印第安土著文化——共同拥有祭祀仪式。这种穿越时空,覆盖全部社会生活的融合,催生了一个特有的传统文化(Morande 1987)。这样的传统文化使现代化在拉美不像在欧洲和美国那样,成为一种民主政体,而是转化为拉美的一个部分特点,一个尚难以成为拉美文化身份的特点。在拉美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传统、保守和独裁、专制和暴力等种种成分。
关于智利的身份,Carlos Cousifio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庄园是作为智利社会的基本结构出现的。从16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期,庄园不仅是土地所有权的形式,而且是形成一个新人种的模子(后一点将在后面阐明)。庄园体制是殖民地时期建立的社会结构,是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式封建制度的延伸,是按家长制庄园形式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庄园主是土生白人,梅斯蒂索人(印欧混血种人)是庄园的主要劳动力。庄园符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家庭特色,其中庄园主与雇工之间不对抗,因为他们的关系建立在忠诚和传统的基础上,他们之间的感情真挚而内敛。另一方面,庄园禁止美国式民主自由思想的萌芽,庄园里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身份是雇农,他们与庄园主是从属关系,在庄园主的庇护下过得舒服自在。智利的特点与历史上欧洲及美国所遵循的民主政体形式不同,Cousifio说,“智利曾经是一个庄园”,这个闭关自守的世界对外部世界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把外面的世界当作威胁,而他们之所以排斥来自外部世界的可能性危险,根源在于雇农对庄园主的信任(Cousifio 2007)。
Cousifio认为,“土地改革”不仅代表了政治、经济上的改革,而且代表了家庭生活的根本改变,因为家庭、庄
园体制、甚至国家政体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其特色是虔诚的宗教意识和严格的社会组织形式(Cousifio 1999)。但是在智利,从60年代开始加快的改革,虽然意味着庄园制度的终结,却不像在别的国家那样——庄园主被推翻,庄园体制被民主政权替代。在智利是另一种情形——即庄园等级在家庭方面得以保留,只是换作女人来维持。女人,作为母亲延续家庭元素,独自抚养孩子,在敌对的社会环境中保护孩子,而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土地改革使农民迁到城市,来寻找能够保护其权利的官方角色,但是他们往往落到没有社会地位,放荡挥霍的地步,他们决不会借助政治暴力来改变自己的境况,而政治暴力一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寡头统治集团家庭的大学生们改变社会的惟一途径。因而,无论是政治,还是社会或市场,都不会给这个数目庞大的刚刚来到城市的人群提供一种新秩序,这样等级秩序在家庭空间再生。母亲,作为家庭的主导性角色,费尽心力、谨慎小心地保护子女,在丈夫或伴侣——如果她有的话——面前,代表秩序和纪律,为孩子辩护,培养出的儿子具有母亲的气质,缺乏勇于承担责任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
Jose Bengoa认为,庄园是印第安文化和西班牙文化融合的得天独厚的空间,在这里庄园主对雇农实施从属统治,庄园是一个在社会和性领域排他的复合体,也就是说,庄园这个“慈善机构”在社会方面和性方面的统治是一体的,二者密不可分。“庄园主拥有一切,是家长,确立他在农村的领地,他说一不二,用暴力的马鞭统治这片空间,空闲的时候出外随意寻欢作乐。”总之,“庄园主”拥有双重涵义:既是庄园的主人,也是性的主人,后一点表明雇员和庄园主之间存在依附关系(Bengoa1996:85)。
然而,在Bengoa看来,庄园时代并非“失去的天堂”,在庄园时代,自然的野性和膨胀的肉欲占主导地位(Bengoa 1996:85)。若将庄园理解为“失去的天堂”,就掩盖了剥削关系和使其合法化的从属文化。《幽灵之家》涉及到“私生子”——庄园主与女仆之间的性交结果——这个话题。Bengoa认为,这些女人“教给她们的儿子爱和恨——爱庄园主,恨强奸者父亲”。雇农的隔代仇恨变成了阶级意识。从阶级意识出发,雇农转变成了矿工、硝石工和无产阶级。一旦脱离了庄园文化合法化的范围,就会产生复仇心理。他们忘记了庄园主上帝,忘记了他们的爱,侮辱的回忆就汩汩流出。仇恨早就诞生在庄园里。
关于“私生子”这一话题,人类学家Sonia Montecino在其杂文《母亲与私生子》中说,西班牙男人和印第安女人之间的关系很少走向婚姻。一般来说,母亲和她的私生子一起生活。她被西班牙男人抛弃后,想方设法维持生计,西班牙父亲则成为缺席角色。孩子只有母亲,而父亲是复数的,可能是这个也可能是那个西班牙男人,即父亲是共同的(Montecino 1996:43)。私生子,穿越时空,延续至当代,覆盖整个社会,特别是集中在社会的中等阶层中。私生子身份变成一个主体身上的烙印,他们不受法律保护,因为种族差别下的法律只保护“婚生子”的利益。这种状况至少差不多到20世纪末才得以改变。
Sonia Montecino认为,在20世纪初,在统治阶层依然保持着非法男女关系以及私生子的出生。“在城市,实行家庭雇员体制,印第安女人代替孩子的母亲抚养孩子;在农村,则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庄园体制,存在非法男女关系和私生子的出生”(Montecino 1996:52)。穷苦的印第安女人、印欧混血女人,仍然是男人那“黑暗中的欲望的工具”;她是家族中男性的性启蒙者;她当保姆,替女主人抚养孩子。在雇农的眼中,庄园主是“邪恶的家伙”,是等级差别的制造者,他的身份地位使他拥有在其领地范围内的农民们的女儿、姐妹和妻子身上繁殖私生子的权利。这样,不计其数的私生子以一种模糊不清的身份遍布农村。
3.2文学反映现实:性暴力成为习惯
伊莎贝尔·阿连德在《幽灵之家》中表现了庄园、家长制家庭及其与雇农之间的关系,但其独特之处并非其所表现的内容,而是表现的方式,贯穿整部小说的张力是阶层之间的冲突。社会等级秩序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随着农民工和城市工人逐步地意识到他们的权利而被逐步地瓦解,这种变化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内部存在着强烈的阶级冲突,这种冲突不但无法解决,而且在《幽灵之家》中,阶级冲突转化为一个不幸的宿命——落在了女人们的身体上:她们被另一社会阶层的男人强奸,与他们保持亲属关系,而这样的关系产生于女人的身体,根据男人的意志而结束。
“他的实际的感官指引他必须寻找一个女人,而一旦作出决定,消耗他的不安就得以平静下来。他的恼火就似乎平静了……他粗野地不顾一切地向姑娘扑去,事先没有任何抚爱,暴力也没派上用场。……潘恰·加西亚没有进行自卫,没有抱怨,也没有闭上眼睛,只是躺在地上,用惊恐的目光仰望着苍天,直到觉出埃斯特万已经平躺在她身边。在她之前,她的妈妈——在妈妈之前,她的奶奶——也曾遭遇过母狗一样的命运。”(伊莎贝尔2007:67-68)
“我在想,一切发生的事情均非偶然,全都符合生我之前已经画好的命运图。埃斯特万·加西亚不过是这幅图画的一部分。勾勒加西亚的线条是粗糙的、歪斜的,但没有一笔是白费的。那一天,外祖父把加西亚的祖母掀翻在河边的灌木丛中,这就为以后必然发生的事件的链条增加了一个环扣。后来,被强奸的女人的孙子对强奸者的外孙女儿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也许四十年后我的孙子又会把他的孙女儿按倒在河边的灌木丛里。如此下去,就会在今后几百年间不断重演这个痛苦、流血和爱情的故事”(伊莎贝尔2007:452)
引用的这两个片段属于故事的两个特别的时刻:开头和结尾。第一个片段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叙述,第二个片段是他孙女阿尔芭在叙述。埃斯特万强奸“第一个女人”——他身上膨胀的肉欲的工具;而阿尔芭则成为潘恰·加西亚的孙子——同时也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孙子——报复的工具。私生子的身份通过富人家女人的身体得到清偿。而众多的命中注定遭受“母狗命运”的女人们和富人家的女人们一样,只不过是同一个门第的“疯狂的男性之间冲突的工具”。
3.3阶层不同,命运各异
阿尔芭和潘恰对无情的命运表面看来都是逆来顺受的,但是阿尔芭没有像潘恰一样遭遇沦为母狗的命运,而是成了报复的牺牲品。小说中叙述的军事政变发生后,她被捕入狱,备受凌辱,被埃斯特万·加西亚——一个出身低微的上校,在历史的转机时刻实施了强暴的仪式。由于阿尔芭没有亲身参加这场革命,所以得以幸存,而关于这场革命,她起初尚懵懵懂懂。通过她对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后来成为游击战争领导人的米格尔的爱情才找到答案:“‘干这种事不能光凭爱情,得凭政治
信念,政治信念你还没有,米格尔回答说,‘我们不能随便接纳业余爱好者。阿尔芭觉得这个回答太粗暴了。只是过了好几年,她才弄明白这番话的全部含义。”(伊莎贝尔2007:349)阿尔芭最终参加了人民的革命斗争,既出于爱情,也出于对她所属阶层的反叛,而不是出于对革命发自内心的信仰。无论如何,她最终克服了“恐惧”,精神上得以超脱。
阿曼达的命运则更加悲惨。阿曼达在故事的中间部分出现,从秘密会团的世界露面,来到克拉拉的女性世界,后者的世界也包括她的儿子之一——尼古拉斯。尼古拉斯诱惑镇上所有的女人,但没有用其父的暴力,而是用母亲的温柔——“他有当地人从未见过的浪子的手段”。阿曼达比他年长一些,“教他学习瑜伽和针灸”,后来她又开始信仰存在主义哲学,穿黑衣服,吸毒,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形象出现,引起了特鲁埃瓦·海梅和尼古拉斯孪生兄弟的兴趣,但是她掩盖了一个秘密:她中产阶级的出身,靠救济生活以及照顾小弟弟的重担。阿曼达的故事不仅是现实的表现,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她在特鲁埃瓦家族中的女人们:潘恰·加西亚们和布兰卡们、阿尔芭们之间的过渡特点。她属于“沉默的中产阶级,他们不甘心过勒紧裤带的贫困生活,又不可能赶上那帮外表金光灿烂的流氓”(伊莎贝尔2007:249)。特鲁埃瓦家族的女人们毕竟属于同一个门第的组成部分,把她们作为争斗中的战利品而拥有她们的男性也一样属于同一个门第;而阿曼达由于时时追随新潮的思想观点,因此她的结局更加悲惨。书中没有明说阿曼达所走过的是什么路,但是提到她吸毒,而且一副饱经风霜的面貌,虽然特鲁埃瓦家孪生兄弟中的哥哥——正义的医生海梅——怜爱她,送她进医院,帮她戒毒,为她治疗病痛,但她最终还是不堪军警们为了让她屈服、揭发其弟弟而加在她身上的酷刑,不幸死于狱中。她完成了她的使命:为米格尔付出生命,给米格尔当母亲,像她所属的中产阶级的人们那样,靠伪装在世上生活。
特鲁埃瓦家孪生兄弟的形象很特别。海梅和尼古拉斯更像是母亲而不像父亲的儿子。他们在美国人开办的寄宿学校里接受教育,学校离家很远,远离天主教的氛围,远离庄园的那套清规戒律。事实上,比起乡下世界,他们俩更属于城市世界,与母亲更亲近,而就是在城市的环境中结识了阿曼达——一个另类女人。但是他们的命运同样也是悲惨的,至少海梅的命运如此。他是医生,是总统身边的人,在城市的平民区履行传教使命,悬壶济世,扶困济危。他不赞成暴力,却最终成为暴力的牺牲品。而尼古拉斯被不能容忍其行为的父亲驱逐出家门,故事的后半部分他没有再出现。
作品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在革命失败后非但毫发未伤,反而获得一席立足之地的惟一的女性形象是特兰西托·索托——这个野心勃勃而且精明能干的妓女,凭借在“三星庄园”附近的妓院里工作时,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借给她的一笔钱,开办了一家著名的妓院,做了妓院的老板,最终成为权力圈内的名人。特兰西托在政治和经济变革中得以幸存,但是在社会变革中处于弱势,“妇女解放”的说法似乎并不适合她。特兰西托掌握了一种普通人家的正派女人不懂的隐秘知识,就像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在得知她成功地帮了他的忙,解决了他求她的事:把阿尔芭从军警手中解救出来时所猜想的那样:“我估摸着,她是利用她了解当权者不可告人的一面,偿还我借给她的五十比索。两天后,她给我打来电话:‘我是特兰西托·索托。您托付的事儿办妥了。”(伊莎贝尔2007:355)。不过,使特兰西托幸存下来的也可能是她对权力的认可。特兰西托从乡下移民到城市,虽然形式上进入了城市,但精神上却停留在城市的边缘。虽然她得到了经济上的成功,而且掌握了权力的网络,但在与特鲁埃瓦的第一笔交易之后的很多年里,后者仍然是她的老板,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认识到这一点,她承认她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因为她的权力在隐蔽的那一部分——性方面——浮出水面。按照民间传统习俗,妓女是惟一可以接触性知识,或者至少可以低调地开放“性”的女人。特兰西托·索托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通过金钱交易建立了性关系,但他们的关系也仅此而已,永远也不可能再进一步。桥归桥,路归路。
4,家庭——国家的缩影:拯救记忆
在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小说中,女人和男人以家庭等级秩序为中心,其外部形象因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建立。特鲁埃瓦·瓦列家族通过对社会成员的吸纳和排斥建立自己的家庭秩序。惟一在外面生存却没能组建家庭的是特鲁埃瓦家孪生兄弟、克拉拉的兄弟等,女人们和镇子里的男人们。
母亲克拉拉·瓦列以某种方式贯穿故事的始终,即她的生活日记——“记录生活的记事本”——连接了整个故事。直到最后读者才知道特鲁埃瓦家族故事的叙述者之一是阿尔芭,她通过其祖母的日记恢复了家族的记忆。可以说通过日记她战胜了恐惧,用某种方式恢复了她的身份。还有另外一个叙述者,是埃斯特万·特鲁埃瓦,他以某种方式缓慢叙述故事的另一部分,逐步评论他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同一社会阶层的男性叙述者和女性叙述者交替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屈从于庄园主的性暴力的乡下女人们,被其他的女人“叙述”,这些女人有类似于她们的经历,而她们一旦成为私生子的母亲,就成为同一个血统的成员内部冲突的导火线。
5,结束语
通过对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的解读,可以看出,在这部作品中,家庭比喻国家。智利的历史就是特鲁埃瓦家族的历史,婚姻关系和和上层资产阶级之间,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世俗主义与宗教之间,等等,存在的亲缘关系。共同的文化身份浮出水面:拉丁美洲的人种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来源和共同的归宿。于是在特鲁埃瓦家族的婚生子和私生子之间,在作为平等的、被承认的和不被承认的、被排斥的之间就产生了冲突。因此,在故事末尾产生的破坏是被拒绝承认的亲属之间的毁坏。像埃斯特万·加西亚那样身份卑微的人的仇恨和不满只能以在历史的转机时刻找到实施强暴,作为其寻求承认的机会而得到发泄。而正是被写入关于特鲁埃瓦家族史的暴力,导致了拉美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命途多舛、举步维艰。伊莎贝尔·阿连德——在军人发动的军事政变中以身殉职的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侄女,在其作品《幽灵之家》中,再现了智利半个世纪动荡不安、波澜壮阔的历史。她通过这部作品告诉人们,只有放弃暴力,和平共处,才能建立美好幸福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