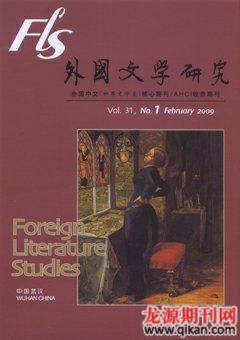做一个“好女孩(人)”:戒律、话语及典仪
王丽明
内容提要:伊迪丝·华顿是20世纪初美国文学界重要的女作家。在中篇小说《夏》中,华顿一改所擅长的刻画纽约上流社会贵妇人的风俗小说创作特色,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主人公夏绿蒂·罗约尔及其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本文试图从性别学、符号学以及人类学等诸多层面上分析《夏》所折射的象征秩序中戒律、话语、典仪等压制女性的因素,指出华顿希望通过对夏绿蒂生活际遇的摹写,反映妇女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既妥协又颠覆的双重态度。
关键词:《夏》象征秩序反抗戒律话语典仪
作为20世纪初美国文学界重要的女作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以其独特视角刻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老纽约”上流社会与她本阶级的女性形象屡获殊荣。她是美国文学史上少数几位获得过国家艺术学院金质奖的女作家之一,1921年又因长篇小说《天真时代》获普利策奖。华顿在作品中隐藏着她对女性社会地位、传统父权制度等问题的严肃思考。华顿在晚年列出最令自己满意的五部作品,分别是《国家风俗》(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1913)、《孩子》(The Children,1928)、《哈德逊河拱桥》(Hudson RiverBracketed,1929)以及《神到了》(The Gods Arrive,1932)等四部长篇小说,另加上中篇《夏》(Summer,1917)(Minot xv)。有趣的是,上述作品中惟有《国家风俗》属于华顿所惯于刻画的反映上层社会的风俗小说。
学界认为《夏》和《埃森·弗洛姆》(Ethan Frome,1911)是姐妹篇,这两部作品是作家根据早年新英格兰乡居所见农家生活中的惨淡悲欢而写就。华顿在《夏》中所提出的是关于女性社会角色和地位问题。故事围绕女主人公夏绿蒂·罗约尔而展开:乡村姑娘夏绿蒂身世不明,由养父母劳耶·罗约尔夫妇抚养成人。小说开始时罗约尔夫人已去世多年,夏绿蒂和罗约尔先生住在一个叫做北多玛的小镇上。罗约尔先生曾试图诱奸她并两次向她求婚。一天,在亲戚的图书馆里帮工的夏绿蒂遇到了建筑师哈尼,爱上了他并怀了身孕。命运多舛的她却发现哈尼已与另一个与他同阶层的姑娘订了婚。在绝望中,夏绿蒂去山上(被放逐的妓女居住之地)寻找生母,但母亲却在两人重逢前去世。后来罗约尔先生在得知她怀孕后,立刻同她结婚。婚后第二天,罗约尔先生对夏绿蒂说:“你是个好姑娘。”此时的夏绿蒂心怀感激,回应道:“我想,你也是个好人”。罗约尔没有强迫她上床,在椅子上度过新婚之夜。故事以夏绿蒂随罗约尔先生回到曾梦想逃离的北多玛镇告终。
辛西娅·伍尔夫和坎迪丝·维德等女权评论家对这一婚姻一致看好。在《字词的欢宴中》,辛西娅·伍尔夫声称“(故事里)乱伦的动机并不凸现;夏绿蒂最后嫁给劳耶·罗约尔不是一桩‘坏事”(Wolff)。维德直言道:“夏绿蒂几乎重蹈她母亲覆辙(沦为妓女),是罗约尔将她救了回来”(Waid)。由此可见,从女性主义视角关照《夏》的评论界更多着眼于对小说的最后一章进行解读,她们更注重夏绿蒂的“幸福的结局”。然而,她们似乎忽视了作品所折射的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一贯性和唯性别论。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奉行这样的思想:本能让位于文明,情感遵从理智,女人屈服于男人。鉴于此,本文认为,《夏》是华顿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正面诘难。夏绿蒂与罗约尔认为彼此都是“好”人,但是这个“好”由罗约尔先出口。何谓好女人?发言权在罗约尔。阅读这样一个表现女性人物心里冲突的文本,读者需要透过世纪之交表面上封闭的戒律、话语体系和典仪来分析作品透出的信息:夏绿蒂先反抗继而又妥协的双面性揭露了传统父权社会的伪善。
华顿在其自传《回眸》中表示《夏》的创作目的暗指女人抗争的情境,而它却为现行的社会代表模式所排斥(Wharton,Backward)。正如肖瓦尔特在《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告诫的那样:“沉默的女性群体必须适当借助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套语来传递她们的信仰……因为语言可以提出问题,妇女的信仰可通过宗教仪式和艺术得以表达,这是一种可由先驱们透过菲勒斯主义表层认识社会实质的解码的表达”(showMter)。因此,一个融合性别学、符号学以及人类学等多层面的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夏》中的女性反抗声音,甚至是无声的语言,理解她如何变成一个“好女孩(人)”,并剖析夏绿蒂的女性话语方式。
小说一开场,夏绿蒂徘徊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身为山上被放逐女人所生,夏绿蒂可谓生来就带有反抗色彩。按照哈尼的说法,那些山里人“是一群怪异之人……形成一个有点独立的王国……她们与山下的人们毫无瓜葛——甚至,事实上蔑视他们”。他注意到“她们似乎完全游离于这座山谷的权利之外。没有学校,没有教堂”。牧师去那里,是为主持葬礼,绝非洗礼或者婚礼,山上人摈弃这些典仪:他们凌驾于象征秩序之上。与她出生之地相比,北多玛象征着“最高雅文明的赐福”。
小说强烈暗示,夏绿蒂就其性别来说也具有反叛性。实际上,“山上”这个概念屡次指涉女性,尤其指涉女性性欲(Ebert)。夏绿蒂与哈尼初尝禁果后,对山上益发好奇;怀孕之后,她想去山上拜见母亲。但当夏绿蒂终于看见已死去的母亲尸体时,她发现了一个在场的缺席,一个缺席的在场,一位张着嘴巴然而不会言语的母亲。
故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妇女是否可以言行、思考,甚而在没有为父权制象征秩序所限定和曲解的话语方式中生存。夏绿蒂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善辞令、没有文化素养。她把北多玛镇哈切得图书馆的馆藏书当作艺术品,而不是读本;她读不懂哈尼的信,夏绿蒂也曾写信给他,却找不到词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只得邮寄一张署上自己名字的明信片。她能表现出来的就是因受养父诱奸而形成的一种模糊的反抗意识和离开他的愿望。
由于其特殊出身,在某种程度上,夏绿蒂同时代表未被男子中心社会统编的“山上”女人和被吸纳进该象征秩序的女人。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斟酌一番夏绿蒂·罗约尔其名。通篇作品中,“夏绿蒂·罗约尔”都不受社会认可,而只是临时性的名字。她努力寻找生母,试图知道母亲姓名,因此也就知道自己乳名,这与逃离罗约尔和北多玛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变得日益强烈。陶丽-莫娃在《克里丝蒂娃的读者》的绪论中把女人比做“关于语言和意旨的异物和他者”(Moi),夏绿蒂正是男权话语中的他者,不断地与北多玛既定的戒律抗争。然而,从故事的发展过程来看,她也被逐步引入北多玛象征秩序。四次典仪形成她进入到父权社会的过程:7月4日的庆祝独立日仪式,老屋庆祝典礼,母亲的葬礼,以及她自己的婚典。每一个仪式中她都在不同程度地反抗,而同时她身上父系社会的烙印也益发清晰了。在故事的结尾,她回“家”了,嫁给了她的养父,成为“合法”的夏绿蒂·罗约尔。可是,这正是《夏》最为有力的一点所在:她打破了接纳她的象征秩序的和谐,因为,尽管她腹中胎儿的合法养父依旧是劳耶·罗约尔,但它依然是私生子。夏绿蒂·罗约尔这个名字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