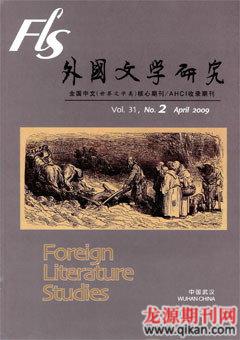“出神”:约翰.多恩爱情玄学的诗性阐释
内容提要:“出神”是约翰·多恩阐释自己爱情玄学的一首真正的玄学诗。诗人凭借对灵魂、肉体相互关系的思考,提出精神之爱必须经由肉体之爱才能达到,灵肉相融的爱情才是真正完美的理想爱情。多恩以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神”概念构思诗歌,阐述的却是与新柏拉图主义大相径庭的爱情观。多恩的爱情玄学与传统的“存在之链”的理论密切相关,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
关键词:约翰·多恩出神灵魂肉体爱情玄学
作者简介:朱黎航,文学硕士,浙江工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约翰·多恩诗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约翰·多恩是17世纪英国玄学诗的开拓者,也是最著名的代表。“玄学”本义是“形而上学”,自从被约翰·德莱顿、塞缪尔·约翰逊用作对多恩诗歌的评判后就成了对多恩一派诗歌的经典定义而沿用至今。其实多恩的多数诗歌并不讨论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玄学并非他的诗歌主题而只是显示了他的诗歌的智性思辨风格。也许有一首诗是例外,称得上是一首真正从主题到创作手法皆为玄学的玄学诗。这首诗就是“出神”,它是多恩抒情诗集《歌与十四行诗》中篇幅最长的一首,也是“多恩爱情诗中最具分析性、概念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具哲学意味的一首”(Leishman 220)。诗人以冷静、理性的口吻阐释了自己对爱情的深刻理解,确切地说,是对性爱的理解,因为在此诗中,爱与性不可分割。在这首充满了肉体和灵魂的神秘思想的玄学诗中,多恩表达了与文艺复兴时期流行于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大相径庭的爱情观。赫伯特·格瑞厄森称此诗是“多恩阐释爱情玄学,阐释肉体和灵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的最重要的抒情诗之一”(Grierson 41)。
一
诗歌题为“出神”(The Extasie)。“extasie”一词源自古希腊语“ekstasis”,原意为“放在外面”、“置于自身之外”,意指灵魂超越自身的状态而与超常实在沟通,常被译为“出神”或“迷狂”。这一思想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著述中,指人的灵魂迷失在当时的意识,达到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在理性的直观中达到与神的合一。希腊化时期重要的犹太哲学家斐洛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著名代表普罗提诺进一步把“出神”作为人与上帝结合的唯一方式,认为人只有在“出神”的状态中,才能借助心灵的眼睛直觉上帝。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又糅合了基督教教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认为要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灵魂必须摆脱自己所依附的感性的肉体的羁绊,净化自己,才能在一种迷狂的状态中达到与上帝的合一。诗歌以“出神”这么一个既富含宗教哲理又充满神秘主义内涵的概念为题,必然会令读者浮想联翩,把这首诗置于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中来解读。
“出神”描绘的是一对恋人的灵魂在热恋中升华,逸出躯体,最后又回归躯体的过程。诗中的这两行清楚地表达了诗人的爱情观:“爱情的秘密确实在灵魂中成长,/然而肉体却是它的书籍”(第71 72行)。这两行诗表达了两层涵义:第一,主宰爱情的是灵魂,恋人双方灵魂的交融与合一才是真爱。诗人肯定了心心相印的灵魂之爱,表达了自己理想主义的爱情观。在多恩最著名的爱情诗“赠别:禁止伤悲”中,诗人歌颂的就是这样的灵魂相契之爱;第二,灵魂的合一离不开双方肉体的结合,离开了肉体,爱就虚无缥缈,没有实际的意义。这种肯定肉体和享乐肉体的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也是大家熟悉的多恩爱情诗的主旋律。显然,多恩“把现实主义的追求自由享乐的肉欲之爱与理想主义的崇尚忠贞契合的灵魂之爱糅合了起来”(傅浩11)。
根据这两层意思,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前12小节多恩描述了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在爱的极致中彼此凝望出神,灵魂逸离躯体,但上升的灵魂并非像新柏拉图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去与上帝沟通,而是去与情人的灵魂交流糅合,互相激活,从而获得新生。“这番出神确实解除疑虑,/(我们说)告知我们什么是所爱;/我们借此看清,那不是性欲;/我们看清,以前不曾看清的动力”(“出神”第29—32行)。多恩清晰地阐述了这样的思想:爱的“动力”不是肉欲,而是灵魂的合一。灵魂为了达到与另一灵魂的交融,它必须首先脱离肉体,当灵魂逸离肉体并和另一灵魂结合,灵魂才能达到它完全的力量,成为“更强的灵魂”(“出神”第43行),就像一株紫罗兰,只有从贫瘠的土壤移植到肥沃的土壤才能够长得更好。这“更强的灵魂”是两颗热恋的心灵合二为一产生的新的灵魂,是多恩在“赠别:禁止伤悲”中表述的“一体浑然”(“赠别:禁止伤悲”第21行)的灵魂,“没有变化能够侵凌”(“出神”第48行)。阅诗至此,似乎多恩的理想爱情只是摒弃肉体享乐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
但诗人的真正用意在诗歌的后半部分。从第13小节开始,多恩笔锋一转,对长期以来中世纪神学所宣扬的肉体的罪恶,要求人们弃绝肉体的思想提出了质疑。实际上,从这一小节开始的诗歌后半部分是此诗的主旨。多恩指出,肉体是灵魂依附的不可或缺的载体,灵魂和肉体的关系犹如“神灵”(inteHigence)和“天体”(sphere)(“出神”第52行)。当时人们普遍信奉的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宇宙论认为,每个天体都有一个神灵坐镇,前者为载体,后者是主导,二者相互依存。而多恩认为,肉体和灵魂的关系也是如此,前者受后者的管辖,同时也是后者存在的基础。在多恩看来,是肉体将“力量、感觉”(“出神”第55行)呈现给灵魂,对灵魂而言,肉体“不是渣滓,而是合金”(“出神”第56行)。
上天的影响并不直接作用于人,
而是首先在空气中留下印记,
同样,灵魂可以流入灵魂,
不过它首先得去依附肉体。(“出神”第57 60行)
古时候的占星家认为,星体对人类这一微观世界所起的影响是以空气为媒介的,空气乃物质元素,并不具有精神的纯粹性。多恩以此类推,灵魂的融合也须借助它们的有形质料——肉体的结合,脱离肉体的爱情是不完善的。多恩在另一首名为“空气与天使”的诗中,也表达了灵魂离不开肉体,爱情必须寄托于形体的思想:“但是既然我的灵魂——爱情是她的孩子——/采用了肉体肢干,否则什么也不能做,/爱情比它的本源更精微,/若不也寄托于形体,必将无法存活”(第7—10行)。多恩认为,只有在爱的“出神”状态中得到升华、获得新生的灵魂重归肉体,在双方肉体的结合中,恋人们新生的灵魂才能交融汇合,达到爱的完满。也只有灵魂与肉体同在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
二
灵魂和肉体是如何结合为一体并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呢?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泰斗费奇诺认为,精气是连接肉体和灵魂的媒介。它是一种非常稀薄的气体,由心脏从血液最纯的部分创造出来,散布到全身各个部分。一方面,精气接收灵魂的力量,并将这些力量传输进肉体;另一方面,精气又通过肉体感官接收从外部世界投射的映像,这些映像不能直接与灵魂交流,而必须以精气为媒介,因为灵魂是超物质的存在(qtd,in McCardes
63)。多恩显然接受费奇诺的这一观点,在“出神”的第61—64行,多恩写道:“犹如我们的血液奔忙,产生/精气,尽量使之近似灵魂,/因为需要那样的手指编织/那微妙的结,造就我们成人。”多恩将精气比做编织肉体和灵魂微妙之结的神奇手指。在后来创作的布道文中他对此作了更具体的阐述:精气是“血液中稀薄和活跃的部分”,具有一种处于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中间性质”,是它将灵魂和肉体结为一体,并将灵魂的智能作用于肉体的器官之中,从而形成完整的人(qtd,in McCanles 61)。与多恩同时代的勃顿(Robert Burton)在《忧郁的解剖》中也把精气描绘为“最微妙的气”(qtd,in McCanles 61),认为它具有调节肉体和灵魂的作用。看来,灵魂由精气与肉体相连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肉体和灵魂如何结为一体的普遍认识。
既然精气是连接灵魂和肉体的媒介,灵魂要与肉体合一,就必须与血液中产生的精气相会,从而随着血液的奔流散布肉体全身:“因此,纯粹恋人的灵魂必须/下降到情感,和机能,/才可以让感官触及并感知,/否则是伟大的王子躺在牢中”(“出神”第65—68行)。最后这行诗很自然地令读者联想到柏拉图《斐多》中苏格拉底的著名观点:肉体是灵魂的监狱,而多恩的这一诗节却表明灵魂如果没有肉体这个载体,就犹如禁锢于监狱。新柏拉图主义认为,灵魂一旦进入肉体就失去了自由,因为它常常受到肉欲的诱惑。肉体感受到、看到的只是现象的世界,只有灵魂才能够到达本质。灵魂本身是神圣而不朽的,它由于沾染了形体世界的质料,沉迷于肉欲才变得邪恶。人生的目的即是使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回归“太一”,与上帝合一。虽然多恩仿造“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创造了“伟大的王子躺在牢中”的著名奇喻,其阐释的意蕴却与新柏拉图主义背道而驰。灵魂只有借助肉体才能自然地施展人的功能;如果脱离了肉体,就丧失了感知能力,就像一个失去自由的王子,脱离了他的臣属,再也无法行使统治权。这就是多恩的结论。
看来,多恩虽然承认爱情的动力源自灵魂,爱情的萌发始于心灵的碰撞,而非对彼此身体的渴欲,但多恩强调自足完善的爱不是纯粹的精神之爱,而是灵肉相融的爱。这种思想显然是反新柏拉图主义的。因为新柏拉图主义认为只有摒弃不纯的肉体才能上升到超凡神圣的精神之爱,而多恩却证明即使是超凡的精神之爱也离不开性,情人们只有通过肉体的拥抱才能达到灵魂的真正契合。多恩以肉体和灵魂的相互依存为理论根据,证明了性爱是获得理想爱情的必由之路。
多恩的爱情玄学在“早安”、“追认圣徒”、“上升的太阳”等诗篇中得到了很好的诗意表达,诗人立足男女的相互钟情,歌咏性爱的欢愉与伟大。“追认圣徒”更是将世俗的爱情与宗教的神秘圣洁相提并论。诗人将肉体灵魂已完全合一的一对恋人比作具有两性特征的不死之鸟——凤凰:“凤凰之谜由于我们而具有更多/玄机;我们俩合为一体,就是它。/对于一个中性的事物两性都适合,/我们死亡又重获新生,且以/这爱情证明我们的神秘”(“追认圣徒”第23—27行)。凤凰是古埃及神话中的神鸟,据说仅有一只,集香木自焚,又从死灰中复生,是西方文化中不朽和再生的象征。诗人借用凤凰意象指出真爱可以在两性的合一中超越死亡,获得新生,这正暗示了从肉体之爱到灵魂之爱的提炼与升华。这类诗篇在多恩的《歌与十四行诗》中虽是少数,却篇篇精品,成为展示其理想爱情的最好范例。
三
多恩在“出神”中表达的思想牢牢地根植于当时人们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是以当时人们所掌握的科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的。多恩在诗中严密论证的是这样一个观点:精神之爱必须经由肉体之爱达到。这一观点与传统的“存在之链”(the chain 0f Being)@理论密切相关。
“存在之链”的理论体现了古代西方人对宇宙万物存在的一种思考,由此形成的宇宙观影响了西方两千年。所谓“存在之链”是指宇宙万物的存在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序列,从最卑微的存在物,渐次通过较高等级的存在物,最终抵达至高至善的存在物——神。根据这个理论,宇宙万物的存在是丰富多彩和井然有序的,万物都必须遵循秩序和等级,任何一种存在物都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是存在之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存在之链中最高级的存在为天使,它与顶端的神相连,自上而下的依次是天使、人、动物、植物,最后是砂石。砂石是无生命的存在物,植物具有生长功能,动物具有生长和感觉功能,而人类除具有生长和感觉功能之外,还有理性,天使则是纯精神纯理性的存在。人在存在之链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介于天使和动物之间,既有天使的理性,又有动物的感性,是存在之链中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联接环。虽然人所处的特殊位置和人具有的双重性使人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自由选择,但人作为半神半兽的存在,既拥有灵魂也拥有肉体,既具有理性又具有感性的-自然需求,对人来说,理想的爱情应是灵魂之爱和肉体之爱的结合,纯粹的精神之爱和完全的肉欲都不应是人之为人的正常选择,因为前者只属于天使,而后者则是人向动物的堕落。
根据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宇宙观中天人对应的思想,人自身就是一个与外在宇宙相对应的小宇宙。人体结构与大宇宙的结构类似,人以肉体和灵魂对应于大宇宙中的可感世界和概念世界,成为存在之链上联结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心环节。多恩也持有这种思想,他直率地称自己为“小宇宙”:“我是一个小宇宙,由四大元素/和一个天使般的精灵巧妙地组合而成”(《神圣十四行诗》第5首1—2行),表明了人与外在宇宙的对应关系。人体内肉体、精气、灵魂的上升等级和顺序正反映了由物质(肉体)到精神(灵魂)的上升过程。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崇尚的亚里士多德的“三重灵魂”说,人的灵魂可划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等三个层次,植物灵魂即生长灵魂是层次最低的,动物灵魂即感官灵魂次之,理性灵魂处于最高层。前两者使人与物质世界相连,后者使人与天使和神相连。很明显,作为小宇宙的人自身也体现了宇宙的存在之链。但根据存在之链环环相扣、逐级而上的原则,人只有经由肉体感觉层面才能升华至精神层面。
在存在之链上,只有天使作为纯精神、纯理性的存在,能体验到不搀杂肉欲的纯精神之爱。对人而言,获得纯精神的爱,只是一种价值追求,是一种信仰,并不具有真实可行性,这就是多恩对爱情的认识。这也正是多恩的多数诗歌大胆地肯定性爱、强调性爱的思想根源。即使在他那首柏拉图式爱情的意味甚浓的诗歌“赠别:禁止伤悲”中,多恩也并未否定性爱,而只是认为灵魂之爱高于肉体之爱,诗人鄙视的是浅薄的、只讲感官享乐的肉欲之欢。
在多恩生活的英国文艺复兴时代,各种思想文化成分纷繁芜杂。流行当时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在多恩的诗歌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在“出神”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觉察到的有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也有经院哲学家阿奎那的思想,甚至还有法国哲学家蒙田的思想等等。如果说这首诗的外壳套用的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脱离肉体的“出神”概念,但其内容却是反新柏拉图主义的。因此有评论者认为此诗的要旨源自阿奎那主义而非新柏拉图主义。0根据阿奎那的观点,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时具有精神性和物质性。肉体是人的感性器官,虽然不参与人的思维和意志的活动,不作用于人的灵魂,但它为理性活动提供资料,有助于人的理性认识,是灵魂获得感知的器官。离开了肉体的灵魂并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处在一种又聋又哑的“反常状态”之中。这不正是多恩笔下的“伟大的王子躺在牢中”(“出神”第68行)?因此,灵魂只有和肉体统一才是符合自然的正常状态。阿奎那虽是基督教神学家,但他并不提倡禁欲主义,而是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对文艺复兴后期的英国文学影响巨大的法国哲学家蒙田同样认为灵魂和肉体不可分割。在他看来,只追求灵魂不朽而蔑视肉体是将人割裂,人应顺应天性,享受自然的幸福。可见,多恩在“出神”中表达的思想并非诗人的独创。正如意大利的文学评论家马里奥·普拉兹(Mario Praz)所言:“尽管多恩的兴趣在思考,但他自己却并非是一个原创的思想者。他的目的是艺术性的自我表达;因此,不管是新时代的试验性的信条还是以往许多世纪的过时学问,都毫无差别地仅仅只是提供给他作为自己写诗和布道的例证”(qtd,in Thomason 92)。
想要在多恩的诗歌中找到诗人一贯的哲学信仰是困难的,我们也很难将多恩庞杂的思想一一溯本求源,因为多恩本人就像复杂多变的17世纪一样,是一个矛盾思想的汇合体,他任自己的思绪在诗歌中自由驰骋。分析多恩的爱情诗,同样不可回避的是多恩爱情思想的复杂与矛盾。在他的爱情诗中很难找到一条清晰一致的爱情思想发展脉络。从戏谑人生的肉欲之欢到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多恩好似一个爱情多面手,游走在爱的两个极端,将自己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真挚深情等种种相互矛盾的情感侧面袒露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人类需求本性的极大多样化。但在“出神”这首诗中,多恩停在了爱的中点,他连结了世俗之爱和精神之爱,并在沉思中悟出了爱情的真谛:灵肉相融的爱情才是真正完美的理想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