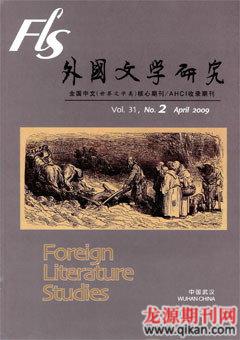论《黑暗的左手》中的雌雄同体
叶 冬
内容提要:《黑暗的左手》是美国当代科幻大师厄休拉·勒奎恩的代表作。作品塑造了“雌雄同体”的独特世界,在继承和发展这一贯穿于人类文化历史的古老命题的同时,通过科幻小说这一“思想实验”形式,揭示出性别对立是人类一切矛盾的根源所在,重新审视被性别差异掩盖之下的人性本质。这个充满女性特征的世界反映了作者明显的女性主义立场,“对立转化”、“阴阳融和”等道家思想的表达使“雌雄同体”这一概念在作品中得到深化。关键词:雌雄同体性别厄休拉·勒奎恩《黑暗的左手》
作者简介:叶冬,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英美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黑暗的左手》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的主要代表作。厄休拉·勒奎恩生于1929年,5岁开始写作,14岁发表作品。她的创作涉猎广泛,文类众多,包括科幻小说、奇幻故事、儿童文学、诗歌、评论、翻译、编选文集等等。从1966年到1968年,她陆续出版了《洛坎农的世界》、《放逐的星球》、《幻象之城》和《地海巫师》等,在文学圈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但直到1969年《黑暗的左手》的问世才最终确立她作为科幻大师的地位。这部作品同时获得象征科幻界最高荣誉的两项大奖:星云奖(Nebula Award)和雨果奖(Hugo Award),从出版至今的近40年间,评论家们从来没有丧失过对它的兴趣。著名文论家哈洛德·布鲁姆在由他主编并作序的评论集中曾赞誉勒奎恩是当代科幻文学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师,其想象力和风格在托尔金之上,更远胜于多丽丝·莱辛,而《黑暗的左手》则是他最喜欢的现代科幻作品(Bloom 2)。
《黑暗的左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未来世界“冬星”(Gethen是勒奎恩虚构的词,意为Winter)上的故事。主人公根利·艾作为星际联盟埃库盟(Ekumen)的使者,到达终年冰封雪冻、名符其实的“冬星”上,试图说服那里的人们加入联盟。艾在“冬星”上结识了喀骇得国(Karhide)的首相埃斯特拉文,并和他一起遭遇了政治风波、驱逐和流放。作者通过艾的观察和各种经历,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地球的世界和迥异于我们的人们,其中最出乎意料的便是“雌雄同体”(Androgyny)的社会新样态。
雌雄同体:源起和发展
“雌雄同体”当然不是勒奎恩的独创,作为一个古老命题,它早就深深根植于人类文化中。从古至今,无论从神话、哲学、宗教、文学还是其它领域的文献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先哲们的思考和探索。从词源上说,它是由古希腊语中表示男性的词根“andro”和表示女性的词根“gyn”共同组成的;与生物学和解剖学上更常用的词“hermaphrodite”相比,“androgyny”似乎更具有一种文化含义,而不仅仅是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双性一体。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记述了阿里斯托芬讲述的关于爱之起源的故事,他说人类最初的形体是一个圆团,后来被一分为二成男性和女性。从此,这两半不断地寻找对方,渴望合二为一,这便成为两性相吸和结合的原型解释。《创世纪》中的上帝就是雌雄同体的,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人类。而人类的始祖亚当也只有当上帝从他体内抽出肋骨创造出第一个女人夏娃后才成为了真正的男人。如此说来,夏娃产生之前的亚当是具有双性本质的。在古希腊的菲尼基,维纳斯以阿斯塔提的别名受广大徒众崇拜。但她与维纳斯的不同就是她兼具雌雄两性——其男体即亚敦尼斯。“因此之故,在祭祀她的节期,女人改妆为男,男则变服为女。这种风俗,一直到今日,尚未消歇。犹太人年中二三月有一个节期,男女俱改穿。异性的衣装”(卡纳65)。而在中国远古神话中也有类似的例子。相传华夏始祖伏羲和女娲本是兄妹,后结合产生后代,繁衍人类。在汉墓出土砖画中,女娲常与伏羲连体交尾,两者都具有人首蛇身的形象。有学者考证,人类母神女娲就是月神女娥,其实都是从日神羲的名号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可以说伏羲女娲同名同姓、连体孪生(何新44 45)。这也是对人类最初雌雄同体的一种想象。
这种远古想象根植于人类集体无意识里,不断反映到后世人们在各领域的研究中。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潜意识双性化”的概念,认为双性是性别差异确立之前的一种性特征尚未分化状态,“代表了性别分化本身的不确定性”(转引自张京媛75—80)。荣格提出了著名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理论,认为在人类学意义上每个人都是雌雄双性体,这个双性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转引自霍尔等53)。柯勒律治在他的《桌边谈话》(Table Talk)中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伟大的思想应该是雌雄同体的”。而英国作家、被誉为女权主义先驱者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更是继承了这一概念并发扬光大,她的小说《奥兰多》跨越了时间、空间和性别的约束,让主人公奥兰多经历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的数百年历史,从男性变为女人,适应社会并完成理想。在小说结尾,奥兰多和谢尔墨丁的结合以及长诗《橡树》的完成,表现出伍尔夫对双性和谐社会的向往,以及她反叛父权社会制度下“逻各斯中心论”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她最富盛名的、被后世奉为女权主义《圣经》的《一间自己的屋子》里,伍尔夫用相当篇幅阐述了雌雄同体的概念和意义:“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只有在这种融洽的时候,脑子才变得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也许一个纯男性的脑子和一个纯女性的脑子都一样地不能创作”(伍尔夫120—121)。如果说《奥兰多》让伍尔夫实践了自己的雌雄同体创作观的话,那么勒奎恩则更自由地借助科幻小说这一文体所赋予的更广泛的领域来驰骋想象力,彻底打破固有模式和社会常规的限制,深入探索“雌雄同体”这一古老命题,给予它全新的理解和阐释。
《黑暗的左手》:一场思想实验
勒奎恩认为:“科幻小说不是预言性的,而是描摹性的。……作为一种思想实验,……科幻小说不是为了预示未来,……也无法预示未来一一而是描摹现实,描摹现世”(xii)。也就是说,尽管在她笔下描写了一个雌雄同体的世界,这并不意味着她在预言未来的人类社会将是雌雄同体的,或者说她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她仅仅是在观察,用一种独特的视角,用适合科幻小说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的方式,设定某种特定的时空条件在观察人类,“用小说家的方式观察人类心理现实的某些方面”(xv)。
也许是受作为人类学家的父亲的影响,勒奎恩在构筑她的想象世界时,从来不是恣意妄为的。她总是用做人类学调查报告一般的全面和细致,乐于在作品中精心构建一种自足完整的社会模式,甚至有意识地以收集记录形式列出种种文化子目录。这一方面让读者能有更直观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将科幻小说这一被列入浪漫主义传统的文类少了些不着边
际的虚构,多了些现实主义的观照。《黑暗的左手》用了第七章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通过根利·艾观察笔记似的记录,描述了奇特的雌雄同体的“冬星人”(Gethenian)。第七章名为“性的问题”,描写这里的人们有特定的性别周期,一个周期大约26天。其中21天到22天人们处于中性期,并无性别之分。在周期的第18天左右,荷尔蒙发生变化,在第22天或23天左右进入Kemmer期,相当于发情期。在此初期,人们都是雌雄同体的,直到遇到另一位也同处情期的人,就会相应发生理、心理、行为举止等诸多变化,成为完全的男人或女人。情期结束之后,人们又回到中性状态。如果此间怀孕,则女性性征将一直保持到分娩和哺乳期结束之后,如此循环往复。但任何人也无法预料自己在下一周期到底会成为男人还是女人,因此一位母亲很有可能是另几个孩子的父亲。
勒奎恩在《黑暗的左手》中所进行的思想实验就是借助“冬星人”雌雄同体的特征,让人们思考当“性别”这一区分人的最基本特征被消解之后,人类将会是怎样?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认知态度、价值取向乃至社会形态直至生存方式上又会产生什么不同?她在“性别是必须的吗?”(“Is Gender Necessary?”)一文中希望“在人生和社会中定义、理解性与性别的意义”(Le Guin,Dancing 8),她说:“我的实验所要思考的问题是:因为制约我们终生的社会条件作用,我们很难搞清楚除了单纯的生理形式和功能,区分男人和女人的到底是什么。在性格、能力、才干、心理过程等方面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区别?…因为完全没有生理性别差异,这个想象的文化形态不存在性别角色。我消灭性别,就是为了看看还剩下些什么。不管怎样,总该剩有——人。这将有助于定义男人和女人共同分享的领域”(k Guin,Dancing 9)。勒奎恩还着重指出其实验结果的三点,即性别消融后,至少在三个方面社会可以获得裨益:消灭战争,消除掠夺,消解作为持续社会因素的性。
在勒奎恩看来,性别对立是一切矛盾的本质根源所在。因为摒除了种族、民族、阶级、文化等各种差异以后,人类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两性的区别。生理区别自然引发出心理、情感、认识、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两性间不可避免的征服与被征服、争夺与被争夺、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又导致了人类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现状。而“冬星人”的雌雄同体生理特点则从根本上消除了男女之间的差异,性不再成为固定特质,两性之间可以互相转换,当然也就不存在为争夺繁衍生息而产生的对女性(作为固定群体的女性)的强占,对更多土地(和该土地上的人们)的强占,以及对自然资源(和提供自然资源的星球)的强占。如果说伍尔夫的奥兰多以一已之力在挑战人类固有社会模式中男人和女人的生存方式,那么勒奎恩就在彻底摧毁这一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作为完整人的人类应该如何生活。
女性主义的缘道之旅
小说发表的年代正是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如火如荼之时,勒奎恩本人也毫不掩饰地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我无法想象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女人却不是女性主义者”。因此,当读者通过根利·艾的视角来观察这个陌生的世界时,会发现被男主人公开始称为“异类”(alien)的地方只不过是有着他所认为的明显的女性特征。“冬星”人的词汇里并没有“女性”(female),艾只是借用了一个表示“另一种生命形式”(the alternate being)的概念才能解释清楚(36)。他这样描述他的朋友埃斯特拉文,“我的女房东,一个喋喋不休的男人”(47),又进一步解释说:“我把他当作女房东,因为他臀部丰满,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脸颊柔软丰腴,心地善良又鬼鬼祟祟,老在窥探别人”(48)。而在总结为什么“冬星”上没有战争的时候,他认为“在这方面,他们的行为方式象动物,或者说象女人。他们的行为不象男人,或者说蚂蚁”(49)。同样,双性同体的“冬星”人最重要的生理特征,即“发情期”的周期性恰恰是女性才具有的特点。如此种种说明,勒奎恩着意构建的就是不同于地球上的以男性特征为中心的社会样态。这里的人们不管从相貌神态、举止言谈还是思维方式都有着强烈的女性色彩,也许只有在这样一个完全颠覆现有模式的小说世界里,才能充分进行她的“思想实验”——思考现世中的两性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其它问题。
人类思维模式中,把万物一分为二,建立等级秩序的所谓“二元对立”是一种基本观念。而根利·艾历经磨难,终于逐渐接受“冬星”人求同重和、交融统一的世界观。这体现在他对埃斯特拉文的认识上,“我终于看见了,而且永远看见了,我一直害怕看见,并假装在他身上没有看见的东西:他是一个女人,同时又是一个男人。害怕消失了,也就无须再解释害怕的原由;最后我所能做的就是接受作为他自己的他。此前我曾拒绝过他,拒绝他的真实。他曾说过,他是“冬星”上唯一信任我的人,也是我唯一不信任的人。他是对的。因为他是唯一视我为人完全接受我的人:真心喜欢我并给我全部的忠诚,因而也希望我给予他有同样的认同和接受。我曾经不愿意给予。我害怕给予。我不想把我的信任、我的友谊给一个是女人的男人,是男人的女人(248—249)。在一个没有性别的世界上,艾取得这样的认识是要经过多重考验的。但性别的消融仅仅只是对这个世界认知的一部分,在一个“消解了人性中强弱两半,保护/被保护,控制/服从,主人/奴隶,主动/被动”的地方,在主导人类思维总趋势的二元观被削弱、被改变的”(94)“冬星”上,人们的对于其他事物的认识也逐渐趋于整合而非分化。“也许他们不大关注人与兽的界限,而是更在意相似、联系,在意万物均为其中一部分的整体”(233)。这一观点可以从这首诗中形象地得以再现,而小说的名字正是出自其中第一句:
光明是黑暗的左手
黑暗是光明的右手
二为一,生与死,
象动情的爱人相拥而卧,
象紧握的双手,
象终点和道路。(233)
这首诗既是全书的主旨和要义所在,又能进一步反映影响勒奎恩“雌雄同体”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中国的道家学说。她14岁开始阅读《道德经》,从此深深迷上了这门东方古老的哲学,她曾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不信基督,而是信道。在研习各种版本的基础上,她历经近40载,终于在1997年出版了自己翻译的《道德经》,这对于一个并不懂中文的人来说其难度和毅力可想而知。诗中最后一句的原文是:“like the end and the way”,这里的“way”有双关含义,既指“道路”,又指“道”。当然,“道”究竟如何翻译还众说纷纭,但勒奎恩给她的英文版《道德经》加了个副标题“A Book about the Way andthe Power of the Way”,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理解。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就是告诫人们雄刚不符合道之法则,要坚守以雌柔为宗旨。虽然这里的“雄”与“雌”并非特指“男”与“女”,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男”、“女”所分别蕴含的特点。勒奎恩在翻译时也选用了这种理解:“Knowing man/and staying woman,/be the riverbed 0f the world”(LeGuin,Lao Tze 28)。在《黑暗的左手》临近结尾之处,勒奎恩更是直接将太极图和阴阳调和呈现出来:“我在圆圈里画了双曲线,然后将图形中阴的部分涂黑”(267),并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阴阳。黑暗是光明的左手……光明,黑暗。害怕,勇气。寒冷,温暖。雌性,雄性……二和一”(267)。
应该说,在《黑暗的左手》这个“思想实验”场上,勒奎恩已经很大程度地消解了“性别”这一概念,企图通过“雌雄同体”的塑造来达到向世人警示在性别掩饰之下,对人性基本问题的思考。但近20年以后,她似乎觉得自己还不够彻底,认为在小说中锁定“冬星”人的性行为必然发生在两种性别之间是一种天真的、实用主义的性观念,并为此感到莫大遗憾(LeGuin,Dancing 14)。其实,当勒奎恩选用根利·艾(Genry Ai)作为主人公名字的时候,既然Ai与I同音,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女作家和男主人公融为一体,已经在有意无意之间达到另一层更为彻底的“雌雄同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