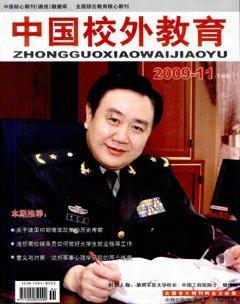语言错位与余华的幽默语言艺术
闫 芳
[摘要] 奇异突兀、幽默感强,是余华小说语言风格的鲜明特色。语言错位,是余华在文本中创造幽默的一种有效手段。余华在作品中故意用一些自相矛盾的语言内容或形式来表达,造成一种不协调,形成语言表达上的落差来激发语言幽默。
[关键词] 幽默 语义错位 逻辑错位
余华是最能体现先锋小说的先锋特征的作家之一。余华认为,“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选择”是“与现实建立了幽默的关系。”他认为,“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的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是“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的方式。”“错位表达”,是余华在文本中创造幽默的一种有效手段。余华故意用一些自相矛盾的语言内容或形式来表达,在语言上造成一种不和谐,然后形成一种表达落差来激发幽默。提高表达中的语言落差,可供选择的手段很多,余华在语言运用上,则是打破了日常的语言系统内在规律,建立起一个自己的话语系统,组成一个奇异、怪诞、残忍的独立于外部世界但又真实幽默的文本世界。余华在文本中所采取的错位表达手段主要有“语义错位”和“逻辑错位”两种表达手段。
一、语义错位——含蓄的幽默
余华认为:“语言要能冲破常识,寻求一种能够同时呈现多种可能,同时呈现几个层面,并且在语法上能够并置、错位、颠倒、不受语法固有序列束缚的表达方式。”语法上的错位必然会带来语义上的多解,实现语义从常用义到临时新奇义的转变,这种语义转变就是导致幽默产生的重要因素。余华正是通过这样的错位、颠倒来表达出一种含蓄的幽默效果:在幽默中表现着阴沉绝望的东西,又让人从中发出笑声。余华作品中的语义错位常采用以下几种表达方式:
1.语义双关
语义双关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本义和转义),使语句所表达的内容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彼此之间产生了双关。
余华在作品中通过语义双关创造幽默的表现手法主要有婉述、仿拟、扩喻等。
婉述亦即委婉地叙述,是指在语境的制约和作用下,体现交际者心理需要而产生的,表达者并不直接说出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是很有技巧的“绕弯子”,让读者去体会其中的含义。说话者故意说些与本意相关或相似的事物,在风趣中间接地表达情感与态度,谐谑成趣。
(1)李广头和宋钢不知道他的胳膊被打成脱臼了,他们觉得看上去很奇怪,像是一条假胳膊挂在肩膀上。他们问宋凡平,为什么左胳膊在郎当?宋凡平轻轻晃了晃自己的左胳膊,对两个孩子说:
“它累了,我让它休息几天。”
——《兄弟》
在孩子面前,父亲的形象是高大的,勇敢的,宋凡平不想让孩子看到自己的落魄,则幽默地给孩子说胳膊要休息,在孩子看来,父亲又是神奇的:胳膊可以随时休息。读者通过话语则能由此及彼地体会那个时代作为一位父亲心中包含的辛酸与无奈,话语表达凄婉而幽默。
仿拟主要是指有意地仿照一些人们熟悉的语言材料,通过某种违背正常逻辑的想象和联想,临时创造出新的语句、篇章,以使语言生动活泼,或讽刺嘲弄,或幽默诙谐,产生一种新鲜、奇异、生动的感觉。仿拟的关键是对毫无关联的事物进行仿照,内容差距越大越能引起惊讶,越能产生幽默的感觉。
(2)后来,毛主席说话了。毛主席每天都在说话,他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人们放下了手里的刀,手里的棍子。毛主席接着说:“要复课闹革命。”于是,一乐、二乐、三乐背上书包上学校了,学校重新开始上课。毛主席又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许三观去丝厂上班,许玉兰每天早晨又去炸油条了,许玉兰的头发也越来越长,终于能够遮住耳朵了。
……
——《许三观卖血记》
字面上是对文革时期,许三观一家人命运的交代,但是透过字面,我们却能体会其中的特殊含义。这里仿拟是《旧约•创世纪》:“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现了;上帝说,水里有生物,空中要有飞鸟,地上要生出活物来,于是这个世界随即万物纷呈,生机勃勃。”这段话运用了仿拟的表现手法,把上帝和毛主席这两位神奇的却毫不相干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作者让我们惊讶的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了这平淡无奇的语言的神奇功效:话语被赋予了神圣的权利,从而对话语背后的权力进行了强有力的戏谑。
语义双关幽默中的扩喻手法运用得也较为普遍。它是比喻的一种,是在描述事物或说明道理时,用与它有相似点的别的事物或道理来打比方。
(3)“我不能收你的东西,”李血头拍了一下桌子说,“你要是半年前送来,我还会收下,现在我不会收你的东西了。上次,阿方和根龙给我送了两斤鸡蛋来,我一个都没要。我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许三观卖血记》
“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就会引发读者的双重联想,因为它本来的意义是指共产党的廉洁奉公,在这里却出自刚入党的贪婪的李血头之口。一正一反,意义不同,既显示出李血头平时的贪婪与冷漠的本性,又具有一种滑稽讽刺的意味。
恰当地使用双关,言在此而意在彼,有一箭双雕之妙。有时幽默诙谐,饶有风趣;有时委婉含蓄,耐人寻味。
2.别解
“别解”顾名思义就是另有解释,主要是利用一些语音或词汇、语法的内在规律,临时赋予一个词语或句子本来不曾有的新的含义,让读者去体会这个词本来的意义和新意义之间的相通之处,从而达到特定语言环境中的幽默效果。
如在《活着》中写队长经风水先生看过后,终于决定选中老孙头家的这块风水宝地做为炼钢铁的地点,老孙头不让,队长只有烧房子时,队长这样说:
(4)“他娘的,我就不信人民公社的火还烧不掉这破屋子。”
“火”在这里就被临时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即“人民公社的火”,既交代了时代背景又对那个特定时代人们的盲目大干进行了含蓄幽默的讽刺。
余华还擅长通过无知者的眼睛给事物赋予一种别样的含义从而创造一种幽默。如:
(5)地主心想糟了,随即看到飞机下了两颗灰颜色的蛋,地主赶紧将身体往后一坐,整个人跌坐到了粪缸里。
——《一个地主的死》
这里通过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地主的眼睛,把日军飞机的轰炸看成一个不知名的东西“下了两颗灰颜色的蛋”。这是余华笔下典型的闭塞环境中的无知人物,余华通过描摹他们眼中看到的,因他们的生活经历、经验造成的特殊世界的特殊事物,获得了与日常经验迥异的生命体验,从而塑造了一种别样的幽默。
3.大词小用
所谓“大词”是指一般用在大场合的或者比较严肃的语言环境中使用的词语,这些词语相对来说意义比较“重大”。如果把这样的词语放到同它不相称的小场合、小事件中去使用,就会小题大做,那么所描述的小事物也会“升级”,这样就破坏了平衡,产生了幽默。
(6)最后一把,我压上了平生最大的赌注,用唾沫洗洗手,心想千秋功业全在此一掷了。
——《活着》
这是福贵回忆自己年轻时在赌馆里赌得倾家荡产仍不回头时说的话。“千秋功业”一般都用在一些严肃重大的场合,放在这里来形容纨绔子弟福贵的心理,大大降低了词义的分量和范围,却大大增加了话语的幽默情趣。“用唾沫洗洗手”在这里也破坏了句中的平衡造成了幽默。
二、逻辑错位——失衡的幽默
在余华的作品里有很多颠倒是非式的、风马牛不相及式的、任意夸饰式的等违反逻辑的语言表达。余华认为,“现实生活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余华对现实生活经验的颠覆是因为他要揭示一种更深刻的精神的真实。而这正是产生幽默感的必备心态。余华作品中与之相对应的语言表达形式为:非理性的对话、粗俗离奇的夸张口语和零度情感的叙述语言。
1.非理性的对话
余华曾宣扬自己是“永远只为内心写作”的作家。在那篇具有宣言性质的写作理论文章《虚伪的作品》中,余华开篇明义:“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余华根据自己的创作体验首先提出了一个挑战性,颠覆性的命题:写作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而要达到真实,必须使用‘虚伪的形式。”余华“不再忠诚于所描绘事物的形态,而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所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更加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采取的怪异的求婚方式——请素不相识的许玉兰吃饭:
(7)“小笼包子两角4分,馄饨9分钱,话梅1角,糖果买了2次共计2角3分,西瓜半个有3斤4两花了1角7分,总共是8角3分钱……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啊呀!”许玉兰惊叫起来,“你凭什么要我嫁给你?”
许三观说:“你花掉了我8角3分钱。”
“是你自己请我吃的,”许玉兰打着嗝说,“我还以为是白吃的呢,你又没说吃了你的东西就要嫁给你……”
“嫁给我有什么不好?”许三观说,“你嫁给我以后,我会疼你护你,我会经常让你一个下午就吃掉8角3分钱。”
“啊呀,”许玉兰叫了起来,“要是我嫁给了你,我就不会这么吃了,我嫁给你以后就是吃自己的了,我舍不得……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吃了。”
“你也不用后悔,”许三观安慰她,“你嫁给我就行了。”
这样的求婚方式明显违背了日常生活的逻辑,尤其是许玉兰最后的一段话“……我舍不得……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吃了”的逻辑更是让人啼笑皆非。作者这样写,是故意向常规挑战,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怀疑和反叛。作者是在启发读者,现实是不真实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实的。荒诞派作家尤奈斯库说过:“荒谬就是没有目的……让人感到迷惘。他所有的行为成为毫无意义、荒诞不经和没有用处。”余华正是用一种违反逻辑的对话,生动幽默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无常。
2.粗俗离奇的夸张口语
余华作品中除了通过人物对话显示的非理性来创造幽默以外,他还常在作品中运用一些粗俗离奇的口语,让读者看了忍俊不禁。
(8)许玉兰仍然响亮地说:“从小我爹就对我说过,我爹说身上的血是祖宗传下来的,做人可以卖油条、卖屋子、卖田地……就是不能卖血。就是卖身也不能卖血,卖身就是卖自己,卖血就是卖祖宗,许三观,你把祖宗卖啦。”
——《许三观卖血记》
“卖身”、“卖祖宗”特别符合文中小人物的身份,幽默地显示了当时的时代特点。
如在刚开始实行人民公社时,食堂天天都排队吃肉,队长感叹道:
(9)“这日子过得比二流子还舒坦。”
——《活着》
这些看似粗俗的语言实则幽默地反映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天天都有肉吃的日子是大家共同追求和向往的目标,可这也预示了即将到来的饥荒年代。
福贵嫌儿子有庆穿鞋坏得快,非常生气就教训他说:
(10)“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
——《活着》
这样独特的问法恐怕也只能出自农民之口了。
老年的福贵在听到两个女人谈论村里挣钱最多的那个男人时这样说道:
(11)“做人不能忘记4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
——《活着》
这里的俗语反映出福贵经历了一生的坎坷起伏后对人生的认识,虽然通俗却独具哲理意识又使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具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
夸张也是余华文本语言违反逻辑创造幽默的一种独特方式,如:
(12)现在,童铁匠气得脸比铁还要青了,他扬起了他打铁用的大手掌,打铁似的“啪”地一声揍在李光头的脸上,让他一头栽倒在地,让他当场掉了两颗牙,让他眼睛里火星飞溅,让他半个脸呼呼地肿了起来,让他耳朵里的响声嗡嗡地叫了一百八十天。
——《兄弟》
“眼睛里火星飞溅”、“呼呼地肿了起来”、“嗡嗡地叫了一百八十天”这些通俗的夸张都形成了余华作品独特的失衡的幽默。
类似的例子在余华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余华以敏锐的眼光、娴熟的笔法选取了普通人日常口语中特有的一些词语,既符合小人物的身份,又充满了幽默色彩。
3.零度情感的叙述语言
余华还擅长通过冷漠的、不合逻辑的平静语言来创造幽默,因而,余华一度被人称为“零度情感叙述”。他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平静地向读者展示着人类之间自相残杀的血腥的暴力,在恐怖的场景中给我们展示一个非人的世界,让人觉得难以呼吸。余华就是在这种平静的叙述中,用不动声色的冷漠语言制造着黑色幽默。
如在《现实的一种》中写到一群医生共同解剖山岗尸体的场面时,作者似乎是在欣赏医生们的刀法,把解剖写得平静而又优美。“脂肪”在作者的眼里是“炫耀出了金黄的色彩”,并且“均匀地分布着小红点”,“解剖的皮肤”在死者身上“好似从头到脚披着几块布条一样”。作者在写这样的血腥场面的时候,总是那样地不动声色,甚至是生动真实。这样的描写又会带给读者一种冷酷、残忍的感觉,在阴沉绝望中产生一种强烈的黑色幽默感。
(13)那女人的锄头还没有拔出时,铁塔的4个刺已经砍入了我的胸膛,中间的两个铁刺分别砍断了肺动脉和主动脉,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出来,像是倒出去一盆洗脚水似的……然后,我才倒在地上,我仰脸躺在那里,我的鲜血往四周爬去。我的鲜血很像一颗百年老树隆出地面的根须。我死了。”
——《死亡叙述》
前面,我们说过余华擅长通过无知者的眼睛来描写世界创造幽默,那么,在这里,余华则是通过死者的视角来细致入微地描写一个死亡的过程:死者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死亡。这里施虐者和受虐者对待暴力的这种异常平静的态度和感受,使文章具有一种近乎残酷的变态的幽默感。我们说,这种幽默是变态的,是因为它突破了日常的生活体验而显得有些野蛮和残酷,而这野蛮和残酷又是真实的,只是人们因为禁忌故意回避罢。
余华小说的这种黑色幽默的精神,与他既不满于浪漫主义的过于主观抒情,又不满于现实主义的过分客观于现实有关。柏格森曾经说过:“通常伴随着笑的乃是一种不动情感的心理状态。笑的最大敌人莫过于情感。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笑一个引起我们怜悯甚至爱慕的人,然而当我们笑他们的时候,必须在顷刻间忘却这份爱慕,遏制这份怜悯才行。”余华的小说语言根本就不存在情感,更不用说去扼制这份怜悯了,因此,才有了余华的前期作品是冷漠的“零度情感叙述”之说。
幽默语言是说话者高超语言运用能力的体现,又是说话者明敏睿智的见证,在表达上具有出奇制胜的独特魅力,深受人们喜爱。余华小说用积极的语言实验,娴熟的错位表达,取得了很好的幽默效果。余华利用语义错位故意拉开话语常规意义和文中临时赋予“新义”之间的差距,形成一种表达落差,有助于产生含蓄的幽默效果;利用逻辑错位中的颠倒是非式的、风马牛不相及式的、任意夸饰的等违反逻辑的语言表达,给小说语言表达提供了一种超越性和客观性,这种极端的反差对立所流露出的幽默感,不是常态的幽默,而是一种失衡的幽默。
参考文献:
[1]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济南:明天出版社,2007.102-103.12.
[2]余华.余华作品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99.
[3]王达敏.余华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7.
[4]王清溪,付维洁.先锋作家余华小说语言新变探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6):20.
[5]耿传明.颠覆常识的艺术[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