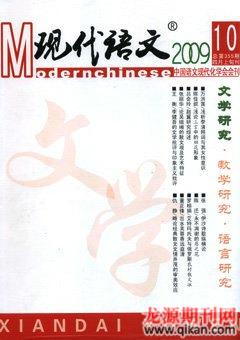略论经典散文文情并茂的审美效应
仇 静
摘 要:散文是情感的产物,是美的化身,经典散文以其真挚自然的情感和绚烂多姿的语言之美给欣赏者以咀嚼不尽的审美享受。真情和醇美构成了经典散文独特的艺术特征。文情并茂的审美效应是经典散文永恒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经典散文 文情并茂 审美效应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一切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莫不是以其动人心魄的情感力量,拨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弦,而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熠熠闪光的精品。而散文,更是被称为“情文”。散文比之小说、戏剧等文学艺术形式,其情感性更为强烈和充沛。它更近于诗,但又因没有格律形式的限制,其情感抒发更为自然诚挚。每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都是一扇向读者打开的情感之窗,引读者步入作者的情感小屋,或慷慨激昂,或娓娓而谈,或深情倾诉……使读者与作者同乐共愁。
散文,又被称为“美文”,它的自由之美、构思之美、意蕴之美……无一不有赖于形象生动的语言建构。以自由为本体性格的散文,其语言经过作者情感清泉的浸润,洋溢着作者本我的独特个性,或典雅清新,或精粹简洁,或气势磅礴,或平易自然,或幽默风趣,或机智犀利……虽风格各异,但莫不体现出语言智慧的华彩灵光,给欣赏者以咀嚼不尽的审美感受。
感人肺腑的情怀沁润了优美动人的语言,优美动人的语言抒发了感人肺腑的情怀,真情和醇美构成了经典散文独特的艺术特征,产生了文情并茂的审美效应。
一、经典散文的真“情”诉说
“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一个‘情字,但是我以为其情之最真、最痴、最自然者,莫过于散文之‘情。”佘树森在《散文创作艺术》中对散文的表“情”性可谓情有独钟,甚至将之称为“‘情种的艺术”[1],在笔者看来,这并非对散文的溢美,而是对经典散文情感特征的精确概述。
经典散文的情感“最真”,它以“真”而动人,它是作者心灵清泉的真诚灌溉而结出的果实,是作者“心底里流出的蜜”。经典散文的情感“最痴”,它深沉洁净,一唱三叹,读来常令读者有荡气回肠之感。尤其是一些“思人念物,追怀往事”的作品,“痛则切肤,悲则彻骨”[2],其“痴情”撼动人心,令人回味咀嚼不尽。经典散文的情感“最自然”,它不是矫揉造作,精心雕琢的产物,它是作者对人生意义,生命意蕴的真切感受、体验、领悟、挖掘和表达。“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园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人事发现的愉快……”[3]所有这一切情感,都自然地倾流在作者的笔下,其魅力非那些雕章琢句、扭捏作态的文章所能比拟,所以才能产生经典散文“所独具的‘永远会令人沉醉或深思的审美效应”[4]。
巴金谈到自己的“写作的秘诀”时说:“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一句话:把心交给读者。”[5]“把心交给读者”,朴素的话语中蕴含着散文贵真、贵痴、贵自然的真谛。凡是能经得住历史浪沙的涤荡,经得住读者审视的经典作品无不是作者的“心”作。
比如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就可称之为“心”作中的精品。名曰《项脊轩志》,“项脊轩”这间百年老屋的前后变迁却只是背景而已,贯穿全文的是作者的情感脉络:“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积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书斋之清静幽雅,之生趣盎然,之“珊珊可爱”,都是作者快慰心情的表露。作者置身书斋之中或静思默想,或高声吟颂,小鸟为伴,月桂为朋,那种融融之乐和少年无忧无虑的活泼情致,透过那自然清新的语言直入读者的心底,让读者与之同享悠然自得的“可喜”。祖母的亲切关怀、谆谆教诲亦可喜之事,然言犹在耳,斯人已逝,作者禁不住伏案大哭: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十五字而已,悲痛之情溢于言表。后文忆与妻子的生活片段情真意切,而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尤令人感怀不已: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亭亭如盖的枇杷树应该是怎样一幅美丽的图景,然而这美丽的景致在归有光的眼中徒增凄婉哀凉罢了!枇杷树为妻子去世之年亲手栽种,其情其景如在眼前,转瞬间树已亭亭如盖,栽树之佳人却早已香消玉殒,睹物思人,怎不令人肝肠寸断!
《项脊轩志》一文,作者或融情于景,或寄情于事,或直抒胸臆,其真挚的情感在人、事、景的描绘中流诸笔端。其悲其喜,几百年来让多少读者为之唏嘘!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司马迁《报任安书》中隐忍苟活,发愤著书的志向;诸葛亮《出师表》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耿耿忠心;柳宗元《小石潭记》中贬谪在外,潭水为伴的凄凉落寞……千百年来多少读者为之撼动心襟,不能自已。
现当代的经典散文亦是以其情感的真挚、自然而动人心魄。林觉民《与妻书》中对亲人的深情与牺牲一己、换取同胞自由的大义凛然,曾让多少读者痛彻肺腑;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沉痛悲愤之情,曾经感染了多少仁人志士从而在沉默中崛起;朱自清《背影》中蘸着泪水勾画的那个艰难替儿子买桔子的父亲的“背影”,曾经多少次撩拨了为人子女的心弦……
情感无国界,外国散文中的经典之作同样是以情动人的典范之作:罗曼·罗兰娓娓地叙事,表达的是母亲对儿子那份执著而又独特的爱(《我的母亲》);乔治·桑对乡村冬天温馨图景的描绘,凝聚的是她对宁静淡泊、自然纯朴生活的向往;海伦·凯勒三天奇特的光明之旅,传达的是她对生命的无比热爱(《假如给我三天视力》)……
遍观古今中外的经典散文作品,其情之真、之痴、之自然,如是也。大浪淘沙,那些空洞无情或应景造情的作品,终因其矫揉造作的虚假之情而被欣赏者摈弃,惟有情真意切的经典之作才会在文学的殿堂中散发永恒的魅力。
二、经典散文的辞采风韵
散文的魅力,来自于真情,也来自于语言,因为无论是深刻新颖的思想、感人肺腑的情怀还是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都是融于语言之中的。经典散文的语言“简洁凝炼、形象生动、清新自然、富有节奏感并饱蘸诗意”,“讲究文采”又“亲切自然”[6],既有美雅之趣,又有生气灵机,给人一种“如听天籁的愉悦”之感(杨道麟教授语)。而具体到每一篇散文,又因作者的年龄、气质、喜好和情感表达需要的不同呈现出摇曳多姿的不同风格,使散文的语言平添一种绚烂多彩的美。
散文绚烂多姿的辞采风韵,很难一言蔽之。林非说优秀散文的语言应“清澈流畅而又蕴藏着感情浓度和思想力量”;佘树森说优秀散文的语言是“华正与朴相表里”;凌焕新认为优秀散文的语言具有“表达思想感情时的适意美”、“语句结构方面呈现的错综美”、“语调声调所显示的节奏美”[7]。他们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散文语言意韵、音韵和形式上的美质。
(一)经典散文语言的意韵美
经典散文语言的意韵美,即凌焕新所说的“适意”,林非所说的“蕴藏着感情浓度和思想力量”,它体现为作者内心情感的自由表达,自然亲切中体现出语言的智慧,飞扬的文采与内容的美相统一。
比如石评梅《心之波》中望月沉思的一段:
今夜的月儿,好像朵生命之花,而我的灵魂又不能永久深藏在月宫,躲着这沉浊的社会去,这是永久的不满意呵!
世界上的事物,没有定而不变的,没有绝对真实的。我这一时的心波是最飘忽的一只雁儿,那心血汹涌的时候,已一瞥的追不回来了!追不回来了!我只好低着头再去沉思之渊觅她去……
这是作者自己心灵的絮语,那细腻柔婉的哀思愁怨在如清泉般自然、清凌而又优美的语言中涓涓流淌。“月儿”是“朵生命之花”,“心波”是“最飘忽的雁儿”,这些美妙的比喻似信手拈来,那么自然妥帖,不饰雕琢,却有一段天然的风流,让人咀嚼玩味不尽,显示出作者出色的语言功底与智慧。
经典散文语言的意蕴美在同题散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老舍的《我的母亲》语言质朴深沉,罗曼·罗兰的同题作品却带着几分谐趣,东方母亲的淳朴,西方母亲的独特,在不同的语言风格中得到完美地凸显。
(二)经典散文语言的音韵美
经典散文的音韵美,即散文语言在音节、声调、节奏上表现出来的音乐美。
比如我们熟悉的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曲曲折折”、“田田”、“亭亭”、“层层”等叠词连用,“零星地”、“袅娜地”、“羞涩地”等修饰词连用,形成一种舒缓悠长的旋律之美。一连串比喻构成的排比句式,又与前面的散句形成整散、长短的变化,在重复与变化的组合中,体现出和谐的节奏之美。细细读来,其感觉正如作者文中的话:“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再看余秋雨的《逍遥游》:
栩栩然蝴蝶。遽遽然庄周。巴山雨,台北钟。巴山夜雨。试目再看时,已经有三个小女孩喊我父亲。熟悉的陌生,陌生的变成熟悉。千级的云梯下,未完的出国手续待我去完成。
这段文字在韵律上有韵无韵相互交融,句式上长句短句错落有致,声调上高低起伏变化,读来琅琅上口、韵味无穷。作者像一个出色的音乐家自由调度着每一个文字音符,张显出经典散文语言的音乐美质。
(三)经典散文语言的形式美
经典散文语言的形式美,即散文语言外在形式上的美感。它或表现为行文的整齐有秩,或表现为语句的长短参差,或表现为色彩的明丽绚烂,给读者带来视觉上、听觉上独特美感。
从前文的许多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散文大家钟情于对偶、排比、反复等手法的运用,这不仅增强了语意、语音上的表现力,而且在句式上形成一种整齐而又错落变化的形态,给读者以形式上的美感的享受。
还有许多散文作家钟情于运用色彩来绘景、写人、状物,使散文的语言充满了一种绘画美。苏雪林《我们的秋天》一组散文中豆荚、黄昏甚至连小宝宝都充满了色彩!作者用她的生花妙笔在读者眼前展开了一幅绚丽的画卷,诗情与画意都在这彩色的语言中流淌。
经典散文的语言可以观、可以听、可以心会玩味,它独特的形式之美、音韵之美、意蕴之美,使散文在文学大观园里独享着“美文”的名誉,它与作家的真挚情感构成了经典散文的两翼。真挚的感情经美“文”而愈感人,美“文”融挚情而添灵性。文情并茂的审美效应——经典散文永恒的魅力所在。
注释:
[1]转引自方遒:《散文学综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11页。
[2]傅德岷:《散文艺术论》,重庆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88页。
[3]李泽厚:《美学三书》,转引自凌继尧:《美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299页。
[4]方遒:《散文学综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10页。
[5]转引自傅德岷:《散文艺术论》,重庆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81页。
[6]曹明海:《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68页。
[7]参考方遒:《散文学综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20页至122页。
(仇静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