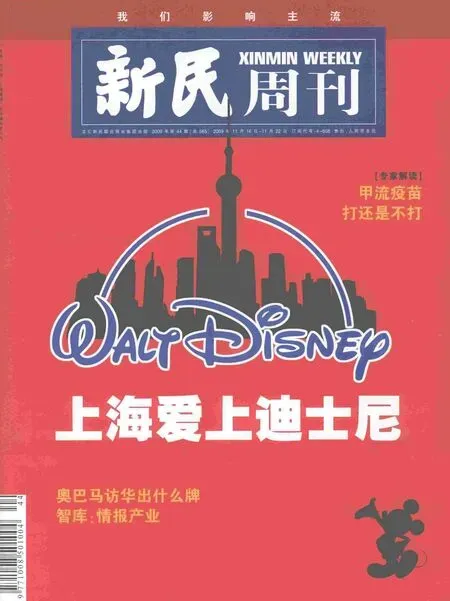我在欧洲,“艺术地”想念故乡
海上鹭鸶
我画中国女子,那些出入于石库门房子里身穿旗袍、永远处于花样年华的上海女人,是我灵魂的化身。
我在欧洲15年,一直努力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在别人眼里,我也是这类人。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相比左岸的知性,右岸的華贵,多了粗放和浓烈,艺术家们在小山广场年复一年地招徕游客。而他们的天地就是一张画板一张小凳,还有半根法国长棍三明治。更惨的是那些没有执照的艺术家,手持画板追赶顾客,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比小贩更得小心谨慎地陪客人笑脸。
想起自己多年前,第一次来到阿姆斯特丹,走进了家不拘一格艺术气氛浓厚的店,当我知道店中的陈列都是店主自己的作品时,我很愉快地和大胡子艺术家打招呼说:“多好啊,艺术家。”没想到他垂头丧气地叹息,“艺术家,这满大街都是艺术家”。让刚从新加坡来的我来愣了愣。当时想,也许可能是他当时的心情不太好吧。后来又遇到一个学校刚毕业的女孩儿,她问我的职业,我说是做艺术,她显得很诧异,一脸同情地问,“能养活自己吗?”
的确不太容易,在新加坡,最潇洒的大都是有钱的业余画家,不用看顾客脸色,讨的只是自己的欢心,因为这些画家都有另一份正式的职业,还有很多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主妇,这些“艺术家”购买的都是最昂贵的材料,画画的时候穿着高级服装,有些为了保护皮肤手上套了塑料手套,颜料每次用起来都畅快无比,最贵的“伦勃朗”一挤就是一大段,根本不用考虑用不完会不新鲜,用不完刮刀一刮,报纸一卷扔进垃圾桶,让一旁拮据的职业艺术家看了无比心痛。有时真想说:下次如果你用不完,就分点到我的调色盘上来吧。南洋诸国不同阶层的民众对艺术的认识,其浅白幼稚让人感到可笑。他们喜欢的大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花花草草,一张华丽精致的脸孔,却掩饰不了内心的脆弱与苍白。一个地方太过净化,就变成了超市产品,画面中充满着恣意,边缘,失意,荒杂,隐喻,独立也随之消解。
欧洲人从小开始就在浓厚的艺术环境下成长,自然而然地认为每个人自己心中都有一个艺术家,很难找到一种统一的审美与认知,也很少受旁人左右,也不需要别人的认同。如果他们买画,就是出于内心喜欢,挂在自己的居所或者办公室里作装饰,艺术创作和市场分开,没有很大的关系,而不是等画升值,再把画再卖掉。成熟的市场体制和智性的文化环境使得西欧很少有炒作艺术品致富的新贵,中国艺术家或艺术品收藏家开名车住豪宅的形象在西方人看来是很震惊的。
西方人对待艺术态度认真,很少扎堆,当然也有秀生活,玩行为,但还是非常注重从自己的传统的文化中延续,文化命脉的把持。我国开放以来,对西方的学习和关注远远大大多于西方对我们的在意,多年的异国生活让自己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常常省视与思考。当我多年前在印象派的摇篮法国诺曼底创作和生活,看着当地那么多白发苍苍的艺术家在勤勤恳恳地描绘他们自己故乡的情景时,我就知道,我的画再五光十色,这世界上只不过多了一个描绘异乡风景的画家而已。于是我会更怀念故乡,专注地画中国女子。那些出入于石库门房子、身穿旗袍、永远处于花样年华的上海女人,就是我灵魂的化身。
(作者为旅欧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