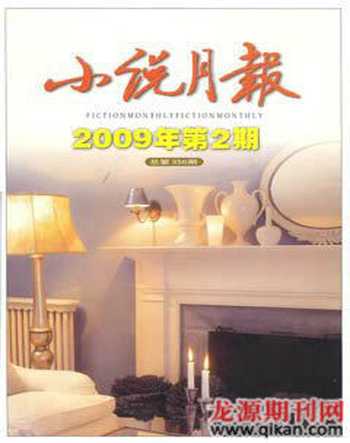种花记
有人说女大十八变,可是王家的孙女王春红才十几岁,就变成怪脾气的姑奶奶了,整天和她的奶奶过不去。奶奶说东,王春红就说西;奶奶说不要开窗,王春红非要开窗;结果呢,放进了一屋子的蚊子,嗡嗡嗡地叫,把奶奶的头都闹大了。为了不让那些蚊子咬到她的宝贝孙子王辉,奶奶只好拼命摇着芭蕉扇,手腕差点儿脱了臼。
差点儿脱了臼和真正脱了臼完全是两码事,可王春红的奶奶非要儿子王得和去先生那里买了膏药,摊在手腕上,像是戴了一只大手表。
如果手腕真的受伤了,怎么可能摇芭蕉扇呢?可王春红的奶奶偏偏不怕自己的话有漏洞,还是拿着芭蕉扇,到处显摆,还把她的“大手表”展示给别人看。如果人家没有注意到,她就会主动跟人家说,你说王春红坏不坏,比“四人帮”还坏,她把我的手腕都弄坏了。
王春红不是你的孙女吗?
什么孙女啊,她是我前世里的对头星!王春红的奶奶说。
最近,王春红和奶奶已不是回嘴的问题了。王春红的奶奶说了,她家真的养了一个“造反派”,竟然动手打她,还骂她是地主婆子。有人就故意问她,你家王春红打你什么地方了?王春红的奶奶指着手腕说,就是这里。
王春红奶奶的手腕上的“大手表”早剥落了,但留有“大手表”的痕迹。
这不是上次脱臼的地方吗?
你瞎说什么?她就是打我了!王春红的奶奶很是激动,我们家养了一个“四人帮”啊。
这一次,王春红的奶奶倒是没有冤枉王春红,王春红的确动手了。起因是弟弟王辉喊了王春红的新绰号。
“六十五度摇摆”,是王春红的绰号。
绰号这个东西,就像人的影子,一旦从人的身后长出来,再把它杀死是很不容易的。谁能够杀死自己的影子?更何况王春红的绰号是轮船码头边开旅社人家的罗开文的绰号的翻版,小痞子罗开文走路,总是喜欢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边摇摆一边吹着口哨,身体晃到了“七十五度”,所以大家叫他是“七十五度摇摆”。
王春红走路其实一点儿也不摇摆。上次看了电影《红楼梦》,王春红就常常梦见自己挑着一竹篮的花瓣去葬花,边葬边哭,有时候还在床上哭醒了。因为喜欢林黛玉,所以王春红就有意模仿林黛玉走路的样子,把左手插在口袋里走路,一只手摆动,看上去有一点儿摇摆。但王春红绝对没有六十五度,连三十度的摇摆都谈不上的。王春红长得瘦,又是小鼻子小眼睛,实际上是有一种杨柳摆风之韵的,杨华和吴文英也在悄悄学了。
可“六十五度摇摆”这个绰号还是传了出去。当初王春红不晓得是她的绰号,那些臭男生对着她喊“六十五度摇摆”,王春红对他们表示了轻蔑的一笑。她才瞧不起他们呢,就像她从来就瞧不起家里最得宠的臭王辉一样,为了生这个弟弟,家里被罚了一万块,所以王春红的奶奶有时候就直接喊王辉为王一万。这个名字也只有奶奶能喊,如果王春红叫“王一万”的话,奶奶就骂过来了,骂得比街上的脏话还要难听,所以王春红索性就躲着王辉,她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这一天,王春红躲不过去了。王辉最近刚刚学会用火花赌博,想要王春红一张夹在书本里的镇江火柴厂火花,王春红的那张火花在他的游戏中是天价——一个亿。王春红坚决不肯给他,王辉就骂王春红,和奶奶骂王春红的话一样难听,王春红不生气,她听惯了。可后来,王辉不骂脏话了,而开始骂“六十五度摇摆”。王春红回骂王辉,你才是“六十五度摇摆”。王辉哈哈大笑,指着王春红说,王春红,你自己骂自己啊,太可笑了,还有自己骂自己的!王春红头一下子大了,“六十五度摇摆”,肯定是她的新绰号!王春红想,她真是一个傻瓜啊,人家都叫了好多天了,可是她蒙在鼓里,还给那些臭男生赔着笑脸——尽管是轻蔑的笑,可在那些臭男生的眼睛里,她王春红还是赔了笑呢。
王春红的奶奶的耳朵平时有点儿背的,可对有关王辉的一切,她都听得清清楚楚。王春红的奶奶一听到了王辉和王春红在对骂,她就立即拿着坏煤勺“护”了过来,喊道,乖乖啊,她是不是又做“造反派”了?一听到奶奶出场,王辉立即摆出了挺委屈的样子,指着王春红说,奶奶,她不是“造反派”,她是小气鬼!王辉说完了,仗着奶奶的势,冲上去就抢王春红手中的那枚火花。
王春红比王辉大八岁,个子本来就比王辉高,王辉就有点儿气急败坏,还差一点儿跌了跟头。说实话,在对待王辉的问题上,王春红并不是一个小气鬼。要是放在往常,王春红肯定会把火花给王辉了,那火花又不是王春红最珍贵的花种子。可是那一天不,那一天王春红的倔脾气犯上来了,再加上奶奶在面前,她偏不迁就。
跌了跟头的王辉立即摆出了十分疼痛的样子,奶奶见状,对着王春红喊了起来,瘟东西啊,不得了了,还没有怎么样呢,就打起兄弟来了!
王春红的奶奶一边说,还一边将手中的坏煤勺砸了过来。王春红一躲,奶奶砸了个空。虽然没有砸着,但王春红很是生气,她一边撕着火花,一边把火花的碎片甩到了奶奶脸上,吼道,给你,全给你,你这个小地主,你地主婆子!
吼完了,王春红就冲出门去了。本来王辉和奶奶想拦住她,可奶奶和王辉哪里是她的对手?!家里的用水都是王春红从轮船码头上往家里拎呢,她的力气慢慢地长大了。王春红不想与奶奶打架,也不愿意和奶奶打架。弟弟的背面还有两个后台呢,一个是爸爸,爸爸从来不明着在女儿面前“护”儿子,可心里还是“护”儿子的,如果王春红有什么委屈,爸爸也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立场。王辉后面还有一个大后台,也就是最坚硬的大后台——妈妈。王春红敢惹爸爸,可她绝对不想惹妈妈,在王辉没有生下来的那几年里,妈妈几乎是天天把她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后来有了王辉,她才没有被妈妈当成一根刺,把她从这个家里拔出去。
王春红从家里逃出去的时候,发现晒在门口的煤球被人家踢翻在路上了,她还俯下身子,拾起那几块煤球,放到晒煤球的门板上。家里没有什么声音了,奶奶肯定在拿什么东西哄住了王辉。
王春红根本就不稀罕奶奶的好东西,她现在最稀罕的是花种子。要花种子就得去找吴文英的。本来王春红是绝对瞧不上说话有点儿大舌头的吴文英的,可是吴文英后街上的姑姑家有花种。想要有花种,王春红就得和吴文英玩儿。去年,王春红家里的黄鸡冠花种子就是吴文英给的,现在,王春红想要五角星花的种子。王春红看过吴文英姑姑家的五角星花,开得实在是太好了,那开出来的五角星花就像小小的五角星,娇小,鲜艳,爬在铁丝上开,铁丝就像是参了军似的,满铁丝闪闪的红星。
吴文英正在家里绕旧毛线,绕得乱糟糟的,就像王春红的心情一样。王春红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坐到吴文英的对面,帮着吴文英绕毛线。绕毛线是需要一个专门的绷子,可吴文英家没有,王春红就找来了一张搓衣板,用搓衣板绕毛线也差不多的。
等王春红把吴文英家毛线绕好了之后,心情竟然好了许多。王春红正准备和吴文英说去她姑姑家要五角星花种子的事,这时吴文英的妈妈下班回来了,王春红就不好说了,吴文英的妈妈和姑姑关系不好,她们经常在街上对骂,把很多年的小事都翻出来说。
离开吴文英的家,王春红在巷子上走了一会儿,想上大街上去,可她还是折了回来,回家吧,如果遇到班上的那些臭男生,又要对着她喊那个绰号了。
王春红就把左手从裤子口袋里取了出来。走了一会儿,觉得特别地别扭,像是要摔倒似的。王春红没有办法,还是把左手插到了口袋里,边走还边看后面,还好,后面并没有什么人跟着。
家里准备开晚饭了,王辉和爸爸坐在桌边,爸爸依旧在喝他每天一杯的白酒,妈妈在洗脸,她在砂粉厂上班,每天筛砂特别的脏。奶奶正在往畚箕里收拾煤球,王春红见状,就进门去找扫帚,奶奶的眼睛不好了,可她还是舍不得掉在地上的那些煤屑,王春红想帮奶奶一把。
王春红和奶奶一起把煤球弄回来之后,就到天井里放扫帚和畚箕了。没有想到的是,只一会儿,王春红就从天井里冲出来了,像一个疯子尖叫着,冲到了奶奶的跟前,推了奶奶一个巴掌。
王春红下手并不重,只是轻轻地刮了奶奶身子一下,奶奶就跌倒在地上了。奶奶倒在地上,死死抓着王春红的衣服,号叫起来,不得了了,出人命了,王得和啊,你养了个杀人犯的丫头啊,打杀人了哇。
王春红绝对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效果,她想把奶奶抓她衣服的手掰下来,可奶奶的手像是粘在她衣服上了,怎么掰也掰不开。
再后来就简单了,王得和冲到了呆在一边的王春红面前,左右开弓几个耳光,王春红的脸上开花了,满脸的血,那血把听到声音赶过来拉架的邻居们都吓呆了。王春红不说话,邻居以为是打得太重了,其实那血都是从王春红鼻孔里淌出来的。
还是王春红的妈妈冷静,她先是让邻居把王春红的奶奶拉到邻居家去,接着她又拉走了气头上的王得和,再后来,她亲手用毛巾替王春红擦去了脸上的血。王春红开始还不配合,可是妈妈的力气比王春红大,再加上妈妈说了句话,让王春红的委屈的心情好了许多。妈妈一边替王春红擦洗着,一边在王春红的耳朵边说,我看到了,是老东西自己跌下来的,你根本就没有碰到她!
本来王春红不想说自己打奶奶的原因,就因为妈妈这句知己的话,王春红就把事件的经过告诉了妈妈。刚才王春红到天井里放扫帚和畚箕,一下子发现她种在旧脸盆里的太阳花、凤仙花和鸡冠花都没有了,被薅掉了,她摸到的只是太阳花和鸡冠花的根,根上还留有花杆的汁液,很冰,很凉。
奶奶从来就反对王春红种花,奶奶还不止一次说过,哪一天她要把这些花薅掉,晒干了点煤球。可王春红太喜欢种花了,人家叫她“六十五度”,是因为王春红喜欢把手放在口袋里面,而王春红之所以把手放到口袋里,是因为左手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伤疤是王春红跟同学杨华抢一种蓝太阳花花种时划伤的,那时她和杨华一起到吴文英姑姑家去。吴文英姑姑的家里长满了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太阳花,单瓣的、复瓣的、大红的、浅红的、紫红的、鹅黄的、淡青的,说不出的好看。还有一种蓝太阳花,王春红和杨华都没有见过,都想要种子,可一下把那盆蓝太阳花打翻了。太阳花的种子实在太小了,比圆珠笔的笔芯尖上的圆球还要小,一旦掉到地上,怎么也看不到的。杨华想要,王春红更想要。王春红是连着地上的泥土一起抓到自己裤袋里的。她的手被碎瓦片划破了。王春红想等到蓝太阳花开出来,她再告诉杨华她受伤的事,可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蓝太阳花还没有来得及开花,就被奶奶薅掉了。
红啊,一股咸菜的酸气都冲到了王春红的鼻子里了,妈妈一边用手背替王春红擦着眼泪,一边说,红啊,哪一天我轮休,我跟你一起跟人家要炮仗花,炮仗花长起来好看,开起花来就像是放炮仗,喜庆得很呢。
爸爸妈妈都上班了,平常的时候,王春红王辉和奶奶待在家里,王辉是个小畜生,他有需要就喊人。有时候王辉会喊奶奶,奶奶会屁颠屁颠地赶过来。有时候,王辉会喊王春红,王春红也会过来。有时候这个小畜生是奶奶和王春红一起喊,奶奶和王春红都会赶过来,王辉见到的就是两个绷着脸的人,奶奶和姐姐都生了一脸的霜。
王春红的奶奶还记着上次的事,经常对着地上觅食的鸡指桑骂槐,说,滚开,滚开,你不看看,长得那么丑,还想吃什么米?
要是放在以前,王春红会和奶奶直接对骂。可现在不了,她回味着妈妈在背后骂奶奶的话,心里像是有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一下子镇定了,故意装着听不见。有时候,奶奶骂鸡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王春红会到米坛里抓出一把米,当着奶奶的面,撒到那些被奶奶冤枉的鸡面前,好好地替它们出了口气。
王春红的奶奶很是舍不得那些米,就骂得更厉害了,还拼命赶那些鸡,仿佛是要和那些鸡抢食。有了撒到地上的米,和王春红有了妈妈这个后台一样,那些鸡根本就不怕王春红的奶奶了。
赶不走那些鸡,王春红的奶奶就索性数落起来,说,你狠,你狠啊,长得漂亮,又会流鼻血。王春红听出了奶奶的意思,立即反驳说,是啊,谁叫我倾城倾国呢,谁叫我羞花闭月呢,谁叫我沉鱼落雁呢。
王春红一口气对奶奶一连串说出了那么多成语,可奶奶一句也听不懂,等于是白说。
更多的时候,王春红和奶奶不吵架,也不说话,只是处于冷战状态。小畜生王辉,是她们之间的传声筒。小畜生王辉,没心没肺的,十分乐意他这个新角色,他似乎忘了,他才是王春红和奶奶真正的导火索。
王春红的妈妈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过了几天,她带了一棵宝贝似的花苗。妈妈一进门就嚷开来了,红啊,红,拿小铲锹来。
王春红一看,妈妈手里是一棵南瓜秧。王春红以为妈妈要在天井里种南瓜了,可是天井那么小,南瓜藤长大了,该朝哪里爬呢?正疑惑着,妈妈又叫她去端一碗水来给“南瓜秧”浇水。
见王春红不像预料中的高兴,妈妈就问她为什么。王春红如实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妈妈听了,笑得咯咯的。妈妈告诉她,这才不是南瓜秧呢,这是比炮仗花还好看的节节高。妈妈说,节节高,开一层花,就长高一层。再开一层,像是花做的楼房呢。妈妈只管说,王春红只是听着,没有说什么。
回到屋里,王春红的奶奶正在用刀板拍王得和最喜欢吃的大蒜头,拍得啪啦啪啦响。她一直对于王得和的婆娘纵容王春红顶撞她很是耿耿于怀,但她对儿媳妇没有什么办法,在小王辉没有生出来之前,她是完全压着这个女人的,可是孙子王辉一出生,多年的媳妇就变成了婆婆。一个家里既然有了婆婆,总得有人成为受气的媳妇。看在儿媳为她生了宝贝孙子的份儿上,她只好就认可了角色的转换,从婆婆变成了媳妇。
听到奶奶把家里敲得咚咚响,王春红只好捂着自己的耳朵。妈妈看出来了,王春红不高兴了,就支使王春红到男浴室门口去接跟爸爸去洗澡的王辉。王春红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站在男浴室门口等王辉,可是妈妈已当着奶奶的面说了,她不好不听话,也就是说,她不好不去。再说了,在搬运站工作了一天的爸爸能替王辉洗澡已是不简单的事了,王得和必须先替王辉洗了,再上来替王辉穿了,先叫浴室的人把王辉带出来,他自己再下去洗,外面总是有人接王辉的。
王春红刚穿上外套,妈妈又叫住了她,给她五分钱,说,红啊,小辉要吃脆饼,你就买给他。
说来也怪,王春红一出门,奶奶就把拍蒜头的声音压下去了,妈妈在家,奶奶就不怎么敢大声做事。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泥巴。如果说王辉是大鱼,妈妈是小鱼,奶奶是小虾,那她王春红算是泥巴吗?
到了浴室门口,王春红见到那些进进出出的男子,觉得满鼻子都是臭气。王春红想走,可又怕接不到王辉,后来她就想自己的花,那粉的红的蓝的太阳花。如果奶奶不把太阳花拔掉,她家天井里也快像吴文英姑姑家的天井了。
王辉出来了,脸上红扑扑的,竟然开口叫了王春红一声姐姐。王春红正疑惑着,爸爸出来了。原来爸爸也洗过了。爸爸见了王春红,立即夸奖起王辉来,红啊,你晓得不晓得,你弟弟自己会洗澡了。
路过脆饼店的时候,王春红拿出五分钱,准备给弟弟买脆饼,想不到爸爸又递上了五分钱,要了两块。一块给了王辉,一块给了王春红。王春红没有吃。爸爸说,红啊,吃吧,一块脆饼,爸爸还是请得起的。
脆饼很香,王春红吃得比王辉慢。王春红又掰给了王辉半块。快要到家的时候,王春红听到爸爸说,红啊,回家要叫奶奶,你奶奶一辈子苦得很呢。
脆饼就卡在了王春红的喉咙里了。一个晚上,王春红都没有说话。好在没有人发现她,奶奶和妈妈都在叫王辉反复说自己会洗澡的事。
有好几天,王春红都像妈妈移植回来的节节高的叶子,蔫了。妈妈叫王春红多浇一点儿水,并要她白天的时候,把花盆移到阴凉里,不要在太阳下晒。王春红根本就不听,既没有给节节高浇水,又没有把节节高移到阴凉里。王春红看着蔫下去的节节高,狠狠地想,枯死了才好呢。
早晨,王春红正准备到外面去刷牙,没有想到的是,奶奶却抢先蹲在了王春红最喜欢蹲的位置,很夸张地刷着牙。挤好了牙膏的王春红只好到天井里刷牙,往花坛那边一看,想不到半死不活的节节高还是挺过来了,竟然抽出了一对新叶,那新叶慢慢地展开,和南瓜叶一样,“南瓜叶”后来越长越大,像一对摊开的大手,似乎就是在对王春红说,你继续怠慢我吧,我不怕!
王春红想不到节节高会长得这么泼皮,她在花坛前待了一会儿,把准备刷牙的一杯水全部泼到了节节高的根下,转身又去水缸里舀了一杯水,没有再去天井刷牙,而是蹲到了奶奶的身边。
满嘴巴牙膏沫的奶奶回过头,看了看王春红,又仰头看了看天。王春红的奶奶不晓得,王春红的心中已经有一座节节高花做的楼房了。
节节高蹿得快。大叶子,高个子,叶子比王春红的手还大,而节节高的个子都快赶上王辉的个子了。再过几天,节节高的个子超过了王辉,快赶上王春红的个头了。王春红看着节节高,感觉那不是节节高,而是一棵有梦想的向日葵。王春红想,节节高肯定是想长得超过了屋檐,然后再在天井的半空中长出一只大草帽似的向日葵匾。
可节节高就是节节高,它不是向日葵,因为它有花骨朵了。节节高的花骨朵很有意思,长在节节高的胳肢窝中间,也就是长在大叶子与茎秆之间,王春红觉得神奇极了。小时候的王春红曾经问过妈妈,她是从妈妈的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妈妈说,是从她的胳肢窝里生出来的。王春红当时不相信,现在看到了节节高那么多的花骨朵,她相信了妈妈说的话。
节节高的花开了,开得大大咧咧的,就这么倚在叶子与茎秆的胳肢窝里。王春红高兴了一天,总想告诉一个人。后来,王春红把节节高开花的事告诉了王辉,王辉看了,不相信是真花,硬说是假花。王春红好说歹说,王辉才相信。王春红后来还告诉了王辉,人和花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胳肢窝里生出来的。王辉更不相信了,王春红说,我骗你是小狗,妈妈就是这样告诉我的。
王春红刚说完,突然听见奶奶骂了起来,王春红,你真是不要脸!
你说什么?!王春红被骂得很冤。
我说你不要脸,你怎么可以跟你王辉讲这样不要脸的事?奶奶说,你一个姑娘家,不要脸也就罢了,可你弟弟还是个黄花郎呢。
我怎么不要脸了?我怎么不要脸了?我是偷人家的了,还是抢人家的了?我还是跟人家私奔了?王春红的眼泪都出来了。
你就是不要脸!王春红的奶奶冷冷地说。
王春红不管节节高了。王春红有点儿像懒虫了,什么也不想管。王春红的奶奶也索性不管她,有什么事情都自己做。有时候,王春红的奶奶做不动,就要王辉帮着做,王辉不想做。王春红的奶奶就教育王辉,你不学将来怎么办?将来她可是人家的人,你怎么办?王春红听了,装着听不见,这是激将法,她才不上这个当呢。
王春红不上当,奶奶只好自己做,连水都是自己到码头上去拎。王春红的奶奶本来还想动员王辉和她一起到码头上抬,王辉坚决不同意。王春红的奶奶只好半桶半桶地拎,拎得气喘吁吁的,像是在王春红的耳朵边拉风箱。王春红实在听不下去了,赌气似的从奶奶手里抢过了水桶。
没有人过问的节节高却越开越盛,真的像一幢花做成的楼房。有时候,猛然一看,真像是天井里站了一个全身都戴了大红花的人。
不要脸!王春红在心里骂了一声。
可被骂过的节节高依旧开得很放肆,像一个嬉皮笑脸的人。王春红很不愿意看到这个“人”。可事情就是这样,她越是不愿意看,那个“人”就越是喜欢挤到王春红的眼睛里来。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王春红闭上了眼睛,在心里指着那棵节节高骂个不停。可不要脸的节节高还是在夜里挤到了王春红的梦里了,那个全身戴满大红花“人”竟然长了一张脸,在梦中,王春红好不容易看清了那个“人”,是那个“七十五度摇摆”的小痞子罗开文。
“不要脸”的节节高是王春红自己毁掉的,她像一个疯子一样,冲到了节节高的面前,跳了几下,才抓到节节高的枝头,往下一拽,节节高就倒了下来。
这么不经拽啊?王春红看着倒在地上的节节高,掉在地上的通红的花瓣,就像是“花人”流出的血。
王春红的奶奶到天井里晾衣服,发现天井似乎亮堂了许多,再一看,王春红也在天井里,正抱着那些跌在地上的节节高哭呢。
哎呀,哎呀!是你自己把它弄掉的啊,老天作证啊,不是我弄的啊!王春红的奶奶大叫起来,到时候你宝贝妈妈回来,可不要赖到我的头上啊。
王得和被王辉叫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乱成一团了。老的说她不想活了,小的说她也不想活了。王得和问王辉发生什么事了,王辉怎么也讲不清。而叫她们讲,两个人像是对他开机枪,吵得他耳朵里像是放鞭炮。
王得和从碗橱里找到一只被王辉打碎过的碗,使劲地砸在地上。碗碎了,安静了。空气中有一股难闻的草臭味,那是节节高汁液的味道。
可能是想解决王春红和奶奶的冷战状态,妈妈对王春红履行了诺言,她到后街上吴文英姑姑家,要来了两棵炮仗花的苗,栽到了原来的花坛里。
炮仗花是连根移植的,基本没有受伤,所以很快就活了,还分了孽,渐渐成了蓬勃的一丛。王春红每天都到天井里晾衣服,炮仗花安安静静地看着王春红,仿佛一个和王春红闹了小矛盾的同学,考验着王春红,看谁熬不住,能够先开口说话。
王春红当然不会先跟炮仗花说话,她更多的是怀疑,这么安安静静的花,怎么可能开出风风火火的像炮仗一样的花呢?
但炮仗花还记得自己就是炮仗花。有一天,王春红走到天井里收衣服。刚刚晒好的衣服有一股好闻的水花香。王春红就是在这股水花香中发现了炮仗花的异样。
炮仗花里有一点儿红!
王春红心里咯噔一声,好像有几颗炮仗在她心里炸响了。没来由的,把王春红的心好好震了一下。
再后来,炮仗花的红越来越大,那“炮仗”越来越多。每看一次,王春红的心里就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王春红深吸了几口气,那“炮仗”炸出来的都是水花香。
炮仗花开了,改变了王春红和奶奶的冷战状态。两个人说话了,有时候,两个人还一起做伴到码头上去。王春红的妈妈很想弄清楚,是王春红先和奶奶说话的,还是奶奶先和王春红说话的?
王春红没有回答妈妈的问话,妈妈以为她不好意思说,其实王春红不是不好意思,而是她记不起来了,究竟是谁先开口说话了。反正就这么说话了,就像炮仗花,它想开,也就这么开出来了。
王春红家的炮仗花开得太好了,简直就像王春红家有喜事,每天都在给王春红放炮仗。噼噼啪啪的。有一天,杨华跟王春红说,我要和吴文英到你家看炮仗花。王春红很是惊讶,她可没有和杨华透出一点儿风声,怎么杨华就晓得了呢?可能是多嘴的奶奶到街上说的。这个奶奶啊,生怕人家不晓得她家的炮仗花开了。要是把她放在吴文英的姑姑家,每天都有不同的花在开,她该怎么去开新闻发布会呢,怎么说得过来呢?
杨华和吴文英到王春红家看炮仗花了。吴文英告诉王春红,炮仗花是可以吃的,它的花蕊是甜的。王春红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杨华也是,她说,吴文英,那你吃吃看,你吃吃看,是不是像糖一样甜?吴文英说,不像糖,是有一点儿甜,我是在我姑姑家吃过的。杨华问吴文英,那是王春红家的炮仗花好看,还是你姑姑家的炮仗花好看?吴文英说,王春红家的炮仗花长得好。杨华有点儿将信将疑。吴文英说,当然是王春红的炮仗花好,炮仗花在她们家,可是独生子女呢。杨华酸溜溜地说,吴文英,你是不是吃多了鸡舌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
王春红听着杨华和吴文英斗嘴,只是盯着炮仗花看,眼睛里全是红艳艳的炮仗花。
每天早上,王春红第一件事件不是刷牙,而是给炮仗花浇水。可有一天,王春红发现炮仗花湿淋淋的,有人给炮仗花浇过水了。王春红问妈妈,妈妈说她没有。王春红想问王得和,发现王得和上厕所去了。家里只有一个正在烧早饭的奶奶。王春红想,没有第二人了,肯定是奶奶了。是奶奶给炮仗花浇了水。
炮仗花真是把王春红奶奶的脾气也变掉了,她不但替炮仗花浇水,她还跟王春红说起了小时候绣花的故事。绣花得有花样子,花样子上的花都是什么牡丹花金菊花。奶奶没有见过这些富贵的花,怎么也绣不好。师傅气得用绣花针刺奶奶,奶奶还是绣不好。后来就放弃不学了。奶奶说,其实那时候也是一个犟脾气,照葫芦画瓢不就行了。奶奶说得很可惜,王春红也很可惜,不然她也会绣花了。
绣花样子上有炮仗花吗?王春红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炮仗花。
奶奶哈哈大笑,露出了透风的牙齿,指着王春红说,傻丫头,怎么可能有炮仗花呢?
怎么不可能呢?王春红还是不明白。
炮仗花是草花啊,傻丫头!奶奶笑得更厉害了。
王春红还是不懂奶奶的话。王春红去问吴文英,你姑姑家有牡丹花吗?
没有。吴文英摇了摇头。
牡丹花有炮仗花好看吗?王春红问。
不知道。吴文英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还是觉得炮仗花比牡丹花好看。王春红说。
吴文英吃惊地看着王春红,王春红刚才说得那么的肯定,好像她见过牡丹花了。其实王春红根本就没有见过牡丹花,只是她心里太偏爱那些在她的心里噼噼啪啪放炮仗的炮仗花了。
王春红似乎惹了花神了,她总是待在炮仗花前看炮仗花。奶奶见了笑话王春红,红啊,你还是抱着炮仗花睡觉吧,要不,将来你嫁个人家,就用炮仗花给你放炮仗。王春红又急又羞,对奶奶说,给你放!奶奶说,真是没大没小了,当心你死鬼爷爷听到了。
开学了,王春红上课去了,可不怎么专心了,经常走神,被先生批评过几次。王春红才把放在炮仗花上的心收回来。可下了课回到家,她第一个事件就是看她的炮仗花,没有她的照料,那些炮仗花总是没有暑假里那么鲜艳,有些衰老了,也有些憔悴了。王春红问奶奶是怎么一回事,奶奶说,花无百日红呗。
王春红当然明白奶奶说的是怎么一回事,顿时就想到了那个林黛玉。无端的伤感就涌到了王春红的眼睛里,王春红怕被奶奶看见了,就仰起头看天,天空中有很多巧云,它们都被夕阳照得五彩缤纷,像是要过年了。
炮仗花出问题了。那是王春红看云的第二天。王春红回到家,发现炮仗花真的大变样了,像是被谁的手捋了一把。王春红再一看,是最上面的炮仗花的花蕊被谁一一抽走了。炮仗花的花蕊是甜的,肯定是被谁偷吃掉了。
奶奶,奶奶!王春红叫了起来,是不是王辉偷吃了我的炮仗花?
奶奶跑过来,看了看,说,哎哟,我以为是怎么回事呢,王辉没有吃,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出门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王春红看着奶奶,奶奶的脸上看不出说谎的样子。不过大人说谎不像小孩子会脸红,大人说话会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再说了,王辉可是奶奶的心头宝贝呢。
既然从奶奶那里找不到证据,王春红就直接去问王辉,王辉也不承认。王春红太着急了,但她又不敢和王辉在外面打架,用力把王辉拖回家了。一到家门口,王辉就杀猪般地叫了起来,奶奶听见了,冲了出来。
王春红和奶奶又打起来了,可能是王春红的力气大了,奶奶再也不能占上风了。王辉还是老办法,又去叫来了王得和。王得和放下手中的板车,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妈妈和女儿两个人正缠着呢,王得和装模作样地吼了几声,可那两个人都不听他的。王得和没有办法,就叫王辉拿一张板凳来,他就坐到了那张板凳上,说,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会打到什么时候?
王春红和奶奶没有打得太长的时间,喜欢吃黄豆的王得和放了几个很响很响的屁,那屁又在板凳上反弹了一下,那屁声就更响了,真像是放了几个大炮仗。
连环屁!王辉一边笑,一边大声地评价说。
也就是这个连环屁,王春红和奶奶都松了手。奶奶还对正在大笑不已的王辉喝道,小畜生,你笑什么啊,你爸爸苦了,太苦了。
王春红没有吃晚饭,王春红的奶奶怕她饿了,就向王春红的妈妈故意说起了炮仗花的事。王春红的妈妈说,说不定是王辉吃的吧。奶奶说不是,肯定不是王辉吃的,有可能是老鼠,老鼠真是一个坏东西。
王春红根本就不听她们在唱双簧,她是在对自己进行惩罚,如果不是她自己多嘴,把炮仗花蕊是甜的秘密告诉奶奶,炮仗花就不会这样了。
王春红的妈妈把晚饭亲自送进来了,可王春红还是不想吃。王春红在心里说,我又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你们抱来的。我不吃你们家的饭。坚决不吃。饿死也不吃。
夜渐渐深了,王春红睡不着,她想着远方的父母,可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们的面容。不知道她的那个真家,有没有长一盆会放炮仗的炮仗花?
被人捋了一把的炮仗花说败也就败了,曾经那么鲜艳的炮仗红慢慢地变灰了,变白了。王春红都觉得像做了一个梦。有时候,王春红都不愿意看到红色的东西。
王春红不但不喜欢红色的东西,还不穿妈妈做的花衣裳,还有,她的脾气变得还特别的火爆,动不动就和人吵架。王春红和杨华吵的时候,吴文英过来劝架,王春红不和杨华吵了,反而和吴文英吵上了。放学了,没有了朋友的王春红孤零零地往家里走,心里全是呼呼的风,风把一切的红色都吹成了灰色。杨华和吴文英都不晓得,王春红是不喜欢别人叫她王春红,王春红的名字中就有一个红字啊。
但王春红还是逃不了“红”字,因为在家里,王辉直接叫总是发脾气的王春红为“炮仗红”。
炮仗红。炮、仗、红。炮、仗——红!
王春红坚决不答应,从心里彻底恨上了奶奶。这个绰号肯定是奶奶给她起的,依王辉那样的小脑袋瓜,怎么可能想出这样一个绰号?
中午,王春红只吃了半碗饭,她的肚子有点儿疼疼痛。到了学校,肚子好像更疼了。去了趟厕所还是疼。王春红默默地坚持着,坚持到了放学,她的肚子就更疼了,像是有东西往下坠,可又不是拉肚子。
王春红几乎是飘着回家的。到了家,王春红就迫不急待地往床上爬。肚子实在太疼了,王春红想,可能自己要死了。炮仗花死了,她可能也要死了。王春红的泪就流了出来,一颗一颗的,像无处可逃的虫子。
奶奶的手从蚊帐外伸进来,先是摸了摸王春红的额头,又摸了摸王春红的背脊,王春红想挣脱,可挣脱不了,奶奶的力气很大。
过了一会儿,奶奶又过来了,递过来一只盐水瓶,盐水瓶暖乎乎的。奶奶把它放到了王春红的小肚子上,王春红顿时就感到疼痛似乎减轻了一点儿。奶奶又往王春红的头下垫了一只枕头,拿着调羹给王春红喂起了水。王春红不想喝,奶奶低声地喝道,红啊,张嘴。王春红只好张开了嘴,调羹就到她嘴巴里了。王春红一抿,甜得很,原来是红糖水啊。王春红的眼泪又出来了。
鼻子很灵的王辉走过来了,问奶奶,炮仗红生的什么病啊?
她小肚子疼呢。奶奶说。
她为什么小肚子疼?王辉又问。
她屙屎不洗手啊。
奶奶说得很严肃,王辉就上了当,走了,他以为奶奶是在借说王春红说他呢。王春红觉得很好笑,小肚子的疼就渐渐退了下去。
红啊,奶奶说,你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个姑娘家,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你以后的好日子长着呢,千万不要贪凉啊。
王春红没有说话,眼睛晶亮晶亮的,像是完全听进去了,又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
第二天中午,王春红在空白的花坛里种着什么,奶奶看见了,问王春红,红啊,又种什么花了?
牡丹花。王春红调皮地说。
唔,牡丹花。奶奶很平静,似乎很相信王春红的话,其实王春红的手里是紫皮蒜瓣。奶奶自己经常说,七葱八蒜。七月种葱,八月点蒜。现在是农历八月呢,是该往花坛里点蒜瓣了呢。
原刊责编 任智民
【作者简介】庞余亮。1967年生,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已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等,短篇小说《甘蔗》、《锈金匾》分别入选《2002年最佳短篇小说》、《2004年最佳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野猫》获得第三届紫金山文学短篇小说奖,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