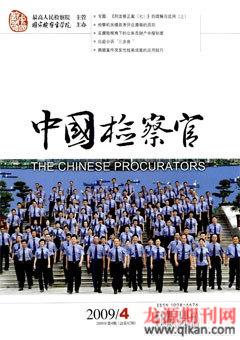我国证明责任分配之现状、问题与制度重构
温长军 陈 娜
证明责任制度作为合理分配控辩双方责任的重要诉讼机制,发端于近代国家限制公共权力滥用,保障公民私权的诉讼理念。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究竟对辩护事由承担何种证明责任,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如何配置控辩双方证明责任,以及其在司法适用中有何种效果和作用等问题。殊值探讨。
一、比较法视野中证明责任制度现状
(一)刑事证明责任概念
我国教科书对证明责任的界定基本一致,即认为证明责任的概念是一个整体,“提出证据”和“加以证实”是一体的责任,并不对二者加以区分,其总的合力方能影响诉讼后果的最终承担。从立法宗旨来看。我国证明责任概念强调对国家公权机关追究犯罪的法律规制,基本同义于控方的指控责任。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概念均为双层次结构。英国采用法定责任(1egal burden)(又称说服责任、终极责任)和证据责任(evidential burden)(即提出证据的责任、推进诉讼的责任)。大陆法系则沿用1883年德国学者古拉色(Julius Glaser)首创的概念,将证明负担(Be—weislast)分为形式的证明负担(Formelle Beweislast)与实质的证明负担(materielle Beweislaat)。法定责任、实质的证明负担的概念与我国的证明责任概念相当:而提出证据的责任、形式上的证明负担是指主张者须证明某种事实,否则在英美法系其主张将不能进入裁判者审理范围,在大陆法系国家则将有被法官忽视的风险。
(二)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除了刑法明文规定,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被告需要举证的例外情形,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这一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模式同样没有涉及对合法辩护事由,被告人是否承担应当证明责任的问题。为了合理分配证明责任,我国学者纷纷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学理建议,但尚未获得立法认可,而地方法院出于现实问题的考虑,也尝试通过“试验立法”,以形成“自下而上”的突破。
两大法系均以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合理界定了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基本框架。基本犯罪构成事实(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属于控方举证的范围,构成要件之外的特定事实(英美法系的合法辩护事由、大陆法系的阻却违法或阻却责任事由),属于辩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对象。美国刑法中合法辩护分为两类(具体内容各州不尽相同)。一类是“可得宽恕”(ex-cuse),如未成年、错误、精神病、被迫行为等,相当于大陆刑法的责任阻却;另一类是“正当理由”(iustifica-tion),如紧急避险、正当防卫、警察圈套(也有人认为此项辩护应列为可得宽恕辩护)等,相当于大陆法系的违法阻却。
(三)证明标准
对于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性质,学界均存在有一些争议,如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还是说服责任。从实务的角度来讲,分歧最终取决于证明标准。我国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法院判决的实体标准,设置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而并没有规定被告人的证明标准。
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具有多层次性,均明确辩方承担较控方低的证明标准。在德国的刑事案件中。辩方只需承担形式的证明负担,符合较低的证明标准——表面可信或初步证明即可。在英美法系,刑事被告人的抗辩适用“优势证据”的标准,美国法院有的采用“可能性”(Probative)一词来进行解释,即“裁定事实的存在,比该事实的不存在,更为可能;”有的则使用“满意”(Satisfaction)一词进行注解。即陪审员内心获得满意即属于“证据优势”。
二、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现实问题
我国刑诉法严格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因此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或有罪的义务,也没有证明责任的承担。这种立法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被告人自证其罪,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但是从司法的层面来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制度设置并非尽如人意。
(一)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价值分析
追溯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对无罪推定原则一直存在误读。早在1935年的Woolming-ton案件中,英国上议院大法官Sankey曾就此提出一段经典的命题:“在整个英国刑事法律中,我们总可以发现一条金线:证明被告人有罪是检控方的责任,但在精神病的辩护以及任何成文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除外。”可见,证明责任制度的合理配置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且从刑事政策和诉讼层面,可以彰显诉讼价值。而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设置基础过于单一,没有考虑到多元的诉讼价值的实现,无法反映重大法益保护和诉讼效益等价值目标。
第一,刑事政策凸现社会秩序保护。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贪污、受贿、贩毒和有组织犯罪的猖獗,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各国政府均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控制上述犯罪,其中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成文法中将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人承担。现代刑事责任的目标就应当完整地定位于“合理而有效的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一定位符合现代刑事责任的发展的历史真实,现代刑事责任正是基于贝卡利亚、菲利、李斯特、安塞尔等人对预防和控制犯罪实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理性关注而发端与发达的。
第二,诉讼效率。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我国检察官对案件有客观全面审查的义务,但是相对而言,由被告人提出合法辩护事由显然更具有证据优势。对于被告不费气力就提出的证据事实,控方需要动用大量的诉讼资源,诉讼效果也未必尽如人意。如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如果被告不说明其超出正常收入的财产具有合法来源,如系海外亲友的赠与,或来源于某些意外之财,控方显然不可能掌握难以知悉的事实。而被告人对这些事实更为了解,如果确实是合法的财产,被告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辩解,诉讼更为高效。
第三,诉讼的相对正义。基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否认司法活动中存在盖然性成分。否则过于苛求将使司法无法运转。诉讼活动就是建立在这样的高度盖然性联系之上,它承认人类生活中的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积累和知识总结。与高度盖然性密切相关的是诉讼合理主义,合理性的核心(即合理之“理”),是经验和逻辑。这里的经验,是指具有普遍性、实在性和可检验性的经验。而逻辑(或称论理)则代表事理、规律和内在关系等。如持有型犯罪中的犯意推定就是建立在经验法则的基础上,被告人需要对不存在主观犯意承担证明责任。
(二)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功能考察
“功能”体现了事物的实际效果和用途。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创设宗旨在于实现一定的现实功能。即通过严格指控和定罪标准,实现“天平倒向弱者”的刑事诉讼理念,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是证明责任制度的司法适用效果显示,司法功能与立法宗旨出现偏离,这一问题从本文引入的杜培武案件审理过程可见一
斑。
第一,证明责任由司法机关完全承担。没有反映证明责任承担的现实状况,不利于被告人积极举证、行使诉讼参与权利。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仅描述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犯罪事实,即积极的构成要件,并不包括证明犯罪事实不存在的合法辩护事由。受实体法理论影响,证明责任的程序创设自然无法突破。司法实践中,当控方证明指控犯罪事实成立时,如果被告人投有积极举证,法官将会默视抗辩事由不存在。对其诉求不予支持。
第二,证明标准的单一规定。造成被告人承担证明标准偏高,无法有效举证,违背“无罪推定”原则本意。由于刑事诉讼法缺乏对被告人证明标准的特殊规定,当法官判断合法辩护事由是否成立时,往往容易抬高证明标准,即认为被告人承担与控方相同的证明标准。由于不具有强势的侦查能力,过高的证明标准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隐形藩篱,使被告人无法打破司法机关的定罪垄断,通过诉讼参与将不利情势予以扭转。
第三,证明责任和辩护权关系错位,形成对辩方责任的认识偏差,最终无法“排除合理怀疑”。降低了刑事指控与定罪证据标准。对于合法辩护事由,审判实践沿袭了古罗马时期“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赋予被告人证明责任的实际承担。不可否认,证明责任意味着额外的举证负担,与一般的辩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刻意区分辩护权与证明责任的做法,混淆了辩方证明责任的本质,进而影响证明标准的实质判断。
三、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体系重构
刑事证明责任构建的核心在于从基本框架上,介入被告人证明责任的制度配置。在我国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是否具有存在的空间,其有无予以实现的现实路径及程序的可操作性都影响到证明责任分配的体系建构。
(一)“卷宗中心主义”模式中的证明责任
目前,我国刑事审判基本以侦查阶段的证据材料为范围。似乎被告人提供证据无从谈起。但是司法者承担调查或者协助调查的义务并不等于承担证明责任,后者是审判层面的用语,其实质意义在于不利后果的承担,司法机关并不承担合法辩护事由的证明责任,因为调查并非为证实本方主张。其次,在普通程序中,控方向法庭提供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照片,如果被告人就遗漏的证据提请法院注意。也是其履行证明责任的一种方式,因为其目的在于通过举证,获得证据证实,获得法院支持,至于证据来源于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不影响法院判断其主张是否成立。此外,辩方还可以另辟蹊径,通过自行调查或向法院申请协助调查。证明自己一方的主张。
(二)中国语境下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现实路径
第一,被告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举证。申请律师代为调查取证、举证是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之一。律师作为被告人辩护权的延伸及利益的当然代表,为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提供了有力帮助。随着今后律师地位的不断提升,其对诉讼过程的影响力将不断加大。
第二,申请法院协助调查也是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重要帮助途径之一。首先,我国法官被赋予案件调查权。其次,目前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偏低,且控辩双方力量存在差距,辩方难以有效取证,有策略的律师往往采取申请法院调查的方法来规避风险。
(三)法院协助调查程序的程序设计
第一,辩方提出合法辩护事由的初步证明。公诉机关的指控以被告人构成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为前提。被告方及其辩护人如果认为存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精神病史或未成年等合法辩护事由,应当向法院提出相应的证据材料。提供初步证据向法院申请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鉴定或重新鉴定。
第二,法官对申请条件的审查。首先,辩方的申请需要附有一定条件;其次,法院需要审查辩方提供的线索是否具体、指向明确。如果辩方提供的线索过于笼统、证据范围过于宽泛,则无法有效查证。
第三,法官的决定权。在申请法院协助调查的情形中,被告人的申请实质上演化为一项程序上的权利。其最终决定权在于法院。法官对被告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后,如果认为其申请符合条件,应当作出同意的决定。如果被告人的申请事由明确,足以使法官产生明显怀疑,为了查清案件事实,法官不应当视而不见,必须进行相关的调查,否则经二审法院查证属实,一审法官将承担事实不清的审判责任。
(四)证明负担的实质判断
在协助调查的情形下,虽然法院可以调查取证、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如果未能查到有力证据或证人不愿作证。最终证明责任仍由被告人承担,这一取证效力同辩护律师协助调查没有本质的区别。
四、证明责任分配配套制度完善
在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大环境下,诉讼进程明显具有不利于被告人的诉讼影响。考虑到我国司法现状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证明责任的重构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完善,在此基础上。证明责任的分配及其功能实现才更具有现实土壤和可行性基础。
(一)理论和学科体系的进一步融合
受大陆法系的影响,我们过于重视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界限,造成两者相当程度的割裂,刑法学在研究犯罪问题时基本上不考虑证据以及与证据紧密联系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刑法研究的一大不足。在此影响下,犯罪构成体系呈封闭的静态结构,只要被告人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即构成犯罪,无法解释被告人行为符合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实体要件,却因犯罪构成之外的事由而不构成犯罪,造成理论无法自恰;另一方面,虽然刑法规定了正当化事由,由于诉讼证明层面无法可循,被告人的主张无法得到支持,使刑法规定的出罪事由成为“无根之木”、“无水之舟”。所以,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重新进行梳理。
(二)证据立法的完善
我国缺乏独立的证据规则和证据立法,刑诉法也仅有证据采信的原则性规定,在判断和采信证据时,司法者依靠习惯定势,造成实践问题,因此证据立法需要科学设置。此外,立法技术需要进一步细化,增强可操作性。为了明确统一尺度,由于我国立法的滞后性和难以穷尽,可以由最高法院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汇编,确立其作为法律渊源的地位,从而指导司法实践中的不同情形。
(三)国内司法环境的改善
自从1996年刑诉法修订以来,无论法学研究还是司法实务都在探索中发展,在诉讼制度的研究和借鉴方面,比较注重新观点、新制度的介绍和引入,努力实现与国际接轨,强调人权保护和文明进步。2007年10月28日新出台的《律师法》,更是对律师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权等作出新的规定,破除了以往要求司法机关许可的限制,赋予律师独立的取证权:律师调查取证的程序更为简易,只需提供资格证明,便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情况;此外,律师享有独立的会见权,不需要批准、不被监视、不受限制。律师法的完善为律师辩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可以预见刑事诉讼法也会作出相应调整,辩护律师生存的大环境也将有所改善,更有利于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维护。
通过证明责任的合理配置,赋予被告人有效参与诉讼的机会,严格办理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能够为司法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施加更多压力,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