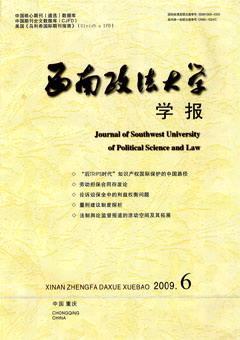论诉讼保全中的利益权衡问题
郭小冬
摘要:保全请求在客观上考验着法庭的审判能力。在快速审理的压力下,法庭必须依据有限的事实迅速裁定。由于这种裁定是在权利义务关系尚未明确甚至诉讼尚未提出之前作出的,因此,容易忽略被申请人的利益,但完全不考虑被申请人的利益是违背法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原则的。保全命令,实质上是法庭在对申请人、被申请人和公共利益等各方利益进行权衡之后做出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诉讼保全;利益;权衡
中图分类号:DF71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6.10
一、诉讼保全中利益权衡的必要性
诉讼保全是一种单方审理程序,这一制度本身是为了保护申请人的利益,避免使其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而设置的;根据迅速性要求,保全程序的构造有别于以处分权主义和辩论权主义为基础而建构的以对审为特征的本案诉讼程序。保全程序中通常不会传唤或者通知被申请人陈述意见,有时甚至还要刻意追求秘密性而避免让被申请人知晓;对申请的审查大多仅依靠申请人的陈述和证据材料来进行。从法律上看,这种单方审理程序是符合正当性要求的,因为这是在紧急状态下做出的应急措施,况且其效力只持续短暂的期间。但是,保全措施毕竟是在权利义务关系尚未明确甚至是诉讼尚未提出之前采取的,申请人诉称的受到侵犯的实体权利是否存在或者申请人是否会提起诉讼以及在诉讼中是否会胜诉都是未知的,这样就有可能给被申请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尤其是对行为的保全,保全措施的适用很多时候是在阻断侵害的同时,也使得实体权利提前实现,导致“请求的本案化”和“功能的本案化”。因此,为了使保全更加具有正当性,在审理过程中就不能一味地追求对申请人利益的保护,还需要适当地考虑被申请人的利益,甚至是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是否准予保全,实质是法官在对诸多利益进行综合考量之后基于自由裁量权而作出的一种利益选择。
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对利益的争夺形成了利益冲突,“当一种利益与另一种利益相互冲突又不能使两者同时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产生了应当如何安排它们的秩序与确定它们的重要性的问题。在对这种利益的先后次序进行安排时,人们必须作出一些价值判断即‘利益估价问题。”既然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估价”、“选择”也是必然的,由此而形成的相关理论,与两大法系的法学传统相适应,分别就有了大陆法系的“利益衡量”理论和英美法系的“衡平”观念。
二、对“利益衡量”的考察
(一)我国对利益衡量理论的认识
在我国当下的法学研究成果中,“利益衡量”这个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但是,对既有的研究成果稍加分析之后会发现,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了两种利益衡量的理论:德国和日本的理论。由此而形成了3种局面:第一,仅承认德国的理论。“利益衡量论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其思想源于德国的自由法学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益法学”;第二,仅承认日本的理论。“利益衡量理论是1960年代由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提出后,在日本民法解释学理论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影响着民法解释理论的发展和民事审判实务的开展”;第三,两种理论的融合。在此认识之下,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存在着3种不同的看法。(1)将二者视为同一理论而共用于对同一问题的阐述:“在客观形态上,法官对衡量尺度的把握一般是在现有法律文本的框架内进行”,其标准“就是一定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或者说一定社会当中对一般公众而言具有较为重要意义的价值选择。”在这段表述中,前一部分的表述实质上是德国理论的内容,后一部分则为日本理论中的“一般人标准”;(2)二者之间具有“源与流”的关系:“利益衡量论作为一种法解释的方法论渊源于德意志的自由法学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利益法学,并受到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的强烈影响。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教授与星野英一教授将其体系化”;(3)尽管同称为利益衡量,但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日本的利益衡量论直接渊源于自由法学,并且直接导人了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却没有德意志利益法学的痕迹。”上述3种认识孰是孰非?目前没有定论。为了准确的运用利益衡量理论对笔者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我们有必要对德、日利益衡量的核心理论进行比较。
(二)溯本清源——两种不同的利益衡量理论
德国的利益衡量理论是德国“利益法学”的核心内容。以赫克为代表的利益法学家认为,利益是法律产生的根源,“正是利益才造成了法律规范的产生,因为利益造就了‘应该的概念。在“利益法学”看来,法律命令源于各种利益的冲突。”因此,对各种利益进行衡量、取舍,是制定法律规则的基本前提。“利益法学”作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更关注法律规则运用的过程中、特别是法官处理案件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和解决问题。“利益法学”是为适应法律的实际目的而创设的一种方法,其目标是发现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但是,“利益法学”并不认为法官有理由自由的创设新的法律秩序。他们的工作是在既定的法律秩序的范围内,使各种利益协调起来。具体来说,“利益法学”从两个着眼点出发关注法官解决案件过程中的利益处理问题。第一个着眼点是,在制度存在的背景下,法官必然要受现行法律的约束。法官必然要协调各种利益,并且循着立法者的路子来平衡各种利益冲突。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使法官面临着各种利益的冲突,但是法官对人们利益冲突所做的判决是要受立法者在既定法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人们利益冲突所做出的评价的限制。“利益法学”的第二个着眼点在于,法律是不健全的,甚至在处理人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冲突时还表现出相当的矛盾性。作为立法者,他们对法律的这种不健全性可谓耳熟能详,因此,他们并不希望法官仅仅在字面上遵循法律的规定,更重要的是,法官应该熟谙法律中所包含的利益,并且在处理案件时,尽量使自己的利益判断能够与立法者在法律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保持一致。法官不仅仅在法律规则的框架内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判断,而且还应该在法律规则出现空白的地方构建新的法律规则,以弥补法律规则的不足。换言之,法官不仅应当运用一些法律命令,而且它还必须保护那些立法者认为值得保护的总体利益。
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被公认为是日本利益衡量理论的共同倡导者。该理论自1960年代提出后,一直在日本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是:强调决定裁判的实质因素不是法律的构成,而是法律之外的、对案件事实中诸冲突利益的比较衡量后所得出的决断。加藤指出:“在最初的裁判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排除既存的法规,在一个全然白纸状态下,考虑这个事件的应然解决。”近年来,日本学界提出的把“事件平息的优良”甚至是“现实的合理性”当作价值判断的形式标准。至于在这种场合下的利益衡量或者价值判断的立场,他们都主张不
是法律专家的立场,而是普通人的立场,而且不能违背常识。具体操作是,先在一种与现行法规相隔离的状态下,以普通人的立场,依据超越法律的标准,对案件事实中诸冲突利益进行比较衡量,得出一个初步的决断,然后带着这个决断回到现行法律法规中,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寻找现行法律上的依据,以增加自己决断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用现行的法律法规来对自己先行得到的决断进行检测,在两者之间不断地试错,最终得出尽可能合理、合法的判决。
(三)与本论文契合的理论
无论是德国的理论还是日本的理论,二者都发端于对概念法学的批判。批判的焦点都是对概念法学所主张的法律的自足性的怀疑,这个自足不仅包括法律自身的自足,而且还包括法律对社会冲突解决的自足。法律不可避免会存在漏洞,单靠法律是无法解决所有社会冲突的,因为法律无法解决其自身的问题,这是他们批判之后得出的共同的结论。既然法律存在漏洞,同时又必须要寻求法律的解决,就需要寻找法律规定之外的解决方案。作为解决方案,他们都主张把视角从法律转向纠纷本身,通过发掘纠纷背后所隐含的利益冲突,指出对纠纷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如何调和案件中相互冲突的利益,都强调利益衡量在裁判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但是,在论及应如何进行利益衡量的标准问题的时候,两者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正是这种分歧,才使它们变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
“利益法学”所主张的利益衡量标准是通过探求立法者的意图来确定保护的对象,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想要保护的那一方利益;只有立法者想要保护的利益才是法庭最终应该保护的利益。法庭必须通过已有的法律规定来探求立法者的意图,最后根据立法者的意图而不是法庭自己所理解的公平正义做出判断。“利益法学”的学者认为,尽管在需要做出衡量的具体问题上,立法者并没有明确他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但是,通过现有法律的规定以及参与立法程序之人的言论,仍然可以做出这种推断,因为“立法者如何评价不同的利益、需求,其赋予何者优先地位,凡此种种都落实在他的规定中”。这样看来,“利益法学”所倡导的利益衡量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法解释学中的目的解释方法。但日本学者所主张的利益衡量标准恰恰与此相反。这种利益衡量是法官主动思维的结果。法官在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时候,不受既定法律的束缚,反对从既有的法律中揣摩立法者的意图,或者说从根本上排斥立法者的意图。它是法律之外或者超越法律的标准,是根据更为抽象的公平和正义的观念做出裁决的标准,它更加强调发生冲突的两种利益之间的比较,因而是司法者所做出的权衡,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
尽管立法者在制定法律之初也是根据公平正义的原理做出规定的,但是法律的制定所考虑的必然是一般情形下的公平和正义,因此,作为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所能够呈现的也只能是立法者对于一般情形下的公平和正义的理解。而作为法官自由裁量依据的公平和正义则是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联系的,因而是具体的公平和正义。这样,在遇有不同于一般情形的特殊案件的时候,根据两种利益衡量理论就有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对行为的保全而言,通常的情形是申请人的利益受到了或可能受到侵害,因此,法律的一般规定必定是要旗帜鲜明地保护申请人的利益。这种立法意图将会指导法庭在任何场合下均会准予保全的请求。但是,这样的判断有时也许并不真正符合一般人所理解的公平和正义的观念。例如,被申请人因为疏忽而在申请人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建筑物,申请人向法庭申请要求被申请人将该建筑物从他的土地上移除。法庭经过评估得知,被申请人移除该项建筑物需要花费1500美元,而申请人的土地价值总共价值15美元。对于此案例,如果依照探求立法者意图的标准进行判断,那么,必然是无视1500美元和15美元的差别而做出命令被申请人移除建筑物的禁令,因为法庭必须要维护法所保护的申请人利益。但如果依照日本的利益衡量理论,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形进行考虑,就会是法官会在1500美元和15美元之间进行衡量,那么,最后的结果是法庭将拒绝移除建筑物的禁令申请而改用其它的诸如损害赔偿之类的替代性救济方式。
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德国的利益衡量理论究其实质不过是法解释学的一种方法。所谓的衡量,事实上是立法者的行为,因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对可能发生冲突的利益的权衡,司法者所能做的,只是将这种衡量的结果揭示出来而已。而日本的利益衡量理论,是司法者在对现实发生的相互冲突的两种利益进行比较后做出判断,这种利益衡量方式能够真正体现出衡量、权衡的本意,因而更符合笔者所说的诉讼保全制度中的利益权衡。
三、英美法系的衡平观念
在英国法律发展史上,衡平法是为了弥补普通法救济的不足而出现的。“衡平法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针对普通法上救济范围的有限性,引进范围广泛的衡平法救济。”我们这里所称的普通法,是专指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至衡平法兴起之前,由英国皇室在全国推行的、统一的、以判例法形式存在的普通法院审理案件时所适用的法律。这个含义上的普通法,是与衡平法、制定法相对应的概念,它与我们现代作为判例法统称的普通法③的含义并不相同。
由于衡平法初创时期,审理案件的大法官几乎全部由代表了英国最高文化水准的教士担任④,因此,大法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不像普通法院的法官那样注重诉讼的形式,而是更多基于道德和良心方面的考虑,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平,是否符合正义。埃思米尔大法官评“牛津伯爵案”时说道:“存在一个大法官法院的原因是因为人的行为形式各异,不可穷尽,一般的法律不可能恰如其分地符合每一个行为以及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况。司法官的职责在于唤醒人对任何性质的欺诈、违反信托、错误和压榨的良知,并且缓解和修正法律的极端性。”而且,人们向由教士担任的大法官申请救济,也可以是看做对身为基督徒的被申请人所进行的良心上的控诉:“但是大法官能做什么呢?他既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达到绝对公平,也没有什么特殊方法了解人们的思想……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启发当事人的良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良心才能辨别事情的对错。……衡平法之所以对人发挥作用,是因为只有人才有良心。”因此,“在所有的场合,为大法官的干预进行辩解的理由是良心的需要。来自不完善的法的解决纠纷办法使良心受到冲击。人家对之起诉的那个人利用法的不健全,为所欲为,是违反良心的。”也正因为此,大法官审理案件所创设出来的规则才被称为“衡平法”或者“公平法”,而衡平法院亦被称为“良心法院”。1875年英国的司法改革将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合并,所有的法院都可以同时行使两种管辖权,适用英国法的全部规则,而不论该规则是在普通法还是衡平法发展起来的。与英国衡平法的发展相一致,美国对普通法与衡平法之间的关系同样
是客观的债权人的利益。但是,相当性原则要求考虑利益平衡:在本案主诉讼全面查明案情之前进行临时性调整,只有在给债权人带来的利不致与债务人的不利不相当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这种调整只有并不损害债务人的重大利益时才属‘必要。”在日本,利益衡量理论在定暂时状态的假处分制度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定暂时状态的假处分之必要性比较单纯,即避免债权人遭受不利益。然而,判断是否允许此类假处分时,必须衡量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利益来决定。如果没有假处分将使债权人遭受的不利益大于有假处分时债务人遭受的不利益,则应允许该假处分;如果允许假处分将使债务人遭受的不利益大于债权人获得的利益,则不应允许此类假处分。”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判例则是在对“重大或显著的损害”进行认定的时候,通过一种比较迂回的语言显示出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所做的考量:“如债务人就声请假处分所欲避免之损害远大于债权人因假处分所受之损害者,即属因避免重大或显著之损害而有定暂时状态之必要,债务人非不得声请定暂时状态之假处分。”
五、“利益权衡”在我国诉讼保全制度中的阙如
长期以来,我国的诉讼保全仅有财产保全一种形式。为了保障裁定得以及时、有效地执行,《民事诉讼法》对财产的保全设置了单方速裁的审理程序。这种程序本身不需要传唤被申请人参加审理,法庭作出裁决的时候,也不需要太多地考虑被申请人的利益。因为只要申请人提供了相当的担保,那么,保全措施即使给被申请人造成了损失,也可以通过担保的财产获得补偿,因此,在保全的及时性与对被申请人利益的保护之间,立法选择了前者。对于现实中存在的对行为进行保全的需要,实务部门可通过“需要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立即制止某项行为”的案件可以先予执行的司法解释来实现对正在进行的加害行为的制止。江伟教授曾于1994年发表文章提出应当将对行为的保全纳入到保全体系中来。之后,我国理论界开始了对该问题的关注。1999年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了强制令制度,强制被申请人实施或禁止实施某项行为。我国2000年和2001年完成了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的修改,增加了对知识产权的诉前司法保护。这两项制度被认为是我国现行关于对行为进行保全的立法规定。
对行为进行保全的需求尽管在我国突出地表现在上述两领域内,但不表明这种需求仅仅存在于这些领域。在其它类型的案件中,尤其是继续性法律关系的案件中同样有着广泛的适用基础。例如,对子女监护权的争执、侵犯人身权、相邻关系、禁止公司董事长行使职务、劳动关系、演艺合同等不涉及财产占有侵害方面的纠纷,都存在申请法院禁止或强制某种非财产处分行为的需求。因此,完整的诉讼保全体制既包括以财产为对象的财产保全,也包括以行为为对象的保全,这在我国理论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就后者而言,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准确的概念。
这样的立法及认识使得诉讼保全中的利益权衡问题得以显现。对行为的保全不同于财产保全的最为重要之处,除了给被申请人可能造成损害之外,就是保全措施一旦错误,损害的后果通常无法回复。因此,法院在审理申请人就行为提出的保全申请时,就没有理由不去考虑被申请人的利益。但我国的上述两项规定并没有体现出对被申请人利益的考量。《专利法》第61条规定专利权人申请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的请求时,需满足“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条件。其中对“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要求,与申请海事强制令的条件相比,在对被申请人的利益保护方面已经有所改善,因为后者是只需要达到“将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即可。但仅对申请人单方利益进行考量就作出裁定的规定,与上述国家在平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利益之后才作出裁决的做法仍然有所差距。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准予假处分的有效条件是为避免显著之损害或防急迫强暴或其它情事,而“所谓避免显著之损害,就假处分所受债务人之损害或不利益,与债权人受侵害所蒙受之不利益两者相比较,后者远较前者之损害不利益为大之情形,即属有显著之损害。”
六、“利益权衡”在保全诉讼中的体现
综观各有关利益权衡的立法和实践,总有一些共同的因素被不同的法庭反复地进行考量。我们可以从中探求一些普遍性的因素,以资在完善我国保全诉讼制度时就利益权衡原则的贯彻方面加以借鉴。利益需要被权衡的前提是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诉讼保全制度中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一般存在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申请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当然,前一种冲突是主要的。因此,在裁定是否准予保全措施的时候,法庭通常应该考虑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
1.如果不准予保全,申请人的利益是否会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
既然诉讼保全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裁定是否准予保全的时候,申请人的利益当然是首要被考虑的因素。那么,被申请人的行为对申请人利益的危害达到何种程度,法庭才可能准予保全申请呢?如果以《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将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为要件,很有可能使判断标准失之宽泛,其结果是申请人轻易就能获取保全的裁定,动辄就通过保全措施来限制被申请人的行为,不仅会影响诉讼的进程,也增加了诉讼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会对被申请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有违法所追求的公平与公正。综观域外之立法规定,尽管表述各异,但实质内容基本相同,除要求“侵害的急迫性”之外,还要求“损害的难以弥补性”。这个标准也正是我国财产保全和申请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裁决要件之一。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是“急迫的侵害”和“难以弥补的损害”?“急迫的侵害”有可能是现实的、正在发生的侵害,也有可能是尚未发生但很有可能发生的侵害。不过,尚未发生的侵害很容易被法庭视为“时机不成熟”而驳回申请。但仅有“急迫的侵害”还不足以使法庭作出保全裁定,必须得考虑“损害是否难以弥补”。
就后者而言,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解释是:“具体而言,系指若使债权人继续忍受到本案判决时为止,其所受不利益或痛苦显然太酷之情形而言。”例如,债务人到处发出损害债权人名誉之印刷品,债务人建筑工作物以妨害邻地所有人行使权利。司法实务界倾向于以“债权人所受之损害是否为不能以金钱补偿”为判断标准。如果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失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通常就可以认为损失是难以弥补的。由此而造成了对于侵犯专利权的案件能否构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争论。因为对专利权造成的损害,通常是可以用金钱计算的,尽管有时候这个数额非常巨大。“难以弥补的损害”这个标准在英美法系同样适用。但更多的时候,英美法系的学者和法官认为,试图用一个精确的方法来定义“难以弥补的损害”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来构筑它的形状。
2.如果准予保全措施,被申请人将会遭受怎
样的损害。
对被申请人利益的考量是衡平观念在保全诉讼中的主要体现。这种衡平经常发生在这样的场合:尽管申请人所遭受的损害对他来说是严重的和不可弥补的,但实际上远远少于被申请人为了遵守对他的裁定而遭受的损害。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庭在这一阶段处理被申请人的利益时会犹豫不决。为了使裁定更加有效,法庭必须在案件进入法院后一段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作出决定。在这种快速审理的压力下,法庭很有可能不会通知被申请人参与程序、陈述意见,即使是在对行为进行的保全中,通常也只是留给被申请人一个非常短的答辩期。这对法庭是一种考验。它要求法庭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他必须根据一些有限的事实,在匆忙的分析法律后去签署一项可能会给一方当事人带来严重后果的命令。由于这些原因,法庭在考虑是否准予保全措施的时候,就应当平衡考虑对双方当事人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在一个尚未确定的案件中,这些因素可能和案件的事实有关,也可能和法律有关,还可能和双方都有关。”
3.对公共利益的影响也是法庭需要考虑的内容,因为公共利益最终会成为有利于当事人一方的因素而对法官的判断形成影响。以美国的诉讼实践为考察对象。涉及公共利益权衡的案件通常发生在环境污染、言论自由等领域。在环境污染领域里面,如果排放污染的企业对公众是必要的,那么这种公共利益的因素就会成为对被申请人有利的因素。在有关言论自由的领域,公共利益的因素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有时候,即使申请人受到了伤害,但法庭也不愿通过禁令限制言论自由。法庭坚持这一观点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即维持自由的社会和公开的交流,并不仅仅是保护诉讼当事人个人。通常,对于申请人来说,获得禁令来限制书籍、报纸或其它交流媒体的出版发行是不可能的。这些媒体上有公众感兴趣的信息、教育甚至娱乐目的。在Krebiozen Research Foundations v.Beacon Press案件中,申请人想要禁止一本书的出版,他声称书中包含了虚假和荒谬的陈述,因为作者对申请人为了治疗癌症而新开发的麻醉药进行了诋毁。但是,法庭否定了禁令申请。法庭认为关于事实真相的揭示对于公共利益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解真相的最有办的方法是允许充分、自由的讨论这一事件。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考虑,法庭更喜欢让申请人试试普通法上的金钱赔偿。
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并不总是使被申请人获利,有时对申请人也会有帮助,它可以促使法庭签署在其它情况下不会签署的禁令。在Harris Dran-ley Coal&Land Co.v.Chesapeake&O.Ry.Co.案件中,铁路公司为了避免引起公路上滑坡的危险,要求法院下令禁止一些矿主在公路上挖坑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法庭可以因为这种行为只是一种可能会导致滑坡的妨害行为而否定禁令申请。然而,法庭授予了禁令。法庭不是基于对申请人铁路公司利益的考虑,而是从乘坐火车的公众成员的利益来看待这个问题。法庭认为,一般说来,这样的灾难只在各种环境因素综合起来的情况才会发生,而这些因素同时发生的机率是极小的,所以,法庭本应该驳回申请人的禁令申请。但是,根据普通的经验我们知道,灾难经常发生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间和预想不到的地方。法庭不能够拿人民的生命做赌注,不管胜败的可能性有多大。因为生命一旦失去,是没有任何救济可言的。因此,以衡平的观念来看,仅对申请人提供损害赔偿的救济就是不充分的,因此而批准了禁令的申请。
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需要就被控行为是否攸关公共利益作出判断。在一些案件中,诉讼看上去似乎是为了个人利益提起的,但实际上可以直接导致公共政策的实行。例如,在Po~er v.Warner Holding Co.案件中的情形;而在另一些案件中,尽管法庭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私人诉讼执行广泛的公共政策,但是法庭也会因为诉讼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而权衡原被告双方的利益。例如Northern Indiana Public Service co.V.w.J.&M.s.Vesey案件。申请人禁止被申请人天然气工厂的经营,因为工厂制造的气体、气味、氨水和烟雾破坏了的附近花房。但法庭最终以天然气工厂的经营是具有公共利益为理由驳回了禁令。
第二,如果准予对被申请人的行为加以制止,那么可接受的替代方式是否充分,公众是否会因之感觉不便。在Hybritech Inc.v.Activated Labo.ratories案件中,法庭认为相对人所研发的产品能够促进公共健康,因此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理由拒绝核发禁令。在Sehenreich et a1.v.Town ofFairbanks,et al.案件中,被申请人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市政当局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决定关闭Weeks Field机场,相应地,原附属于Weeks Field机场的飞行员培训学校、控制塔等服务设施停止使用。受到该决定影响的公民向法庭申请中间禁令和最后禁令,希望法庭能够阻止该项决定的生效和执行。申请人方提出的理由就是该机场属于公共设施,市政当局的决定违反了公共利益,是非法的行为。但是,被申请人方提出了一系列的理由来反对申请人。例如,政府的财政无力负担该机场营运所需要的支出;就在两英里之外的地方有一个修建的更好更安全的大型机场可以使用,而Weeks Field机场只能起落小型飞机;新的学校已经在Weeks Field机场跑道附近落成,如果继续使用该机场,所威胁的不仅仅是使用机场的人的安全,也会影响到学校的学生和附近的居民;从公共利益和一般公众的需要而言,进一步使用该机场是不必要的。法庭最后采纳了被申请人的抗辩理由,拒绝颁发中间禁令。申请人向第九巡回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庭认为,关闭Weeks Field机场不会危害公共利益,因此肯定了地方法院驳回中间禁令申请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