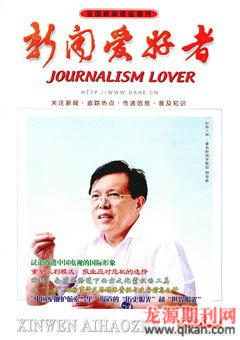八大山人和“洋八大”的形而上
马 更
摘要:古今中外的艺术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人们的审美取向也有所不同,但是当我们去除繁杂的枝节后却发现,在接近人性的歌颂中却有着相似的和弦。然而在20世纪的意大利,有位画家的艺术精神气质却酷似中国的八大山人,人们将其戏称为“洋八大”,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艺术形式的画家,在作品中渗透着相似的气质。在他们视野里的事物早已脱去尘俗的繁杂,变得朴素、纯净、本源而简约。他们对绘画的热爱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们将绘画作为自己的信仰,虔诚地将每幅画当作他们一次庄严的顶礼膜拜。
关键词:八大山人莫兰迪意境精神
艺术作品创作的灵感和其精神价值都来自艺术家的生活,作品里面折射出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技艺修养,更有生命历程的痕迹与世事内化于精神的升华。生命经历带给了艺术家无尽的情感体验,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艺术精神价值。生命经历的丰厚宽广净化了人的心灵,洗去了凡俗的尘埃,画家从中得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精神世界、一种超然的世界观,再回归到现实生活看事物就有了形象以外、与画家精神特质一致的特征,从而画中的瓜果、器皿、静物也成为“活物”。画家从精神层面赋予对象以生命,赋予作品个性化的精神气质,从而才有了艺术家哲学理念上的一元论、天人合一、物我不二、画如其人的说法,而这些正是艺术家生活体验的参悟。
“道”与“器”
“形而上”出自《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是不同的。形而上是指思维的和宏观的范畴。形而上学则是指认识事物的方式,走到了极端、僵化的程度。形而上的东西就是指道,既是指哲学方法,又是指思维活动。形而下则是指具体的、可以捉摸到的东西或器物。形而上的抽象,形而下的具体;形而上比较虚,形而下比较实。在绘画的理论上我们可以领会其多层的意义,其道,可指精神内涵、意境、气韵;其器,可指绘画的技法、构图用笔、施色用墨。或者是上品之画谓之道,下品之画谓之器,尊画理之画得道,违画理之画成器。
从某些方面看中国文人画是重道而轻器的,西洋画是重器而轻道的。中国文人画尚写意,草草几笔却是整个画家哲学理念、道德经纶、人格精神的真实写照,画家在画中倾其所有的是时间积累、内心参悟的从内而外的“熟外熟”的综合修养。艺术作品的灵感和精神价值都来自艺术家的艺术修养,这些艺术修养大多数是在画外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积累。给作品赋予精神层面的生命价值,便是艺术家移情于物、移情于画的转换。
处境与画境
“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是清“四僧”之一石涛大师对八大山人艺术的赞誉,评价之高,世所罕见。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仍然用石涛的这两句话来概括,同样是那样的贴切精当、恰到好处。八大山人(1626—1705)是清代著名画家,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八大山人是他的名号之一,身为明朝皇族江宁献王朱权的第九世孙。八大山人天赋很高,年幼又受祖辈的艺术教养,8岁能写诗,11岁能画青绿山水,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然而在他19岁时,清兵入关,他从此遭受到国亡家破之痛,忧伤悲愤无处发泄,由口吃而佯装作哑;后又隐姓埋名,削发为僧,过了13年的僧侣生活。还俗后不久,在江西南昌修建青云谱道院,韬光养晦,自59岁,直至80岁去世,以前的字均弃而不用,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前二字又似“哭”字,又似“笑”字,而后二字则类似“之”字,哭之笑之即哭笑不得之意,作为他那隐痛的寄语,他有诗“无聊笑哭漫流传”之句,以表达故国沦亡,哭笑不得的心情,他这个号一直用到去世。
八大山人一生主要精力是从事绘画,由于时代特点和身世遭遇,他抱着对清王朝誓不妥协的态度,把满腔悲愤发泄于书画之中,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所以画中出现的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甚至禽鸟一足着地以示与清廷势不两立,眼珠向上以状白眼向青天。画上还有很多隐晦艰涩的诗句跋语,表示对清廷极端的仇恨和蔑视,充满倔强之气。他一生对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这样的形象,正是他自我心态的写照。即便是山水画,也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怀旧之情溢于纸素,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八大山人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八大山人的笔墨特点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秀,清逸横生,不论大幅或小品,都有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他性情孤傲倔强,行为狂怪,以诗书画发泄其悲愤抑郁之情,他一生清苦,命运多舛,这形成了天才艺术家必须的人生苦难,更造就了其作品独特的艺术价值。
人类的文化根据地域、时代、习俗不同有着千差万别,但是回归到人性的层面上,却无太大差异。在艺术的发展上也是一样,古今中外的艺术表现形式都千差万别,人们的审美取向也有所不同,但是当我们去除繁杂的枝节后却发现,在接近人性的歌颂中却有着相似的和弦。世界各地的史前艺术形态相仿,比如岩洞里面的画以及其内容的一致性是如此的惊人;西方古典油画的审美特征和中国工笔画的惊人相似;然而在20世纪的意大利有位画家的艺术精神气质却酷似中国的八大山人。人们戏称为“洋八大”的画家——乔治·莫兰迪,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艺术形式的画家,在作品中却渗透着相似的气质。
巴尔蒂斯说:“莫兰迪无疑是最接近中国绘画的欧洲画家了。按照道济的说法,莫兰迪也是‘有笔有墨的,他把笔墨俭省到极点!他的绘画别有境界,在观念上同中国艺术一致。他不满足表现看到的世界。而是‘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感情。”乔治·莫兰迪(1890—1964)生于意大利波洛尼亚,是意大利著名的版画家、油画家。
莫兰迪选择极其有限而简单的生活用具,以杯子、盘子、瓶子、盒子、罐子以及普通的生活场景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把瓶子置入极其单纯的绘画风格之中,以单纯、简洁的方式营造最和谐的气氛,平中见奇,以小见大。莫兰迪总在画同样的东西,但是每次又画得不一样,每一幅都是新的。如果将他的画从中国的书法角度来看,景物形象就是笔墨点画,其余空间便是“余白”,其中不仅讲究用笔和墨色之间的呼应变化,而且讲究“布白”,已经上升到“计白当黑”的境界,他的心中不再是现实中的客观逻辑,而是两者在时空中的艺术构成关系。在莫兰迪的色彩世界里,我们能感受到脱尽火气的温和高雅精致的静谧,他有着极高的色彩修养,这些孤立看起来毫无光彩的颜色在他的安排下却透露出娴雅浪漫的恬淡安静。他是静观默想型的艺术家,虽然身处蜗居但是却创造了虚无而幽邃的无限空间,每幅作品都是他参禅的顿悟,以一概万,小中见大。莫兰迪的画关注的是一些细小的题材,反映的却是整个宇宙的状态。
西方评论界认为:“他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陈腐的一种表现形式带来了新的生命力:绘画,不是用来做装饰的,而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公开宣言。”艺术作品是艺术家自己人生最好的注解。莫兰迪一生孤寂、平凡,厮守着生活中的坛坛罐罐,用静物演绎艺术的真谛。诚如他自己所说:“我本质上只是那种画静物的画家,只不过传出一点宁静和隐秘的气息而已。”
形而之上
自古就有“真景易写而画意难工”的说法,意者心音,是画家的情绪和精神气质的反映,而意境则是这种精神气质迹化笔下的形象所形成的,是画家情绪借助笔墨宣泄的过程,是“受之于眼,游之于心”的主观感悟借助对象幻化为画面的形象,是画家物我冥会的结果。八大山人和莫兰迪的作品带给我们空灵和静谧的境界是对人生命本体的一种共鸣。“画如其人”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亦如此,艺理相谐,殊途同归,莫兰迪也不例外。由于画家的禀赋、学养、师承、思想、品位、气质、人生经历的不同,画面的意境多有明显的不同,而他们的作品在意境的营造上都秉承了:境虽臆造而能合自然之理,画虽简而境深的道理。简约的画面中充分表现出画家深厚的功力和修养,在画面上呈现出非凡的视觉张力和精神魅力。
从时间和地域上可以说他们一古一今、一中一外,但是他们在绘画思想和审美情趣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的相似不是巧合,都源于发自人性根深蒂固的呼唤。他们是在画布上画出诗歌的诗人,在他们视野里的事物早已脱去尘俗的繁杂,变得朴素、纯净、本源而简约。他们的特殊经历使他们将绘画作为唯一的精神寄托,他们与自己的画交流谈心,将自己生命中的所有热情奉献给了自己的作品。他们对绘画的热爱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们将绘画作为自己的信仰,虔诚地将每幅画作为他们一次庄严的顶礼膜拜。虽然两位画家都不能与我们进行交流了,但是每次观赏他们的作品都如同接受了一次心灵上的洗礼,因为我们又一次接近了人性的本源——真实、向善、美妙,带给人直接而亲切的心灵对话。
——评朱良志先生《八大山人研究》(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