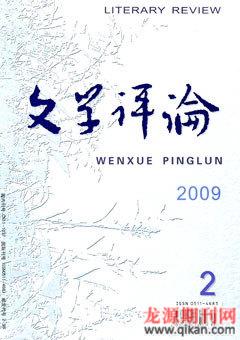评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
张 兵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亦有一时代之研究方式。宋之前,资料传世相对稀少,点与点之间往往缺少可以联结的可信材料,要靠研究者的眼光、学识和想像力来弥补,宋之后,资料传世渐夥,尤其是清代,大量的文稿、日记和书信尚保存于世,为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第一手材料,作家事迹的探讨甚至可以具体到某日某时,某种程度上,相对客观地复原某段历史场景并非奢望,研究者在注重宏大叙事的同时,更应该将这种宏大叙事建构在对文献深挖细掘的基础上,以期触摸到历史的深层脉动,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真正的史的意义。正如胡明先生所说:“深井一口一口地挖必有史的意义与功德,水脉连缀一片必有江和海的浩荡景观。”(《文学所的五十年和我的二十五年》,《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张剑的《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以下简称《长编》)就是这样一部撰著。
一采铜于山的精神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鄙亭,又号紫泉、弭叟,贵州独山人。他是晚清大儒、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以及宋诗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但由于生前所刊著作较少,与自身行历、志趣关系密切的诗文著作只刊刻《鄙亭诗钞》六卷。卒后其子莫绳孙又陆续刻成《鄙亭遗诗》八卷和《鄙亭遗文》八卷。但他传世的各类稿钞本多达百种,特别是十几册日记和数百封书信,收藏地分散和隐秘,如日记即分别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家图书馆、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使研究者难以对其有全面把握。《莫友芝年谱长编》则以洋洋百余万字的篇幅,编入存世的所有《鄙亭日记》及二百余封鄙亭书信,绝大多数系首次面世;并竭泽而渔地吸收了海内外莫友芝刊本、稿本和钞本文献,用心勤苦,令人敬佩。由于张剑挖掘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将之整理公诸于众,莫氏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发现和推进。
一般认为莫友芝首次入京会试时间在道光十六年,但从道光十一年莫友芝中举人至道光十六年间,进士科考试举行了三次(道光十二年恩科、十三年、十五年),很难解释莫友芝为何皆未参加。看了《长编》始知,道光十二年友芝新婚燕尔,故未赴试,道光十三年癸已的会试则是参加了的,《长编》引《鄙亭日记》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为证:“益三,辛卯同年,道光癸巳正月,自扬州同赴春官。”如果没有《长编》将《鄙亭日记》整理出来,我们就无法知道莫友芝首次会试的正确时间。
莫友芝的《韵学源流》是我国第一部简明扼要的音韵学史,影响极大,但因其多钞录《四库全书总目》而被人疑非莫氏所著,张剑曾专门写有《<韵学源流>作者考实》(《文献》2007年第3期)一文考定作者即莫友芝,在《长编》中,张剑没有简单重复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又在南京图书馆藏钞本《鄙亭遗文》中,找到了汪士铎致莫绳孙原信:“《韵学》虽钞自《序》文,而国朝诸先生论定者,实皆不刊之语,其搜罗宏富,得未曾有。弟意可变细字刻之,半页十二行,行廿五字,与尊公诗文集别式,亦一道也。……《韵书》错字多,皆就本书改定,祈恕狂瞽。”又找到了台湾所藏莫绳孙光绪二十二年致黎聪函:“先君遗著《影山词》及《韵学源流》、《壬子以前诗抄》等均已抄成清册,《书画经眼录》尚待编次另抄……”从而为这一问题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其他如同治年间金陵书局补刻毕沅《续资治通鉴》,苏州书局补刻胡氏《通鉴》,都是中国近代刻书史上盛事;莫友芝同治四年奉曾国藩札委,往扬州、镇江一带搜求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残本;同治五年受李鸿章委托,游历江南诸郡,续完采访两阁四库全书公干,兼查各儒学各书院官书兵后留存情况,也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对详细情况多语焉不详,得于耳食之谈。《长编》则详引日记、书信,使这一段历史较为鲜活地浮现出来。
清代顾炎武《又与人书十》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判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顾炎武《日知录》自序)《长编》的编纂,无疑发扬的是古人“采铜于山”的精神。
二精审的提炼考辨
《长编》不是简单和漫无目的的资料堆砌,其选材、系年及相关问题的考辨都体现出《长编》撰者不凡的学识才力。
莫友芝传世诗歌达一千五百余首,《长编》不可能也无必要将之全部罗列出来,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选材提炼的问题。《长编》不欲徒充篇幅,“重点选录那些能够反映传主性情才识和重要事迹的作品”(《长编·凡例》)。如友芝早年近四百首诗作俱收入钞本《影山草堂学吟稿》中,道光十六年秋他陆续作成《秋问杂兴》诗十九首,寄与六弟庭芝,并题诗于后,吐露心曲。《长编》于此组诗并未征引,只评价说:“《秋间杂兴》时露峥嵘不平之气,颇得汉魏五古风神。《汇(杂兴>诸作寄示芷升,复题其后》有句云:‘世心戡欲尽,傲气屈逾悍。友芝个性从中可见一斑。”(见道光十六年谱)但对于((鄙亭诗钞》的压卷作《甲辰生日,伯茎兄来遵义省先墓,述呈,兼示诸弟侄六首》,因其反映出友芝性情及家庭伦理之爱,并“表现出友芝诗歌已由刻凿渐入朴拙之境”(道光二十四年谱)而予以全录。这样就恰当地掌握了材料繁简的平衡关系。
在如何选取莫文的问题上,张剑同样秉承这一原则,大部分莫文都未征引或只征引片段,但像颇得韩愈《祭十二郎文》神韵的《祭子厚八弟文》(咸丰元年谱)、真实反映出友芝对官府看法的《癸丑三月遵义三异记》(咸丰三年谱)、有关友芝家世生平的重要文章《影山草堂始末》(同治二年谱)等则全部移录。特别是《癸丑三月遵义三异记》一文,系友芝手稿,是反映遵义县当时社会状况的第一手材料,该文详细记载了咸丰三年三月发生在遵义的天灾、考试之乱和征粮之乱,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咸丰四年杨龙喜的遵义起事,从此遵义干戈遍地,民不聊生。但此数事皆不见于官修《续遵义府志》,从《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以及《鄙亭遗文·丰乐桥记(代)》中看,当时的遵义知府佛尔国春完全是一副爱恤民生的形象,1999年4月5日遵义出土的丰乐桥石碑,也有他捐俸三百金修桥的记录,如果仅凭这些材料,佛尔国春似乎真是一个清正廉明的能吏。但《癸丑三月遵义三异记》里的佛尔国春则是另外一副嘴脸:“某守莅遵今五年,于事一无所知,于士民皆若邈不相属。唯日持筹握算,与吏胥争税课,锱铢较量,甚于市侩。其吏胥乘势滋扰,有因只猪匹布不经税所而破家者,有实无丝货不经税所而毙命者,商贾皆视遵义为畏途。”对于当时的县令楼一枝,-友芝更是毫无好感:“而县令署遵将币岁,日吸鸦片六顿,非朔望祭祀、考试必正午方起,听谳、接客奄奄如泉下人。……自去夏及今春,课士劝农,未闻有所奖与,而赏其差役,则袍挂料狐裘等以数十计,酒食之劳,动辄数十卓。遵
义差役本豪横,而官又奉之如此,愈虎而加翼矣。”形象反差如此之大,哪个记载才是真实可信的?对此《长编》评论说:“中国传统士人秉承儒家温柔敦厚诗观,由自己审订之诗文集往往经过正统眼光的过滤,期于符合儒家士人角色,结果所反映的思想大同小异,许多站在民众立场和生活立场上看到的历史细节被过滤掉了。而由自己后人编订的诗文,虽然出于孝道,收录较为宽松,但像友芝早年反映尖锐社会矛盾的《有豺》、《义仓行》、《后义仓行》、《癸丑三月遵义三异记》等诗文,还是不便公开。但这也正是这些材料的历史价值所在。”《长编》将这些文献整理出来,不仅补苴史阙,而且更真实触摸到莫友芝本人的民间立场。
与材料的取合精审相比,更让人佩服的是《长编》中的考辨功夫。《长编·前言》曾云:“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莫友芝上百种稿钞本中,多数是没有明确系年的,书信也往往只有月日而无纪年,这些数据如果混乱地、不加分析地放在一起,不惟不能清晰莫友芝的一生,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混乱。”但张剑对于莫友芝传世的几乎所有作品,几乎都作了系年。《日记》的系年相对简单,书信不准常不具年,且抬头常书字号,有些底稿中字迹不清,考辨尤难,如台湾所藏,《鄙亭父子藏札》二册中有莫友芝函札底稿三通,均未署日期,前二通皆未署致何人,第三通抬头字迹不清,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丛书部》认作“襄郡伯大兄大人左右”,并认为“似是致薛介伯者”。而《长编》则据相关史料细心钩沉,考出首函为同治九年重九日致庞省三者,次函为咸丰七年九月致遵义知府窦千山者,第三函首句为“襄臣郡伯大兄大人左右”,乃友芝咸丰九年致石赞清者,诸如此类,二百余封书信何时致何人,在《长编》中皆历历可考。
即使是诗歌部分,由于《鄙亭诗钞》系莫友芝按年编排,《鄙亭遗诗》系其子莫绳孙按年整理,系年似乎轻而易举,但也并非没有问题。如莫绳孙整理《鄙亭遗诗》,将咸丰九年庚申所作编为卷五,其最末一首诗为《息凡将之天津,口占送之》,因友芝到达陈息凡所守的赵州时已是腊月廿九日,研究者据此得出大年三十息凡有公务须之天津的不情推断。然《长编》据国家图书馆所藏《鄙亭诗钞》一卷手稿,此诗题作《开岁四日,息凡有天津之行,口占绝句为别,即口占送之》,并录有陈息凡原作。证明息凡天津之行为咸丰十年正月初四,莫绳孙编订诗集时偶有所失。在《长编》考订之前,研究者均沿莫绳孙之误。
除了系年,《长编》对所取材料的辨析也常有精彩之笔。如《长编》所收同治元年七月廿二日莫氏日记云:“《鄙亭日记》:懿甫来谈,遂晚饭,琴西、伯常相过,一更后乃去。懿甫索《埤雅》,以蔡元度《毛诗名物解》予之。元度盖全窃农师书,一字不易,前人皆未之觉也。”《长编》加以案语:“此说影响甚大,不仅友芝在《(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二《经部·诗》中重申旧说:‘卞此书自首至尾并钞陆佃《埤雅》之文,未曾自下一字,不知刊《经解》者何以收编,《四库》又何以入录。其人其书皆可废也。且郑振铎《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1927年《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皆采其说。然细较二书,多有不同,友芝此说似未妥。”再如同治三年四月三日,曾国藩设书局于金陵,延绩学之士分任校勘,一般皆认为莫友芝理所当然会供职金陵书局,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先发此论,至田中庆太郎刊本《(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董康序:“同治中初,军事甫平,曾文正督两江,独山莫征君友芝领书局。”更以莫友芝为金陵书局总校,此说流传极广。然《长编》详引《张文虎日记》、《鄙亭日记》及同治四年湘乡曾氏刊本《王船山丛书》所录校刊姓氏,考出莫友芝虽与金陵书局关系密切,但实未入其中任职,他任总校的是江苏书局和扬州书局。可谓发百年之覆,断讹误之源。
精准的取舍眼光和高水平的考释辨析,大大提高了《长编》的学术质量和利用价值。
三独特的结构体例
《长编》在结构体例上颇显独特。它虽然也分为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但其谱前系莫友芝父亲莫与俦年谱,谱后则系莫友芝子莫绳孙年谱:其实是一个家族三代的合谱。莫友芝幼承庭训,其人生观和学术观都与父亲莫与俦关系密切,对莫与俦没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就很难对莫友芝本人有更为深刻的了解。莫友芝的儿子莫绳孙虽不能“雏凤清于老风声”,但跟随莫友芝时间最长,保存莫友芝资料最多,莫友芝的大部分著述,都是由莫绳孙整理刊刻的,不了解莫绳孙的生平事迹,对莫友芝著述的许多方面也将难以措手研究。《长编》通过《谱后·莫绳孙年谱简编》这种形式,使我们对《黔诗纪略》、《(吕阝)亭遗诗》、《(吕阝)亭遗文》、《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等名著的成书及刊刻过程有了准确的把握。如《谱后》收入同治十二年七月十九日莫绳孙致黎庶昌的信中,讨论了《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的编订:
先君《旧本书经眼录》,侄编为三卷,附录一卷,缮成清稿二册寄上。请姑丈细阅删订后为作一序,再行付梓。侄有小跋二,亦请删改。昨已将此书请张啸山先生阅过,其签示各条,已照删去。唯其云“子不可以名父书”,而此书之名乃先君原稿所题,末及告之也。侄前编次时检家中书,唯《天禄琳琅》一书专载旧本,乃以宋元明刊本、旧钞本各为类,故侄约依其例编之。因书太少,亦嫌琐屑。然已录清册,若再钞一次,又须耽延时日。若姑丈亦谓不宜以刊版时代分类,侄复另写。就统编二卷,目录数纸,又以朱笔于本书当条之下记其次序,即可令写宋字者照次缮写。然又恐易致错乱,校对时亦多不便,又寄上格纸二百张,请用此格令写宋上板,其中缝字用墨书压之无碍也。既可与诗文稿等大小一律,刷印时用毛泰纸六裁,亦稍省费。又啸翁所校误字各条,其未改者,原稿亦误。己于旁加抹,笫未改耳,请酌之。再:啸山先生驳拜经主人跋一条甚善,侄欲竟删去此跋,亦请酌之。
《长编》考辨云“此信对了解《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的成书过程及编订思想有重要作用。信中啸山先生指晚清著名校勘学家张文虎(1808—1885),他曾为《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担任校勘,在校勘过程中,对书名与实际内容不符有所质疑,并有便笺致莫绳孙:‘此书尊公既未定名,不可以子名父书,且“宋元”两字亦不能包括。故僭易其名,而见之跋中。又卷帙无多,不必依《天禄琳琅》例,层层插目,并不必标经史子集字样,只依四库次序暗分之,其附录亦然。若照鄙见,则原跋中须有更动字,或与莼翁商之。(信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另案:莫绳孙信中所云‘编为三卷、附录一卷,缮成清稿二册,其稿尚存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中间即夹有有张文虎驳拜经楼主人之跋。”《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的成书过程昭然若揭。
《长编》的四个附录也颇具价值:一是传记资料,选录包括正史、文集、手稿中的莫氏家族人物传记及家乘资料;一是家族人物简表,便于了解莫氏家族人物关系;一是莫友芝事迹简编,由于《长编》字数较多,为了便于省见传主事履,提要钩玄作此简编,相当于《长编》的纲目;一是莫友芝江南收书记,记录了莫友芝游历江浙等地的购书目录及价格,从中可窥传主访书情形及当时书籍流通情况。与《长编》主体相辅相成,俱有可观之处。
莫友芝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晚清发生的若干大事,他都耳闻目睹。他一生交游广阔,又曾托身胡林翼、曾国藩幕府,所接触的多是各行业名人,如祁穷藻、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郑珍、刘熙载、俞樾、马新贻、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翁同铄等,都是晚清政界或学界的代表陡人物。《长编》编入存世的所有《(吕阝)亭日记》和所能罗致的鄙亭书信,这种体例利于凸显《长编》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了解晚清政治史和社会史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长编》中载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莫氏与丁日昌首次相见,丁自言“曾入航海,历海外数国,颇获其文籍掌故,译而记之,其风俗、物产、兵制皆得大要”,丁后来能够成为与西人交涉的能臣和重臣,从早年经历中已经不难窥知。同年十二月十日,《长编》又记“晚过雨生,论今夏湖南所刻《辟邪宝录》,播鬼子之奸恶,开人心之蒙昧,有补不小。昔杨光先为《不得已》一书,一时从鬼教者多自拔,而书中鬼之忌,鬼即重价购而毁之,此书即附此二文,而引据尤博洽,虽不无一二风雷语,而语意危悚,其足以散从鬼教之顽民,而复其气,则可尚也。曾遇苏、常间人,独痛诋此书,以为污蔑洋鬼,必为天地所不容,诚不知其何心也。”反映出咸丰年间不同地域对于洋人迥然不同的态度,可供研治社会史者玩味。
《长编》采铜于山的精神、精审的提炼考辨、独特的结构体例,具有学术范式意义。宋梅尧臣《汝州后池听水》诗云:“春水泉脉动,分岩临涧源。”《长编》中蕴含的丰富价值,相信以后会不断被人发掘出来,各自生发为具有独特意义的学术命题。像《长编》这样厚重的撰述如果累积到一定规模,整个文学史及文化史的书写必将愈显生动和深刻。
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