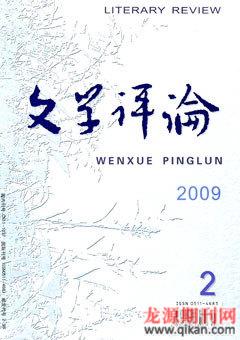从失范家庭结构中走出来的一代
韩 敏
内容提要一群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生代”作家已经成为当前文学创作的重要角色。他们来自新中国第一代核心家庭,其处女作或成名作不约而同地将视野集中于对一代人成长家庭的回忆与想象,“失范”的母亲与“缺席”的父亲是他们共同的家庭记忆,在新生代作家笔下,那一代人不得不接受现代家庭生活“游荡者”的历史命运。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新生代作家,如韩东、荆歌、盛可以、李樯、刘建东、刘庆等,如今已是人到中年。“晚生代”、“六十年代后出生”、“新生代”等都是对这些作家的命名。在诸多命名中,使用最多是“新生代”,本文也就沿用这种说法。“新生代”之“新”,在于他们与前辈作家——“知青作家”、“先锋作家”相比,拥有新的写作资源与文学空间。新生代作家主要成长于20世纪中国家庭模式最大变革后的核心家庭,家庭记忆必然成为他们进入文学空间的首要写作资源,如1989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李樯,由他编剧的成名作《孔雀》,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刘建东的小说《全家福》(《收获》2002年第4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刘庆的《长势喜人》(《收获》2003年第4期,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等,它们都从成长角度书写了家庭记忆。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家庭是一个又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逼仄的生活空间与冷漠的家庭关系,“残缺”的父亲与“失范”的母亲,这种家庭结构成为他们少年记忆的重要文本,而这一切又深刻影响了新生代作家审视生活的态度。本文旨在梳理这些作品的家庭记忆,以及对这种写作策略的研究。
一家庭记忆:新生代作家的写作资源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期的新生代作家,“文革”在童年记忆中更多是一场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的集体狂欢,艺术的想象遮蔽了政治斗争的严酷以及人性的异化,他们不能像“知青作家”那样以切肤之痛去触及历史的真相,最多只能像王朔的《动物凶猛》,“文革”成为这群少年成长的历史背景,同时也给予他们自由的成长空间。与前辈的“知青作家”、“先锋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也有自己的成长史,他们在连环画阅读中度过了童年时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中完成小学教育,在现代主义的审美潮流中完成大学教育,在90年代的消费主义大潮中,他们开始真正步入社会生活。大学时代张扬的理想主义文化与艺术精神和现实的物欲潮流之间的断裂,迫使他们进入社会就面临艰难的生活选择。这种人生的矛盾就如李樯与顾长卫第二次合作的电影《立春》中展示的:新生代作家的理想有如王彩玲的歌喉,那是美好的,那是可以在法国歌剧院展示的;新生代作家面对的现实则如王彩玲的相貌,那是真实与丑陋的,也是充满谎言的。1989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的自杀事件,则是这一代人面对这种选择所采取的决绝策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诗人已经远离了那一代人,而那一代的其他人依然要在这个“物质生活”的时代构建自己的生活空间,寻找自己的生活位置和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这或许就是新生代作家迥异于前辈作家的不同的艺术使命。
与前辈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缺乏知青作家所拥有的由国家改写个人生活历史的写作资源,这是将个人记忆与宏大历史完美结合的写作资源,因此非常容易获得震惊的艺术效果;他们也缺乏先锋作家以小说叙述革命所带来的形式上的震惊效果。新生代作家的生括经验和成长记忆更多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场景中的个人体验,这种生活记忆决定了他们进入艺术世界之后,首要的任务是在建构个人生活历史的同时,还要寻找与宏大历史叙事的契合点。对于沐浴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精神的新生代作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不仅面临对传统文化的缺失,而且还面临对个人生活史的悬置,少年的生活空间已经在“现代化”的名义下被大型“挖掘机”修饰殆尽,新生代作家在享受20世纪最快速的发展所带来的物欲享受的同时,却不得不面临这种“现代化机器”剪断了个人历史之后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很多人说童年和青春就是一个梦,一个最美好的梦,梦远比现实生活更丰富和灿烂。但是,这种梦境却从不属于新生代,因为梦境与现实缺乏一种连续性,或者一种逻辑性。因此,新生代作家以不同的故事建构着本质相近的个人生活历史,童年和青春的记忆应该是建构这个家园的出发点,承载这个家园的就是他们的家庭记忆。
二核心家庭记忆:新生代作家的艺术起点
在物质匮乏的70年代度过童年生活的新生代作家,他们的童年记忆是与父母和家紧密相连的。他们的父母大多数是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是在男女平等的思想潮流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新中国青年,也是新中国第一代核心家庭的建设者。核心家庭是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形式之一,是由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这种家庭内部通常只有一个权力和活动中心,故名核心家庭,因此奥兰和森冈清美把核心家庭也称为夫妇家庭。核心家庭在中国的建设始于新文化运动,在启蒙理性思想影响下,禁锢个性的中国大家庭模式开始瓦解。
在传统的大家庭中,父亲是家庭凝聚的核心,随着新文化运动冲击,大家庭模式不断解体,大家庭的核心凝聚力已经跟随“觉慧”(巴金《家》)一代人的“出走”而在实际上被消解了。这些出走的“觉慧”与“娜拉”,以崇尚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名义开始了小家庭建设。譬如予君和涓生,他们从各自的家庭中走出来,在吉兆胡同的一个破屋“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但是,这个小家庭最终以涓生的无限倦怠和悔恨,以及子君孤独的魂归天国作为结局。他们满怀希望的“小家庭”之梦,在子君对涓生无尽的期望中破碎了。
涓生和子君小家庭的破碎,不是缺乏爱,他们的爱不可谓不深,否则当子君去世后,涓生就没有那样深沉的悔恨与自怨。从高府那样的大家庭到涓生和子君的小家庭,尽管家庭的外在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家庭的核心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却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大家庭中,主要体现为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关系。就女性来说,她们对男人的爱,如马斯洛所说是一种“缺失性爱”,“缺失性爱是被满足缺失需要、尤其是被满足从属和爱的需要的缺乏所驱使的”。这种爱源于自身某些方面的缺乏,而需要从对方获取。因此,这种爱是一种以丧失自我为代价的爱,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在子君和涓生的小家庭中,尽管这个家庭已经没有高老太爷那样的绝对的父权形象存在,但是子君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大家庭那种男人与女人的依赖性的爱。子君对失业后的涓生,依然满怀改变小家庭物质生活的期望,这种期待的眼睛令涓生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无奈。尽管子君能够从自己的大家庭中走出来,与涓生建设他们所向往的“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但是社会却并没有为子君提供建设这种家庭的物质条件。这种条件的获得是在几十年后的新中国,政策法规赋予女人和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同等位置,获得了经济独立的女人在核心家庭中,第
一次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力。新生代作家就是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空间。
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新生代作家的父母是在新中国男女平等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缔结了新中国第一代核心家庭,这是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实施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新家庭模式,这种家庭模式之所以能够建成的核心要素在于,女人具有参与社会工作的权利。美国社会学家曾经断言,家庭模式的革命是当代席卷全世界的重大革命的一部分。新中国时期,这种家庭模式的变化给予新中国的青年以深刻的影响。在“觉慧”、“拉娜”等人所憎恶的“高宅大院”垮掉之后,传统的母亲与父亲形象也随之解体,对于新生代作家的父母来说,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核心家庭的母亲与父亲形象,因此他们记忆中的父亲与母亲往往都显得无章法可依,手足无措,这也使得他们关于家庭的记忆往往都是支离破碎的。
三双重挤压下的核心家庭:“失范”的母亲与“缺席”的父亲
一般说来,家是一个人人生的起点,也是终点,更是孕育一个人社会理想的温床。新生代作家的视野中,他们成长的家庭普遍缺乏温情,比如2005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银熊奖的《孔雀》,其编剧是出生于1968年的李樯,《孔雀》展示了新生代作家典型的家庭生活场景:逼仄的生活空间与沉闷的家庭氛围。一家人围坐在走廊的小饭桌旁边吃饭,没有任何言语。为了那不切实际的伞兵之梦,为了逃离那些家长里短的同事,为了逃离缺乏温情的家,姐姐将结婚和离婚作为逃离的手段。他们的家缺乏“和合”之力:父亲沉默寡言;母亲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姐姐痴迷于自己的伞兵梦;弟弟在外边,跟着一个带小孩的卖艺女人也不愿意回家。
生于1967年的河北作家刘建东近年来发表与出版了《时间的雕刻》(《花城》2002年第6期),《全家福》、《情感的刀锋》(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午夜狂奔》(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等,这些小说超越先锋作家对小说叙述形式的痴迷,形成一种将故事与精神相契合的沉稳的小说品格。获得河北省第十届文艺振兴奖的《全家福》展示在“福”字装饰下一个破碎和冷漠的家,与《孔雀》一样,它也是一个在“家”的屋檐下,已经失范的悖谬性存在。作为新生代作家来说,童年最深的记忆,或许就是每年春节全家人都会去本城那些不大的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家中的某一面墙上挂满了各个年月所照的“全家福”,“全家福”由此成为反映新生代成长史的重要符号。
刘建东的成名作《全家福》通过家庭记忆开始建构自己的成长史。小说从母亲的一双皮鞋开始,皮鞋无疑是物质匮乏时代的奢侈品,由于有爱美的母亲穿皮鞋,才使小城里有了并不多见的摇曳多姿的身影。尽管没有鞋油,对于在肉联厂工作的父亲来说,这不是一件难事,从工厂偷偷带回的猪油为母亲的皮鞋增添了些许光彩;为母亲擦皮鞋是父亲每晚都要举行的“仪式”。大哥徐铁的女朋友,被“我”称她为“金银花”,她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穿上母亲的皮鞋与大哥上街炫耀,被大哥得罪过的一群小流氓追逐,他们在雨水中奔逃,皮鞋也损坏了,父亲每晚的擦鞋“仪式”由此告终,家庭也由此产生裂隙。此后,母亲每天在百货商场橱窗前,在一双父亲看来十分昂贵的皮鞋面前流连忘返,她后来穿上了一双来历不明的上海皮鞋。继之,家里除“我”之外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转折:父亲莫名其妙成为植物人,躺在屋檐下搭建的小屋的床上;大哥徐铁到离家最远的青海当兵;大姐徐辉身边多了一把“小刀”;二姐开始了更为莫名其妙的药片收集生涯;母亲则每晚开始“夜游”……“我”的家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皮鞋的故事而变得冷漠、破碎。
当父亲无法为母亲再次购买她心仪的皮鞋,而当母亲的脚上拥有了比原来更高级的上海皮鞋后,整个小城都飘满了关于母亲的谣言。“我”的母亲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含辛茹苦”的经典母亲形象。她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物质与身体的欲望;皮鞋和男人。因此她可以毫无愧疚地在失去行动和思维能力的父亲床前与别的男人偷情。此刻的“我”的母亲是一位身体自主的女人,完全卸去了传统母亲的文化与道德的约束。夜晚的母亲与白天的母亲截然不同:夜晚的母亲游荡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是陷于物质与身体欲望不能自拔的女人;在白天,她似乎又想扮回“慈母”的角色,苦苦地哀求离家出走的二姐回家,但由于夜晚的母亲无法控制自己,最终二姐再也没有回家。“我”的母亲是游弋在白天和黑夜的两个女人,她最终都没能在传统角色和欲望本能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母亲于“我”家来说,显然是一个“失范”的角色。
最初父亲细心地守护着“我”的家,就如父亲每晚细致得有些过分的擦皮鞋“仪式”,当他无力为母亲支付一双新皮鞋的钱时,就注定了父亲在“我”家的“出局”——父亲偏居屋檐外的小屋,这是父亲对家庭生活在身体上缺席的象征,父亲成为植物人,则是在他在家庭精神中“缺席”的隐喻。就在大家都以为父亲行将就术的时候,他的头发开始疯长,这又预示了父亲顽强的生命力。此后父亲在家庭生活的所有重要场景都以“幻象”的形式出现:大哥徐铁第一次想与女朋友金银花发生性关系失败的时候,大哥听到了父亲沉重的叹息之声,由此阻断了徐铁成为男人之路,二姐感情上受挫,在河边顾影自怜时,看到父亲尾随而来的幻影,母亲的情人毫无理由坠楼前,小城传闻父亲曾经在楼顶上出现过……植物人的父亲本无力行动,但他似乎又无处不在。对于“我”家来说,母亲和父亲并没有给孩子提供家庭生活的场景与范式,身体健康的母亲实际上是家庭的缺席者,而植物人的父亲尽管似乎与“我”的兄妹有一丝联系,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那是远远不够的。“我”关于家庭的影像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结构。
父亲的缺席与大哥的性无能,是家庭生活中男性力量衰败的象征,这是新生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的文化隐喻。20世纪初期的思想革命浪潮割断了中国大家庭的文化传统,这种大家庭传统是所谓中国传统文化“超稳定结构”的核心元素。在大家庭文化传统中,“我”是无个体身份的,是处于人伦关系中的“我”。20世纪初期的启蒙主义以个性解放的名义,解除了“我”身上的蛛网般的伦理道德关系,“我”开始以个体身份出现在艺术空间。随着大家庭传统的解体,还有传统家庭的守护者——父亲形象。“守护者的主要特征是其在传统秩序中的地位而不是其‘能力”,当女人获得了同等的工作机会,也即拥有与男人同样的家庭建设能力之后,父亲在传统秩序中的位置也就被解除了。新生代作家视野中的父亲形象已经被解除了守护者的权力。
因此这些父亲形象都是一些残缺不全的。生于1968年的吉林作家刘庆的《长势喜人》,则描写主人公李颂国周围的残缺的男人群像。李颂国的生父是强奸自己母亲的人,生父的行为导致了李颂国私生子的社会身份,这是他少年时期饱受同伴欺侮的原因。李颂国法律上的父亲是马树亭,这个父亲完全是母亲为了解决儿子的社会身份而采取的临时策略。被李颂国视为最像父亲的是医生曲建国。但是曲
建国却是一位生活在女人荫翳下的男人,前半生在极有主见的小学教师的母亲的阴影中长大;后半生在强悍的妻子阴影中生活。作为李颂国的精神父亲的曲建国就是在这种强悍的女性阴影中丧失了男性的力量,最终摧毁了李颂国对父亲的想象和崇拜。生活在家庭关系紊乱中的李颂国,注定是残缺的。
四家庭传统断裂:前喻文化的崩溃
《全家福》中,在母亲角色和女人角色之间徘徊的母亲,以及植物人的父亲;《长势喜人》中,李颂国和一群残缺的父亲形象……从这样的一系列描写中,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家庭都深受父母缺席的精神困扰,其中子女成长的家庭环境就是玛格丽特·米德界定的“前喻文化”的崩溃时期。所谓的“前喻文化”是“晚辈向长辈学习”的文化,人们通过长辈所具有的个人尊严和历史连续感来体现过去和未来,新生代作家的父母大多数都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文化精神。一方面由于新型家庭——核心家庭的建立,家庭的前喻文化实质上处于被质疑和消解的地位,对于新型的家庭模式中的性别角色,尚处于探索、不成熟的阶段。“父权制的最大收益在于为性别角色提供了一种模式,使他(她)们免于陷入个体选择的困惑与冲突之中,得到一种‘安全感”。随着传统大家庭模式解体,父权制也随之解体,对于新生代作家所描写的父母形象来说,必然会陷于个体选择的困惑与冲突之中,他们无法为下一代提供完整的父母形象,也无法提供他们进入成人世界的成熟的家庭生活经验。“由父母和年幼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实际上是一个高度自由灵活的社会团体,在这种状态下,居民中的大部分或每一代人都必须学习新的生活方式”。而新生代小说中的父母很难给孩子这样的指引。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这是中国民众日常生活开始变化的年代,也是一个刚刚从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年代,人们悄悄地将目光转向自己的身体和欲望。新生代作家的父母一辈人正经历有生以来第一波的物质与身体欲望解放潮流的冲击,加之他们所建立的核心家庭,缺乏文化继承的传统,最终导致新生代作家的那代人,大多数在少年时代便通过家庭感受到社会和时代潮流对这个核心家庭的冲击,这是一个在风雨飘摇中的家庭。
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缺乏完整的父母形象便是一段残缺的记忆。《全家福》中的“我”的大哥徐铁从蔑视岳父到最后去祈求岳父的帮助,完全丧失男人的尊严,变成他的无能的父亲的复制品。大姐和二姐是母亲的分化物:大姐继承了母亲娇好的身材,她上中学时离家出走,但能够充当美术模特以维持生计,二姐继承了母亲妖娆的姿容,在为数众多的男人中生存却能够游刃有余。面对欲望和亲情,大姐和二姐采取了完全对立的策略,大姐随身携带的“小刀”是她阻隔欲望和亲情的符号,二姐有收集药片的嗜好,这是其放纵欲望的象征。面对“变异”的母亲和家庭,大姐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选择了离家出走,并开始随身携带“小刀”。这把小刀割伤了爱慕她的中学同学,也拒绝了一生痴爱她的大学同学。大姐的“小刀”既割断了她与男人世界的关系,同时也毫不犹豫地了结了她与家的关系,“小刀”是大姐拒绝欲望与亲情的象征。
大姐的“小刀”与二姐收集药片的癖好恰好成对比。二姐骨子里的妖娆,令她在初中时期就过早地沉浸在男女的情欲之中。她对男人的体悟首先来自于体育老师健硕的肌肉,仅有十多岁的二姐精心设计了“受伤”阴谋,完成了她抚摸健硕肌肉的愿望。但是不久这位老师就在80年代初期的第一次所谓“严打”中以诱奸少女罪入狱了,那次“严打”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肉欲犯罪。80年代的第一次“严打”实际上就是针对改革开放初期日渐失范的欲望的一次整肃。二姐从此就有了收集各种味道药片的嗜好,这些药片诱惑着她身边无数的男人。男人对于二姐,就像她盒中的药片,多一个男人就多一种味道。如果说大姐的“小刀”是对本能欲望和人伦关系拒绝的象征,那么二姐收集药片的嗜好则是她放纵本能欲望的象征。大姐对欲望与亲情的拒绝来自对“失范”的母亲的绝望;二姐流连于男人的身体,则是对“失范”母亲的单向度的复制;无能的大哥即是缺席的父亲的延续,这种失范的家庭已经难以培养健全的“女人”与“男人”,也难以培养完整人格的“父亲”与“母亲”。
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文化语境是非常尴尬的。他们一方面固守传统文化的教义,人伦亲情依然是他们无法割合的,另一方面他们的生存语境却到处飞散着西方文化的泡沫。他们没有比自己更年轻的一代“80后”的洒脱,而只能仰望漂浮在空中的色彩斑斓的梦。面对传统日益远离现实生活,欲望化的彩色泡沫浸染在新生代生活的每个角落,面对这样的现实,新生代作家缺乏精神归属。这种漂浮感促发了他们建构自己成长史的愿望。据中国社科院婚姻家庭研究室专家的调研报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目前已经属于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而对婚姻的满意程度调查表明,40岁上下年龄阶段的人对婚姻的满意度则滑落至谷底。比如对2006年重庆市武陵区离婚登记人群的年龄结构进行了100对(200人)的随机抽样调查,31岁到40岁的年龄段的离婚人有118人,占抽查人数的59%。尽管追溯到个人,离婚的情况可能各式各样,但新生代作家所揭示的这一代人少年时期残缺的家庭生活记忆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关于家庭的前喻文化崩溃的时代,缺乏完整的母亲与父亲形象的家庭生活,必然导致新生代作家笔下的人物,成为现代家庭生活的“游荡者”。
责任编辑董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