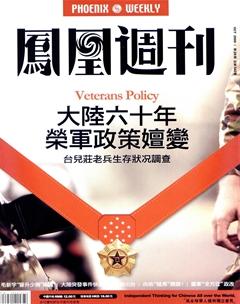台湾的1949历史热
苏惠昭
1949,缠斗4年的国共内战进入终章。对于溃败的国民党,这是告别无限江山,“转进”台湾,背负着失败耻辱重新筹谋“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的一年。对于共产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下一步就是拿下台湾,完成统一大业。
这胜利者与失败者一起改写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改变了成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命运。
到今天,时间过去60年,一个甲子,60年摧老青春少年,埋葬了彷若不死之身的伟大巨人、民族救星。几经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台湾既没有“反攻大陆”,大陆也没有“血洗台湾”。60年,中国大陆和台湾隔着海峡,挟尘俱沙的风却由西伯利亚不停地吹向南方岛屿。时间像一列火车轰轰隆隆不断向前,10年、209、30年……台湾人、台湾的外省人,多少人胸中爱恨情仇的记忆如潮水翻来搅去,无处可以收容,需要一个停靠站便于回首并瞻望。
60年,当然是一个停靠站。
台湾文化圈卷入的1949历史热始于2009年夏初,这股热潮以文化界、历史学界、文学界为核心向外辐射。7月,天下杂志推出《超越六十》专刊,丢出火种,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持续加温,8月再由龙应台的报导文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燃起漫天烽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如野火燎原,《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的《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1949浪淘尽英雄人物》,辅大历史系副教授林桶法《1949大撤退》,政大历史系副教授刘维开《蒋中正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也在之前或之后出版,众声喧哗局面始成。又拜架设家族部落格之赐,作家成英姝记述了父亲成汤的流亡回忆,集结成《我曾是流亡学生》,很巧也是在2009年。9月出版的《台湾,请听我说》里,让17位不同世代、不同领域的台弯当代人物,踩在台湾土地上,从头吐诉他们独特的成长故事,以及省思过后的生命情思。
相对于中国大陆,在台湾,这比较像一场有意无意的不约而同,没有人特别发起,官方保持沉默,但是“中华民国在台湾60年”像一场无声的风雪下在心头,甚至在“反共文学”销声匿迹许多年后,1949重新成为小说的某个重要场景,毕竟那是改变人生的一个魔幻数字,很多故事从这里开始,不然便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其中《悬浮》是资深作家冯青睽违20年后的新作,小说借由眷村出身女主角周晓宾的经历刻画政治和族群的困境;小说家蔡素芬也推出构思10年之作《烛光盛宴》,主角之一白泊珍即是1949年随国民党军官丈夫庞正来台军眷,她以眷村为基地展开她的瓜子蜜饯事业,并与“台湾人”菊子的命运交织,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
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等五书当然会在“过气”许多年后重新受到关注,看大时代的一名小卒如何被拨弄,他又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日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历时17年,终于在这时间的停靠站交出终卷,其中《关山夺路》写的正是国共内战。他感叹书中所有新闻名词俱已成了历史名词,云烟往事,必得重新注释年轻人始能理解。资深作家季季早一年出版的杂文集《行走的树》,对1949年后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也有第一手记录。
为这股历史热暖身的应是名制作人王伟忠煽起的“眷村怀旧风”。王伟忠出生成长的嘉义眷村就要拆了,为了保留独特的眷村文化,他不遗余力拍纪录片、写书,并与赖声川表演工作坊合作了一出舞台剧《宝岛一村》,复又制作眷村连续剧《光阴的故事》。在高挂蒋中正照片的客厅中,在翻来覆去的爱情里,《宝岛一村》和《光阴的故事》再现眷村文化,轻轻浅浅演绎了一场族群融合,悲欢离合。
《光阴的故事》前,有冯小刚电影《集结号》在台湾上映,给恒常背对1949的台湾上了一场震撼教育课,接下来还将承受2009《建国大业》带来的冲击。从电影中,台湾人特别是老国民党看到这最不堪回首的一块,从而产生奇异的认同错乱。
2009年9月,《联合报》亦开始向大众募集“我的1949”照片/故事。
历史有两面,胜利者与失败者各自一面。淮海(徐蚌)战役是怎么回事?国民党军队是怎样丢掉大陆的?对现在台湾的2300万人来说,1949那场原来事不关己的内战确是一个矛盾与对立的开始。那一年,在短短几个月内,原来600万人口的台湾涌入了200万人,彻底动摇了岛民的结构。200万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用陌生的眼神看着这块湿热岛屿,其中具有军人身份者和家属被安置(或说隔离)在俨然自成一国的眷村;他们以为第二年、第三年就会回转故乡,没想到再也回不了头,那一片大陆成了前世,台湾才是今生。
“靠不住的军力”、“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丧失公众信任与尊敬”、“美国调停与援助之失败”、“社会与经济改革迟滞”,国民党之败于共产党历史已有定论。而中华民国在台湾60年,台湾经历了准备反共、白色恐怖、去本土化,到经济起飞、党外运动、蒋家神话的退幕,再到政党二次轮替、台湾意识高涨,其间国民党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道歉并赔偿,美丽岛事件获得平反,蒋中IE55年来无有间断的手写日记也已公诸于世。
这说的是台湾最大的骄傲,走向民主之路,只是民主并未化解族群的矛盾与对立。对台独基本教义派来说,这60年的台湾故事简直可以精简成一句“腐败的国民党丢掉大陆,逃到台湾”,然后跳到一个画面:“外省人欺负台湾人”。这矛盾和对立也被利用成为抹黑政敌、夺取政权的工具,成为检验“爱台湾”的试剂。
曾和丈夫段世尧回返大陆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台籍作家陈若曦在接受采访时则说,“可惜蒋经国去世太早了,否则他不只在临终前解除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和大陆探亲,也能对‘二二八作反省和补偿”,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早走是好事,让台籍的李登辉加速民主化,为‘二二八平反,进行总统直选,继前人的经济奇迹后,又创造民主奇迹”。
评论家南方朔认为,民主后的下一课是融合与创新,历史曾经厚待台湾,让台湾在风雨飘摇中依然挺立,如今历史给台湾的新选择是——积极参与中国事务,建立所谓的“新主体性”,“也只有如此,台湾那种被扭曲的悲情心态才可被超越升华”。
所以天下杂志《超越六十》专刊用一段话总结其专题制作精神:1949我们经历大迁徙,对立、矛盾。2009我们努力融合、创新、再出发。站在2009回首1949后的一甲子,不是为了怀旧,而是要向前瞻望。
这等于承认了矛盾与对立在经过60年后依然存在。但如何在融合中创新,于怀旧中瞻望?方法之一就是说出当时事当时情。年轻的记者每每因为故事而落泪,站在历史面前,主编李雪莉写道:“这本专辑,了遂我长期的渴望:为失语或被覆盖记忆的国度,说故事。”
换句话说,60年来,台湾从威权专制到民主开放,从贫穷到富裕,从富裕到价值失落再到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眼下就要签下“能让你赚大钱,也能让你失业”的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这一路走来,到头来仍旧是一个失语或被覆盖记忆的地方,除了有官方说法,也只有权力者的回忆录能够界定历史。
原因之一是故事过剩,过剩到“每一位迁台者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内容不尽相同”(林桶法)。之二,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下,言论自由受到压抑,经济发展凌驾一切。之三,这是一个没有听众的市场。
来到2009这时间的停靠站,很多故事再不说就永远来不及了,或者已经来不及。说故事的人遂以一种奋不顾身的认真和热情,抓住夕日没海之前的最后一刹那,这一回,听众奇迹似的慢慢聚拢过来了。
新出土的、掩埋已久的、重新整理与组合的、理性论述的、感性回顾的,因为来到了时间的停靠站,关于1949以来的许多故事于是如繁花盛开,如火山进发,这是2009年的台湾,而故事不只是故事,它的深层更是一种对历史的态度,这态度是全面向历史开放,不能只站在一面看历史,也不能只从权力者的角度看历史。
所以无论《超越六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巨流河》还是《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那么多人不约而同潜入历史大海到底层打捞,去释放压抑的记忆,还有那些无人肯听的絮语里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总合起来看,为的都是替族群的困顿找到融合的出口——给同一个世代以及下一个世代的人。
应该说,除了掌握最高权力的人,那200万人或600万人,个个都是命运的棋子,随风飘零,套一句王鼎钧的话,“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而命运可以荒谬到,让生长在台湾的原住民青年加入国军到大陆打日本,然后在国共内战后被俘,又摇身一变成解放军,派去打了韩战,劫后余生后回到台湾,这是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说的一个故事,大时代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故事。
要为国军或解放军打战背后看似有一套严肃的思想,真相有时却是轻到难以承受。加入军队最多人是为了不饿饭,有饭吃就好,为谁打战都一样,张拓芜是个中代表。大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写道,“在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当时他胸怀壮志,梦想当拿破仑指挥大军,因此排除“打带跑”的游击队,“如果不是当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员了,不跟从毛泽东,就是追随蒋介石。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刚好发生在我个人身上”。
如果跟随国民党,多数人的命运就是退迁台湾;如果选择留在大陆,一场“文化大革命”又将人像丢骰子一般四处抛掷、践踏。
在大时代的命运面前,人何其脆弱无奈又何其坚强;在大时代的命运前,人因为经历太多太大超越语言甚至超越想象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以至于无言以对,又在后来的“大台湾主义”强风压境下失语失忆,这是2009台湾回看1949时,一个基本、共同的历史态度。换言之,要把历史发言权还给每一个小小的个人,让那200万人和600万人,相互交换各自的创伤和流离,不如此,便不足以把被扭曲的悲情心态扭转回来,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解,为下一个60年筹谋。
以后的历史,也许将这样记忆台湾的2009——个温暖温柔的,抚平族群矛盾与对立的停靠站。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1949年,国民政府迂台首次国庆阅兵,装甲车部队接受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