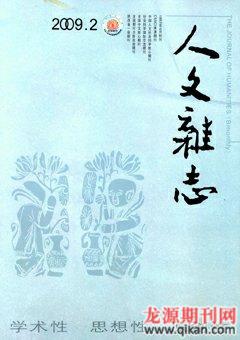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艺术表征
王维国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艺术表征主要体现在各个区域迥然不同的文学创作上,即最适宜这块文学土壤生长的那些艺术品种。各区域文学的主体艺术表征是在行政当局所制定的文艺政策这一大框架下,经过多种文学成分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最后在达到某种平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取自区域统治者、文学家和读者三者需求的平均值,是它们相互妥协、接受和适应的产物。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中国文学地理 艺术表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2-0132-04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是典型的政治气候变化的产物,各方政治力量所占据的区域造成了中国文学的地域性间隔,这种文学地理的艺术分野在各区域文学艺术的诸多方面都有鲜明的呈现。鸟瞰战时的中国文学地理,在1942年前后的中国文学版图上,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个规则不等的条块状文学带犹如地球上分布的热带、亚热带、温带一样,具有明显的区位特征。这三条文学带虽不规整却界限分明,如果用地图的特殊语言——色彩来标示的话,可以分别饰以红色、黄色和灰色,这些文学板块上的斑斓色彩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形象化的艺术表征。
一
文学地理同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农业地理的经济表征体现在不同区域出产的物种上,譬如,南方水田生长水稻,华北平原盛产小麦,东北大地出产大豆等等。文学地理的艺术表征也体现在各个区域迥然不同的文学创作上,即最适宜这块文学土壤生长的那些艺术品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别区域文学的主体艺术表征,即什么是该文学区域的代表性艺术特征?一般来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者的文学观在区域文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各种文学现象发挥着重要的规约和影响作用。但文学艺术是一个驳杂的复合体,由包括统治者所倡导的文学艺术在内的多种文学成分组合而成。区域文学的主体艺术表征不同于主导艺术表征,前者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后者是一个规约性概念。统治者所倡导的文学艺术可能成为区域的主导艺术表征,但不一定能发展为主体艺术表征。后者是在多种文学成分的相互作用下综合而成的。在抗战时期,战争及战争身后巨大的政治身影为各区域的文学打上了鲜明而深刻的意识形态印记,但各区域文学并非单纯的清一色,国统区有“党化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左翼文学、进步文学、中间文学、通俗文学;沦陷区有“国策文学”、汉奸文学、市民文学、现代派文学;解放区也有宣传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民间文学等多种文学成分。对于这些文学成分,各区域行政当局通常都要倡导和扶植体现各自政治意旨的文学,排挤和压制异己的文学,同时又允许那些“中性”文学存在和发展,并通过它们来点缀升平、装饰门面,制造区域社会稳定、政权大得人心的景象。与此同时,其他文学成分也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样一来,各区域在具体的文艺运行中都要在政府、出版商、作家、读者等各方面的需求上寻找某种契合点,在上述多种文学成分之间求得某种平衡,并以留有“缝隙”的方式来使文学艺术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繁荣”,从而维持某一区域范围内居民最基本的文学消费和文化娱乐活动。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大前提,即各区域统治者给予文学创作的所有“松动”,均被限定在行政当局所制定的文艺政策的框架之内,各区域文学的主体艺术表征便是在这一大框架下,经过多种文学成分之间的冲突、碰撞、迁就、妥协,最后在达到某种平衡的基础上得以形成。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这一特点在各区域戏剧电影的演映方面表现得最为典型。戏剧电影这一文艺样式直接与观众进行集体的面对面的交流,极易产生巨大的现场效应和社会影响,因而成为广受各区域行政当局重视的一种公众艺术。据此,各区域统治者都要依据各自的政治意旨及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制定一系列戏剧电影政策。在国统区,行政当局于1941年4月曾明示在戏剧电影创作中“杜绝描写颓废生活和暴露黑暗”⑤
李道新:《中国电影史1937——1945》,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277页。),1942年2月又专门制定了《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对现实题材戏剧作了种种限制。对此,进步戏剧家以历史剧来进行曲折的抗争。双方碰撞的结果是,政治锋芒毕露的作品受到压制,《屈原》只在重庆演出了十余场便被禁演,《高渐离》始终未能搬上舞台,《草莽英雄》难以在抗战期间发表,而体现行政当局政治意向的《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尽管得到行政当局的倡导和奖励,却因受到进步戏剧界的批评而声名不佳。在重庆戏剧界,剧作家们不可能与官方的文学政策正面对抗,他们可以批评一些由《茶花女》改编的《天长地久》等类“软性”作品的演出向锦江:《对当前电影戏剧映演的杂感》,《新华日报》1941年4月18日。),但那些抨击腐败官僚政治的讽刺剧、揭露社会问题的现实剧也不为行政当局所放行,抗战前期所创作的《雾重庆》、《乱世男女》等一批剧作均被行政当局禁演。囿于现实环境的制约,1942年之后的国统区剧坛除了《北京人》、《家》、《戏剧春秋》、《风雪夜归人》等进步戏剧之外,上演的现实题材戏剧多为表现抗战时期各地国人不畏强暴、忠诚爱国的剧作,如《大地回春》、《祖国在呼唤》、《法西斯细菌》、《长夜行》、《国家至上》、《黄白丹青》、《杏花春雨江南》、《万世师表》、《桃李春风》等,这类反映民族大义和爱国精神的一般性抗战作品构成了国统区戏剧创作的主体。
沦陷区对戏剧电影有着更为严格的控制,行政当局规定:凡“违背政纲者、有伤国体者、妨害治安者、有碍风化者、有危险性者”戏剧游艺节目不得上演(注: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南京市管理公共娱乐场所及艺员条例》(1938年8月),南京市档案馆藏。)。“有损中华民国之尊严”、“有违反东亚和平之意义”、“妨害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注:伪维新政府内政部:《电影检查暂行规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二○一○/3767))的影片一律不准上映。在这种环境中,统治当局扶植和倡导的戏剧电影均为“国策”作品,如为日本“大东亚战争”鸣锣开道的影片《万世流芳》,为日本侵华战争寻找借口的影片《春江遗恨》以及《和平之光》、《新桃源》、《哑夫人》、《火烛之后》等。但这类“国策”影片在上映的故事片中所占比重很小,“满映”出品的114部影片中只占16%,“华北”出品的16部中占13%,上海沦陷区的120部中占3%⑤,实际上充斥于沦陷区舞台和银幕上的作品多为没有政治色彩的“娱乐影片”和追求“票房价值”的商业性戏剧演出。1942年之后,上海沦陷区舞台上喜剧曾经兴盛一时,对于这一文学现象,作为主力作家之一的杨绛曾解释说,上海沦陷后“剧坛不免受到干预和压力,需演出一些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作为缓冲”徐廼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68页。),作家的这种“缓冲”之说即是适应现实文学环境的应对策略,而喜剧盛行这一文学表征在沦陷区出现,则是在环境挤压下多种文学成分进行平衡调整的必然结果。
解放区也对演剧活动下达过指令,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要求直属陕甘宁边区文协的抗战剧团“密切注意新中华报、解放报上的文章以及首长的各种报告,彻底了解政治形势和我党政治策略的演变”,并“在你团舞台上很深刻地表现出来。”(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周扬同志对抗战剧团的指令》,《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这一指令表明,此时的解放区对戏剧创作已经相当重视。在1942年5月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中,延安剧坛对边区两年来出现的“演大戏”现象进行了批评和遏制,对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延安生活素描》这组反映延安日常生活中某些缺陷或思想意识问题的短剧作了批判,剧坛面貌为之大变,整个解放区此后“几乎没有不为当前的现实斗争服务的戏”(注:张庚:《解放区的戏剧》,《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重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224页。)。由此可见,解放区剧坛“平衡”的结果与国统区、沦陷区截然不同,当局的倡导与剧团的演出在共识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统一。这一时期得到普遍推广的剧作是歌剧《白毛女》、秦腔《血泪仇》、话剧《穷人乐》等。前两部剧作因“在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尖锐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重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860页。),而成为整个解放区进行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穷人乐》则因“真实地反映了边区群众的翻身过程”(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的决定》,《晋察冀日报》,1944年12月23日。),受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表彰和推广。这类剧作因主题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相吻合而迅速成为解放区剧坛上的主流品种。
二
区域文学的主体艺术表征在行政当局控制较严的戏剧电影界表现得颇为典型,而在控制较松的流行文学领域也同样如此。流行文学是各区域出现的一种文学畅销书,这类销量甚佳的正式文学出版物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受众的接受趋向和阅读心理,其本身便是各方面利益和各种文学成分妥协平衡的结果。这类所谓“能够说的话”⑥季疯:《言与不言》,《杂感之感》,新京益智书店,1940年版,第23页。),取自区域统治者、文学家和读者三者需求的平均值,是它们相互妥协、接受和适应的产物。由于这类话语在内容上均不涉及激烈冲突的社会现实,易于得到区域行政当局和作家的共同认可,因而成为作家们在“言与不言”⑥之间的最佳选择。这些“能够说的话”在三大文学空间具有明显的差别,致使它们能够从另一个层面上标示区域文学的主体艺术表征。
沦陷区出现的流行文学有苏青的《结婚十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秦瘦鸥的话剧《秋海棠》等。国统区广为流行的文学作品是徐訏的《风萧萧》、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等。解放区的流行文学则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陕北秧歌剧《兄妹开荒》和《夫妻识字》。这些畅销作品在可读性强这一共同的形式特点之外,作品的内容分别带有各个文学板块所独有的区位特征。沦陷区当局严禁文学创作中出现“激发民族意识对立者”徐廼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的作品,在这种谈政治色变的社会环境中,作家们的创作和读者的兴趣都被挤压在述说百姓日常生活、谈论个人身边琐事的狭小圈子里,市民文学由此而兴盛并畅销起来便不足为奇了。国统区行政当局倡导抗战文学,却对反映当地现实生活的文学题材做了种种限制。于是,两部畅销小说只能将故事的场景放在了孤岛和沦陷区,或者以韩国军官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通过他们惊险神秘、奇异浪漫的诱人故事来曲折地表达抗日爱国的思想情感和反抗侵略压迫的民族意识。解放区在寻求民族解放的同时强调人民翻身和阶级解放,这些歌颂解放区军民生产和斗争生活的作品之所以流行起来,一方面是契合了上面的政治要求,得到了当局大力提倡和推广,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蕴涵其中的乡村情趣和民间兴味,即不仅在“政治上起作用”,而且“老百姓喜欢看”(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731页。)。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些流行文学正是各个区域政治取向、商业利益和读者趣味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总体上看,各文学区域迥然不同的主体艺术表征源于该文学板块所处的不同地理区位。日伪的殖民主义军事占领和异族统治与奴役的本质,决定了沦陷区是一个“文学的全黑时代”(注: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是一个文学创作的“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注:迅雨:《论张爱玲小说》,《万象》第3年第11期。),这种状况使得沦陷区的文学“不要说反抗,只要稍稍触及到‘民生之多艰就根本不可能得到发表。”(注:朱缇:《枯槁的心原上洒下一片阳光》,《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3辑。)面对如此的政治高压,作家们遭遇到严峻的个体生存危机,在创作上必然要考虑“以个人生活为主,不致于牵涉到另外的事情。写的是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的麻烦。”(注:楚天阔:《一九四0年的北方文艺界》,《中国公论》,第4卷第4期。)他们着眼于普通的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琐事上升为作品的主流内容,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伦理亲情之间的纠葛纷争占据了题材的高地。文体上则流行周作人之类谈天论地、闲情逸致的文史小品和描摹风物、记述田园的散文随笔,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事实上只允许作者笔于这种文体”(注:楚天阔:《1939年北方文艺界论略》,《中国公论》,第3卷第4期。)。
在国统区,行政当局利用统治权力强制作家创作宣传“三民主义”和“新生活运动”的作品,不允许他们“站在劳工立场”上写作“憎恨”的作品(注:葛一虹主编《中国话剧通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页。)。官方专制的文艺政策限制了作家们的创作自由,中国共产党也不主张国统区的文艺家在严酷的检查制度面前以身试法。周恩来在1941年告诫演剧队:“要谨慎小心,不要冲动急躁,不要自己带上‘红帽子”,要“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注:夏衍:《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人民戏剧》,1978年3月号。)在这种大势下,国统区文坛出现了三种创作趋向,茅盾将它们概括为:既然不许反映黑暗的现实便转而去写借古讽今的历史题材;既然没有描写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自由便转而去写敌后游击区、沦陷区和“阴阳界”,去写“小城风波”、乡村土劣和知识分子的苦闷脆弱;既然不能上阵厮杀便转而以介绍世界古典名著的方式来研习兵法(注: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5页。)。这些创作趋向及其结晶不能不说是在国统区这种恶劣的文学环境中,不同政治力量斗争和多种文学成分碰撞与调整后的无奈结局。
解放区被称为“明朗的天”,文学艺术的工农兵方向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其政治方针所实施的一种重要举措和步骤,或者说是其政治主张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解放区,文学与政治,作家与战士,文学创作与现实需要实现了空前的一体化。解放区文学中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气质和明朗欢快的艺术基调,正是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翻身的广大农民对解放区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高度认同的形象化表现,是获得实惠的解放区农民喜悦心情的自然表达。惟感缺憾是,解放区文学艺术所发出声音与色彩不免有些轻浅和单调,这些不足恐怕正是解放区原有多种文学成分碰撞调整至一体化后所应付出的必然代价。
梳理和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之外,它还有着巨大的文学史意义,即通过这一研究强化人们的文学地理观念,切实改变研究者和读者头脑中原有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概念,从而对全部中国现代文学获得真正完整的认识。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明确认识抗战时期文学的多样性特征,不再将某一区域的文学定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标本,从根本上感知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应有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正视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地理区位特征,科学地认知不同区域社会环境给作家文学创作带来的客观制约,不再片面地以某一区域的文学来比照和要求另一区域的文学,从而恰如其分评价某类作家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并实事求是地确定他们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作者单位: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
责任编辑:心 远